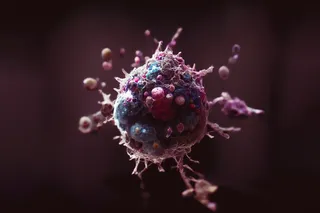本文发表于 2020 年 9 月/10 月的《Discover》杂志,原标题为“Healing Architecture”(治愈建筑)。订阅以获取更多此类故事。
2013 年 2 月,位于芝加哥的一家名为“关爱与发现中心”的 10 层医院正式对外开放。随着第一批患者涌入,他们也带来了自己的微生物。他们在门厅散播细菌,在走廊里撒播病毒,在床上留下真菌。他们还将这些微生物与病友分享,将它们传递给房间的下一任住户。
微生物生态学家 Jack Gilbert 说道,当病人搬进新房间时,他们的身体“实际上会短暂地被房间里的某些细菌——前住户的细菌——所感染”。他领导了对这家新医院微生物长达一年的研究。他说,即使房间已经被清洁过,这种情况也依然存在。
然而,一天之后,微生物的流动发生了逆转,它们从病人体内流向房间的表面。24 小时内,床栏、水龙头和其他表面的微生物就与病人带来的微生物极其相似。病人出院后,这个循环会不断重复,新入住的病人在最初会感染前一位病人的微生物,然后他们自己又会将微生物散布到这个空间里:一场永无止境的微生物电话游戏。
这种微生物交换发生在各种各样的建筑中。但在医院里,由于许多人携带病原体,这种情况可能尤其危险。在过去几个月里,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情况的发生,新型冠状病毒 SARS-CoV-2 席卷全球,在医院和急诊室传播。即使传播这些病原体的患者已经出院,病原体仍然可能存在;当一名住院患者患有艰难梭菌感染(可能导致严重腹泻甚至死亡)时,该房间的后续住户患上 same 疾病的风险就会增加。
许多住院患者的免疫系统较弱或有开放性伤口,这使他们容易感染。抗生素耐药菌株和真菌的传播使得这些医院获得性感染——影响全球 7% 至 10% 的患者——更加危险且难以治疗。
这些挑战促使医疗保健建筑师开始考虑微生物来设计。除了微生物的传播,研究人员还积累了大量证据,表明医院设计会影响患者的治疗效果。合适的设计决策可以减轻压力、缓解疼痛、遏制感染并加速康复。数千项研究已经清楚地表明:良好的设计就是强大的药物。
细菌,快走开
2005 年,瑞典马尔默的 Skåne 大学医院的管理者决定重建他们的传染病科时,他们试图创建一个在他们称之为“抗生素后时代”安全运行的建筑——在这个时代,有效的抗生素正在消失,流行病可以以闪电般的速度传播到世界各地。
为了将空间共享降至最低,规划团队决定每位患者都将拥有单人病房,这已知可以减少传染病的传播。效果可能是显著的:2002 年,当蒙特利尔总医院将 ICU 从多人病房改为单人病房时,患者感染潜在病原体(包括几种耐药菌株)的几率下降了 50% 以上,平均住院时间缩短了 10%。
但设计团队做得更多——他们甚至不希望患者在走廊里擦肩而过。因此,他们创造了一个圆形建筑,病房所在的上层有环绕整个病房的阳台。每间病房都有两个入口:一个主要供工作人员使用,另一个供患者使用。前者通向面向医院内部的走廊,允许工作人员运送清洁的用品和材料;后者则允许生病的患者通过面向户外走道的门进入独立的病房。

(图片来源:杰伊·史密斯)
杰伊·史密斯
“你可以让患者直接从外面进入他们的病房,这样他们就不会坐在候诊区咳嗽发烧,”传染病科主任、参与规划过程的 Torsten Holmdahl 说。一楼的门诊部和急诊部也有直接从医院外部通往独立诊室的入口。
无论是内部入口还是外部入口,都通向一个小的前厅,工作人员和访客可以在那里洗手消毒,并在必要时戴上口罩和穿上防护服。尽管证据不一,但一些研究表明,提供便利的洗手池和手部消毒液可以改善医务人员的手部卫生,从而降低医护人员在患者之间传播细菌的几率。
前厅装有气密门,并且是加压的,这可以防止污染空气流入其中。“这保护了患者免受外部侵害,也保护了外部免受患者侵害,”Holmdahl 说。故意设计得较大的病房在发生疫情或流行病时可以改造成双人病房,或者通过提高通风率和锁上前厅门来改造成高风险隔离病房。
Holmdahl 告诉我,这座于 2010 年启用的建筑总体上运行良好,疾病似乎不像在旧设施中那样容易传播。尽管科学家们尚未对患者的治疗效果进行正式分析,但这次重新设计预示着一个建筑师认真对待微生物生命的未来。而且,这正发生在医院,一个被称为“循证设计”的学科的发源地,这也很贴切。它不仅仅是让患者远离他人的细菌——他们的康复同样会受到其所处环境设计的极大影响。
走风景路线
这一相对较新的思潮可以追溯到 Roger Ulrich,他现在是瑞典 Chalmers 技术大学的建筑学教授。Ulrich 改造现代医院的道路漫长而曲折。它也始于一个。作为密歇根大学地理学博士生,Ulrich 决定将他的研究重点放在人类空间行为上,采访了数十名安娜堡居民,了解他们如何选择去当地购物中心的路线。

(图片来源:杰伊·史密斯)
杰伊·史密斯
他的受试者都住在同一个居民区,靠近限速 70 英里/小时的高速公路。如果他们走高速公路,可以在不到六分钟内到达购物中心。但他们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选择走一条较慢的路线——一条弯曲、多坡的林荫大道,两旁是茂密的树林——因为它风景更美。
这一发现并不令人震惊,但当时它是为数不多的提供硬证据表明人们重视自然风景的研究之一。“在人文科学领域——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社会科学界——普遍认为美是情人眼里的,”Ulrich 说,“是科学探究无法触及的。”
获得博士学位后,Ulrich 继续在特拉华大学进行研究,他深入研究了户外景观如何影响人们的情绪和情感。在他 1979 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他向刚刚参加完一次长考的大学生展示了一系列幻灯片。一半的学生看到了描绘日常自然场景的幻灯片——例如树木和田野的图片——而另一半学生则看到了街道、建筑、天际线和其他城市环境的图片。
那些看过自然场景的人在幻灯片放映后感到更快乐、更少焦虑,而那些看过城市景象的人则往往感觉更糟,报告的悲伤水平比看图片之前更高。在随后的几年里,Ulrich 证实并扩展了这些发现,并开始考虑它们的潜在应用。“这有用吗?”Ulrich 问道。“我们社会中有多少人会在一段时间内经历相当大的压力?显而易见的答案是医院。”
Ulrich 深知这一点。他小时候体弱多病,是链球菌的“磁铁”。“我不幸地总是得到链球菌性咽炎,”Ulrich 回忆道,他成长于密歇根东南部。有时链球菌会引发肾炎,一种肾脏炎症。因此,他相当熟悉美国的医疗保健系统。“我相当疲惫,经常去看医生和办公室,而且往往是在相当糟糕的情况下,”他说。“它们很消毒,情感冷漠——通常是现代主义和功能高效,但情感上不支持。”他更喜欢在家里的床上康复,窗外高大的松树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安慰。
他回想起那棵松树,一个想法开始形成:他要找一家医院,一些病人可以看到自然世界的景色,而另一些病人则看不到,然后比较他们的状况。
滋养自然的自然
Ulrich 沿着东海岸上下考察,最终找到宾夕法尼亚州一家拥有 200 张床位的医院,他认为那里将是进行这项研究的理想场所。在医院的一个病区,病房几乎一模一样,除了视野:有些可以看到一小片树林,而另一些则可以看到砖墙。“这几乎就像一次自然实验,”Ulrich 回忆道。
Ulrich 分析了 1972 年至 1981 年间在该医院接受胆囊切除术的 46 名患者的病历。“结果表明,[患者的]疼痛受到了很大的影响,”Ulrich 说。平均而言,有自然视野的患者——约占总样本的一半——比那些只能看到砖墙的患者需要的镇痛药物剂量更少。他们的住院时间也平均缩短了大约一天。
当时,医疗保健建筑师更多地依赖直觉而非证据,并且很少回到他们设计的医院去看看它们运行得有多好。“似乎缺乏关于医疗保健环境及其如何影响临床结果的严谨研究,”Ulrich 说。“我曾想过,‘难怪医院设计得不好。’”
Ulrich 的研究于 1984 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经常被认为是新时代的开端,即所谓的循证设计。医生宣誓“不伤害”——医疗保健建筑师难道不应该做同样的事情吗?
康复膏
此后多年,研究人员发现了改善医院环境的多种方法。许多人扩展了 Ulrich 的初步发现,提供了更多关于大自然治愈力量的证据。他们发现,几乎任何形式的自然似乎都能起作用。
20 世纪 90 年代初,Ulrich 报告说,被随机分配观察自然景象的心脏手术患者比那些观看抽象艺术或没有任何景象的患者术后焦虑更少,并且需要的强效止痛药剂量更少。其他研究人员发现,观看草甸壁画并听大自然声音的患者在接受支气管镜检查时报告的疼痛更少,而自然视频则减轻了烧伤患者换药时的焦虑和疼痛。室内植物也有益;病房里有植物的外科患者血压较低,报告的疼痛和焦虑较少,并且使用的止痛药比没有植物的病房少。
但是什么让大自然如此有效呢?Ulrich 认为答案在于所谓的“亲生命假说”。这个假说由著名的昆虫学家 E.O. Wilson 提出,认为由于我们的进化方式——在大自然的粗粝环境中——我们对自然世界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近感。因此,自然环境和景象吸引我们的眼球并吸引我们,使我们心情愉快,并将我们的注意力从疼痛和焦虑中转移开。
“大自然能够以一种不费力、无压力、恢复性的方式有效地分散人们的注意力,”Ulrich 解释道。在医院的环境中,这可能意味着快速康复与漫长而艰难的康复之间的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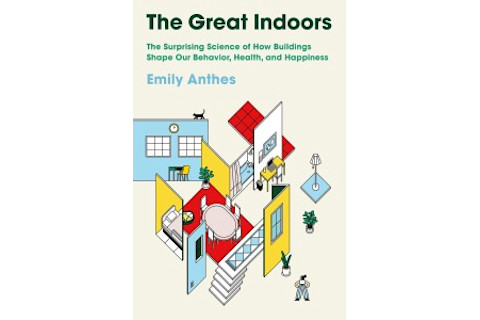
摘自:《The Great Indoors: The Surprising Science of How Buildings Shape Our Behavior, Health, and Happiness》(室内环境:建筑如何影响我们行为、健康和幸福的惊人科学)作者:Emily Anthes。由 Scientific American/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出版,2020 年 6 月。版权所有 © 2020 Emily Anthes。保留所有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