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9月27日,我43年来的世界结束了。
我当时正坐在伊利诺伊州莫顿格罗夫奥克顿路和格罗斯角路交叉口的一个红绿灯前,准备去德保罗大学的一个郊区校区讲课,前面停着另外两辆车。天空中下着蒙蒙细雨。
毫无预警,一辆吉普车在湿滑的路面上打滑,撞上了我的马自达轿车尾部。我的头撞到身后的头枕,然后又向前甩去。我眼前冒金星,昏迷了一秒钟。我感到头晕,但还是把车开出了繁忙的十字路口,转过弯,停在了格罗斯角路边。我感觉受到了惊吓,但只是像任何经历过相对轻微车祸的人一样。
一名莫顿格罗夫警官赶来记录事故报告,我下车与他见面。
“回车里坐着,直到救护车来!”他看了我一眼后说道。“我正在打电话叫救护车。”这让我很困惑。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如此担心。
救护车来了,两名年轻的护理人员,一高一矮,让我坐在里面,他们对我进行检查。
“你知道你的名字吗?”高个子问道。
我思考了一下。这似乎是一个足够简单的问题。但什么都没有立刻浮现在脑海里。我试图在脑海中通常的地方寻找,却一无所获。真奇怪,我想。一分钟后,我总算说出了:“当然。克拉克·艾略特。”
“好吧,艾略特先生,我想你最好跟我们去医院检查一下。”
“等等!”我说。“我不能去。我得上课。”
“听着,艾略特先生,”矮个子护理人员说。“请原谅我的措辞,但你这里的情况很糟糕。我们真的需要带你去医院。”
“谢谢你的关心,”我冲他笑了笑说,“但我很好。我真的不能跟你们去,因为我今晚有课要上。”
我没怎么受伤。在过去的12年里,我讲了上千次课,从未缺席。要让我缺课需要很大的理由。我的学生们正等着我很快出现并讲三个小时的课。我感到很奇怪,但我记不起不奇怪是什么感觉了。
我无法理解他们要我做什么。我无法以正常的方式理解。所以我拒绝去医院。
“好的,”高个子护理人员说。“我们不能阻止你。你必须签署这些免责表格,然后我们才会让你走。但你正在做错误的事情。”我爬出救护车,回到我的车里。
我的马自达尾部被撞得稀烂,但车仍然运转良好。于是我开车去上班,无意识地沿着我以前走过无数次的路。那天晚上晚些时候,我感到奇怪的是,我记不起我开车去上班途中剩余的任何事情。我晚上课程讲座的细节零星散落,但我记得我是自动驾驶式工作的,而且是坐着讲课的。有时在讲座中途停下来,不得不把头靠在桌子上休息。但德保罗大学的研究生们是一群聪明、多民族、脚踏实地的人,我们开玩笑说我的迷糊是车祸造成的。我们都没有把它当回事。
当我最终回到家时,我很难从车里出来。我很难从车走到房子。我开前门时遇到了一种奇怪而持续的困难。第二天早上,我仍然身体疲惫。我试图起床开始我的一天,但我动不了。我向我的身体发出命令:“起来!”但它不听。最后,漫长的三分钟后,一旦我能做到最微小的动作启动,我就能站起来正常活动了。
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我注意到更多次我无法启动行动的情况。我把所有担忧都抛到一边,告诉自己我的肌肉只是比我前一天在事故中意识到的“震动”得更厉害,而且由于肌肉酸痛疲劳,很难让它们做出反应。我又花了四天时间——以及一个令人费解的插曲,我花了六个小时才意识到我把鞋子穿反了——之后我才终于去了急诊室,得到的诊断是:脑震荡。
脑震荡与平衡
除非你经历过脑震荡并丧失了平衡系统的效能,否则你可能不知道这会对一个人的生活造成多大的破坏。由于内耳损伤——车祸的另一个结果——我每天都不得不处理平衡问题。
大致来说,平衡系统使用三个重叠的组成部分:前庭系统,或称“内耳”系统;视觉系统;以及本体感受,即我们身体在周围空间中的感觉——一种位置-运动感觉。虽然前庭系统是主要的,但其他两个也很重要,而且这三个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比我们通常认为的要复杂得多。
我们的前庭系统和本体感受系统向我们的身体提供直接信息,帮助它们保持直立。但这两个系统——在大脑的脑干中处理——和我们的眼睛之间也存在一个关键的反馈回路。

每当我在大学里走动时——我整天都得思考——我都会简单地用食指沿着墙壁滑动,就像我在玩闹一样。人们往往不太注意这一点,尤其是如果我把手放在墙壁的低处,而且这比在走廊和教室里摇摇晃晃看起来像醉汉要好得多。凯文·宫崎/Redux摄
例如,前庭眼反射利用大脑对位置和速度的评估输入来稳定我们运动时的凝视。当我们的头部移动时,眼睛会立即调整以固定在一个物体上,因为这种反射会对外眼肌进行微控制调整,使眼睛对抗头部和身体的运动。你可以通过照镜子直视自己的眼睛并移动身体来观察这种效果。此外,这些亚秒级的微调整与我们同时调整以追逐环境中移动物体的能力相结合,因此我们可以在转动头部和身体的同时仍然跟踪飞过院子的鸟的路径。所以我们的平衡系统控制着我们的眼睛。
但我们的眼睛和平衡系统之间的关系也反向作用,我们的眼睛控制着我们的平衡。当前庭系统功能不佳时——头部受伤时常发生——我们的眼睛可以承担大部分负荷。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练习来说明这一点:1)睁开眼睛单腿站立,另一只膝盖抬高;通常这问题不大。注意支撑脚的肌肉调整。2)闭上眼睛,但继续单腿站立。根据你的前庭和本体感受系统的有效程度,当你失去视觉输入时,你会经历不同程度的难度增加(同时脚的微调整也会相应增加)。你的平衡越依赖视觉,你闭上眼睛时就越容易摇晃。
运动迷向
像许多脑震荡患者一样,我多次出现晕动症发作,给我带来了麻烦。例如,车祸几周后,我试图乘坐高架火车进城。没过几站,我就感到非常恶心,以至于在车厢里呕吐,不得不滚着穿过车门,来到站台上。
“对不起!”我向那些或厌恶或关切的乘客说道。“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对不起。”我花了三个小时才恢复过来,能够步行回家。
近一年后的一个晚上,我因为上课而筋疲力尽,走路都很困难——我花了一个小时才从教学楼的楼梯上下来。我不想再面对爬办公室所在大楼的楼梯,所以我就说服自己,乘坐电梯上六楼会没事的。这是一个错误。电梯门在六楼一开,我就摔倒在地板上,爬到墙边,在那里我能支撑住自己。我在那里休息了15分钟,每当学生经过时,我就假装坐在地上看书。然后我手脚并用地爬到办公室,在地板上休息了一个小时,以恢复我的平衡。
平衡、视觉与思考
由于我的前庭系统受损,我本已超负荷且功能不良的视觉系统不得不承担额外的负荷,以满足我许多平衡需求。但与此同时,任何高层次的思维活动也需要相同的视觉/空间系统来创造思维的内在“图像”。
因此,我们有以下情况:在思维的认知负荷下——这几乎总是涉及到可视化、模式匹配和生成空间图像以形成类比——我受损的大脑会迅速疲劳。视觉/空间电路会超载,无法再兼顾弥补前庭系统的双重职责,我就会失去平衡。当我必须使用我的视觉/空间电路来解释复杂感官输入(例如言语或商店货架上复杂的视觉模式)的含义时,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最糟糕的组合之一是当我必须同时使用大脑中的视觉系统进行复杂思维或感官解释以及密集的平衡计算时。
即使在短暂的认知负荷期间,我的大脑疲劳也会加剧,我的平衡会逐渐恶化,几乎立即就会出现恶心感。根据我正在思考的内容或正在进行的体力任务,我会在五分钟内开始失去平衡。
我发展出一种秘密的补救平衡技巧:每当我在大学里走动时——我整天都得思考——我都会简单地用食指沿着墙壁滑动,就像我在玩闹一样。人们往往不太注意这一点,尤其是如果我把手放在墙壁的低处,而且这比在走廊和教室里摇摇晃晃看起来像醉汉要好得多。
我的一个神经学怪癖,你可能在有平衡问题的脑震荡患者身上注意到,是我的食指会向上弯曲,拇指伸出,而其他手指则向下放松,在每只手的拇指和食指之间形成一个弯曲的“L”形。如果你将手臂伸出略小于45度的角度,并以这种方式抬起食指,你可能会将其视为一种平衡警惕的姿势。
身体的尽头
我们的平衡系统也与其他重要但很少被考虑的系统整合在一起。例如,位于顶叶上部的一组神经,大致在头顶下方,被认为有助于我们区分身体的终点和外部世界的起点。如果没有能力进行这种区分,我们将很难在一个充满了障碍和通过它们的开口的世界中导航。当这个区域的大脑活动自然减少时——例如,当我们睡着或进入深度冥想状态时——我们对身体终点的感觉会相应地最小化。
这种身体划界感对于没有经历过脑损伤的人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但当它意外消失时,可能会相当令人困扰。考虑大脑的视觉皮层、我们的平衡系统和这种身体与周围环境的划界感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的经验表明它们之间存在联系。在脑部压力下——主要是视觉压力,尤其是当我对视觉系统施加过度要求以保持平衡时——我的身体与世界其他部分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

我的平衡系统失灵了,我只能依靠眼睛来辨别方向。感官的数据洪流让我不堪重负:电锯引擎的轰鸣声;消音器上油燃烧的气味;树枝到处压迫着我的感觉;木屑、咸汗和刺鼻的两冲程废气进入我的眼睛,我嘴里尝到了它们。凯文·宫崎/Redux摄
这在我几乎无处不在(尽管相对轻微)的穿过门、走下隧道(如楼梯和飞机登机桥)以及大脑疲劳时进入汽车的困难中最容易被注意到。我必须伸出手去“感受”开口的空间性——用我的眼睛仔细检查我的手与周围物体之间的区别——从而手动引导自己通过。
一个更引人注目的身体-环境界限丧失的例子发生在车祸五年后,是由于一系列强烈的视觉-平衡要求所致。
我家后院的一棵50英尺高的树得了荷兰榆树病,这种病可以在整个社区蔓延,所以必须将其砍掉。这种高梯树木作业强度大,不适合胆小的人。为了说明这一点,可以想象一下,一对之前在我家地基上做过重体力活的超级强壮的日工出现,并说他们会以预算价格砍掉这棵树。他们在爬上梯子开始工作之前互相嘲笑和挑衅,但他们每个人在一分钟后就下来了——膝盖不可控制地颤抖。他们很快就放弃并离开了。我负担不起请其他专业人士来砍伐,所以最终我不得不自己动手。
我知道我不仅要应对如此高空作业带来的正常、相当惊人的本能反应,还要应对大脑损伤带来的额外并发症。以下日记段落记录的是我爬上30英尺高的树,砍掉最高树枝(这些树枝本身又高出我头顶20英尺)的一天。这一事件同时考验了我的视觉/空间系统处理三项独立任务:对重型树枝的砍伐和坠落进行密集的空间规划;对涌入的感官输入进行有意义的解读;以及主要依靠不断变化的视觉输入来保持平衡的必要性。
我感到迷失方向,因为我无法向下看,只能通过观察树木的某些部分来获取视觉方位,而这些部分本身又在风中摇曳。周围一片阳光下绿色的混沌旋涡。我的平衡系统已经崩溃,我只能依靠眼睛来判断方向。感官数据如潮水般涌来,让我应接不暇:电锯引擎的轰鸣声;消音器上机油燃烧的气味;树枝无处不在地压迫着我的感觉;木屑、咸汗和刺鼻的两冲程废气进入我的眼睛,我嘴里也尝到了它们。我很难掌握将我自己——我的身体,以及我手中的电锯——置于移动的树木环境中的几何关系。就好像我失去了——我的内心自我与周围外部世界之间——界限的划定点。除了我透过安全眼镜的迷雾,紧盯着我的靴子和锯子正在切割我靴子所站立的树枝时,我的眼睛能告诉我的一切,我无法区分两者。我必须手动,持续地,在树的枝杈中,以及我身体的差异枝杈中,摸索着连接。我无法分辨它们之间的区别。在这种情况下,这令人恐惧,但也令人着迷……
不用说,我爬下来后,无法走路,甚至无法站立。在没有自然保护(即知道自己身体的边界在哪里)的情况下操作电锯,强度极大,这种真正奇特的经历所产生的原始恐惧是极端的。我花了一周时间才把树砍下来,之后又花了两个星期我的大脑才恢复过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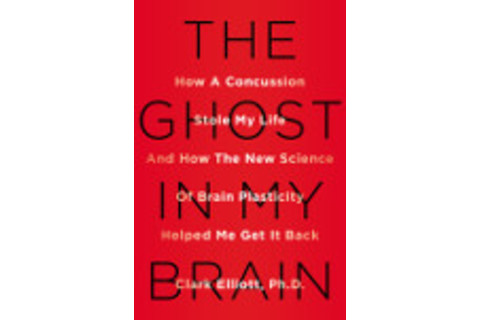
摘自克拉克·艾略特(Clark Elliott)的《我大脑中的幽灵:脑震荡如何夺走了我的生活以及脑可塑性新科学如何帮助我找回它》。经维京出版社(企鹅集团(美国)有限责任公司成员)许可转载。版权所有 © 2015 克拉克·艾略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