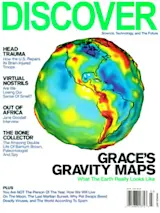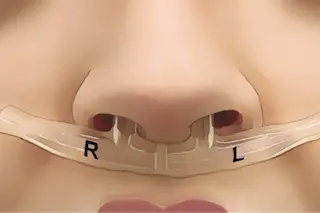瞬间,爆炸将空气焚化,喷溅金属,烧灼血肉。简易爆炸装置(IED)引爆几毫秒后,迫击炮弹爆炸眨眼间,超压波吞噬人体,紧接着,负压波随之而来又消失。耳膜破裂,血液中出现气泡,心跳减缓。士兵——或平民——可以在没有单一穿透伤的情况下幸存下来,但仍然得到最糟糕的诊断:创伤性脑损伤,或TBI,伊拉克战争的标志性损伤。
然而,就在爆炸释放混乱的瞬间,它也启动了历史上最有组织、最复杂的创伤护理。在数小时内,士兵可以被医疗后送至最先进的野战医院,安置在飞行重症监护室中,并在千里之外接受持续的重症监护。(在越南战争期间,获得这种水平的治疗平均需要15天。今天,军队可以在13小时内完成。)英勇的措施可能正在产生前所未有的生存率,但它们也带来了一个严峻的后果:没有其他战争创造了如此多的严重伤残退伍军人。士兵们在某些脑损伤中幸存下来,但只有脑干完好无损。
尽管五角大楼以安全问题为由,尚未公布脑损伤士兵的具体数字,但脑损伤专业人士对国防部和退伍军人脑损伤中心、国防部以及退伍军人事务部(VA)等其他与军事相关的来源报告的数字范围表示担忧。一位来自退伍军人事务部的专家估计,未确诊的创伤性脑损伤(TBI)病例超过7,500例。近2,000名脑损伤士兵已经接受了某种程度的护理,但创伤性脑损伤——被简化为缩写的人类——仍在不断涌现。
“我们每月大约有300架直升机降落,都带着某种程度的创伤,”Elisha Powell医生说。他是一名骨科医生,曾担任伊拉克巴拉德美国空军战区医院的指挥官,该医院被描述为“强化版战地医院”,大多数严重脑损伤患者都在那里接受治疗。
在巴拉德空军基地接受治疗的士兵有96%的生存机会;每月有数百人在此接受治疗。我问曾在伊拉克担任少数神经创伤外科医生之一的Gerald Grant医生,医院是如何让病人活下来的。
“这很复杂,因为它不仅仅是医学上的进步,”他告诉我。“这场战争的不同之处在于空运系统非常出色。能够让受伤人员如此迅速地进入您的护理机构,并且有许多前线外科医生和专科医生靠近前线,这在这个战区是一个新颖的概念。”
受伤士兵一踏上巴拉德的直升机停机坪,便被卷入重症监护的旋风。这是世界上唯一一家有多达10名外科专家全力以赴抢救生命的急诊室。患者被排队接上静脉输液和导管,接受CT扫描和X光检查,然后直接进入手术台——医院的最佳时间是18分钟。头部和颈部团队处理他们的创伤,而心胸外科医生和血管外科医生则对胸部进行手术。他们与泌尿科医生肩并肩,泌尿科医生又与首席创伤外科医生擦身而过,首席创伤外科医生则在骨科外科医生钻入外固定器的嗡嗡声中协调一切。这里拥挤不堪,炎热异常。
在拥挤的喧嚣中,医生们正在突破医学的界限。他们正在使用成箱的血友病药物因子VII,这种药物尚未获批用于创伤治疗,但在止血方面却是一种奇迹药物。每瓶3,000美元,每剂量两瓶,这个价格与恢复关键阶段产生的费用相比只是九牛一毛,而未来几周的费用很容易超过一百万美元。据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哈佛大学预算专家称,脑损伤士兵的终身护理费用可能达到350亿美元。
如果诊断结果显示与爆炸相关的脑部创伤呈阳性,神经外科医生将根据可观察到的创伤迹象采取行动。根据爆炸中脑部是被拉扯、推挤、扭曲还是刺穿,神经外科医生可能会选择进行大手术。
“我们的口头禅是‘要么全力以赴,要么回家’,”格兰特说,“我们真的想做我们知道对他们有益的决定性手术。”
几分钟之内,外科医生就会将颅骨锯成两半,并丢弃受损部分。之后会有塑料替代品等待。弹片被切除,脑组织肿胀,头皮被拉紧并缝合回膨胀的脑部。由于外科资源丰富,在美国任何一家综合医院需要数小时的手术,巴拉德的外科医生可能只需要30分钟。“我们医院能力的秘诀是周转效率,”鲍威尔说,“我们必须不断地运转。那些会压垮大型医院的事情不会压垮我们。在最糟糕的事件中,我们在90分钟内收治了35名患者,全部通过直升机送来,都带着可怕的伤势。”
格兰特说:“有些软组织创伤,我们没有头皮,没有眼睛,也没有颅底。我们必须在一次手术中紧急处理。”
许多在巴拉德接受治疗的士兵不会记得在那里。离开前线医院后,他们被装载到一架巨大的C-17运输机上,这架飞机经过改装,可以容纳一个完整的重症监护室——多达8名危重患者和27名非危重担架患者。它基本上是一个嗡嗡作响的空中仓库,里面有穿着盔甲的临床医生和便携式生命支持设备。被称为危重症空中运输团队,每个团队由一名危重症医生、一名危重症护士和一名呼吸治疗师组成。空军有249个这样的团队,服务于所有武装部队。
五小时后,C-17降落在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通过卫星追踪系统进行准备后,兰德斯图尔地区医疗中心(就在拉姆施泰因高速公路对面)的医生们已经对任何患者的治疗需求有了清晰的了解。在巴拉德,外科医生没有时间检查医疗记录或预先指示,因此不惜一切代价挽救每一条生命。但在兰德斯图尔并非如此。除了作为过渡设施,兰德斯图尔也是家属可以对其亲人命运发表意见的地方。
“你能看着一个人,知道他们将无法生存,”兰德斯图尔神经外科前主任吉恩·博尔斯医生说,“当你看到这种情况时,你会直接告诉家人。但很多时候,你了解得不够多。当你在军队时,你不质疑,你只是挽救生命。我在那里时,我们的行动方式是维持他们的生命,让他们活着回到美国。”
“由于通讯非常困难,我们在伊拉克很少与家人接触,”格兰特解释道,“家人可以在德国与患者见面。他们在那里为患者做决定,他们可以在那里撤回护理,无论患者是否有预先指示。”
一位退伍军人的妻子米歇尔·里德在兰德斯图尔与医生谈论她的丈夫皮特时,惊讶地得知他在2004年5月2日的一次袭击中幸存下来。她收到一些与他一起服役的朋友的葬礼通知后,一直担心他已经去世。海军工程兵皮特·里德是三名在伊拉克拉马迪遭到迫击炮弹袭击而严重受伤的军人之一。那次袭击中,30人受伤,6人死亡。
“他们先告诉我他失去了眼睛,大脑正在出血,”她说,“但后来他们说,他们认为他活不下去了。”
米歇尔要求把电话放到皮特的耳边,她告诉他坚持住,她想看到他康复。当天晚些时候,皮特从昏迷中苏醒,睁开眼睛,问护士他什么时候能见到妻子。团队立即将他飞回美国,去见米歇尔。
一旦部队返回华盛顿特区的沃尔特·里德陆军医疗中心或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国家海军医疗中心,积极的护理水平就会持续。在沃尔特·里德,部队接受旨在帮助他们恢复独立性的强化治疗。里德被转到贝塞斯达,米歇尔在那里等着他。
“他们让我见到他时,我崩溃了,”她说,“当他们掀开床单时,我看到了他开放的伤口。他什么也没说——他只是紧紧握住我的手。”
在贝塞斯达的重症监护室,医生告诉米歇尔,她丈夫康复的几率只有1%,如果他能活下来,也会成为植物人。
“我哭了,我祈祷,我咒骂,我尖叫,”米歇尔说,“几天后,皮特把头转向我,说:‘够了,我会好起来的。’”
+++
从沃尔特·里德医院出来后,士兵们被分流到全国的退伍军人多重创伤中心之一,在那里艰苦的工作才开始。(只有4个多重创伤中心和21个指定的多重创伤康复点,对于大量的伤兵来说,这个数字实在太少了。)几周前,一名陆军上士可能还在进行复杂的战术行动;在多重创伤病房里,他最大的挑战可能只是抬起头离开枕头。另一名有序列问题士兵可能会在康复室里尝试拆卸化油器。这名士兵随后可能会被带去进行物理治疗,以改善平衡。由于大脑的复杂性,每一种损伤都会带来自己独特的挑战。
明尼阿波利斯多发性创伤中心的心理学家罗斯·科林斯博士说:“所有多发性创伤中心都为患者提供高度个性化的护理。我的职责之一是减少阻碍您参与康复的障碍。”士兵并不是唯一在中心得到解决问题的人。“我的部分工作是帮助他们的家人,”她说。“您如何从这种经历中获得积极的意义?您如何哀悼模糊的失落?在某种程度上,家人会为死亡的可能性做准备,但他们不会为严重残疾的可能性做准备。在现实世界中,有谁会想到创伤性脑损伤会带来终身障碍?”
在佛罗里达州坦帕市的多发性创伤中心,米歇尔对她丈夫的状况有了更好的了解。他到达中心时,头皮上有一百多针,一只眼睛失明。外科医生切除了他部分腹部肌肉和部分髋骨,并将其移植到他的右腿。米歇尔可以接受他的身体损伤,但创伤性脑损伤(TBI)引起的人格改变让她觉得她的丈夫完全变了一个人。皮特右侧额叶的损伤导致严重的冲动控制和推理问题。
“刚开始的时候,皮特会扔尿壶,还会掐别人的脖子,”米歇尔说,“他以为自己还在伊拉克,甚至还想用笔扎瞎他唯一一只完好的眼睛。他从来不能一个人呆着,从不。”
在明尼阿波利斯退伍军人事务部的多重创伤病房里,墙上装饰着军事徽章,环境异常平静——这是脑损伤治疗中心所必需的。入口前的彩色地砖有助于那些无法再阅读房间号码的士兵。走廊和门道特别宽,所有家具都是可移动的,甚至浴室设备也对截肢者友好。该病房最近经过重新设计,完全专注于治疗。像巴拉德、兰德斯图尔和沃尔特·里德一样,多重创伤中心代表了研究和资源的巅峰,是许多私人医院都渴望达到的护理水平。该病房的患者代表着世界上最复杂的治疗挑战之一。
我在那里遇到了一位年轻的士兵,他接受了军队的全部服务。他被炸得支离破碎,又被重新组装起来,但还没有完全康复。他头部的左上方缺失,正在等待一个新的颅骨板,其余部分则点缀着深色头发的簇状物和弹片留下的凹痕。他没有两肢,取而代之的是假肢——一条手臂,一条腿。他身体可见的部分充满了新鲜的皮肤移植,使他看起来不均匀,像是拼凑起来的。在某些方面,他看起来不太可能,但因为他能说话、互动和行动,他是一个成功的案例。我没有见到的那个停在前厅角落的家伙,情况就不太好。他从头到脚都裹着厚重的白色毯子,只有嘴巴和一只灰色的手露在外面。一根塑料管从他的嘴唇后面一直延伸到椅子后面;在我访问期间,他一动不动。从远处的一个房间里,另一位脑损伤患者愤怒的哭喊声打破了平静。当我经过那个士兵的房间时,我看到他坐在床边,向试图帮助他的护士挥舞着手臂。行为爆发,特别是那些由激动引起的爆发,是脑损伤的常见副作用。
现在对我们来说超凡脱俗的事物,几年后将变得司空见惯。根据退伍军人事务部最近一份报告的预测,全球反恐战争中部署的40万退伍军人将申请残疾津贴。如此庞大的数字能得到充分治疗吗?随着平民脑损伤的终生费用不断上涨,地方社区是否为许多退伍军人所需的复杂治疗措施做好了准备?
玛丽莲·普莱斯·斯皮瓦克(Marilyn Price Spivack)穿着高跟鞋和商务套装,看起来不太像摇滚明星,但在脑损伤专家圈里,她恰恰就是这样的形象。她天生坚韧、大胆、充满活力。斯皮瓦克解释说,认知、神经行为和心理健康服务严重缺乏。军队中的男男女女会暂时获得优质护理,但最终,他们将回到自己的社区。
斯皮瓦克说:“军队在拯救年轻士兵并对他们进行急性康复治疗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她曾在波士顿的斯波尔丁康复医院与脑损伤人群合作。20世纪80年代初,她创立了脑损伤协会,如今该协会是创伤性脑损伤幸存者最重要的倡导组织。
“现在政府必须承诺帮助他们康复,但资源从何而来呢?作为脑损伤专业人士,我们知道全国许多地方都没有创伤性脑损伤服务,而且我们意识到系统存在巨大漏洞,”她说,“坦率地说,我对政府拒绝为创伤性脑损伤人群提供他们迫切需要的支持感到沮丧和愤怒。”
斯皮瓦克并非轻率,巨大的漏洞显而易见。许多州没有一个脑损伤康复中心,而提供一定程度TBI治疗的州中,很少能提供足够的帮助,以获得最基本的专业护理。急性TBI康复的费用每天可能超过一千美元,因此很少有美国家庭能负担得起一个月的治疗费用,更不用说建议的至少90天了。
就在2006年7月中旬,退伍军人事务部监察长办公室承认,患者和家属正面临严重的不足。事实是,大多数州根本没有基本的护理水平。
军方没有预料到问题的严重性,现在他们正争相增加新的脑损伤项目和服务。患者和家属遇到的问题包括与病例管理人员沟通不足或缺失、缺乏后续护理以及被迫自掏腰包支付必要的治疗和药物费用。
医学研究所对TBI项目和服务的评估读起来就像一份控诉清单。它得出结论:“寻找所需服务,往往是一项极其艰巨的后勤、经济和心理挑战……急性期后TBI服务系统的质量和协调仍然不足。”
在加入海军陆战队之前,小塞缪尔·雷耶斯从未听说过“创伤性脑损伤”这个词。作为一名在费卢杰附近移动路线上巡逻的机枪手,他深知肢体和生命的丧失。他经常目睹难以言喻的事情,然后亲身经历。
2004年9月6日,雷耶斯和他的巡逻伙伴以及伊拉克国民警卫队的成员乘坐一辆七吨补给卡车的后部。一名自杀式袭击者驶到卡车旁边,引爆了装载的C-4炸药和250毫米炮弹。爆炸将卡车炸成了一堆残骸,只剩下一些被嚼碎的传动轴。只有雷耶斯和另外四名海军陆战队员幸存下来。
雷耶斯的身体在袭击中遭受了各种创伤。爆炸的冲击将他的舌头撕裂成两半,并从肋骨到肚脐撕开了他的腹部。冲击力将他的双膝撞向金属屏障,弹片飞溅在他的背部。他的左臂被炸得骨头外露。
“我记得醒来时,我躺在街上,热得像着了火,”雷耶斯回忆道,“人们跟我说话,问我听不懂的问题。有人告诉我被简易爆炸装置(IED)击中了,我害怕了,因为我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雷耶斯无法猜到他的头颅内发生了什么。
像雷耶斯所受到的与爆炸相关的脑损伤可能会导致多重创伤性脑损伤。首先是气压伤,身体承受着与深水下相同的压力。据推测,在此阶段,大脑的一部分会几乎瞬间肿胀和减压,导致整个大脑出现一系列细胞缺陷。弹片和碎石等物体穿透颅骨,在颅骨壁内来回弹跳。爆炸的冲击力随后将个体撞向物体,如墙壁或屋顶,导致头部钝器创伤。最后,为了应对这些损伤,大脑释放出代谢级联的神经化学物质,对脑组织产生毒性作用。雷耶斯没有穿透性碎片;他经历了四种爆炸伤害中的三种。
雷耶斯在军队医疗系统中的经历并不像大多数人那样顺利。医疗后送直升机从未抵达,所以他被卡车运送到急诊室。在前往巴格达的途中,他的心脏停跳了两次。雷耶斯在模糊的绷带中醒来,周围是其他受伤的士兵。当天晚些时候,他的排长从模糊中出现,告诉他七个朋友在爆炸中丧生。他说,随行的伊拉克士兵也全部遇难。
“在那之前,我已经失去了很多朋友,这次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雷耶斯说,“这种感受、听闻和知晓真是糟糕透顶。”
中尉让雷耶斯独自承受他的悲伤,最终雷耶斯的思绪转向了他自己的健康状况。“那时一切都真的在走下坡路了,”雷耶斯说,“我不知道我的军旅生涯会怎样,或者我是否还能在其他地方找到工作。想到这一切,真是难以承受。”
受伤时,雷耶斯离退役只剩下两周服役期。他天生是运动员,原计划参加海军陆战队侦察队(特种作战部队的一部分)的选拔,然后进入军官学校。他梦想着有一天能领导自己的排,然后逐步晋升,直到退休。当他无助地躺在伤员中间时,他整个未来开始崩溃。
+++
不到一天,雷耶斯被送往巴拉德,在那里一支重症空中运输队陪同他前往兰德斯图尔。在那里,他恢复了足够的体力,得以抵达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国家海军医疗中心。
“我只是在贝塞斯达等着,”雷耶斯解释道,“那时我走路好了一些,但我仍然有很多头痛,很多疼痛,以及视力模糊。”受伤前,雷耶斯视力完美;现在他开车需要戴眼镜。
住院几天后,雷耶斯出院前往圣地亚哥附近的彭德尔顿营地,在那里他父亲自他受伤后第一次见到了他。
“我很高兴看到他还活着,还能走路,但我知道有些地方不对劲,”老雷耶斯告诉我,“从他脸上的表情,我能看出他一开始不认识我。”
雷耶斯陪同父亲回家休了三周病假。在他通过军队最精锐的治疗中心整个旅程中,没有人向他提及创伤性脑损伤——最多讨论的是轻微脑震荡的可能性。与此同时,雷耶斯的注意力不集中,耐受力低下,并且他仍然无法摆脱剧烈的头痛。他认为自己只是有点受惊,很快就会恢复清醒。
在家康复期间,雷耶斯没有告诉家人或朋友他的记忆空白。最初,他不认识任何人。雷耶斯的父亲越来越担心。
“我不得不一直向他解释事情,”老雷耶斯说,“他会问我大家怎么样了,我不得不告诉他他们是谁,以及他和他们是什么关系。”
雷耶斯微笑着与高中好友和表兄弟握手,相信他的记忆会恢复,但其他问题开始悄然出现。有一次,他开车送一位前女友上班,然后就迷失了方向。他送完她时,油箱是满的。几个小时后,他开到自家车道时,油箱里只剩下不到四分之一的油。雷耶斯也开始酗酒;这是唯一能缓解他头部剧烈疼痛的方法。
那年十月,当他回到彭德尔顿营地时,雷耶斯抱怨连连,但海军陆战队让他回去训练新兵。他认错了枪支;他忘记了提及特殊作战程序的细节。海军陆战队花了一个月才意识到雷耶斯已经不一样了,但他表示,他们没有深入调查,而是简单地让他呆在营房里玩电子游戏,而他的朋友们则准备再次前往伊拉克执行任务。最终,在2005年6月,由于担心雷耶斯持续不断的头痛,一名平民医生为他进行了神经系统问题检查。这是雷耶斯第一次听到“脑损伤”这个词。
“我不知道脑损伤是什么,它是如何引起的,它会造成什么影响,或者它会对我的身体造成什么影响,”雷耶斯说,“这只是另一个术语。他们告诉我,我余生都将面对这些问题,我需要努力适应并找到与它共存的方法。”
军队将雷耶斯直接送往帕洛阿尔托的多发性创伤中心。“他们告诉我,他的轻微脑震荡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轻微,”老雷耶斯回忆起他与帕洛阿尔托治疗团队的第一次会面时说。团队告诉父子俩,记忆损伤可能是永久性的,但儿子仍然可以从严格的康复训练中受益。
在帕洛阿尔托,雷耶斯花了一年多的时间重新学习。康复团队给了他一个手持式日程提醒器,当他有预约时会发出蜂鸣声。他们教他冥想,希望能缓解他的愤怒。他们向他普及了脑损伤知识,并警告他这可能会对他的社交生活造成困难。
雷耶斯目前仍驻扎在彭德尔顿营地。他的主要职责是驾驶一名上士在基地里活动,他对这份工作感到很适应。随着他对自身局限性的认识不断加深,他开始将自己的伤势与对生活的影响联系起来。
“我不太会跟别人说起我的伤势,”他说,“我根本不喜欢出门。我呆在家里,和认识的人一起做些事情。我跟朋友们聊天少了。当我非常心烦的时候,我甚至会忘记如何让自己平静下来。”
雷耶斯的伤势可能还很新,但他所面临的挑战与我从其他幸存者那里听到的抱怨如出一辙,即使是受伤多年之后。孤立、上瘾、躁动——这些都是严重创伤性脑损伤的典型特征。当我询问退伍军人事务系统官员是否了解爆炸伤幸存者面临的长期后果时,他们只是耸耸肩。这种伤势太新了,研究仍在进行中,这本书还在撰写中。
我问雷耶斯的父亲,他对于其他正在应对爆炸伤影响的家庭有什么建议。“真的没有简单的办法可以度过难关,”老雷耶斯说,“你必须拼命地希望有人能帮你。”
经过贝塞斯达和坦帕退伍军人事务部医院之间五个月的多次转运,海军工程兵皮特·里德终于获准回家。他仍然经常与噩梦搏斗,有时会要车钥匙,以为自己还能开车。他现在每隔几天才发作一次行为失控。
“当有人去世时,你会经历所有的悲伤阶段,”他的妻子米歇尔说,“当有人经历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时,你一遍又一遍地悲伤,因为创伤性脑损伤永远不会消失。这在情感上、身体上和经济上撕裂了我们的家庭。他曾经是那个坚强地维系我们生活的人,现在我们的角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彼得·里德清楚自己失去了什么,又剩下什么。“我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注意力不集中,”他说,“但我也很想念能够开车和做家务。被照顾、不能自己洗漱和上厕所,这让人很沮丧。”
里德知道他不会再回到部队服役,但他仍然怀有强烈的责任感。我问他十年后会做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希望帮助其他退伍军人,这样他们就不必经历我妻子所经历的一切。对我来说,我们似乎有大量文书工作和烂摊子要处理。如果他们费尽心思把我治好,那他们也应该帮助我们度过这些繁文缛节。”
在雄心勃勃的救死扶伤努力中,军方没有预料到幸存士兵将面临的严峻困境。对于大多数其他类型的伤害和疾病,都有丰富的服务可供选择。任何心脏病患者都可以在城市范围内找到负担得起的治疗,任何肾病患者都可以在州内获得透析。但脑损伤患者却被困在他们的社区中,没有基本服务,被孤立起来。我们为何投入如此巨大的努力来维持生命,却在支持和滋养生命方面投入如此之少?我们为何对如此严重的问题变得如此短视?
斯皮瓦克同意这种不平衡。“我们的政府将在药理学和技术上不惜一切代价来拯救人们,如果他们没有死亡,那就可以了,”她说,“防止死亡。他们说他们关心,但与此同时,服务正在被削减,获取服务也成问题。当我们最初开始这项工作时,每个人都谈论生活质量,最大化功能。这需要金钱和一生的投入。”
今天,小塞缪尔·雷耶斯尽管面临障碍,仍在坚持不懈。他计划上大学,攻读商业管理专业。“我预计学习会非常艰难,但我只是想尝试一下,”他说。
在这些障碍背后,你仍然能感受到士兵的气质。雷耶斯的决心只有他对海军陆战队的忠诚能与之匹敌。他相信他们会照顾他,永远忠诚。我愿意相信雷耶斯,但我知道服务提供方面存在明显问题。当他和其他人退出现役时会发生什么?在我看来,他是未来。他是成千上万将与脑损伤中心保持常规联系、寻求建议和帮助的退伍军人之一。博尔斯指出,伊拉克受伤士兵的实际人数可能是报告的两倍。地方退伍军人事务部医院是否会有脑损伤临床医生准备好应对大量的心理和社会问题?已经不堪重负的社区能否承受新涌入的退伍军人?
军方在修复身体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但尚未学会如何重建生活。“更多生命得到挽救,”博尔斯说,“与此同时,那些获救的人伤势更重。永久性残疾人士的发生率更高。”美国尚未为伤员的医疗需求做好准备。在“梦之队”般的护理结束后,士兵们发现自己陷入了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