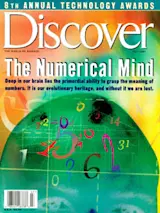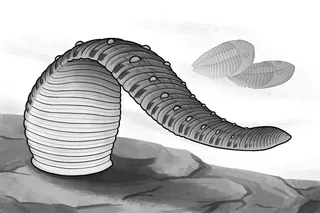没有人确切知道 N 先生身上发生了什么;也许他只是绊倒了,或者可能是中风导致了他摔倒并因此头部受伤。1986 年的一天,他出现在奥尔良的一家医院,大脑左半球有巨大的血肿。外科医生阻止了他因失血而死亡,但他们在手术过程中无法阻止病灶变得更大。到他们完成时,他左侧颞叶、顶叶和枕叶的大部分——基本上是半球的后半部分——都失去了功能。三年后,当斯坦尼斯拉斯·德阿纳(Stanislas Dehaene)来看他时,很明显 N 先生将终身严重受损。这是一件悲伤的事情:这名男子四十出头,曾是一名成功的推销员,已婚并育有两个年幼的女儿——但现在他的妻子和孩子已经离开了他,他被迫搬回与年迈的父母同住。德阿纳是一位年轻的神经心理学家,他自己也有家庭,他对同情心的负担不亚于任何人。但他还感受到了其他一些东西,七年后,当他回忆起这件事时,他的脸上仍然充满了光彩。他问 N 先生的第一个问题是:2 加 2 是多少?当 N 先生回答 3 时,德阿纳知道他遇到了一例引人注目的病例。
那次会面发生在巴黎的萨尔佩特里耶医院,德阿纳的朋友兼研究伙伴、神经学家洛朗·科恩(Laurent Cohen)在那里工作。N 先生的省医生将他送到了这家著名的医疗中心,寻求专家的帮助。实际上,对他能做的事情很少,而且治疗 N 先生也不是德阿纳或科恩的工作。他们的兴趣在于找出创伤对他处理数字的能力留下了什么。当他们仔细询问他时,所剩的能力远比他 2 加 2 的表现所显示的要多。即使他在那样的测试中表现出显著的失败也具有启发性。N 先生可能会说 2 加 2 是 3,或者是 5,但绝不会说它是 9 或 47。他从不荒谬。
N 先生失去了计算的能力——但似乎没有失去近似的能力。对他来说,数字只以近似值的形式存在,数字越大,近似值就越模糊。受影响的不仅仅是他的算术;他对数字事实的记忆也同样模糊。一年大约有 350 天,一个月 15 或 20 天。N 先生对 9 的含义没有精确的了解,但他知道 9 个孩子对一个母亲来说太多,而对一所学校来说太少。德阿纳问他一打有多少个鸡蛋,他没有回答法语单词“douze”(12),而是说 6 或 10。不过,6 或 10 不是 60 或 100。它接近目标。在他大脑深处的后部褶皱中,N 先生仍然对数字有一种直觉的、几乎原始的感觉。
这对他说当然没什么安慰。当 N 先生意识到他无法判断一个数字是奇数还是偶数,而只是猜测时,他变得非常沮丧,以至于德阿纳不得不停止实验。
在 1880 年 1 月 15 日的《自然》杂志上,英国人类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发表了一篇在一百年前仍然可以发表的奇特小研究笔记。作为一项关于心理意象的普遍研究的一部分,高尔顿向一群朋友和熟人分发了一份问卷,要求他们报告是否能看到数字,如果能,是以何种方式。似乎有些人能,主要是女性。(“我惊讶地发现女性在心理意象的生动性和内省能力方面通常优于男性……高尔顿写道。前者通常表现出意想不到的智力,而后者中的许多人则出乎意料地迟钝。”)通常,数字是沿着一条线或一系列线排列的,随着数字变大,它们逐渐变得不那么清晰,有时会消失在心理距离中。有时数字有颜色或质地(“在十位上有一些羊毛状的块,”一位受试者报告道)。有时它们具有非常鲜明的个性:“9 是一个了不起的存在,我几乎感到害怕,8 我把它当作他的妻子……6,没有特定的性别,但温柔而直率……”这份报告来自一位视觉能力异常强的男性哲学家。
高尔顿本人认为他的结果是一种奇特的现象——主要在于它们揭示了心理特征在家族中遗传的倾向。(他是一位早期的优生学家。)直到 1967 年,《自然》杂志上的另一篇论文才提供了证据,表明我们所有人都有某种心理数轴,即使是根据现有证据,我们中 95% 的人看不到它。两位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罗伯特·莫耶和托马斯·兰道尔,测量了一个人通过翻转左手或右手开关来选择两个单个打印数字中较大者所需的时间。他们发现至少需要半秒钟。但两个数字之间的差异越小,所需的时间就越长:例如,决定 6 和 7 之间的大小比决定 1 和 9 之间的大小多花了十分之一秒以上。这种距离效应强烈表明,大脑在比较数字之前,正在将其转换为模拟量——例如,线段。选择两条线段时,它们长度越接近,难度就越大。
此后,距离效应得到了斯坦尼斯拉斯·德阿纳的反复验证。德阿纳在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并在那里继续研究直到去年年底。(他现在在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INSERM)领导一个研究团队,该机构位于巴黎郊区的奥赛。)正是在他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遇到了科恩,后者当时是同一个实验室的研究生。德阿纳完成博士学位后不久,他和科恩就遇到了 N 先生。德阿纳称他为“近似人”的 N 先生赋予了数轴新的意义。他显然仍然拥有它——他仍然可以判断两个数字中哪一个更大,尽管他不能轻易地读出它们,更不用说将它们相加或相乘了。N 先生表明,通过将数字翻译成近似的模拟量表示来理解数字意义的能力,以及精确计算的能力,是两个至少部分发生在大脑不同区域的不同过程。
德阿纳与科恩合作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最近又于今年一月在法国出版了一本书,并定于今年秋天在美国发行(英文书名:《数字感》)。在书中,德阿纳勾勒出了大脑如何处理数字和进行简单算术的粗略模型。该模型的核心证据来自脑损伤患者。N 先生的病灶非常大,以至于他并没有透露太多关于数轴可能位于何处的信息——除了它可能必须存在于右半球和左半球,因为他的左半球大部分都被破坏了。但 N 先生绝不是第一个或最后一个患有失算症的人。就神经系统缺陷而言,它相对常见。在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一位名叫约瑟夫·格斯特曼(Josef Gerstmann)的维也纳神经学家研究了一系列此类患者,他注意到他们往往也有其他缺陷:他们混淆左右;他们无法说出手指的名称,也无法在被叫出手指时找到它(指失认症);他们也无法书写(失写症)。格斯特曼还注意到,他的患者都倾向于在同一个特定部位有病灶:左半球的下顶叶皮层——在大脑的侧面,耳朵上方和后面。
科恩说:“有些大脑区域,你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它们的功能。视觉皮层——那里是视觉信息到达的地方。初级运动区,那是运动指令发出的地方。但下顶叶皮层参与了许多事情。它接收来自各种感觉模式和额叶皮层的输入。所以很难用两个词来概括它的功能:它做了很多事情。”
但其中一件事是处理数字。科恩和德阿纳最近有一位病人,一位名叫 M 的退休艺术家。在冠状动脉搭桥手术中,他似乎大脑供血不足,更具体地说,是右侧顶叶皮层。格斯特曼综合征通常是由左侧顶叶损伤引起的,但 M 是左撇子,这大概意味着他的大脑是正常的镜像。无论如何,他有一系列的格斯特曼症状。特别是,他的数轴一团糟。
M 无法对单个数字进行除法;他无法说出两个数字之间是哪个数字。“这也许是这个病人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德阿纳回忆道。“我们会说,‘2 和 4 之间是什么?’他会说,‘我不知道——也许是 7?’他 80% 的时间都答错了。而且问题是,他非常理解这项任务。例如,他可以用一周中的日子来做——‘星期二和星期四之间是什么?’他对此毫无问题。或者字母表中 b 和 d 之间,或者音阶中 re 和 fa 之间——都没问题。但纯粹涉及数量,数字数量时,他就迷失了。减法也让 M 感到困惑。德阿纳和科恩报告说,在病人第十个问题(3 减 1)失败后,减法测试停止了。”
M 先生高度局限性的病灶——他大脑的其余部分完好无损——将数字线定位于下顶叶。然而,它没有说明大脑的该部分如何将数字表示为数量。德阿纳说:“我们知道哪个区域参与其中,但我们绝对没有证据表明该区域内的神经编码是什么。我的想法是,不同的神经元将参与编码不同的数量。因此,例如,如果你正在思考大约 6 的数量,某些神经元群会活跃起来。也许这些神经元在皮质表面有拓扑排列。”
也许,换句话说,数轴不仅仅是一个隐喻,正如德阿纳有时所说,指代大脑将数字表示为模拟量的能力;也许我们的大脑中硬连线着一个字面意义上的数轴,每个数字对应一个专门的神经元集群,这些集群按照数字本身的顺序一个接一个地排列。它不一定那么简单,但它可能如此:毕竟,视觉就是这样运作的。落到视网膜上的图像被逐点映射到视觉皮层中的神经元上,而不会破坏图像的几何结构。德阿纳认为,数字与视野中物体的空间关系或它们的颜色没有什么不同。它是大脑构建世界的根本维度之一。
目前还没有人研究过恰好是老鼠、鸽子或黑猩猩的脑损伤患者的算术能力。然而,如果你能做到并做到了,你可能也会在它们身上发现类似数轴的东西。老鼠可以学会按杠杆 4 次或 16 次以获取食物,或者在迷宫中走第四个左转。鸽子可以学会啄击目标 45 次而不是 50 次。黑猩猩会选择有 7 块巧克力的托盘而不是有 6 块巧克力的托盘,尽管在数字比较中它们也受到距离效应的影响:当试图选择两个数字中较大的一个时,如果两个数字靠得很近,它们更容易犯错。黑猩猩甚至被教会了加法分数。
德阿纳说,所有这些证据表明,感知和操作数字的基本能力是我们进化遗产的一部分——我们生来就有的。对人类婴儿的实验也证实了这一点。也许最著名的是几年前亚利桑那大学的凯伦·温(Karen Wynn)报告的实验。温向五个月大的婴儿展示了一个米老鼠玩偶,然后将其藏在屏幕后面;然后她将第二个米老鼠玩偶在观众的视线中带上舞台,并将其推到屏幕后面;然后她放下屏幕。当她因此露出两个米老鼠时,婴儿们平均观察了大约 13 秒。但是,当通过一些实验技巧,屏幕放下后只出现一个米老鼠时,婴儿们平均多看了半秒钟,这表明他们对消失的老鼠感到惊讶——温说,这表明他们理解一加一应该等于二。一个类似的实验表明,他们也对二减一不等于一的证据感到惊讶。
温自那时起跨越了分类学和公司界限,从米老鼠转向了达菲鸭:她发现,习惯了在舞台上看到达菲木偶进行三次垂直跳跃的婴儿,在每次跳跃之间会以分散注意力的方式猛烈摇晃头部,如果它只跳两次,就会感到惊讶,反之亦然。换句话说,婴儿可以计数动作和物体——再次表明他们掌握了数字的概念。其他实验表明他们可以计数鼓点。“无论婴儿使用何种心理过程来枚举事物,它都是抽象的,”温说。“它以最抽象的层面接收‘单位’——这是数字初始定义所需要的。如果你的所有单位都是盐瓶,你就没有数字。但我们测试过的所有种类的事物,婴儿都能计数。”
温最初的米奇实验已被包括德阿纳在内的其他研究人员复制。在他看来,这些实验表明,婴儿出生时就带有一个数轴,使他们能够掌握小数量,最多三到四个,甚至对它们进行基本算术。当婴儿成长为儿童并最终上学时,会发生两件事。一是数轴随着孩子学习更大的数字而扩展和完善。二是孩子学会执行精确的计算,这些计算超越了动物的能力和数轴所能实现的范围。这时,除了下顶叶之外,大脑的其他部分也参与进来。这时,数字与语言联系起来。
在德阿纳和科恩的模型中,两个大脑半球都能感知阿拉伯数字。两者都能通过将这些数字定位在下顶叶皮层的数轴上来提取它们的含义。但只有语言半球——也就是左半球(除了像 M 这样的一些左撇子)——能够进行计算。最直接的证据来自那些大脑半球之间连接(胼胝体)因手术或中风而断裂的患者。对于所谓的“裂脑人”,可以通过在左或右视野中显示数字或算术问题,一次只向一个半球呈现。在这些实验中,右半球通常表现出无法选择基本算术问题的正确答案。(实验不要求受试者大声说出答案;无论如何,右半球都无法完成这项任务。)
德阿纳和科恩说,为了进行超越数轴粗略能力的任何算术运算,数字不仅必须以数字的形式在大脑中表示,还必须以单词的形式表示——因为算术的基本事实是以单词的形式存储在记忆中的。“这种说法非常有争议,”德阿纳说,“尤其是在非法国研究人员中。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但现在我怀疑是否存在某种文化差异。因为在法国,事实就是这样教的——至少是乘法,这是最重要的例子。也许现在不那么多了,但至少我们遇到的那些病人,他们都受过训练,我也受过训练,去背诵乘法表——你知道,全班一起,‘三乘三:九。三乘四:十二。’你就是这样学的。也许在美国是不同的,也许在英国是不同的,我的大多数同事都在那里。他们不太相信语言编码非常重要。但我们有一些相当不错的证据。”
证据就是 B 女士。她是一位退休的学校老师,德阿纳和科恩遇见她时 60 岁,她的病灶与 M 的一样局限,但不在下顶叶——她没有格斯特曼综合征。她的病灶甚至不在皮层,而是在左半球的中央附近,一个叫做基底神经节的多部分结构中。在皮层和基底神经节之间运行的神经回路似乎是许多我们非常熟悉以至于无需思考的事情的存储库——例如刷牙等运动序列,以及通过死记硬背灌输到我们大脑中的语言序列。B 女士从事教师职业,向一届又一届的年轻斯坦尼斯拉斯和洛朗灌输法国文化的基础知识。现在,中风后,她再也无法背诵《主祷文》或拉封丹的寓言;再也无法唱《月光曲》;甚至再也无法背诵字母表了。她的乘法表也支离破碎了。
德阿纳接着说:“也许我给你们的印象是她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但事实上,这只是一个非常狭窄的障碍领域,因为她仍然可以读写数字,就像其他病人一样,而且这些病人无法完成的所有任务,她都能完成。在数字比较方面她没问题,减法她也没问题,绝对没有问题。她可以完成各种数量任务。‘2 和 4 之间是什么?’——她完美无缺。所以这就像是一种纯粹的死记硬背的缺陷。”
B 仍然可以做减法,因为减法不是通过死记硬背学会的。减法涉及到大脑语言区域的其他回路——德阿纳不知道是哪些——它像除法一样,受到数轴中体现的量化直觉的引导。乘法和较小程度的加法是通过死记硬背学会的——这就是为什么 M 尽管其口头半球的数轴消失但基底神经节完好无损,仍然可以背诵乘法表,即使他无法完成 3 减 1。他的中风抹去了数百万年进化产生的直觉,同时保留了教育的表层。在 B 夫人身上,情况恰恰相反。M 保留了算术的机制;她保留了意义。
斯坦尼斯拉斯·德阿纳相当好地经受住了法国数学教育体系的考验。高中毕业后,他掌握了乘法,并通过了臭名昭著的数学入学考试,进入了法国精英学校之一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正如法国人所说,他有“数学的疙瘩”——字面意思是“数学的凸起”。(这是一个颅相学遗留下来的表达,也是德阿纳为他的法文版著作选择的标题——带有些许嘲讽,因为他最不相信的是大脑中存在一个单一的疙瘩,一个单一的算术中心。)然而,获得硕士学位后,德阿纳放弃了数学研究,转而试图理解大脑是如何进行数学运算的。
十年研究之后,他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大脑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德阿纳在他的书中写道:“严谨的计算对于智人来说并不容易。像许多其他动物一样,它生来就带有一个模糊和近似的数字概念……尽管我们的文化发明了逻辑和算术,我们的大脑却保持不变,甚至对最简单的算法也感到不安。”德阿纳认为,小智人(他有三个孩子)应该尽可能免受这种痛苦。他认为他们应该减少乘法表的死记硬背,完全摆脱长除法的负担,更不用说手算平方根了。他不能忍受这种基础性工作能培养孩子的性格甚至数字直觉的观念。他会让他们尽早使用电子计算器。
他说:“大脑无法在不集中精力于机械运算的情况下学习长除法。这需要极度的集中,当你看到大脑活动时——它是巨大的。这确实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同时,它并没有集中精力于它所做的事情的意义,当它犯错时,那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我认为孩子用计算器计算会更好。至少他们可以马上得到结果。他们不用花一分钟思考如何得到结果,他们可以将结果的大小与他们最初的数字进行比较,从而培养他们的直觉。
有些人拥有惊人的算术直觉,使他们能够在脑中乘或分解四位数字,以极快的速度相加更大的数字,并通常在数轴上自由驰骋。其中一些计算神童也曾是伟大的数学家——例如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德阿纳认为神童和真正的数学天才彼此之间没有太大差异,在基因上与我们其他人也没有太大差异。也许他们的心理数轴更生动详细,正如其中一些人所报告的那样;当然,他们对数字事实的记忆一定更为广阔。这两种差异都必须以某种方式反映在他们大脑的解剖结构中,但在德阿纳看来,它们更有可能是早期强化训练的结果,而不是天生的天赋。
“我指的是如何成为专家,”他说。“如果你问街上的人,他们会告诉你,‘哦,你知道,那是天生的。你生来就是数学家,这在你的基因里。’我不相信是这样。我相信专家是那些付出巨大努力的人,如果他们的基因里有什么,那就是激情——对一个有点抽象的微小领域感到兴奋的能力。现在唯一还能成为计算神童的人是自闭症患者,因为他们是唯一愿意专注于一个毕竟非常有限的领域的人。伟大的数学家很快就会失去兴趣。但潜在的机制是相同的——他们充满激情。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最终对数学对象产生了巨大的亲密感。难道给孩子们电子计算器不会阻碍这种亲密感的发展吗?你真的想培养神童吗?”德阿纳回应道。
目前还没有人真正知道神童或数学家的大脑是什么样子。德阿纳希望改变这种状况。奥赛的研究中心配备了最新的脑成像设备——PET 和功能性 MRI 扫描仪。正常大脑的图像已经证实了一些病变研究的发现——例如,下顶叶皮层在大多数数字处理过程中活跃,并且左基底神经节在乘法过程中尤其活跃。德阿纳非常希望有一天能让一些专业数学家接受他的 MRI 扫描,同时要求他们选择两个数字中较大的一个,计算 8 乘以 7 等等。他可能会发现专业人士大脑中某个皮层区域系统性地扩大了。
德阿纳和科恩都对此感到兴奋的另一项研究涉及将头发般细的针状电极插入人体受试者的大脑。当然,这不会对健康人进行。它针对的是重度癫痫患者,他们是手术的候选人:电极会留在原位长达一周,期间患者住院,希望能精确地定位其癫痫发作的焦点,以便更好地切除它。德阿纳和科恩与雷恩一家医院的外科医生团队合作,外科医生允许他们在这一周内对愿意的患者进行数字处理实验。电极非常精细,可以记录小神经元集群的电活动。有时电极可能会碰巧放置在下顶叶皮层。德阿纳和科恩认为,通过检查许多患者,他们有可能真正定位数轴。总有一天,电极可能会穿透一个神经细胞集群,该集群仅在患者看到,例如,数字 6 时才放电。
他们的研究中另一个幸运的突破将是找到另一位具有惊人数字障碍的患者。在萨尔佩特里耶医院,科恩——一半是研究神经心理学家,一半是普通神经科医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治疗坐骨神经痛、视力模糊和其他常见疾病。与此同时,他希望能有另一位 N 先生走进诊室。
一月冰冷的阳光透过检查室的窗户,这是一个黄色、消毒、没有个人细节或丝毫装饰的房间。科恩坐在一张旧金属桌前,对面是 F 夫人。她四十多岁,比科恩本人大几岁,但与没系领带的科恩不同,她打扮得一丝不苟。鲜红的夹克,酒红色的头发,圆润的红脸颊——人们会把她想象成一位歌舞厅女演员,而不是她最近残疾前的市场经理。将她归类为“爆竹”般的人,人们就越能感受到她大约一个月前从医院回家的悲痛。人们看到她无助地看着洗衣机却一头雾水——最后试图阅读说明书,好像她从未用过这东西上千次一样。或者站在地铁里,熟悉的地铁,盯着路线图,却也一头雾水;带着朋友同行以求安全。或者焦虑地走进银行,因为她不确定支票上该写什么数字。
当科恩首次检查 F 夫人时,距离她颈动脉血栓切断左半球两个不同区域——布罗卡区(语言中心之一)和下顶叶皮层的血液供应不久,她的语言能力严重受损,数字方面的问题尤其严重。科恩让她用 3 减去 1:她做不到。他让她看手表报时:她做不到。他让她指出一条底部标有 0,顶部标有 100 的线上(一个简化的摄氏温度计)应该位于哪个数字,她说:“一百万?”科恩回忆道,她会随便说什么,任何东西。
一个月过去了,科恩终于有机会再次见到她;如果他要详细分析她的数字缺陷,他将不得不对她进行更多的检查。“收集和解释这些数据是一项巨大的工作,”他在会前解释道,“最终你只会得到一篇文章。所以,我时不时会遇到这样的病人,我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然后……当你作为一名认知神经心理学家工作时,你的科学家兴趣与你作为人类的职责和情感之间总是存在着一种张力——既希望你的受试者的大脑以一种有启发性的方式出现故障,又希望他们康复。中风患者常常会好转,通常是在中风后不久。患有格斯特曼综合征的患者,就像 F 夫人一样,由于某种原因尤其以好转著称。科恩解释说,在最初的几天、几周和几个月内,会有一个逐渐的改善——部分甚至全部缺陷的自发恢复。你常常会看到一些有趣的事情,然后……当你仅仅是观察神经心理学家检查病人时,你会感受到同样的张力,但你的理由远不如科学家本人充分。”
“这里剩下的不多了,”科恩终于对 F 夫人说道,指的是她的疾病。此前,她已经看了几次他的手表,并在一系列算术题中快速作答,只有少数错误和正常的犹豫:3 加 5,5 加 4,13 减 4,12 减 9,6 除以 2。这种我们与老鼠和鸽子共同拥有的数字感,以其基本形式而言,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东西——用德阿纳的比喻来说,它并不比感知空间或颜色的能力更特别。即便如此,没有它仍然是可怕的。F 夫人经历过这一切,今天她只是向医生抱怨说,她的中风神秘地消除了她每天抽两包烟的冲动。当科恩完成他的一系列问题时,F 夫人像一个急切的学生一样回答着——完全平淡无奇,完全正常,完全无聊——很明显,这位女士今后将与神经科学无缘。而总的来说,这样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