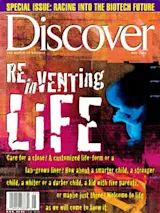每一次安德烈亚伸出舌头,都越来越像是在试图告诉我什么。我才认识她十分钟,但已经知道了她的背景。安德烈亚在 13 个月前的一场车祸中严重头部受伤,警方七个小时后才发现她。送往医院的途中,她曾心脏骤停。急救人员成功重启了她的心脏,但她再也没有恢复意识。
她的三个成年子女竭尽所能帮助母亲从昏迷中恢复——物理治疗、播放她喜欢的音乐、抚摸她、使用香薰,甚至恳求她。但几个月没有任何反应后,他们感到沮丧,开始认真考虑如何才能帮助实现母亲的遗愿。安德烈亚是一名离异的心理学家,她曾和孩子们谈论过凯伦·安·奎因兰的案例,这位年轻女子曾陷入多年的昏迷,当时这件事还在新闻中报道。她让孩子们答应她,如果她 ever 陷入所谓的 pvs(持续性植物人状态),或者严重残疾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愿,他们就允许拔掉她的喂食管,让她可以死去。
如今,在昏迷 13 个月后,安德烈亚的家人通过律师请我为她进行检查并对她的大脑进行 pet 扫描。pet,即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是一种在注射或吸入放射性同位素标记的化合物后进行的医学成像技术,这些同位素会发射带正电的电子(正电子)。借助这项技术,我们可以测量不同脑区的血流量和葡萄糖或氧气代谢。
我所在的医疗中心的调查人员和我之前已经研究了九名长期昏迷的患者。我们认为安德烈亚也处于其中,大多数都是植物人状态。她们的大脑因创伤或心脏骤停而遭受了广泛的损伤。她们的 pet 扫描显示脑血流和代谢显著下降——甚至比患者在深层手术麻醉期间大脑静止时还要低。
然而,有少数患者并非真正昏迷,而是被“囚禁”了。这些患者通常在大脑底部一个更原始的区域——脑干——遭受了广泛的损伤。脑干中有一团神经纤维,称为脑桥,大脑和大部分肌肉神经之间的信息在此交换。脑桥受伤的效果有点像切断一座城市的主要电话通信所产生的影响。这座城市(大脑)仍在运转,但无法与外界(身体)交流,因此从所有意图上来说,这座城市似乎已经被遗弃了。被囚禁的患者失去了自主控制身体的能力,但保留了控制面部的一些能力。她们通常只能移动眼睛。尽管她们意识清醒,但无法交流。我们只研究过少数被囚禁的患者,但她们的 pet 扫描显示出的脑血流和代谢比植物人患者的 pet 扫描更接近正常。
尽管 pet 扫描能告诉我们很多关于大脑功能的信息,但我一直认为,仔细的神经学检查能比这些高科技工具更能了解个体患者。作为一名临床和实验神经学家,我曾检查过数百名在心脏骤停等医疗灾难后昏迷至少六小时的患者。基于最初几天昏迷时的简单床边检查,我和同事们开发了决策树——一种评估一系列症状和反应的方法——能够识别出独立生活前景特别差或前景相对较好的患者。许多患者介于两者之间,即使是谨慎的预测也无法做到。我从不认为这些决策树是万无一失的,但大多数家庭(和法院)都能理解,当患者重返独立生活的几率低于 20 分之 1 时意味着什么。美国人可以接受概率,似乎只有少数人要求 100% 的确定性。
第一步是像她清醒和意识清楚一样向安德烈亚介绍自己。在我看到的绝大多数植物人患者中,我只看到一张无表情的面具,但安德烈亚的脸上却带有一丝生气。我以为她后面可能有一个聪明的灵魂。但这只是我的印象。可观察到的事实是,她不说话,也不移动四肢。我让她先抬起一只手,再抬起另一只手,并让她移动脚。我让她从右到左看,并注意到了一些眼球运动。我给她看了几条书面指令,以防她听不见我说话。没有反应。我大声拍了一下手,她的身体猛地一颤,这表明她的听力没有严重受损。
然后我让她伸出舌头。她慢慢地伸了出来。又伸出来一次,再伸出来。我说她名字的时候,让她做同样的事情。玛丽——没反应。卡罗尔——没反应。苏珊——没反应。安德烈亚——舌头又伸了出来。又问了几个问题后,我越来越确信安德烈亚的意识不仅清醒,而且出奇地完好。我直奔主题。169 的平方根是多少?用舌头数出来,告诉我答案。
她的舌头一进一出地重复着。最后她数到了 13,然后就停下了。就是这样。答案。十三。她真的就在那里和我在一起。我们建立了一个代码:舌头伸出一次代表是,两次代表否。这很慢,但我继续问了她几个关于她生活、地理、国家历史的问题。她每个问题都答对了。通过问一些与她护理相关的问题,我很快了解到,她能回忆起过去几个月在她养老院房间里发生过的几件事。她可能至少有四个月的时间意识到了床边有人在对她说话。从工作人员那里,我得知有些人曾认为她有时会对指令做出反应。但她的反应很少且不一致,没有人确信她有意识。这就是“囚禁”状态——在某种程度上比植物人状态更残酷。
现在,问题来了。我知道你曾指示你的家人,如果你 ever 成为植物人或严重残疾,就让你死去。这是真的吗?舌头伸出一次:是。你仍然这么想吗?又一次,舌头伸出一次:又一个“是”。
我该怎么办?这是否意味着她想死?现在?当时,我想,我是唯一知道她有意识的人,而她似乎在告诉我她想死。我一直支持家人停止对植物人患者的治疗。我甚至支持患有绝症的患者自己做出这样的决定,只要他们不是在抑郁的阴影下做出的决定。但我从未处于过这种境地。安德烈亚是有意识的;我难道不应该告诉她的家人吗?
安德烈亚的呼吸和脉搏加快了。她显得很激动。她想表达什么,但无法做到。在几个错误的提问方向后,我意识到安德烈亚试图表达的是什么。如果她知道自己永远不会好转,她仍然想死。但现在她的意识被发现,她确信自己将接受强化治疗,会好转,并且会真正恢复正常。是这样吗?她的舌头伸出一次——是的。我给家人打了电话。
她的孩子们花了点时间才接受安德烈亚有意识,但他们很快就适应了。她的 pet 扫描结果显示,她大脑的血流和代谢接近正常——与其他少数被囚禁的患者相似,与植物人患者不同。她的 ct 扫描,一种先进的 X 射线技术,显示她大脑中有斑点状损伤,但脑干的损伤比大脑皮层(负责复杂精神功能的上层区域)更严重。
安德烈亚很幸运拥有可观的经济资源,这使她能够接受广泛的治疗。虽然这花费了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她确实有所好转。几周之内,她就能用左手指向字母板上的字母,拼写单词和句子。过了一段时间,她得到了一台配备程序的电脑,屏幕上会显示一连串字母;她可以按一个按钮来选择她需要的字母。在选择了第一个字母后,程序会显示最有可能的后续字母,甚至单词,所以安德烈亚的表达方式虽然仍然很费劲,但变得更容易了一些。最终她开始说话。她的言语很难理解。对她和听她说话的人来说,这都需要巨大的努力,但她甚至成功地通过电话让别人听懂了她的话。
安德烈亚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非凡的康复,是什么原因呢?与大多数被囚禁的患者不同,她的大脑损伤显然保留了重要的连接,并允许她通过持续的努力恢复功能。而这种努力又是由她渴望独立和控制自己世界的强烈愿望所驱动的。她对独立的渴望加速了她的康复,但有时也阻碍了她的进步。通过坚持自己的方式做事,她经常惹恼那些试图帮助她的人。这种需要坚持控制的欲望在我们所有人身上都很常见。尤其是在我们生病时,这种欲望更容易理解。如果医务人员、家人和其他人能够接受这一点,有时就能取得巨大的进步。但这也会在工作人员中引起怨恨和疏远,而这在与安德烈亚共事的人中发生过几次。
有时,即使在善意的包围下,她对控制的渴望也会伤害到她。安德烈亚非常自豪她能说出结构良好的句子。问题是,她的言语虽然可以理解,但含糊不清、含糊不清。我们许多人经常误解她的话。尽管别人请求她换一种说法,她还是会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同样的句子,一字不差,当然我们也会一次又一次地听到同样的错误。她本来可以帮助沟通,但却选择用她的句法(一旦我们理解了)来让我们惊叹。
又过了几年,安德烈亚住在曼哈顿自己的公寓里,几乎需要全天候的帮助。我和妻子一天晚上见到她,陪她乘坐电动轮椅穿过现代艺术博物馆。她坚持要自己坐公交车回家。另一次,她和我一起去看了一场电影。之后,我们去喝咖啡。安德烈亚自己端着咖啡杯,虽然有些洒在她裙子上。在她五十岁生日时,她出乎意料地自己走了几步。她最终说服了一位法官撤销了为帮助她而设立的监护权,她掌控了自己的财务。
安德烈亚尽力赚钱,但她受损的言语使她难以恢复心理学家的执业。她为大众和专业期刊撰写了几篇文章;她的培训使她能够提出对许多面临类似困境的家庭和患者有益的见解。但这些文章在经济上并没有帮助她。她试图将她的生活故事改编成电影,但失败了。她在一个地方政府残疾人委员会任职,但那是志愿工作。她正在慢慢破产。
结局与安德烈亚的生活一脉相承。最终,她的治疗耗尽了她的财力。她只看到了两个选择:要么结束自己的生命,要么接受政府援助——被机构化——并且,在她看来,失去掌控自己生活的能力。她拒绝考虑和她的孩子们同住,或接受亲戚的支持。她最终得出结论,她唯一的选择是自杀,并向媒体宣布了这一决定。接下来的几周里,出现了一些报道,并做出了一些无效的法律努力来阻止她,但她完全掌控着自己的思想。尽管她曾希望这次宣传能带来捐款,但并没有实现。她设定了一个秘密的自杀日期。她知道吞咽对她来说非常困难,如果她服用镇静药片,她可能会在服用足够剂量致死之前就睡着了。但当人们发现她死亡时,空药片瓶就放在她身边。
她死的方式与她活着的方式一样,通过巨大的、英勇的意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