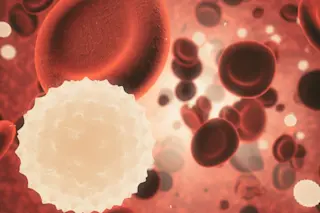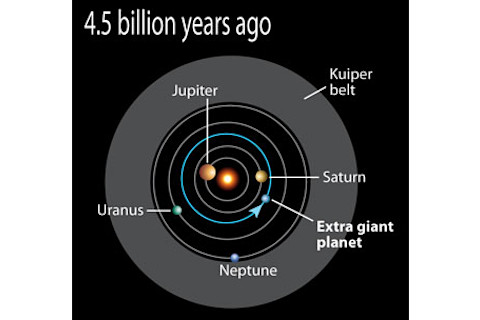
对除了神经科医生之外的任何人来说,帕特里克·伦尼奇 (Patrick Rennich) 的偏头痛似乎是一种诅咒。它们以一种反常的规律性,在他踢足球或打篮球等运动后发作——任何需要沿着球场或球道冲刺的运动。在他被头部一侧令人作呕的疼痛击中前不久,伦尼奇会经历一种被称为视觉先兆的神经紊乱——这始于他左侧视野中心附近的一个缓慢扩大的盲点。不久之后,伦尼奇看到静态图像,就像电视屏幕上的雪花。这种先兆看起来“就像我在沸水中移动一样”。这种模式是如此可预测,以至于28岁的伦尼奇,一位来自马萨诸塞州阿克顿的电气工程师,可以这样说:“如果你想让我在下午两点出现带先兆的偏头痛,我就可以在两点给你一个带先兆的偏头痛。” 这正是神经科医生迈克尔·卡特勒 (Michael Cutrer) 所希望的。卡特勒在波士顿的马萨诸塞州总医院和布莱根妇女医院工作,多年来一直在寻找像伦尼奇这样的人。这位神经科医生希望,在患者出现先兆期间进行磁共振成像 (MRI) 扫描,能够为他头骨内部发生的事情提供线索。1998年之前,没有人这样做过,而且原因充分:几乎没有偏头痛患者能够按指令召唤出先兆,而且很少有人愿意躺在引发幽闭恐惧症的MRI管中等待先兆的发生。卡特勒曾遇到过一些潜在的患者,但都没有成功。一位患者承诺生洋葱会奏效,“但我们让他躺在那里咔嚓咔嚓地吃——什么也没发生,”卡特勒说。伦尼奇似乎值得一试,所以卡特勒请他和妻子简 (Jean) 到他研究实验室旁边的基督教青年会 (YMCA)。这对夫妇玩投篮游戏,输的一方在篮球场上来回冲刺,但有一个修改:“如果我输了,我就跑,”伦尼奇说,“如果我妻子输了,我也跑。”
大约一小时后,伦尼奇开始注意到视力出现扭曲,于是赶紧跑到旁边的实验室,仰卧在MRI机器不透明的白色管子里。进去后,他将目光聚焦在管内屏幕上投射出的交替棋盘图案上。同时,MRI监测着伦尼奇大脑皮层,特别是控制视觉的区域的活动。稍后,结果将进行处理并用颜色编码——红色表示神经活动高的区域,橙色和黄色表示较低的水平,白色对应最小的活动量。根据MRI结果,伦尼奇进入管内38分钟后,他的脑部图像上出现了一个黑暗区域——完全没有颜色——表明大脑皮层一小部分区域的神经元不再传输视觉信息。该区域缓慢扩大,“就像小石子投入池塘产生的涟漪一样,”卡特勒说。伦尼奇的先兆发作了。
十年前,伦尼奇的医生绝不会检查他的大脑来寻找偏头痛的来源。事实上,大脑本身可能是导致问题的原因这一观点,对头痛研究人员来说一直难以接受。“甚至在15年前,提出这种观点都会被认为是异端,”伦敦大学学院的神经科医生彼得·戈兹比 (Peter Goadsby) 说。首先,大脑本身没有感觉,即使通过颅骨切口插入探针也感觉不到。“由于大脑没有感觉,头痛的疼痛位于外周,所以很多人都认为问题出在那里,”戈兹比说。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大脑不仅是疼痛的帮凶,更是主要嫌疑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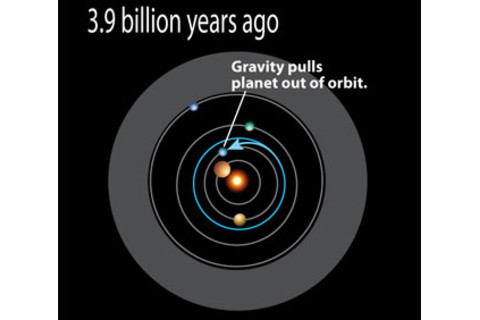
大脑是问题根源的观点一直难以被研究人员接受。
在偏头痛先兆期间观察大脑的电化学活动,只是理解头痛奥秘的新途径之一。神经科医生早已了解物理证据。大脑外层,即脑膜中的血管变得过度扩张并对流经它们的血液变得过度敏感。但寻找头痛疼痛的真正原因多年来一直困扰着神经科医生和患者。随着卡特勒MRI等技术的发展,这个谜团变得更加令人费解。通往疼痛的路径清晰可见,但为什么这条路径会存在仍然是个未知数。
神经元的活动虽然复杂,但通常是可预测的。当神经元受到刺激时,钠离子涌入细胞,钾离子涌出,使神经元带正电化学荷。这迫使细胞放电,从而将信息传递给其他神经元。然而,在偏头痛患者中,神经元不再理性地活动。卡特勒认为,在伦尼奇的先兆期间,他的视觉神经元开始相互之间略微不同步地放电;它们似乎在没有相互传递信息的情况下放电,而不是响应视觉刺激。在MRI上,这种几乎同步的放电模式类似于一道波浪滚向海岸线。这种现象以前只在动物实验中观察到,被称为皮层扩散性抑制。卡特勒认为,伦尼奇MRI上的黑暗区域是这一过程的摄影记录,并揭示了伦尼奇不断扩大的盲点的进展。卡特勒说,伦尼奇在先兆中看到的闪烁光线,很可能是钠离子涌入并过度刺激视觉神经元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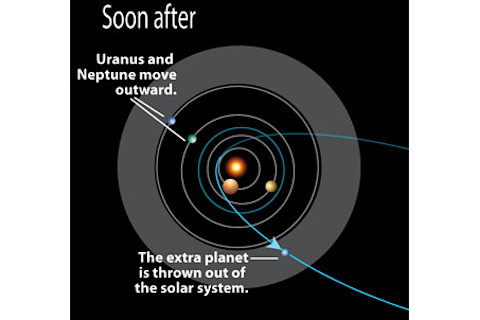
如果研究越来越将慢性头痛的罪魁祸首指向基因,那么环境因素——从巧克力和坚果到阳光和压力——又如何成为诱因呢?几十年来,科学家们一直认为某些食品添加剂会导致头痛。例如,酪胺是一种存在于红酒和陈年奶酪中的化学物质,被认为可以扩张血管。“但人们给头痛患者服用酪胺提取物,他们并没有头痛,”哥本哈根大学神经科医生杰斯·奥莱森 (Jes Olesen) 说。

虽然咖啡因具有收缩血管的作用,因此咖啡作为早期有效的头痛疗法,但许多医生现在将任何形式的咖啡因——咖啡、茶或可乐——视为强效头痛诱因。“咖啡因的特性使其与鸦片类药物相似,”纽约头痛中心的亚历克斯·莫斯科普 (Alex Mauskop) 说,“当你定期服用它时,你的身体会对其产生耐受性,并产生身体依赖。”
研究表明,每天习惯性饮用少至两杯半咖啡的人,如果突然戒断,就会出现头痛,这种现象被称为反弹性头痛。“但对于容易头痛的人来说,影响可能更为极端,”莫斯科普说。毫不奇怪,他治疗新患者的第一步就是帮助他们戒除咖啡因。“否则,其他治疗方法都无法有效。”
大约30分钟后,伦尼奇的先兆消退了,他感觉相对正常近一小时。然后他的偏头痛发作了。在皮层扩散性抑制期间异常放电的视觉神经元,释放了大量的钾离子。随着时间的推移,钾离子从视觉皮层扩散到脑膜中控制疼痛的神经元。这些位于脑膜血管壁中的神经元开始放电并释放神经肽,告诉大脑记录疼痛并使血管扩张。扩张的血管随后促使疼痛神经元再次放电。本质上,一个导致疼痛的反馈回路被启动,产生了偏头痛的痛苦。对于没有先兆的偏头痛患者,疼痛的原因不那么明显。一些神经科医生怀疑皮层扩散性抑制可能始于大脑中不参与感觉处理的区域,因此最初的影响不明显。
更大的大脑,更多的头痛?
主要类型头痛的起源仍然是个谜:头痛似乎是由完全正常的大脑结构异常功能引起的。但是,最近,由伦敦大学学院神经学家彼得·戈兹比 (Peter Goadsby) 领导的一个团队,发现了丛集性头痛患者大脑内部存在结构差异的证据。“目前关于丛集性头痛神经生物学的观点需要彻底修正,”他说。
从1997年开始,戈兹比的团队开始使用功能成像技术,比较丛集性头痛患者和正常患者的大脑。1998年发表在《柳叶刀》上和1999年发表在《自然医学》上的结果显示,丛集性头痛患者的下丘脑区域异常增大,下丘脑是大脑中调节昼夜节律的部分——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这些头痛倾向于周期性发作。戈兹比尚不清楚所涉及的脑细胞是否比正常患者的更大,或者是否仅仅数量更多;那需要解剖大脑。“我们正在照看一些患有丛集性头痛的老年患者,”他说,“但目前很清楚,中枢神经系统是关键所在。”
在某个时候,我们大多数人都经历过头痛——一个信号,表明我们处于压力之下、过度劳累,或者前一天晚上喝了太多酒。但大约有4000万美国人患有原因不明的严重头痛。多年来,研究人员一直认为问题要么出在脑膜血管中,要么更常见的是出在患者本身。“如果有人膝盖被踢到,他们会感受到疼痛;这是合理的,”戈兹比说,“但我们发现慢性头痛患者的疼痛没有物理刺激;这是不合理的。”当医生们用尽所有可能的解释时,他们通常会将患者转介给精神科医生。“由于医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他们有时会试图指责患者想象事情,”从14岁起就患有偏头痛的卡特勒说,“现在我们知道,大脑本身是头痛研究的新领域。”

梅奥诊所网站提供最新的头痛信息:www.mayohealth.org/index.htm。
+++
一名丛集性头痛患者感觉“眼睛好像被强行推出眼眶”

在慢性头痛患者中,大脑似乎对光线和压力等环境因素、女性每月荷尔蒙周期,或诸如生吃洋葱或打篮球等怪异的事情敏感。“我们的研究从认为大脑不参与,到现在我们确信它参与其中,”戈兹比说。这一新观点已经导致了专门药物的开发,这些药物可以在头痛发作中期停止头痛并完全预防头痛。
头痛药物简史
在漫长的岁月中,慢性头痛带来的痛苦只有治疗造成的损害可与之匹敌。在古代阿拉伯世界,将一瓣大蒜埋在太阳穴皮肤下会导致化脓,这被认为可以缓解头痛。其他可疑的疗法还包括注射砷、氰化钾,甚至放射性元素钍。
即使在今天,19世纪末开发的头痛药物衍生物仍然存在。麦角胺,一类收缩血管的药物,来自攻击黑麦的有毒真菌。在中世纪,那些大量食用感染麦角菌的黑麦面粉的人会患上“圣安东尼之火”,这是一种以晚期坏疽为特征的疾病。现在,麦角被有效且相对安全地用于药物中,例如甲基麦角酰胺,以预防偏头痛。有了这些麦角衍生的药物,坏疽不再是威胁。医生们更担心的是恶心和心脏血流量减少。
“真正的悲剧是,很多人不知道有帮助可寻,”费城托马斯杰斐逊大学医院的神经科医生大卫·西尔伯斯坦 (David Silberstein) 说。相反,许多绝望的头痛患者滥用成瘾性药物,如巴比妥类药物和鸦片类药物。即使那些服用非处方止痛药的人也可能不安全。阿司匹林、对乙酰氨基酚和其他止痛药也可能导致反弹性头痛。西尔伯斯坦说,严重过量使用可能导致肾衰竭和死亡。
对于那些头痛患者来说,这无疑是个好消息:仅在这个国家,就有大约600万人患有所谓的慢性紧张性头痛,类似于每个人偶尔会遇到的那种——只不过对这些人来说,它们几乎每天都会发作。偏头痛通常影响头部的一侧,困扰着2300万到2600万人。不幸的是,偏头痛的诊断数量一直在稳步上升:《神经病学》杂志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1989年(与1979-1981年的数据相比),女性偏头痛诊断发生率增加了56%,男性增加了34%。大约一百万人患有丛集性头痛,这是一种极其剧烈的现象,主要发生在男性身上。根据18世纪首次记录的此类头痛描述,患者感到“好像他的眼睛被缓慢地强行推出眼眶,疼痛如此剧烈,以至于他几乎发疯”。
“我们现在看待头痛的方式,就像我们看待癌症一样”

也许大脑本身可能是导致头痛的第一个线索是在20世纪40年代发现的。意大利的研究人员发现证据表明,刚刚经历偏头痛的人的尿液中含有神经递质血清素的分解产物。这一发现暗示血清素在偏头痛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其过程仍然是个谜。当研究人员发现注射血清素耗竭剂会导致偏头痛,即使这个人以前从未患过偏头痛时,这个想法获得了更大的动力。“目标是开发能够模仿血清素作用的药物,”亚利桑那州斯科茨代尔梅奥诊所的神经科医生戴维·多迪克 (David Dodick) 说。这种方法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一种名为曲普坦类的新型药物问世,以Imitrex和Zomig等品牌名销售。这些药物与脑膜血管中发现的一种特定血清素受体亚型结合。这会导致血管收缩并关闭释放神经肽的神经末梢,从而中断导致疼痛的反馈回路。尽管远非万无一失,但曲普坦类药物可以在偏头痛发作中期停止疼痛。
随着新的研究——例如卡特勒关于先兆本质的理论——为定制有效的药物带来了更多可能性。“我们正处于治疗新时代的开端,”哥本哈根大学神经学系主任兼《头痛》一书编辑杰斯·奥莱森 (Jes Olesen) 说。最有希望的研究集中在理解另一种化合物——一氧化氮的作用。研究头痛的神经科医生长期以来都知道一个不寻常的事实:当心脏病患者将一小片硝酸甘油片含在舌下以预防心绞痛发作时,硝酸甘油在体内转化为一氧化氮,并立即扩张心脏血管。然而,在一些患者中,它也会在六小时内引发偏头痛。“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副作用,”奥莱森说,“而且似乎极有可能大脑中的一氧化氮在引发偏头痛中发挥着作用——不仅在心脏病患者中,在所有患者中都是如此。”通过解开一氧化氮的精确作用(它似乎与大脑中血清素的分解有关),奥莱森和其他人相信他们可能能够开发出比曲普坦类药物更有效的抗头痛药物。“这是目前药物研究最热门的领域,”他说。
一个女人的传奇
自1986年她的第二个女儿出生以来,44岁的凯瑟琳·希利 (Catherine Healy),一位来自缅因州巴港的自由摄影师,一直饱受慢性、恶心性头痛的折磨。“它们是我每天形影不离的伴侣,”她说,“我的病无法通过CT扫描、MRI或X射线来定义。”尽管如此,这些头痛改变了她的生活。最初的几年里,希利的头痛每月发作三到五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频率和强度都增加了。“我感觉自己连50英尺都走不动,”她说,“我尝试吃饭时,餐具都会从我手中掉落。”医生们怀疑过狼疮,然后是多发性硬化症,她说,“有一两个医生甚至提到精神科医生。”
在麻省总医院拜访神经科医生迈克尔·卡特勒后,最终诊断是伴有视觉先兆的偏头痛。希利说,疼痛是可怕的,但先兆可能更糟。“有时候我正在和我丈夫说话,然后我发现我看不清他的脸,”她说。她的幻觉包括“恶毒的蛇在空中飞舞;这太可怕了。”希利有一次在楼梯上遇到她的狗,惊讶地停了下来。“她就像毕加索立体主义时期画的一样,”她说,“图像就是那么扭曲。”
头痛有效地结束了希利的职业生涯。为了限制头痛的频率,她戒除了可疑的诱因。“结果,我过着非常无菌的生活,”她说。她戒除了所有腌制和熏制食品、巧克力、香蕉、苹果、橙子和贝类。甚至维生素也可能有问题。20世纪90年代初,当一类名为曲普坦的药物问世时,希利曾使用过它们,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的疗效逐渐减弱。她现在主要服用一种名为甲基麦角酰胺的麦角胺(参见“头痛药物简史”,第61页),但长期使用可能会导致心脏和肺部损伤。
“我选择与哪个魔鬼共眠——偏头痛还是组织损伤,”希利说。为了平衡两者,卡特勒给她开了六个月的甲基麦角酰胺,之后两个月希利主要服用止痛药——并且每天都会偏头痛。“偏头痛对一百个人来说可能是一百种不同的事情,”希利说,她已经为其他患者成立了一个支持小组。“我需要尽我所能帮助他人。”
越来越多地,神经科医生怀疑基因异常可能是某些(如果不是所有)头痛的根源。在20世纪90年代,研究人员将一种特别罕见的头痛类型——家族性偏瘫性偏头痛(作为显性遗传特征在家族中遗传)的病因追溯到19号染色体上的一个单一基因。这条染色体编码神经细胞膜中钙通道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调节离子进入神经细胞,该通道控制神经元何时放电。这种突变使大脑周围动脉中的神经处于持续的过度活跃状态,导致它们产生疼痛。“目前尚不清楚钙离子流经通道是增加还是减少,”奥莱森说。
尽管家族性偏瘫性偏头痛很罕见,但染色体起源的发现改变了所有头痛研究的方法,神经科医生已经开始在头痛患者的多个染色体位点寻找其他异常。“我们现在开始像对待癌症一样思考头痛,”戈兹比说,“我们相信它们有特定的遗传基础,在一个人的一生中以某种方式被触发。”最近,戈兹比证明,下丘脑后部——大脑中参与昼夜节律的部分——在患有丛集性头痛的人中明显更大。
然而,找到遗传原因并不能阻止疼痛。虽然神经科医生在他们的双盲实验世界中辛勤工作,但医生和患者都在寻找更直接的治疗方法。曲普坦类药物比以前的药物更有效,但远非万无一失。“它们可能在80%的时间内有效,但在一些患者中,由于我们不确定的原因,它们会失去疗效,”奥莱森说。患者因此被迫探索替代方案,尝试从针灸(可能影响血清素水平)到被称为A型肉毒杆菌毒素(或肉毒杆菌)的细菌混合物。“这与人们注射到额头以暂时麻痹肌肉和减少皱纹的物质相同,”曼哈顿纽约头痛中心的亚历克斯·莫斯科普说。整形外科医生注意到肉毒杆菌注射有一个令人惊讶的副作用。
它们似乎能抑制偏头痛。1999年的一项研究表明,这种毒素可以使易患偏头痛的患者的偏头痛减少多达50%。“没有人能解释其机制,但我已经见过它奏效数百次了,”莫斯科普说。
对于丛集性头痛,病因和治疗方法甚至更模糊。丛集性头痛倾向于周期性发作,每天发作一到两次。它们更可能袭击吸烟者,可由酒精触发,并且通常可以通过吸纯氧来缓解。“一位病人只有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开车,头伸出窗外才能缓解,”莫斯科普说。医生们称丛集性头痛为“自杀性头痛”,因为已知有些病人会选择最终的解脱。
然而,仅仅开发更有效的治疗方法并不意味着患者能够负担得起。例如,曲普坦类药物价格昂贵。一次口服剂量来终止一次偏头痛需要10到15美元;一次注射需要35美元。一个典型的患者可能每月需要超过六次。但对于丛集性头痛,费用呈指数级增长。例如,新泽西州律师韦恩·韦纳 (Wayne Weiner) 是少数患有慢性丛集性头痛的人之一,这是一种罕见的疾病,头痛每天发作多达10到12次,需要10到12剂曲普坦。韦纳查看的一项保险计划每月只涵盖六次注射。现在通过他家族的律师事务所进行自保,韦纳自己支付费用;去年花费了4万美元。“无论从身体上还是经济上,这都是一种令人疲惫的疾病,”他说,“它会让你筋疲力尽。”
为了降低成本,管理式医疗公司试图将患者转导到其他药物,要么是不同制药公司生产的更便宜的曲普坦类药物,要么是完全不同类别的药物。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导致灾难。“我曾看到保险公司建议患者改用成瘾性麻醉剂,”费城托马斯杰斐逊大学医院的神经科医生大卫·西尔伯斯坦 (David Silberstein) 说。
医生们开始反击。他们成立了国家头痛联盟——由西尔伯斯坦担任联合主席——旨在建立头痛患者的护理和治疗标准。“现在,任何想开办头痛诊所的人都可以开——我的意思是谁都可以,无论是医生、脊椎治疗师还是心灵导师,”西尔伯斯坦说。有了更严格的标准,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但如果实施更严格的处方协议,医生和医院将有能力迫使保险公司承担他们推荐的治疗费用,西尔伯斯坦说:“当全世界的医疗机构联合起来反对他们时,没有任何保险公司会争论。”
在此之前,患者只能自行寻找治疗方法,与保险公司斗争,并等待下一阶段的研究以获得更好的药物。“我可能会减少打篮球了,”帕特里克·伦尼奇说,“但我感到一些安慰:我现在知道问题不在我身上——而是在我的大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