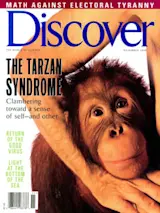曾经,海底似乎是一片黑暗的沙漠。众所周知,阳光通过为光合作用提供能量,使生命成为可能,而阳光只能穿透海洋深处最初的几百码。在更深的地方,少数生物可能仍然靠搜寻从海面漂流下来的有机碎屑维持生计。但在数千英尺深、漆黑一片的海底,几乎不可能有任何生命。
然后,在1977年,水下探险家发现那里确实有东西,而且数量相当多。在中洋脊,新的海底从地球内部以熔岩的形式上升,冷海水与上升的岩浆混合,被加热到650度,通过烟囱状的热液喷口喷涌而出,研究人员偶然发现了熙熙攘攘的生态系统。烟囱两侧附着着厚厚的白色细菌垫;周围是八英尺长的茎状蠕虫,在水中摇摆,而无眼的虾则像蛆虫一样在烟囱周围蠕动。所有这些都依靠喷口硫化合物中蕴含的能量茁壮成长。海底可能仍然黑暗,但现在它被发现点缀着花园。
然而,在过去的八年里,水下探险家发现这张图景仍然不完整:海底有光。热液喷口发光,虽然光线微弱到人眼无法察觉,但这绝不意味着它没有意义。物理学家认为,尽管有些光可能是由强烈的热量产生的,但大部分光必须归因于某种尚未知晓的过程。与此同时,生物学家表示,这些喷口有足够的光线进行光合作用。研究人员还不能确定是否有任何生物实际上靠这种光生存,但如果它们是,它们将代表第一个已知的不依赖阳光的自然光合作用实例。进化的意义可能更深远:不仅这种深海光现在可能正在为光合作用提供能量,而且在38亿年前,它可能开启了整个过程。
这种现象的探索以及围绕它的许多猜测的幕后人物是名叫辛迪·李·范·多佛(Cindy Lee Van Dover)的女性。范·多佛对深海光的追寻始于1986年,当时她在科德角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正在寻找一个博士项目。就在一年前,探险家们在大西洋发现了第一个喷口,并捞起了一些生活在那里的灰虾供生物学家研究。范·多佛的导师弗雷德·格拉斯尔(Fred Grassle)拿到了一些保存下来的样本。范·多佛回忆说:“我刚开始读研究生,弗雷德说,‘辛迪,你可以把这个作为你的项目。’我当时正在研究它们的摄食生物学,试图弄清楚它们在整个生态系统中的位置。”
乍一看,这些虾和生活在水面附近的更常见的亲戚没什么两样。主要的区别是这些虾没有眼柄。考虑到它们栖息地的黑暗,这并不令人惊讶——据推测,虾已经失去了眼睛,因为它们不再需要。事实上,探险家们将这种虾命名为Rimicaris exoculata,即无眼裂缝虾。
但当范·多佛查看在喷口处拍摄的虾的录像带时,她注意到每只动物的背部前三分之一处都有一对奇怪的亮条纹。她之前在她的标本上没有发现它们,因为它们在保存过程中已经变得暗淡。她切开虾的背部,发现这些条纹实际上是两片组织瓣,它们连接并通向一根大神经。它们似乎是某种感觉器官。这时,范·多佛有了一个她称之为“愚蠢”的想法:她想,这个器官会不会是某种眼睛?
她联系了史蒂文·张伯伦(Steven Chamberlain),他是锡拉丘兹大学的神经科学家,专门研究无脊椎动物的眼睛。“她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我想让你看看这个,告诉我它是不是眼睛,’”张伯伦回忆道。她把东西寄给我,一开始我说,‘天哪,我不知道它是不是眼睛。也许吧。’他把一些组织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其精细结构。组织已经分解——很可能是因为虾保存不当——但张伯伦仍然得出结论,他看到的是受损的光感受器。“我能想象它在被损坏之前是什么样子。如果你毁了一只眼睛,它就会是这个样子。”
范·多佛接下来求助于伍兹霍尔的生理学家埃特·舒茨(Ete Szuts),他是色素分子专家。舒茨从器官中分离出色素并进行测试,以确定它吸收哪些频率的光。他发现其吸收模式与一种名为视紫红质的物质相同——视紫红质是人类和其他动物视网膜中的色素,它捕获光线并使我们能够看见。现在范·多佛只能得出结论,她那个“愚蠢”的想法是正确的:虾有眼睛,尽管它们已经被进化彻底改造。它们无法形成图像,但它们密集的感光细胞表明它们是敏感的光探测器。然而,如果一只虾生活在无尽的黑夜中,它又能看到什么呢?她开始怀疑喷口是否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黑暗。
这是一个可能性,即使只是勉强。当水或岩石被加热到热液喷口周围的温度时,它会像加热的烤面包机线圈一样,以光的形式辐射出部分能量。大部分辐射将是红外波长,因此所有已知活体动物都看不见。但其中一小部分将出现在可见光谱的低端,也许虾能够收集到这一点微弱的光。很难说有多少光可能可用;喷口周围的冷海水可能吸收了大部分光,但没有人计算过在这种奇异环境中会有多少热辐射是可见的。当然,也没有人注意到这些地方有任何光线。
范·多佛需要有人下去看看。她找到了华盛顿大学的地质学家约翰·德莱尼。德莱尼计划乘坐“阿尔文”号潜水器执行任务,他打算使用灵敏的数码相机调查华盛顿州海岸胡安·德·富卡海岭喷口周围的海底。范·多佛很快说服他在一次潜水中将相机配置为寻找喷口光。于是,在1988年6月,德莱尼潜入海面以下一英里半,将自己定位在距离喷口汹涌水流一英尺半的地方,他做了一件以前任何喷口访客都没有做过的事情:他关掉了灯。这是一个危险的动作,因为喷口烟雾可能会熔化相机或使“阿尔文”号的窗户变黑。范·多佛在母船“亚特兰蒂斯二号”上,在甲板上踱步,而德莱尼将相机对准在他看来一片漆黑的地方。然后,当“阿尔文”号开始一个小时的上升时,她收到了来自海底的一条简短信息:喷口发光。德莱尼的相机捕捉到喷口处一道清晰的光芒,像柴郡猫的笑容一样在黑暗中徘徊。
范·多佛最初的运气让她登上了科学和大众媒体,但她首先承认她的工作远非无懈可击。即使德莱尼进行了第二次潜水并在镜头前放置了一系列滤光片,范·多佛也只能粗略猜测喷口正在产生什么样的光。关于她的虾也有疑问。发现一些类视紫红质的色素和一些看起来像感光细胞的结构固然很好,但如果她记录到神经对光的反应或观察到虾在野外使用其集光器官,她的论证会更加坚实。一些怀疑论者认为这些器官很可能是无功能的、退化的眼睛。另一些人甚至认为这些结构可能根本不是为了视觉,而是为了听狂暴的喷口水流,或闻其携带的臭鸡蛋气味的硫化物。
然而,接近真相却很困难。如果像范·多佛所说,虾拥有极其敏感的光探测器,那么即使在阿尔文号灯光下暴露一瞬间,它们也会永久失明。因此,观察虾的自然活动方式是不可行的。但张伯伦觉得,如果他能获得更多的虾并妥善保存,可能会有更多发现。“解剖学是一门艺术,”他解释道。“如果你拿着朱莉娅·查尔德的食谱尝试做一道法式乳蛋饼,你第一次肯定会弄得一团糟。那些制作第一批样本的人有一个好食谱,但他们没有经验。”
张伯伦做到了。1993年,他捕获并保存了一批新的虾,它们的器官完好无损。然后,在锡拉丘兹,他与同事们成功绘制出虾所谓眼睛的结构图,他们所看到的一切都证实了范·多佛的灵感直觉。这些器官被证明是为收集微弱光线而精心设计的,超大的集光感光细胞占据了大部分可用空间。虾有复眼,很像苍蝇,有多个晶状体将光线聚焦到独立的感光细胞组上。大多数虾在感光细胞之间有黑色的色素细胞屏障,以防止光线从一组泄漏到另一组并模糊图像。然而,在R. exoculata中,色素细胞被藏在眼睛下方,不碍事,让所有感光细胞都有机会接收微弱的光子雨。如果张伯伦对他正在看的是眼睛还有任何疑问,那么当他的团队检测到其他虾只在眼睛中使用的神经递质(化学信使)时,这些疑虑就烟消云散了。张伯伦说:“对我来说,这只是锦上添花。”
张伯伦的团队此后在大西洋同一喷口发现了第二个虾种,也具有同样的眼睛。这些更小、橙色的动物也将眼睛背在背上,张伯伦认为这个位置对这两个物种的生存至关重要。这些动物生活在烟囱的侧面,以细菌垫为食。由于光线从烟囱顶部倾泻而出,虾通常生活在它的阴影中。如果它们移出阴影,喷口光线就会落在它们的背上。记录到微弱的光芒会告诉虾它们处于错误的位置。它们可能只是从喷口漂流到开阔水域,或者它们可能犯了更严重的错误,沿着烟囱侧面向上移动,直到它们离喷口太近——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可能会被冲走并立即被煮熟。
张伯伦说,有人需要研究喷口处所有其他动物的视觉结构。没有人做过这件事,因为我们都认为它们是盲的。鱼呢?螃蟹呢?它们的眼睛长什么样?我们对这些都一无所知。
在喷口光芒中短暂亮相后,辛迪·范·多佛的生活很快变得忙碌起来。1989年获得博士学位后的第二天,她加入了“阿尔文”号团队,成为该潜水器第一位女驾驶员。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深海生物研究让她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奔波。直到1993年,她才抽出足够的时间再次研究光线。
到那时,她已经知道她最初对喷口光的测量(德莱尼通过在相机前放置不同的滤光片获得的)是极其粗糙的。结果有点像看电影,几分钟只看到红色,然后只看到蓝色,然后只看到黄色。范·多佛只是需要更清晰地看到光线。幸运的是,她能够与一位能给她一双新“眼睛”的人合作。
艾伦·查维(Alan Chave)在伍兹霍尔以海洋物理学家的身份谋生,但海底探险家们却依赖他作为非凡传感设备发明家的才能。在自愿帮助范·多佛之后,他很快就发现她需要的是一台工业级光度计,用于观测地球上最微弱的光线。他掏空了一根透明的有机玻璃棒,并在里面放置了四个光电二极管,这些二极管每次受到光子撞击时都会发出电流。查维说:“建造起来很棘手,因为在那种光线下,光电二极管中的电流并不大。你已经接近一个像样的放大器的噪声水平。一点点杂散电流就能要了你的命。”
他把自己的发明命名为opus——水下光学特性传感器。就像虾的眼睛一样,opus无法形成图像,但它可以测量微弱光的强度。最棒的是,查维可以在每个光电二极管前面放置一个滤光片,这样它就可以同时测量四个不同频段的光线。
1993年,以及去年春天,范·多佛和查维总共进行了十几次潜水,带着 opus 下去。每次他们浮上水面,都不知道自己确切看到了什么,直到他们把 opus 带到马萨诸塞州剑桥的哈佛-史密森尼天文台。在那里,他们可以用一种通常与望远镜相机结合使用的设备来校准它的灵敏度,这种相机可以捕捉微弱的星光。在普林斯顿物理学家乔治·雷诺兹的帮助下,他们才能够进行计算,从而确定从喷口发出的光子数量。
这次深海数据采集进展缓慢,但物有所值。正如范·多佛和她的同事们今年夏天报告的那样,喷口处的光芒并非普通光。例如,在某些地方,它实际上是间歇性闪烁的,这不是单纯热辐射就能产生的模式。他们发现,喷口光在所有频率上都比雷诺兹预测的单纯热辐射光谱亮得多。在某些波长下,它的强度甚至比预测高出19倍。
查维说:“当然有热辐射,但也有别的东西。除此之外,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那是什么。”候选者比比皆是,而且大多数都很奇特——例如,矿物质可能正在开裂并发出光芒,或者气泡可能正在内爆,高压可能正在产生光芒。查维正在建造一台新相机,它将能够缩小可能性范围:与 opus 不同,这台相机将能够看到图像。它将由一个大型数字相机芯片组成,带有九个不同的镜头,每个镜头都聚焦在芯片的不同区域,并且每个都设置为收集不同频率的光。查维说,当他明年秋天带着新相机进行潜水时,他基本上能够用一台非常灵敏的相机拍摄九部不同的喷口影片,灵敏度之高,几乎可以测量单个光子。
与此同时,opus 的结果足以让范·多佛兴奋不已。在陆地上,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一棵树每平方英寸每秒大约被十万亿亿(10的18次方)个光子沐浴。但研究人员发现,一些生物在远低于这个水平的光线下也能进行光合作用。黑海的细菌保持着记录:它们在水下240英尺的地方勉强生存,那里它们每平方英寸每秒只接收到大约一万亿(10的12次方)个阳光光子。opus 检测到的深海喷口光线大约处于同一水平。换句话说,有足够的光线进行光合作用——一种完全非太阳能的光合作用。
自从范·多佛首次发现热液光以来,光合作用的想法就一直萦绕在她的脑海中。“1988年我们下船后,我和一位同事喝啤酒,我说,‘嘿,如果光线足以进行光合作用呢?’他只是说,‘多么愚蠢的想法。’但那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吸引力。如果真的有呢?”
如果细菌在喷口光下进行光合作用,它们可能只是最近漂流到喷口并适应了微弱光线的新来者,就像虾一样。另一方面,它们的血统可能要古老得多。喷口周围耐热、食硫的微生物是地球上最原始的生物之一,一些研究人员认为生命本身就起源于那些岩石口。对范·多佛来说,这些都只是她有时在会议演讲中为了智力乐趣而抛出的一些想法。然而,在1994年的一次演讲中,她的听众中有人认真对待了她。
伦敦大学的古生物学家尤安·尼斯贝特(Euan Nisbet)专注于地球存在最初20亿年间的生命。当他听到范·多佛的演讲时,他想知道她是否正在指出光合作用起源的一种解释。“光合作用是查尔斯·达尔文时代就存在的问题,”尼斯贝特说。“当中间步骤的优势难以理解时,你如何构建如此复杂的东西?”
光合作用发生在植物和某些细菌物种中,当叶绿素或其他色素分子捕获光线并将能量传递给相邻分子时,会激发其一个电子。然后,第三个分子抓住电子,并将其沿着一长串其他分子传递,每个分子都会吸收一点能量,并用这些能量来驱动将氢和二氧化碳转化为生物体燃料所需的众多反应之一。
尼斯贝特认为光合作用可能始于趋光性——生物体对光刺激做出反应的简单运动。这个想法又回到了一个基本事实:当你生活在热液喷口时,知道自己在哪里是很有益的。细菌没有像虾那样的眼睛来判断自己的位置,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它们是盲的。许多微生物都能感知光线。例如,一些沼泽居民会穿过沉积物,到达可见光较弱但红外线仍能穿透的层;这恰好是它们能找到最多食物的地方。
尼斯贝特和范·多佛共同勾勒出了光合作用起源的以下设想:想象早期地球上的一个热液喷口。最初,以喷口周围硫化物为食的微生物无法感知它们的位置,有时它们会漂流到寒冷的地方并冻结;有时它们会离烟囱口太近而烧焦。但有些细菌携带着偶然吸收喷口发出的光线的分子。渐渐地,这些细菌的后代发展出利用光线使自己处于安全位置(甚至弄清楚喷口上食物最多的地方)的能力,这些细菌因此得以繁荣。
这个故事接着说,数百万年后,一些具备趋光能力的细菌从海洋的黑暗深处漂浮到浅层温泉,在那里它们可以继续食用硫化物的老食谱。然而,现在它们不再生活在喷口微弱的光雨下,而是生活在来自太阳的巨大光流下。多亏了它们的喷口血统,它们已经能够捕获光子;它们现在所要做的就是对可见光变得敏感,然后找到一种方法来利用这些捕获的能量,通过进化出一套分子系统,将捕获的能量转化为燃料。现代光合作用由此诞生。
尼斯贝特说:“我们只是提出了一个起始步骤,但在许多情况下,起始步骤是最难想象的。它最初是一种热探测机制,生物体被带到浅水环境中,它们恰好拥有探测阳光的设备。现在它们拥有了一些可以从上面的阳光中免费获得食物的东西,然后那里就有一个全新的世界。”至于支持证据,他指出,最原始形式的细菌叶绿素在范·多佛在热液喷口测量的频率带上吸收最多的光。此外,当今的光合作用利用了某些元素——铁、锰和硫,举例来说——这些元素在热液喷口周围非常丰富。这不是证据,但它很巧妙。我们只是说事实与假设是一致的。”
今年春天,范·多佛开始在大西洋一处名为“地狱之洞”的喷口寻找光合作用的蛛丝马迹。“我们抓住了烟囱顶部,带着一块硫化物块装在盒子里回来了,”她说。回到她现在工作的阿拉斯加大学实验室,范·多佛开始溶解岩石。如果她足够幸运,她将能在其中找到色素,如果找到了,她会观察吸收模式。“任何叶绿素都会有非常典型的吸收模式,”她解释道。“如果找到了,我们就可以考虑进行分子工作。”下一步将是收集更多的岩石,并尝试提取细菌DNA片段。
说实话,范·多佛对她最新的搜寻并不抱太大希望。“我真的不指望能找到色素。感觉我要是能在海底找到光合作用,那可就太幸运了。但这会像深海里所有其他事情一样。我们不断地对新想法说不。我们认为深海是寒冷的、不变的、平坦的,但它并非处处寒冷,也并非一成不变,更不是平坦的。虾有眼睛?‘不,’我们说,‘虾不可能有眼睛!’但那里有光!所以我想我还是会带着我的天真继续前进,看看我能发现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