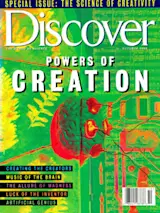五十五年前,在一个寒冷的早春清晨,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从她在英格兰苏塞克斯郡罗德梅尔的乡间别墅走到附近的乌斯河畔。她在那里放下拐杖,捡起一块大石头,把它塞进大衣口袋。然后她继续走着。石头起了作用;三个星期后,她的尸体才在对岸浮出水面。
她给丈夫伦纳德留了一张便条,放在壁炉架上。亲爱的,便条上写着,我确信我又疯了……这次我不会好起来了。我开始听到声音,无法集中注意力。……我想两个人不可能比这可怕的疾病来临之前更幸福了。……弗吉尼亚。
伍尔夫从1915年到自杀前四天所写的日记表明,她可怕的疾病可能是躁郁症,现在也称为双相情感障碍。这种病症被精神病学家归类为心境障碍,包括一系列情绪高峰和低谷,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高峰和低谷通常会变得更高、更低、更密集。一些患者经历严重的抑郁和中度的躁狂发作;另一些人则经历中度、短暂的抑郁,但会变得非常躁狂,以至于开始出现幻觉。
伍尔夫的抑郁发作是周期性的——有时是季节性的,有时与完成一本书有关。然而,在她的抑郁和完全躁狂发作之间,她设法保持了高度的生产力,并且常常活泼迷人。她的朋友奈杰尔·尼科尔森回忆道:“我每次离开她时都觉得喝了两杯上等的香槟。”“她是一个生活增添者。”
如果诊断准确,双相情感障碍让伍尔夫跻身于令人印象深刻的行列。这不仅意味着她有资格加入那些在流行创意形象中一直存在的疯狂艺术家行列。双相情感障碍将她提升到一个更精英的群体。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甚至一些神经科学家开始提出,双相情感障碍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创作艺术的能力。他们说,这种神秘而仍然是假设的联系,可能解释了更普遍的陈旧刻板印象的持续存在。
即使是这种联系最热情的倡导者也承认,大多数创造力与精神疾病无关,而且大多数精神病患者,无论是双相情感障碍还是其他疾病,都不比我们其他人更有创造力。然而,他们说,西方文化中如此多的巨匠的生活和工作经历都呈现出与双相情感障碍相似的模式,这一定不仅仅是巧合。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心理学家凯·雷德菲尔德·贾米森,她关于这个主题的许多书籍和文章使她成为艺术与疯狂联系的实际负责人,她编纂了一份这个不幸俱乐部的艺术家名单,读起来就像千年鸡尾酒会上的A级名单。其中包括诗人威廉·布莱克、约翰·济慈、珀西·比希·雪莱、埃德加·爱伦·坡、艾米丽·狄金森和安妮·塞克斯顿;小说家埃米尔·左拉、玛丽·雪莱、列夫·托尔斯泰、马克西姆·高尔基和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剧作家尤金·奥尼尔;视觉艺术家米开朗基罗、泰奥多尔·杰里科、爱德华·蒙克、保罗·高更、文森特·梵高、马克·罗斯科和乔治亚·奥基夫;以及从亨德尔到查理·帕克的音乐家。事实上,她几乎包括了经典中所有著名的饱受折磨的艺术家。
然而,这份名单的广泛性也引发了一些质疑。批评者指责,对已故艺术家进行追溯性精神病诊断,然后将这些诊断作为证据,这是一种客厅游戏,而非科学。旧金山加州大学的精神病医生弗兰克·约翰逊说:“关于灵感是神圣的,有着悠久的传统。”他直到两年前退休,一直参与一个为艺术家治疗心理和身体问题的项目。“医学文献中这种更现代、技术化的版本,将疯狂视为创作诗歌或从事哲学的条件。”
此外,正如约翰逊等批评家所指出的,双相情感障碍只是与创造力相关的众多有机疾病中的最新一种。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酗酒是首选的文学疾病;在本世纪早些时候,癫痫和梅毒性麻痹被与天才联系在一起。难道正如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观察到的那样,精神错乱仅仅是我们世俗的自我超越神话的当前载体吗?
自我超越神话的批评者指出,现在许多被追溯征召到双相情感障碍行列的艺术家——包括济慈、雪莱、坡、高尔基、史蒂文森和奥尼尔——的才华,曾经习惯性地被归因于神秘而常常致命的肺结核,而不是精神疾病。像躁郁症一样,肺结核也涉及交替的过度活跃和倦怠期;它也被认为能产生一种精神上的升华,使患者更容易获得非凡的洞察力。这种联系的信念如此普遍,以至于一位世纪之交的批评家将文学和艺术质量的明显下降归因于肺结核的逐渐消失。
还有另一个反对意见——不那么微妙,但也许比任何学术上的吹毛求疵都更发自内心——由亲身经历过双相情感障碍的人提出。他们指出,10%到15%患有严重形式疾病的人最终会自杀。即使在少数无法量化的创意人群中,艺术与疯狂之间存在联系,那又怎样呢?他们认为,强调这种联系美化了杀手,粉饰了它的破坏性,并使那些拼命努力保持平稳生活的普通人更加艰难。劳拉·M(Laura M.)患有双相情感障碍已有15年,曾两次尝试自杀,目前正在运营几个双相情感障碍支持小组。她说:“生病已经够糟糕了,我们为什么要应付人们期望我们有创造力?”同为患者和小组组员的凯瑟琳·T(Katherine T.)补充道,她通过药物治疗成功地担任陶艺家和画家,她说:“我讨厌人们欣赏创造力,却支持一种以自杀这种对自我如此犯罪的行为告终的疾病。”
在西方思想史上,关于创造性天才与疯狂之间联系的观念源远流长,尽管并非一帆风顺。柏拉图认为,没有缪斯疯狂的诗歌总会被受启发者的疯狂表现所超越。亚里士多德则想知道,为什么所有在哲学、诗歌或艺术方面杰出的人都是忧郁的?
古希腊的观点塑造了西方的流行态度,直到18世纪,平静短暂地取代了焦虑,成为灵感的源泉。散文家乔纳森·理查森在1715年写道:“一位画家应该拥有一种甜蜜而愉悦的心境,这样伟大而美好的思想才能在那里得到接纳。”查尔斯·兰姆在111年后评论道:“不可能想象一个疯狂的莎士比亚。”这是对天才与理智必要伙伴关系的赞颂。(像许多对这个主题感兴趣的人一样,兰姆的写作源于个人经验:他的妹妹兼文学合作者玛丽在一次躁狂发作中刺死了他们的母亲,查尔斯本人也曾在疯人院呆过一段时间。)但兰姆与他所处的时代格格不入。随着19世纪的诗人拜伦、雪莱和柯勒律治——兰姆的同代人——西方文化再次被狂野、受苦的艺术家形象所吸引,他们似乎在引导着某种超越自身的力量。
最近,诸如R. D. 莱恩在20世纪60年代的校园经典《经验政治学》等著作提出,精神分裂症患者创造了一些最真实的艺术,因为疯子比正常人更贴近他们的内心自我。回想起来,这个结论似乎是政治战胜理性的结果;当代精神分裂症研究人员更关注这种疾病的破坏性而非其创造性丰饶。
为什么艺术与疯狂之间的联系理念在流行想象中如此根深蒂固?一些临床医生将其归因于一种相当令人不快的人类特质:他们说,非凡的成就让我们其他人感到不安。哈佛精神病学家阿尔伯特·罗滕伯格说:“在这种文化中,我们对有创造力的人只有两种反应。要么崇拜他们,要么嫉妒他们。”
约翰逊补充说:“我们对运动员和艺术家都这样做。我们称他们的技能‘不可思议’,这是一种反向的成就病理化,而不是赞扬他们的毅力。”
在约翰逊看来,像波德莱尔那句高傲的“我感受到了疯狂翅膀的风”这样的观察令人欣慰;它给我们带来一丝颤栗,然后让我们放松下来,在沙发垫之间摸索遥控器。无需努力创作诗歌或任何其他东西;艺术是疯子的领域。
但可能有一个更简单的原因,让这个问题每一代人都会重新感到着迷:因为难以获得解决这个问题的数据。如果研究人员向过去的伟大艺术家寻求答案,僵局是不可避免的。双方都有自己的名单。一个开朗的简·奥斯汀能胜过一个忧郁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吗?一个务实的资产阶级安东尼·特罗洛普能超越一个嗜酒、抑郁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吗?割腕的马克·罗斯科,是不是比安详逝世的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更真实的艺术家?
研究在世艺术家也同样不容易。一些研究人员选择接触那些在社会上被定义为有创造力的人——例如,获奖者——并试图评估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但是这些艺术家可能不代表整个艺术界:许多前卫作家和画家从未进入经典。而且这种策略可能无法获得甚至这些主流天才的准确样本。受试者可能因为精神疾病的耻辱而拒绝参与。凯·贾米森承认这个问题时说:“抑郁症某种程度上是受人尊重的,但躁狂症则不然。如果你躁狂,你就真的疯了。”
然而,两项有效地重新唤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兴趣的研究,都采用了这种方法。1974年,南希·安德烈森在爱荷华大学攻读精神病学住院医师期间,开始尝试验证当时关于精神分裂症与创造力之间联系的观点。拥有英国文学博士学位的安德烈森,对爱荷华大学著名作家工作坊的30名教员进行了访谈,并将这些教员与非艺术专业的对照组受试者进行了匹配。她发现,80%的参与作家表示曾患有抑郁症或躁郁症,而对照组受试者的这一比例为30%。(其中两名作家最终自杀了。)她回忆说,这种双相情感障碍的联系“简直让我大吃一惊”。
但是当她的研究结果在1987年发表时,这种联系并没有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罗滕伯格反对她的对照组,他认为这组人与创意人群无法真正比较,并指出安德烈森本人进行了访谈和诊断,没有进行任何常规的交叉核对以确保客观性。罗滕伯格本人花了30年时间采访杰出的创意人士——其中包括诺贝尔奖和普利策奖得主——并确信创造力是由心理健康而非疾病促进的。然而,安德烈森对自己的信念像罗滕伯格一样坚定。她坚持认为:“双相情感障碍与创造力之间的联系是真实且极其牢固的。”
凯·雷德菲尔德·贾米森关于这个主题的第一项研究,一项1989年针对创意人群情绪障碍的研究,比安德烈森的研究获得了更多的公众关注。在牛津大学休假期间,贾米森接触了一大群杰出的英国人,并要求他们完成关于情绪波动和创造力的详尽问卷。她最终的样本只包括了文化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皇家学院成员、布克奖得主、《牛津二十世纪英语诗选》的撰稿人。
她发现的是大量的精神痛苦。在普通人群中,双相情感障碍的发生率约为1%,重度抑郁症影响人口的5%到15%。然而,在贾米森的样本中,38%的艺术家接受过情感障碍治疗(包括单纯性抑郁症和双相情感障碍),其中四分之三的治疗已超出谈话疗法,涉及锂盐、抗抑郁药、电击或全部三种。显然,即使对于这些最成功的艺术家来说,强烈的精神痛苦也与创造力如影随形。
贾米森承认,每个类别中的艺术家数量很少——例如,八位小说家和八位剧作家——但仍然认为结果具有说服力。她说:“当然,我们的研究存在方法论问题。”“但它们都指向了相同的关联。所以你必须问自己:是否存在一种趋势?这种趋势是否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你至少必须考虑这些研究可能是正确的可能性。”
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研究似乎证实了安德烈森和贾米森发现的关联。阿诺德·路德维格的著作《伟大的代价》副标题说明了一切:《解决创造力与疯狂之争》。十年来,路德维格和他的研究伙伴们筛选了1004位杰出男女的2200多份传记,以了解哪些因素结合起来才能产生那种令历史学家为之侧目并引起注意的高层次创造力。
通过使用二手资料,路德维希避免了贾米森和安德烈森受到批评的一些抽样问题。而且他对传记本身存在偏见的异议也给出了答案。他说:“总的来说,我认为传记作家——他们花数年时间了解他们的研究对象——会比那些提出标准化问题或进行问卷调查的临床医生有更好的视角,因为问卷调查本身就包含了理论或诊断假设。”“毕竟,你在临床访谈中得到的是自传,而那是所有记录中最不准确的。”
路德维希发现,作为一个群体,创意艺术家表现出的精神疾病水平远高于他们在更结构化职业中的创意同行。青少年时期,29%至34%的未来杰出艺术家表现出精神症状——从疑病症、情绪低落和内省发作到精神病性幻觉和自杀企图——相比之下,科学、体育和商业领域的未来成功者只有3%至9%。(确切的百分比取决于诊断标准的严格程度。)成年人之间的差异同样显著,诗人、音乐表演者和小说家的患病率在70%至77%之间;画家、作曲家和非虚构作家的患病率在59%至68%之间;而杰出的自然科学家、政治家、建筑师和商人仅为18%至29%。
路德维希在对这一发现的意义上与贾米森和安德烈森有所不同。安德烈森和贾米森认为双相情感障碍能增强艺术视野,而路德维希的解释则更为平实。他认为,精神疾病的创意人士,几乎是默认地,投身于艺术而非商业或科学。
在路德维希看来,原因是不言而喻的。他说:“在科学界,有利的特质包括理性、毅力和冷静。你需要撰写研究计划,进行实验,与人相处融洽,按时上班。”他认为,双相情感障碍可能出现的狂热和瘫痪性抑郁交替发作,对科学成就来说是致命的,但艺术家可能会从中汲取灵感。
而且,出于文化原因,一位有抱负的诗人几乎没有动力去克制夸张的行为;事实上,一定程度的戏剧性是必须的。路德维希说:“如果一位政治家酗酒或抑郁,他或她会试图隐藏它。例如,看看当人们发现托马斯·伊格尔顿因抑郁症住院时发生的事情。”(伊格尔顿在1972年作为总统候选人乔治·麦戈文的竞选搭档呆了两周,之后被从选票中剔除。)“但是当你听说一位诗人酗酒或患有精神疾病时,你会想,‘那又有什么新鲜的呢?’”
然而,路德维希并不认同那种只有情绪对了才能创作的灵感艺术家刻板印象。他说:“任何取得创造性伟大成就的人都是专心致志的。”“这些人坚持不懈;他们几乎是偏执狂。想想毕加索,或者塞尚。在他看来,这种奉献精神导致了伟大的真正代价,那不是疯狂,而是看似不可避免的家庭破裂。工作对伟大的艺术家来说至关重要,而且会带来很多家庭后果,”他说,“你不能飞得那么接近太阳而不被灼伤。”
任何关于艺术与精神疾病协同作用理论的关键症结在于解释其运作机制。一些临床医生认为,各种精神和身体问题——从抑郁症到严重的儿童疾病——都会赋予局外人地位,而感觉自己处于主流之外可以激励人们成为艺术家。哥伦比亚大学的精神病医生鲍勃·克利兹曼说:“不一定非得是疯狂。”“你可能会因为是同性恋、女性、南方人或黑人而感觉自己是局外人。任何让你觉得你所看到的世界与他人看到的世界不同,都可以激励你想要讲述自己的故事。”
其他解释,虽然通常引人入胜且直观,却可能令人恼火地含糊不清。即使路德维希直截了当的社会学解释,当他试图确定创造力与疯狂的交集时,也变得柔和起来。他引用了心理不安的概念,他称之为一种不安、不适、表达自我的需求。他认为,情绪健康的创意人士拥有它,并将它附着在一个问题上;当问题解决后,它会激励他们去寻找新的问题来解决。他说,精神病患者也有这种不安,但他们的不安更普遍、更自由浮动。用他的话说,他们“更难把心理的盖子重新盖上”。
但最有远见的解释则留给了双相情感障碍艺术家的创作过程。安德烈森说:“我认为双相情感障碍患者乐于接受矛盾,他们敢于冒险,他们蔑视秩序。”“这些特质使他们比我们其他人更容易受到伤害,也更具原创性。”
而当凯·贾米森谈到双相情感障碍的影响时,她听起来简直有些神秘。贾米森在1995年出版的回忆录《不安的思绪》中透露,她从青春期起就患有躁郁症,她描述了一种超乎寻常的对周围环境的感知,一种比人类更像动物的环境敏感性。她说,双相情感障碍赋予情绪极大的范围和强度,然后可以转化为艺术。你无法预测你明天会变成什么样。我认为双相情感障碍的情绪反映了自然世界,它是如此季节性和流动性。这是一种危险的、两栖式的存在。
除了让一位诗人躺在脑部扫描仪中并指示她写一首十四行诗之外,很难想象如何以文化中立的方式评估创造力。通过功能性神经影像技术,研究人员实际上正在缓慢地开始了解情绪障碍患者大脑中发生的事情,但他们所学到的主要集中在抑郁症谱系的一端,这纯粹是出于实用原因:躁狂症涉及身体和精神上的不安。一个处于躁狂发作中的人无法长时间保持静止以便进行脑部扫描。然而,研究大脑语言的神经科学家们注意到了一种模式,这可能有助于解释双相情感障碍创造力中至少一个元素:语言流畅性。
德国精神病学家埃米尔·克雷佩林首次描述双相情感障碍时曾指出,他的患者喜欢押韵和双关语,这一观察已得到其他治疗师和研究人员的证实。事实上,轻度躁狂的官方诊断标准之一就是语速过快,可能包括笑话、双关语、文字游戏和无关内容。
认知神经科学家迈克尔·波斯纳及其俄勒冈大学的同事最近将大量电极连接到志愿者的头皮上,并在他们执行两组词语联想任务时测量他们大脑中的电活动。在第一次测试中,受试者被要求仅仅阅读一份名词列表,例如“锤子”和“扫帚”,并为每个名词想出一个平实的用途:例如“敲打”对应“锤子”,“扫地”对应“扫帚”。
这些直接的词语生成任务激活了左半球的额部和侧部。这并不是什么新闻;神经科学家们长期以来都明白这些区域与语言有关。但是当受试者被要求为每个名词想出一个不那么寻常的联想时——比如“女巫”与“扫帚”,“投掷”与“锤子”——情况发生了变化。电活动来自右顶叶半球的一个区域——这与左半球侧面区域的镜像对称。
一些语言技能存在于右脑半球的线索已经浮现:右脑半球中风会削弱对词语的敏感度,使这类中风患者变得非常字面化,无法理解隐喻或双关语。尽管早期关于躁狂症是右脑半球现象而抑郁症是左脑半球现象的假设已被抛弃,认为过于简单化,但右脑半球显然与某些类型的躁狂症有关。例如,右脑半球的某些癫痫发作会诱发类似躁狂的症状。
那么,至少有可能处于躁狂期的人,由于右脑半球功能障碍,可能更容易接触到大脑中与文字游戏相关的区域吗?波斯纳说:“这可能有点跳跃。”“而且它没有解释躁狂症如何影响被认为涉及左脑半球的活动,例如音乐。”
这类猜测未能说服那些认为创造力是心理健康产物的人。罗滕伯格继续坚持认为,创造过程的本质是能够同时在头脑中容纳几种对立的观念,这项任务需要强大的心理健康。他说,艺术与疯狂之间只有一线之隔的说法听起来可能不错,但其心理过程却截然不同。
罗滕伯格的最终反对意见是哲学上的。他认为,将创造力归因于精神疾病是最低级的审美还原论。他说,悲剧性的世界观就是那样,它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称之为抑郁症的症状就是将其琐碎化,就是在说,“我不需要认真对待它。”他还怀疑将艺术与疯狂联系起来对精神病患者具有破坏性。他说,如果人们认为精神疾病在某种程度上让他们变得有创造力,这会让他们没有理由努力变得更好。
然而,倾听那些与双相情感障碍抗争的人的痛苦,这最后一种可能性似乎微乎其微。支持小组成员凯瑟琳·T用她那因药物而沙哑的低沉声音说:“有时我想上帝把创造力的天赋作为安慰奖赐予我,但我仍在受苦。我不知道这种病从何而来,但我真希望它能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