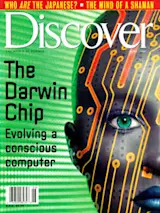我们正从阿尔伯克基向南行驶,执行一项仁慈的任务,而且我们迷路了。这不是好事,因为杰瑞·德拉古和我都带着三个活的定时炸弹在他颠簸的皮卡车的后斗里。如果它们爆炸了,就会毁掉一个本该完美的新墨西哥州的一天。至少,对我来说会毁掉这一天。德拉古,他在新墨西哥大学担任博士后研究员,在那里他负责生物学教授泰瑞·耶茨的遗传学实验室,他对此毫不在乎。
德拉古是一个臭鼬学家,粗略地说,就是个臭鼬专家。他对臭鼬科(Mephitidae)着迷。事实上,他很喜爱这些小臭家伙。他研究它们的谱系。他养了四只作为宠物。
当德拉古需要臭鼬来研究时,他会深入野外,发现一只,追上它,然后把它抓起来。字面意思。抓尾巴(不,这不会伤害它们)。动物会喷射吗?当然会。德拉古在乎吗?不在乎。这会打击动物吗?也许它觉得数百万年来辛苦进化的地狱般的腺体都白费了?人们可能会这么想。
德拉古被喷的次数比,比如说,某个总统被抓到偷吃饼干的次数还要多。不过,早些时候,我问他是否有特别难闻的记忆。他沉思了片刻,然后回忆起在德克萨斯州的一次经历,那时他和他的研究生导师以及一些潜在的研究生在一起。他们在一辆卡车里,发现了一只臭鼬,并计划悄悄地接近它。
我想给自己长点脸,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于是我跳下车开始追它。它开始跑,也开始喷射。所以我追了上去,但很快我就累了,臭鼬也开始跑远。于是我扑倒了它,发现自己正盯着它的屁股。
不用说,臭鼬的屁股变成了自由射击区。我吸进了它的气味,进了耳朵,糊了眼镜,进了眼睛,钻进鼻子,进了嘴巴……
进嘴里?!我忍不住惊呼。
到处都是,他说,边笑边说。我不得不承认,这并不愉快。它刺痛。我好几分钟看不见东西,嘴巴麻了好久。
考虑到他对动物那刺鼻气味的似乎无动于衷,我打赌你一定以为德拉古吸入的不是臭鼬的气味,或者他穿着那种头盔式的危险品防护服去追捕这些动物。实际上都不是。真是巧合,德拉古的鼻子根本不工作。他闻不到气味。(虽然他一直有鼻腔问题,但他表示直到开始研究臭鼬时,他才意识到自己感官上的缺陷有多严重。)当然,缺点是德拉古无法享受品尝美酒的芬芳,也无法闻到家常菜的浓郁香味。不过,好处是,他不会被站在下风处喷射的臭鼬所带来的嗅觉冲击所击垮,这对于嗅觉正常的人来说是难以忍受的。
哦,当然,德拉古也偶尔会遇到尴尬的时刻,比如他忘了自己被喷过,然后去当地的小超市买瓶汽水,结果把店员和所有人都熏跑了。还有一次,他说,带着一丝笑容,我在一个会议上,注意到人们在嗅空气,互相问有没有闻到臭鼬味。我不得不举手说:“各位抱歉,那是我。”但那是我年轻的时候;现在我的妻子照顾我得更好。
是的,德拉古确实结婚了,娶了一位名叫格温的非常好的女士,她是一名兽医技师,能闻到气味,而且看起来头脑也很清醒。所以,当我们在一天晚些时候见面时,我忍不住问她如何忍受德拉古工作带来的危险。真爱,她回答。还有大量的漂白剂。估计经过大量而疯狂的实验,她发现稀释的漂白剂是去除气味最有效的物质。
在皮卡车里,德拉古愉快地谈论着他的工作,并分享了一些关于捕捉臭鼬的趣事(它们总是喜欢转圈,寻找藏身之处)。而我,则有点紧张。我闻到臭鼬气味最近的一次是在一辆飞驰在高速公路上的汽车里,而它的气味通常会引起车内乘客齐声惊呼“我的天哪”。
在离开25号州际公路后,我们行驶在更慢、更宁静的116号公路(或者304号?我不确定)。我们绝对迷路了。德拉古说,我担心臭鼬。他担心它们的体温过低(条纹臭鼬不冬眠,虽然它们在48个邻近州都很常见,但出乎意料的是,它们在严寒中表现并不好)。他一点也不担心,而我却很担心它们会变得,字面意义上的,“被惹毛”。
因此,我听着德拉古的讲述,一边做笔记,一边揣摩着膝上的皱巴巴的兰德·麦克纳利地图(我们怎么可能错过占地22万英亩的塞维列塔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呢?),同时一只鼻孔朝向后座的三只臭鼬。目前的目标,考虑到德拉古对三只臭鼬的福祉的担忧,以及我对自己的担忧,是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将这三个小家伙放归野外。由于我们现在的乘客都是成年臭鼬,一旦找到没有房屋的空地,就可以立即放生,这样它们就不会回到某人的温暖地窖里。
德拉古对“佩佩·勒皮尤”式(Pepe Le Pew,一个喜欢追逐臭鼬的卡通角色)的喜爱源于他对小型动物的兴趣,尤其是他在电视上的各种自然节目中看到的 sea otters(海獭)。他说,我小时候很小,所以我想我认同那些小动物。后来,在德克萨斯农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一位导师鼓励德拉古研究猪鼻臭鼬(hog-nosed skunks)。他从此着迷,至今已研究臭鼬约12年了。在1997年5月发表于《哺乳动物学杂志》(Journal of Mammalogy)的一篇论文中,德拉古通过DNA分析证明,臭鼬亚科(Mephitidae)应该提升到科的地位。Mephitidae,当然是拉丁语,它的词根意义非常贴切:有毒的气味。
德拉古还有一种慈善情怀。他从研究生时期就开始进行臭鼬搜救。将报告臭鼬问题的人引导到一个名为“野生动物救援”(Wildlife Rescue)的机构,然后他们就会得到德拉古的电话号码。他说,接下来人们就会给我送来小臭鼬;他们担心狂犬病。他说,人们普遍认为臭鼬天生就患有狂犬病,这是一个常见的误解。德拉古不认为臭鼬比其他野生动物更危险。他说,我被臭鼬咬过很多次,从来没有得过狂犬病,他轻描淡写地说。当然,那可能是因为可怜的狂犬病毒在穿透他的皮肤之前就被毒死了。
臭鼬在二月下旬到春季繁殖,孕期约60天;因此,德拉古最忙碌的搜救任务是在夏季。那时你会发现母臭鼬和幼崽在人们家底下筑巢。所以在这二月下旬的一天,德拉古还没有接到求助电话。一位住在贝伦小镇(Belen)的女士,距阿尔伯克基以南约30英里,需要他的帮助。至少有三只臭鼬侵入了她家房下的爬行空间,她被 fumes(烟雾/气味)呛得喘不过气来。她说,‘拜托,我受不了了,’德拉古说。前一天晚上,在我到来之前,德拉古开车去了那里,在动物们挖的洞旁边放了三个陷阱。当我第二天早上与德拉古会合时,他告诉我,那位女士打来电话报告说,确实有三只动物被成功捕获。
当我们前往贝伦时,德拉古解释说,他用通常的诱饵——狗粮和香蕉——来诱捕。顺便说一句,金枪鱼不行,因为它会吸引猫,但是……香蕉?臭鼬在热带有亲戚吗,还是怎么回事?实际上,我得知有一次我没有诱饵了。我当时在吃香蕉,于是我扔了一块进去。臭鼬似乎很喜欢。
当我们到达贝伦的家时,那位女士在后门迎接我们,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纸巾。我不知道她眼中流下的泪水是感激还是痛苦。我闻到了从她厨房飘来的熟悉的臭味。德拉古安慰了她,然后拿起他的工具——垃圾袋。他告诉我,当我们走向房子的前面时,‘如果我能盖住笼子,它们通常就会平静下来。’或者如果我够快,我可以拿个袋子挡住它们喷射的气味。
当我们绕过拐角时,德拉古告诉我,这些很可能是三只雌性臭鼬,它们为了冬天一起筑巢以节省体温。有时一只雄性和几只雌性会一起筑巢——对于幸运的雄性来说是繁殖的幸福。德拉古说,臭鼬通常不会在它们的巢穴喷射,所以气味很可能是来自它们的粪便。因为臭鼬不仅仅有普通的腺体。不,它们有肛门腺,这意味着粪便在通过时会沾染上气味。反过来,这意味着房子里的气味,即使没有臭鼬,也会一直存在,直到粪便分解。但他告诉我,当看到三个小笼子时,“我没有心告诉她这一点。”
果然,每个笼子里都塞满了看起来像巨大的毛球的东西。仔细一看,我看到了它们狭窄的面孔和熟悉的白色条纹。我僵住了,强忍着后退的冲动。去吧,男孩,我想,看着德拉古走近笼子。
他开始轻声地和三只动物说话。一只看起来在发抖。我焦急地问,这是它准备喷射的信号吗?不,它冷,他轻声说,然后单膝跪下。当他轻轻而缓慢地把袋子移向离他最近的笼子时,另一只臭鼬突然转过身,抬起了尾巴。他说,这是它准备喷射的信号。哦,太棒了。臭鼬的喷射可以传播十英尺多。而我晚上还有飞机要赶。如果它开始跺脚,这是它即将按下发射按钮的警告信号,我就要跑了。
令人惊讶的是,德拉古能够轻轻地提起盖着垃圾袋的笼子,并安然无恙地把它抱到他的皮卡车上。我远远地跟着。他又用同样的方法处理了另外两只,包括那只抬着尾巴的。一旦三只都被放进卡车后斗,德拉古拉过一块他带来的木托盘,嘈杂地把它放在笼子上面,以防它们滑动。我小心翼翼地爬进驾驶室,轻轻关上门,而德拉古则站在外面,接受一位泪流满面的房主的连声感谢。然后他跳进卡车,砰地一声关上门,发动机发出轰鸣声。他发动了吵闹的V8引擎,倒出车道,驶上了颠簸的砂石路。我们又上路了。
当我四处寻找一家可以买到漂白剂的商店时,我提到了我对这些动物仍然如此平静感到惊讶。他说,它们可能因为整夜待在笼子里而有点晕头转向和寒冷,但臭鼬通常只有在感到生命危险时才会喷射。我若有所思地说,这大概也包括被一位热情的、抓住它们尾巴的研究员追捕的时候吧。他笑了。哦,是的,但通常臭鼬不会把喷射当作攻击武器,他说。即使两只雄性在打架,一只喷另一只也很少见。他说,臭鼬似乎也受气味困扰。它们会极力避免沾到自己的毛上。这就是它们喷射时尾巴举那么高的一大原因。
这说得通。主要的臭鼬臭味成分是一类叫做硫醇(mercaptans,或thiols)的有机化合物。硫醇含有硫,根据化合物的不同,它们是洋葱和大蒜的气味以及臭鸡蛋味的罪魁祸首。
现在,我们所在的公路已经缩窄成了一条小路。我们过了一座小桥——德拉古说,也许下面是个放生牠们的好地方,他指着桥下的一条沟渠。五分钟后,我们到了桥下,三个笼子都放在地上。德拉古每次都抱着笼子穿过带刺铁丝网,毫发无损地从卡车上搬下来。(我强忍住帮忙的冲动。)德拉古说,希望它们不要跑到公路上去,他放出了第一只臭鼬。它逃走了,紧随其后的是德拉古,他盯着它的屁股。他注意到,那是只母臭鼬,它从桥下经过,向左转,开始爬向公路。德拉古耸耸肩,放出了第二只。它跟在第一只后面,德拉古也跟在后面。他说,那是只母臭鼬,第二只也开始爬坡。
第三只臭鼬背对着笼子的开口,似乎有点不愿后退。德拉古轻轻晃了晃笼子,温和地赶它出来。他摇晃得更用力了些,我后退了一步。最后,第三只臭鼬退了出来,转过身,跑到了桥下,德拉古跟在后面。它消失在桥木的缝隙里。他说,我没看见那只,但我敢打赌它是一只母臭鼬。
我们爬上公路,但三只臭鼬都不见了。德拉古满意地点点头。它们会没事的。它们可能会躲起来直到晚上,然后才出来探索。它们附近有水(格兰德河在西边半英里)。到了傍晚,我们来到了德拉古的家,它坐落在阿尔伯克基郊外的山区。那里弥漫着淡淡的臭鼬气味。德拉古寻找他的臭鼬宠物,它们的腺体完好无损。他告诉我,他和格温对待它们就像对待任何宠物一样。我们和它们玩。我会和它们玩闹——在地上滚来滚去——但它们从来不喷我。它们也和我们一起睡觉,他说,这让我很好奇,如果半夜翻身压到它们会怎么样。
果然,德拉古发现一只臭鼬蜷缩成一团毛球,睡在他的被子里。我说,那是迪亚布罗(Diablo)还是奥利奥(Oreo),我忘了。近距离看,臭鼬和它们长得一样可爱,跟浣熊和兔子一样。德拉古把它举到手上,让我紧张地盯着它的屁股。就像盯着一杆上膛的步枪。一股刺鼻的气味升上来,让我想起——算了,不管了。他邀请我感受一下腺体的大小。腺体又大又软。德拉古告诉我,臭鼬的肛门两侧各有两个乳头,可以调节和控制喷射。他说,我曾被喷过细雾,我称之为它们的‘霰弹枪式’;我也被喷过,我称之为它们的‘0.357马格南式’。
看着德拉古找出另外两只睡在衣柜里的臭鼬,我想,他把职业生涯献给了这些生物,真是太棒了。我也觉得拥有一只像臭鼬这样不寻常的宠物很酷——太酷了,以至于我想去佐治亚州奥古斯塔参加下一届全国臭鼬展(National Skunk Show),和来自全国各地的臭鼬爱好者交流。然而,直到我了解到,家养臭鼬的主人会通过一次100美元的手术切除宠物的腺体。真是胆小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