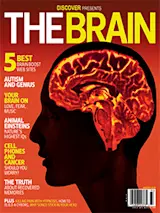一,请你做一件事:抬头。二,请你做两件事:慢慢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三,请你做三件事:呼气,放松眼睛,让身体漂浮。想象你漂浮在浴缸、湖泊、热水浴缸里,或者只是漂浮在太空中。每一次呼吸都变得更深、更轻松。
这位病人80岁了。她躺在哈佛大学贝斯以色列女执事医疗中心手术室明亮的灯光下,放射科医生埃尔维拉·朗正要通过她的动脉插入一根导管。这根细小的管子将进入她的一侧肾脏,阻断该器官的血液供应。外科医生计划第二天切除这颗肾脏。对肾脏进行栓塞将有助于使手术简单、安全、整洁。但这位女士正在发烧,她的肾脏可能受到感染。由于她当天早些时候吃过东西,不能使用镇静剂。原本应该是一项常规手术,却变成了一场磨难。
“这是你安全而愉快的归属地,”朗的一位同事从一张塑封卡片上念道,“从某种意义上说,你可以用它来捉弄医生。你的身体必须在这里,但你不需要。”
朗是越来越多的医院医生之一,他们除了麻醉外还使用催眠。她与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教授大卫·施皮格尔合作,对手术室中的催眠进行了广泛研究,通常取得了显著成果。通过添加催眠,她可以使手术更短、疼痛更少、对药物的依赖性更低。手术中最困难的部分是让其他医生接受它。
多年来,一系列严格控制的研究证明,催眠可以减轻疼痛,控制血压,甚至可以使疣消失。但由于很少有研究试图找出其作用机制,大多数科学家对其力量持怀疑态度。批评者认为催眠与安慰剂效应无异。它们都利用暗示的力量让思想控制身体;两者都不能替代药物。
这种怀疑促使施皮格尔和其他研究人员深入研究催眠期间大脑中发生的事情。他们发现,恍惚打开了一扇通往想象本质的窗户。通过它,我们开始瞥见大脑如何区分白日梦和现实。
施皮格尔是第二代催眠师。他的父亲赫伯特·施皮格尔是一位精神病医生,他第一次使用催眠是在二战期间作为一名战地外科医生。1943年,他在突尼斯马特尔被德国坦克迫击炮击中时,甚至对自己使用了这项技术。一块钢壳碎片突出他的脚踝,但他设法屏蔽了疼痛。
催眠受试者能够比未催眠的受试者多忍受一分钟的剧烈疼痛。
回家后不久,老施皮格尔被聘为纽约布伦特伍德梅森将军医院军事精神病学学院的战斗精神病学教授。在那里,他利用催眠治疗了数百名返乡退伍军人,并且越来越相信它的有效性。与此同时,第一批关于催眠的临床研究开始出现。1961年,精神病医生拉尔夫·奥古斯特发表了一项对850名在催眠下分娩的妇女的研究。只有4%(34名妇女)需要止痛药。其他研究发现,催眠受试者能够比未催眠的受试者多忍受一分钟的剧烈疼痛,比服用安慰剂止痛药的受试者多忍受30秒。
到了20世纪60年代,赫伯特·施皮格尔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临床催眠,他的儿子也在他的学生之列。大卫·施皮格尔后来进入哈佛医学院学习,并像他父亲一样专攻精神病学和临床催眠。1978年,这对施皮格尔父子合著了后来成为该领域标准教科书的《恍惚与治疗:催眠的临床应用》。
现年62岁的大卫·施皮格尔身材高大,略显凌乱,有着他父亲那样的椭圆形脸。他以一位曾面对众多不信者的人的坚忍耐心倾听。“催眠从一开始就备受争议,”他说。“问题是,它就是不会消失。这种现象有太多有趣之处。”施皮格尔说,在该领域的研究人员中,存在两种思想流派,并且它们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一种流派认为催眠从根本上改变了受试者的心智状态;另一种则认为催眠没有什么激进之处,所有通常与催眠相关的奇怪经历和异常行为都可以在没有实际处于催眠恍惚状态的人身上观察到。施皮格尔属于第一种流派,多年来,他一直与对立面的两位科学家进行持续辩论:英国赫尔大学的心理学家欧文·柯希和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斯蒂芬·科斯林。
科希并不否认催眠可能有效。在他仍在临床执业时,他经常使用这项技术。“通过催眠,你确实能让人进入不同的状态,”他说,“但你不需要恍惚就能做到。”他喜欢用催眠行业的一个标志物来阐述这一点:一根链子上挂着的怀表。他建议,把你的手肘放在桌子上,用拇指和食指夹住链子,让重物自由摆动。现在,尽可能保持手稳定,想象摆锤平行于你的胸部来回摆动。“只需专注于它朝那个方向,左右摆动,”他说,“忽略其他一切,想象它以自己的节奏左右摆动。”一旦它这样摆动(它不可避免地会这样),想象它以另一种方式摆动——比如顺时针方向,或者向你和远离你——只是为了向自己证明这并非巧合。再次,重物会服从你的思想。这个小把戏对即使是最怀疑和最无法被催眠的人也有效。你不需要进入恍惚状态,你的潜意识和身体——在这种情况下,你手指上的微小肌肉——就能对暗示做出反应。“我本可以催眠你,做同样的事情,但这不会是催眠的结果,”科希说,“那将是你专注于将其朝特定方向移动的结果。”
施皮格尔不同意。他承认单独的暗示是一个强大的工具,但他认为催眠会放大其效果。他最著名的研究之一发现,当受试者被催眠并接受暗示时,他们的脑电波模式会发生变化。在施皮格尔的另一项研究中,被催眠的人被告知他们的前臂麻木,然后对他们的手腕施加轻微的电击。他们没有退缩,也没有以任何方式回应,他们的脑电波类似于那些经历了微弱得多的电击的人。
对柯希来说,这仍然不足以证明恍惚的力量,但斯蒂芬·科斯林开始思考。科斯林是一位极其礼貌的男士,留着灰白胡子,眉毛总是高高挑起。他说,催眠文献充斥着受试者模仿他们认为是催眠行为的例子。这种“需求效应”正是安慰剂如此有效的原因。至于脑电波研究,实验室中的其他事件——例如与研究人员的互动——也可能导致受试者心智状态的改变。“这只是在演戏吗?”科斯林第一次看到施皮格尔的数据时疑惑道,“还是大脑中真的发生了一些事情?”
为了查明这一点,施皮格尔和科斯林合作进行了一项研究,重点关注大脑中一个被充分理解的区域:梭状回通路。该通路是枕叶的一部分,已被发现处理颜色感知。神经科学家通过让受试者躺在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 (PET) 扫描仪中,测量大脑血流量,同时让他们观看带有彩色矩形的卡片,从而锁定了该通路。施皮格尔和科斯林想知道受试者在催眠状态下通过想象颜色是否能激活相同的通路。
第一步是找到合适的研究对象。人群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在催眠圈子里被称为“高敏感者”——能够进入深度恍惚状态,就像只有少数人完全无法被催眠一样。我们其他人则介于两者之间。施皮格尔和科斯林从125名潜在受试者中选择了8人;随后科斯林的团队在波士顿马萨诸塞州综合医院进行了实验。与之前的研究一样,受试者被置于PET扫描仪中,并显示带有彩色矩形的幻灯片,同时绘制出他们的大脑活动图。然后他们被显示黑白幻灯片,并被告知想象其具有颜色。这两项任务在催眠状态下重复进行。
当他们仅仅想象颜色时,只有右半球的梭状回通路被激活。但是当他们在催眠状态下被要求想象颜色时,这些受试者的大脑反应方式与他们实际看到颜色时相同:左右梭状回通路都被激活。在催眠状态下,想象似乎带有了幻觉的特质。
当高度易受催眠的受试者被要求想象颜色时,他们的大脑反应与他们实际看到颜色时完全相同。
科斯林目前没有参与正在进行的催眠研究,但这一发现最近得到了柯希的两位同事朱莉安娜·马佐尼和安娜-莱娜·维内里(Giuliana Mazzoni and Annalena Venneri)的复制和扩展,他们在2008年夏天举行的美国心理学会会议上报告了初步结果。研究人员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成像大脑活动,发现当高度易受催眠的受试者被要求想象颜色时,他们的大脑反应与实际看到颜色时完全相同。所谓的“低敏感者”——不容易被催眠的人——没有表现出相同的大脑活动。“我们仍然不能声称这是一种意识改变状态,”马佐尼说,“但我倾向于认为高度易受催眠的人具有独特的技能。”
“我现在绝对相信催眠可以增强心理意象的作用,”科斯林说。但柯希仍然持怀疑态度。柯希说,色彩实验表明人们“确实体验到了催眠暗示的效果”,但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进入了恍惚状态。
对科斯林来说,这项工作展示了大脑如何区分想象和感知。大脑的右侧处理事物的具体例子,而左侧处理更普遍的概念和类别。例如,左侧知道斯波特是一条狗,而右侧知道这条狗是斯波特。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想象一种特定的颜色时,大脑的右侧会亮起来,而左侧却保持“冷淡”:白日梦的细节可能看起来真实,但它们不适用于更大的现实。
“想象和感知领域并非完全截然不同,”施皮格尔说,“这可以追溯到康德等哲学家。我们所认为的现实是我们对感知输入的处理。”我们从与完整图景相去甚远的小线索中对什么是真实的做出假设。如果你期望在餐厅遇到一位朋友,而一位陌生人穿着同样的夹克和发型进来,你可能会叫出你朋友的名字,但你一看到脸,你的错误就会很明显。“我们不是被动地接受感知,而是让想象和感知进行竞争,”施皮格尔说,“想象可以改变感知——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总是这样。但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催眠状态下,这种区别就会消失。
科斯林认为催眠能让身体挖掘潜在的储备。他将其效果比作打破体育世界纪录:它改变了我们对可能性的认知。“多年来,没有人能在四分钟内跑完一英里,”他说,“这就像音障——人们认为四肢会开始脱落。”然而,在英国跑者罗杰·班尼斯特于1954年最终打破纪录仅仅六周后,另一位跑者再次打破了它。“现在,40岁的人也能做到,”科斯林说。催眠可能也有同样的效果。“它改变了我所谓的假设常态。它可以在四分钟一英里中扮演罗杰·班尼斯特的角色。”
施皮格尔首先是一位临床医生。他认为,催眠的“为什么”不如医生认识到其力量并开始使用它重要。为此,他和朗在手术室对该技术进行了测试。1995年,他们招募了241名即将接受血管或肾脏手术的患者,并将他们分为三组。一组接受标准护理;另一组接受标准护理并配备“富有同情心的护理提供者”;第三组接受标准护理、富有同情心的护理提供者和催眠。手术期间,患者头部被置于不透明、隔音的屏障后,以便外科医生无法分辨他们正在接受哪种护理。每15分钟,患者被要求评估他们的焦虑和疼痛水平。他们还连接到静脉输液,并按需给予止痛药物。
这项研究的结果发表在《柳叶刀》杂志上。施皮格尔和朗发现,平均而言,催眠受试者使用的药物更少,疼痛更轻,焦虑感也远低于其他两组。未催眠的患者,无论接受多少药物,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感到更多疼痛;而被催眠的患者在整个手术过程中保持同样的舒适度。催眠患者的手术平均比其他患者短17分钟,标准放射学手术的费用从638美元降至300美元。
朗此后通过一项对200名接受乳腺癌活检或乳腺肿瘤切除术的患者进行的试验,进一步证实了这些发现。患者被分为两组:一组接受常规麻醉加“非指导性同理心倾听”,另一组接受15分钟的术前催眠,该催眠提供愉悦的视觉意象,提供放松和平静的技巧,并给出以症状为重点的建议以减轻疼痛和恶心。接受催眠的患者使用的镇静剂和麻醉剂显著减少;他们还报告说疼痛、恶心、疲劳和情绪困扰更少。研究人员估计,催眠为每位患者节省了772.71美元,这主要归因于手术室时间的缩短(平均10.6分钟)。在另一项针对接受大芯针乳腺活检的女性(这是一种既痛苦又会引起焦虑的检查,因为通常是癌症筛查)的近期研究中,催眠减轻了疼痛和焦虑。
朗并没有测试她的病人是否高度易受催眠。她说,病人对某个手术越焦虑,他们就越有可能从催眠中受益。“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抱有最坏情况设想的人,往往具有很好的想象潜力。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一个非常生动的头脑。”研究表明,恐惧症患者往往高度易受催眠。朗认为人们每天都会进出恍惚状态——每个人都会有完全投入的时刻,以至于听不到别人对他们说了什么。“这种屏蔽外界的能力在全世界都很普遍,尤其是在已婚夫妇中,”她说。学会控制这种投入提供了一种学习控制疼痛的方法。
朗那天在哈佛进行的那次肾脏手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位80岁的病人一度从恍惚中醒来——“这些关于海滩的胡言乱语是什么?”她问道——但医生很快又用一个简单的催眠暗示让她再次进入恍惚:“你的眼睛不会闭上,直到你的内心允许你。”
2007年2月,波士顿一家繁忙的私人诊所——北岸磁共振成像中心,请朗和她的同事们对他们的MRI团队进行催眠培训。患者在MRI机器的管状空间中经常感到幽闭恐惧,他们被告知不能动,而扫描可能持续30到60分钟。惊慌失措的患者可能会带来昂贵的代价:如果客户在管中移动或从检查台上摔下导致图像丢失而需要重复扫描,费用可能高达3000美元。朗对成像中心的15名员工进行了催眠培训,自那时起,每月大约减少10名患者在检查过程中从检查台上跳下来。
催眠背后的现象可能仍不清楚,但只要它能帮助患者忍受痛苦或引起焦虑的医疗过程,患者就不需要知道其原因。“我认为这应该基于数据,而不是信念,”施皮格尔说,“但最终,它为什么有效并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