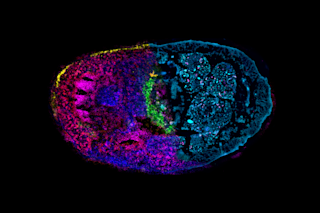最普通的变形虫都能完成分子操纵的壮举,这令任何人类工程师都羡慕不已。变形虫能够快速且精确地组装复杂的生物结构,是纳米技术将惰性物质转化为奇妙形式的活生生证明。变形虫——以及你体内的细胞——之所以精通这些技能,是因为它们有数十亿年的时间来完善它们的分子工具包。加州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和生物工程学教授埃里克·温弗里决心利用所有这些经过进化磨练的机制。他正在探索利用细胞生物学方法来创造一种新型分子尺度工程的方法。尽管仍处于早期阶段,但这项研究有望带来治疗疾病或通过“培育”而非“组装”部件来制造复杂机器的革命性方法。
温弗里于2000年获得了麦克阿瑟“天才奖”,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DNA这种储存遗传信息的分子上。我们的细胞利用这些信息来构建构成我们身体结构并完成几乎所有生命活动的蛋白质。但温弗里正在超越生物学。他希望利用DNA独特的化学性质,像计算机一样处理信息(运用分子编程和DNA计算等新兴科学领域),甚至将DNA分子用作构建有用结构的支架。温弗里向《发现》杂志高级编辑斯蒂芬·卡斯讲述了他的工作、其对理解生命起源的启示,以及这种研究在遥远未来可能走向何方。
您从事生物分子计算领域。这究竟是什么? 对不同的人来说,它意味着不同的事物。对我而言,这意味着理解化学系统能够进行信息处理,并且可以被设计来执行各种任务。我观察它的一种方式是类比:我们可以设计计算机来执行各种信息任务,当你可以将这些计算机连接起来控制机电系统时,它们尤其有用。例如,你可以从摄像机获取输入。你可以向电机发送输出。生物分子计算的目标是为化学和分子尺度系统开发类似的控制。你如何编程一组分子来执行指令?
您是如何涉足这个相当奇特的研究领域的? 在高中之前,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初,我就对生物学和计算之间的联系产生了兴趣。那时我正在学习如何编程Apple II电脑,同时也在读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自私的基因》之类的书。这些事物在我的脑海中融合了。我对编程生物系统——玩进化正在玩的游戏——很感兴趣。我对各种形式的生物复杂性也很感兴趣,特别是神经复杂性:大脑是如何工作的?与此同时,我爱上了算法。我在芝加哥大学本科学习数学和理论计算机科学。我作为研究生去了加州理工学院,对用于机器人的神经网络很感兴趣。然后我做了一场关于[南加州大学计算机科学家] 伦纳德·阿德尔曼(Leonard Adleman)关于DNA计算的工作的报告。这是一种思考分子系统和计算之间联系的全新方式。它不仅仅是理论家的游乐场,而是一个你可以真正开始构思分子算法并在实验室中进行测试的领域。
您不是家里第一个获得麦克阿瑟奖学金的人——您的父亲亚瑟·温弗里在1984年因其将数学应用于生物学的工作而获得该奖。他的思想是如何影响您的?
我小时候,他不是麦克阿瑟研究员;他只是爸爸。也许还有点古怪。他喜欢给我们这些孩子展示东西。我养成了从不真正相信任何事情的习惯,因为他总是试图找出我们的漏洞,让我们独立思考。我小时候遇到的他很多朋友最终自己也成为了研究员,所以我从小就认为他们那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存在方式是正常的。
这些麦克阿瑟奖的联系在你的一生中一直伴随着你,不是吗? 有些是偶然发生的,有些则不是。我父亲参加麦克阿瑟会议时遇到了史蒂芬·沃尔弗拉姆(Stephen Wolfram)[一位独立数学家,创建了有影响力的Mathematica软件],之后我为他工作了一年。所以那不是偶然。但后来,我的博士导师约翰·霍普菲尔德(John Hopfield)是一位麦克阿瑟研究员,我猜我是偶然遇到的,因为我一直在寻找我真正尊敬的人。然后我遇到的一些其他人也成为了研究员。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待了一段时间,遇到了迈克尔·埃洛维茨(Michael Elowitz),他教我显微镜学;他于2007年成为了研究员。还有保罗·罗瑟蒙德(Paul Rothemund),他曾是我实验室的博士后;他也获得了奖学金。
这种自由自在的社区氛围是否反映了您在加州理工学院管理实验室的方式? 我努力鼓励我的实验室里有一种非常独立的态度,部分原因是我知道我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我的导师给了我很大的自由。实际上,他的说法是给了我足够的绳子来自缢。我回想起古希腊哲学家们如何聚会讨论,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故事和过程来到桌前。所以当一个学生来到我的实验室时,我喜欢说:“好的,那么想一个项目,下周告诉我你将要做什么。”有时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他们可能需要不是一周,而是一个月、一年甚至两年才能真正弄清楚他们感兴趣的是什么。尽管这可能很痛苦,但我认为这比告诉人们去执行具体任务,让他们进入一种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的模式要好。
真正的生物系统主要使用蛋白质来完成工作,但您的实验室专注于使用DNA。为什么?
蛋白质比DNA复杂得多。DNA更可预测,但它能执行范围广泛的功能。它就像纳米尺度构建的乐高积木;比用蛋白质更容易将部件组合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没有做任何新的事情。生物学家有一个假设,即曾经存在一个RNA世界 [RNA是DNA的单链近亲,在DNA和活细胞中的蛋白质工厂之间充当翻译者]。如果你看看地球上生命的演变历史,可能存在一个蛋白质进化之前的时代。那时RNA既是信息存储系统,也是活性元素,执行着细胞内的大部分功能。这个愿景告诉我们,核酸,无论是RNA还是DNA,都能做很多事情。
好的,那么用工程化DNA可以完成哪些任务呢? 这确实令人兴奋。我们将不同类型的分子系统视为计算模型。对于计算机科学家来说,计算模型是一组基本操作以及将这些基本操作组合起来以获得系统级行为的方式。
例如,数字电路设计者有简单的逻辑门,如“与”和“或”,作为基本操作。你可以将它们连接成电路以执行复杂的功能。[例如,你的个人电脑就是使用这些命令运行的。] 但计算机科学中考虑了许多不同类型的计算模型。
我的主要兴趣之一是研究哪些计算模型适合思考分子系统。在过去的四年里,我们对化学反应网络产生了兴趣,在那里你有一组反应:分子 A 加上分子 B 反应形成分子 C,X 加上 C 形成 A。传统上,化学反应被用作解释我们在自然界中看到的事物的描述性语言。相反,我们正在将它们视为编程语言的元素,一种表达我们试图获得的行为的方式。当你能够将分子的一部分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时,这就像计算机算法对数据进行操作。在分子世界中,数据结构实际上是一个物理结构——例如,在 DNA 分子中。因此,从 DNA 中生长出某些东西可以被认为是修改数据结构。挑战在于采用用该语言编写的程序并用真实分子实现它——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演示,我们非常感兴趣地想看看我们能走多远。我们还在思考如何获取一个分子并控制它,使其折叠成一个非常具体的结构。保罗·罗瑟蒙德(Paul Rothemund)开发了这项技术。[罗瑟蒙德在 2006 年因用编程 DNA 建造微观笑脸而登上新闻头条。] 然后还有分子级马达。所有这些东西都已用 DNA 系统以原始形式进行了演示。
这从理论角度听起来很吸引人,但这种分子控制方式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关于智能疗法有很多令人兴奋的地方,它将化学与生物系统结合起来治疗疾病;基于计算机科学的视角可能会发挥作用。对于这类工作,我们需要区分传感器、执行器和信息处理单元。在宏观尺度上,我们熟悉传感器和执行器必须与物理世界打交道的概念,但信息处理单元是与物理世界隔离的。它是完全象征性的:零和一。它不关心零和一的含义;它只是处理它们。在智能疗法中,需要大量的传感器和执行器工作才能以有意义的方式与生物系统连接[例如检测和操纵分子以治疗疾病]——这真的很难。但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构建一个DNA处理单元,它可以连接到这些传感器和执行器,并决定要针对哪些细胞或产生哪些化学物质。这相当具有推测性。我自己离生物医学研究还很远。
那么,利用生物分子计算来培育设备或机器——这可能如何实现呢? 同样,这里的想法是,工作的一部分可以由 DNA 完成——可编程部分。然后还有一部分,你需要一些化学上可行的物质,它与 DNA 相连;这是执行器部分。有一整套化学方法可以将蛋白质、碳纳米管或量子点[具有有趣光学特性的 5 到 10 纳米金属点]等物质附着到 DNA 的特定位置。这表明,如果你能用 DNA 搭建一个支架,那么你就可以对其进行化学处理,从而获得有用的东西。例如,将结合到 DNA 上的碳纳米管排列可以变成导电电路。为了构建这个 DNA 支架,你可以让它由短 DNA 片段制成的“瓷砖”自组装。这些瓷砖被设计成具有相互粘附的结合规则。这基本上是一个可编程的晶体生长过程。你可以放入一个包含你的程序的种子晶体[将其放入 DNA 砖块和其他原材料的混合物中]。然后种子晶体就会生长出你编程它创造的任何物体。
在哲学层面上,这项工作之所以令人兴奋,是因为它是一个纯粹的非生物生长过程,却具有我们通常与生物学相关联的许多特征。我太习惯于将 DNA 视为最终的生物分子,以至于很难想象它被以非生物方式使用,但实际上,将生物成分用于非生物目的有着悠久的传统。就像我坐在一张木桌旁,但树木并没有制造桌子、船只、房屋或我们用木材制造的任何东西的意图。因此,以这种方式使用 DNA 完全符合人类技术传统。它之所以显得奇怪,仅仅是因为我们对 DNA 的所有联想都是生物学的。
当您将DNA视为一种技术时,这会改变您看待人类或普遍生命的方式吗? 以这种方式使用DNA,确实能让我们对生命是什么有一个不同的视角。这是一个哲学家们经常思考的话题,因为你根本无法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生命定义。生物学家通常对此不屑一顾,只是继续研究它。但当你采取还原论的方法——即我们看到的现象可以用组成部分以及这些组成部分如何相互作用来解释——生命就是一个机制,你所寻找的是能够做很多有趣事情的分子。这正是我们用DNA发现的:它是一种信息载体分子,具有很强的可编程性。我们可以设计DNA分子来充当门、充当马达、充当催化剂。这些发现使得将生物体视为化学编程语言中的软件更加合理。
在将所有惊人的概念变为现实的过程中,您面临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我希望能够制造出按我要求工作分子!对于受过理论计算机科学训练的人来说,作为一名实验实验室研究员开始职业生涯是困难的。我们构建和测试系统,但我们实际构建和测试的系统比我们在纸上写下的系统简单得多。在纸上证明我们可以用DNA实现5000行长的化学反应集是一回事。构建一个涉及三到四个反应的系统——并且仍然无法按照我们想要的方式工作——又是另一回事。在如何构建程序的概念层面上有很多有趣的事情需要思考,但目前我们非常关注实现问题,并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那里。有几个问题限制了我们。例如,当我们设计分子组件时,会存在各种串扰。我们的DNA基组件相互碰撞。一些不应该相互反应的组件仍然会反应。某些应该发生的反应却没有发生。
您打算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需要建立容错机制。目前还不清楚这会如何发展。一个提出的原因,解释了为什么生物系统不断制造然后破坏蛋白质,是为了我们手上总是新鲜的分子而不是“发霉”的分子,这可能是解决串扰问题的一部分。另一个问题是,如果你有许多组件,它们都必须保持相当低的浓度,而在低浓度下,操作会非常缓慢。
有没有办法让生物分子计算以我们与传统计算相关的快速速度进行? 我们不会与电子计算机竞争。我们正在做不同的事情。想想制造某种新型仪器或设备,它像苍蝇或昆虫一样极其复杂和精心编排。在我看来,要制造这样的东西,你需要培育它们。然后就与生物发育进行了比较。如果你看看生物发育的时间尺度,它们通常是几个小时或几天。你需要正确的事情在正确的时间发生,才能生长出结构的不同部分。
还需要多久,才能真正用编程DNA设计复杂的系统和治疗方案? 大约一年前,我做了一个图表,查看了DNA计算和纳米技术领域有影响力的论文。1980年,纽约大学的内德·西曼(Ned Seeman)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大约32个核苷酸[连接形成DNA的分子]的系统,开创了这个领域。如果你绘制此后人们组合的核苷酸数量,增长大致呈指数级。我们有一篇新论文描述了一个包含大约14,000个核苷酸的系统。设计中核苷酸的数量大约每三年翻一番。再翻六番——大约20年后——我们将达到一百万个核苷酸,这大约是一个细菌基因组的大小。这个大小不一定能衡量你能用这个系统做什么,但它确实告诉我们,为了保持这种增长速度,我们需要掌握复杂性。我们需要玩计算机科学一直在玩的游戏来处理那些复杂的系统。让这些系统工作将极具挑战性,可能需要真正的概念性突破。这就是我喜欢这个领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