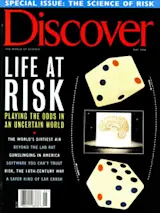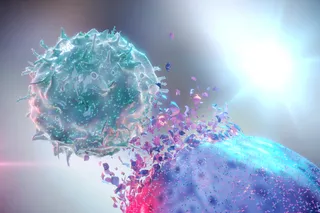癌症已经够糟糕了——在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宣布对其宣战 25 年后,它仍然难以治愈,常常是难以忍受的痛苦,而且令人遗憾的是,发病率很高。1994 年,美国因癌症死亡的人数达到 538,000 人,占该国总死亡人数的五分之一以上。尽管在临床上它很糟糕,但它引起的恐惧加剧了它的痛苦。我们无法将癌症追溯到任何单一的致病因素或命中注定的事件。它从构成我们细胞生物化学的数十亿复杂相互作用中滋生出来;正如数十年的研究表明的那样,它的病因多种多样。有些是遗传的——比如称为 BRCA-1 的基因,其功能失常似乎是许多乳腺癌病例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许多是环境因素,因此可能可以避免:众所周知的石棉;烟草;空气污染;蔬菜和水果摄入不足的饮食;酒精;阳光中的紫外线辐射。
如果我们能用一只手、两只手甚至十二只手指头数出危险,我们就可以认为自己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但随着研究人员筛选的物质越来越多,实验室里出现了大量带有骷髅头和交叉骨图案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物质。花生酱、芥末酱、根汁啤酒——它们都被发现含有至少痕量的已知致癌物。可能的致癌物清单已经变得如此之长,以至于产生了一种宿命论。你每次吃一片培根或深深吸一口你活动房里充满甲醛的空气时,你真的在招惹恶性肿瘤吗?生命本身就是万恶之源吗?
表面上看,没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忽视这些警告。传统上用于衡量毒性的动物实验是完全合理的。研究人员让一群在实验室培育的家鼠或大鼠在一段时间内接触可疑物质,然后与未接受试验化学品的一组基因相似的同类啮齿动物进行比较,以测量肿瘤的出现数量。如果暴露的动物恶性肿瘤显着增加,那么含义似乎很明确:你已经发现了一种致癌物。
这种系统的许多优点在于其简单性。实验室动物的基因是统一的。与人类不同,它们的生活很单纯。它们没有吃过成千上万种食物,没有接触过数百种化学物质,没有呼吸过数十种大气。你可以对它们进行精心设计和严格控制的实验,给它们服用疑似致癌物,同时避免接触其他可能干扰你结果的物质。如果它们对你的实验产生了可疑的症状,你可以相当有信心地认为,这并非由于你无法追溯甚至无法想象的很久以前的暴露所致。相比之下,试图监测大范围人群的疾病则要麻烦得多。假设在一个被致癌物笼罩的城市里,有一千人患上了癌症。你可能会合理地推断他们的疾病源于空气——但你永远无法绝对确定。其中十人、一百人或九百五十人可能来自你忽略的某种隐藏原因:当地饮食的怪癖或公交车站地下室里的一块被遗忘的钚。
然而,在评估癌症风险时,一些科学家对完全依赖啮齿动物感到不满。首先,家鼠和大鼠虽然与我们人类同属哺乳动物,但在基因上与我们相去甚远。一些实验中常用的品系自然比人类更容易患肿瘤,而且它们患上的恶性肿瘤也与通常折磨我们的肿瘤不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生物化学家布鲁斯·艾姆斯长期以来一直引用这些差异来批评我们使用动物模型来确定癌症风险的方式。在一项测试中,艾姆斯和他的同事调查了 226 种已知致癌物:结果发现,96 种在小鼠中引起癌症,但在大鼠中没有;56 种在大鼠中致癌,但在小鼠中无害。艾姆斯问道,当你从啮齿动物跨越到人类这片大峡谷般的鸿沟时,你能期待什么?
问题的根源在于,癌症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疾病,当你深入研究导致癌症的微观过程时,它会不断地分支。致癌物可能通过导致癌基因突变来发挥作用——癌基因是一种基因,如果它功能失常,就会为它所处的细胞不受控制的增殖奠定基础。但其他一系列因素也可能发挥作用。例如,艾姆斯说,每当你毒害健康细胞时,你都会增加肿瘤发生的可能性,因为任何一种细胞损伤都会刺激细胞分裂。你毒害的细胞越多,你引起的细胞分裂就越多,自发性癌变发生的可能性就越高。
正如艾姆斯指出的那样,这给动物测试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动物测试经常使实验动物承受疑似致癌物的大剂量。这些高剂量的目的是为了找出低剂量的致癌物。但是,如果你用高剂量的测试物质淹没动物,它可能会通过毒害大量健康细胞来产生癌症,即使它本身无法引发癌变。当然,这对被它淹没的小鼠或大鼠来说,它是一种致癌物。但如果它是一种人类永远不会接触到足以杀死健康细胞的物质呢?
因此,研究人员一直在寻找一个更可靠的联系,将致癌作用的微观领域与个人和政府在面对癌症威胁时有时需要做出的昂贵且具有破坏性的实际决策联系起来,也就不足为奇了。什么可以安全食用;什么会带来真正的癌症风险?我们可以在水和空气中允许哪些物质;什么是有害的,应该——无论付出什么代价——被消除?
有一个正在发展的科学领域,旨在以新的信心和准确性来解决这些困难的问题。它被称为分子流行病学:分子,因为它利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开创的技术来窥探细胞与外来化学物质相互作用(有时是与之搏斗)的亚微观领域;流行病学,因为它关注疾病如何在人类社会传播以及如何控制它。
该领域可能最终为可疑化学物质是否真正是人类致癌物而非仅仅是啮齿动物致癌物提供确切答案。更重要的是,一旦某种物质被确定为致癌物,分子流行病学就能区分该物质的微不足道的剂量和可能有害的剂量。它甚至可能能够确定单一剂量的物质对不同个体造成的不同风险。最终,它可能会产生一个简单的血液测试,显示你是否携带临床上危险剂量的致癌物质。
分子流行病学不会取代实验室老鼠。正如该领域的先驱之一,哥伦比亚大学的弗雷德里卡·佩雷拉指出,动物实验在预测能力方面表现良好。然而,分子流行病学旨在通过监视疑似物质与人体细胞之间的生化相互作用来实现更高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希望能够在潜在致癌物启动癌症过程时将其“人赃俱获”,或者将其洗脱嫌疑。然后,在掌握了亚微观证据后,分子流行病学家希望为他们的微生物学数据与人类疾病之间的联系做出清晰的阐释,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社会。
佩雷拉和该领域的同事们的工作不是从啮齿动物开始,而是从人类开始。他们收集患有癌症或接触过可疑化学品的志愿者的人体组织和体液样本。然后,他们仔细检查这些组织,寻找可疑的生物标志物——揭示可疑致癌物与人体细胞之间相互作用的化学产物。
分子流行病学家追踪各种各样的生物标志物,因为他们希望监测癌症进展的各个方面,从麻烦化学物质的首次侵入到随后导致全面恶性肿瘤的身体反应的复杂阵列。通常,他们正在寻找的“确凿证据”——例如,活化的癌基因——表明你的身体对致癌物做出了致命的细胞反应。但其他生物标志物可以揭示更早的阶段——例如,致癌物质首次进入你体内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研究人员最常寻找的是加合物——该物质与人体 DNA 之间可疑的化学键。
DNA-致癌物加合物可以是细胞分裂过程中破坏 DNA 复制过程的第一阶段。这可能导致突变。因此,当加合物沿着癌基因形成时,细胞复制的机制可能会失控,为恶性肿瘤的发生奠定基础。在过去的十几年半里,研究人员已经设计了几种高灵敏度的检测方法,用于检测人体 DNA 与各种致癌物之间的加合物。发现高水平的加合物是危险信号,表明癌症的某些条件已经具备。
佩雷拉认为,最终,分子流行病学家可能会建立加合物和其他生物标志物在某人体内组织中的数量与该人患癌症的可能性之间的联系。理想情况下,你可以通过简单的血液测试精确计算你的个人风险。如果发现风险很高,你就可以采取预防措施。佩雷拉指出,加合物本身不是疾病,但如果某人有高水平的加合物,我们可以减少或消除他的暴露,或者给他补充某些微量营养素——如维生素 A、C 或 E 以及类胡萝卜素等抗氧化剂。它们都抑制加合物的形成。
然而,目前,生物标志物与风险之间的这种联系还不切实际。任何对个人风险的现实评估都需要等待广泛研究的完成。据佩雷拉称,最有潜力获得有益结果的方法是前瞻性研究。在这种研究中,你组建一个志愿者群体,收集并储存血液和组织样本,然后长期监测他们的健康状况。每当该群体的一名成员患上癌症时,你就可以通过回顾患者在你试图评估的任何生物标志物方面的历史波动来进行所谓的嵌套病例对照研究。然后,你可以从同一群体中找到对照组——那些在各个方面(年龄、性别、吸烟史、种族群体以及接触可疑致癌物的历史)都与生病志愿者匹配,但却没有生病的人。如果在生病者和未生病者之间 DNA-致癌物加合物水平存在显着且一致的差异,你就走上了开发出有意义的测试之路。
积累足够多的此类数据后,就应该能够设定参数——决定你血液中某种 DNA-致癌物加合物的水平是多少,才能表明你已暴露于严重危险之中。也可能能够计算出某个特定族裔群体是否对某种癌症特别容易感。佩雷拉说,如果研究人员能够组建一个足够大的加合物和其他生物标志物的库,每个都对应着从最初暴露到肿瘤的漫长路径中的不同转折点,我们就可以捕捉到通往癌症的中间阶段,而不是知道某人已经暴露,然后盲目等待 20 年才能知道他是否会生病。
多环芳烃(简称 PAHs)的研究很好地说明了分子流行病学的工作原理。PAHs 是煤燃烧的副产品,在工业化程度高的地区普遍存在,是世界上最知名、最恶劣的环境致癌物之一。一旦它们进入人体,就会很容易与细胞 DNA 形成加合物。佩雷拉与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 Regina Santella 一起,一直使用这些加合物作为人群暴露于 PAHs 的指标。例如,1990 年,他们监测了波兰癌症高发区西里西亚地区一个污染极其严重的城镇格利维采居民的 PAH-DNA 加合物的发生情况。随着居民将煤炭供暖的副产品排放到格利维采本已令人窒息的工业烟雾中,空气在每个冬天都变得更糟。佩雷拉发现,志愿者血液样本中的 PAH-DNA 加合物确实随着城镇碳氢化合物浓度的季节性波动而上升和下降。
过去十年对芬兰铸造厂工人的研究得出了与波兰工人一致的结果。芬兰人是良好的研究队列,因为工厂每年七月关闭四周进行休假,此时每个人同时经历污染物暴露的急剧下降。在返回工作岗位后的几周内,他们的 PAH-DNA 加合物水平急剧上升。同样,一群吸烟者,他们的尼古丁习惯也使他们暴露于 PAHs,在戒烟几个月后,PAH-DNA 加合物水平显着下降。当然,这些结果强烈表明,PAH-DNA 加合物是在接触致癌污染物后出现在血液中的。
尽管如此,你可能会问,这些加合物是否真的与癌症有关。显然,这里的答案也是肯定的。在纽约哥伦比亚长老会医疗中心最近的一项研究中,佩雷拉的团队发现,即使在调整了吸烟情况后,肺癌患者的血液样本中的 PAH-DNA 加合物水平也显着高于没有患病的人。他们的结果表明,癌症患者对烟草烟雾造成的基因损害特别敏感。
当然,所有这些研究都只照亮了一个广阔而复杂景象的微小角落。在波兰和芬兰进行的工作表明,当你暴露于空气中的 PAHs 时,血液中的 PAH-DNA 加合物会迅速增加,而且这些加合物与癌基因的癌前突变相关。但没有人知道,有多少患有 PAH-DNA 加合物水平升高的波兰和芬兰工人最终会患上疾病。没有人知道早期血液检测中这些加合物的水平是多少才构成“忽略后果自负”的警告。佩雷拉说,加合物只是一种指纹。
这些不确定性突显了分子流行病学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佩雷拉和她的同事们现在正忙于扩大他们的生物标志物库。他们已经研究了除了 PAH 之外,人体 DNA 与其他致癌物之间的加合物。他们还采集了其他类型的指标,这些指标可以作为替代品,例如致癌物与 DNA 产生的蛋白质之间的加合物(这些很有用,因为即使在非常小的血液样本中也很容易找到)。
当然,要实现完整的分子流行病学,你需要一套标记物,能够反映每一种已知的致癌物,并准确记录从初次暴露到肿瘤的每个阶段。它们需要保持一致,以便血液样本中的特定水平能够可靠地表明你在每个阶段完全进展的机会。而且它们还必须易于采集,例如,可以从血液样本中获得——你不想每次去购物中心进行健康筛查时都捐献一块肝脏。然后,通过细致而详尽的统计研究,这是流行病学的基础,这些标记物将需要随着时间与足够大的群体(能够产生有意义的结果)的癌症状况变化相关联。
佩雷拉和她的同事们相信,这项努力最终将带来双重回报。最早可能的收益将是普遍性的:准确了解哪些潜在致癌物对整个人群的威胁最大。我们将能够更好地利用动物模型;我们将更清楚地知道需要对我们的动物结果进行何种调整才能将其应用于人类。如果我们能够记录人类遗传或其他临床前损伤的范围,我们就可以针对整个人群微调风险。我们将有更好的信息来制定环境标准。
之后,回报可能会变得更加个性化。佩雷拉观察到,你和我可能接触到完全相同数量的化学物质,但我们的反应却不同,因为我们代谢致癌物的方式不同,因为我们的 DNA 修复率不同,或者因为饮食等获得性因素。事实上,我们估计,在个体对致癌物的反应方式上可能存在五十到一百倍的差异。
换句话说,分子流行病学是一项旨在联合宏观和微观、理论和实践的事业。研究人员梦想着有一天,他们的工作将为我们提供一个简单的测试,最终告诉你,如果你接触了致癌物,你最想知道的是什么:你是那些可以安全忽略它的人吗?还是你处于危险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