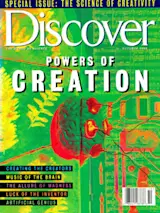安德鲁·怀尔斯让我心碎。从小到大,我一直打算只要一有空就证明费马大定理。但首先我有很多法语作业要完成,然后是我表弟的婚礼,我必须在办公室加班写备忘录,而且八月太累人了,然后怀尔斯就去证明了它。
当然,还有一些伟大的未解问题:一两个希尔伯特问题,哥德巴赫猜想,以及曲速9到底是多少光年每秒?我想我最好赶紧行动,以免又有人抢在我前面。但是当我清理了桌上的空间,坐下来,拿着两支2号铅笔、一本法律便笺、一个量角器和一台克雷超级计算机时,什么也没有发生。我削尖了铅笔。什么也没有发生。我把法律便笺换成了坐标纸。我又削尖了铅笔。什么也没有发生。
我遇到了创作瓶颈。
我打电话给我的老朋友迈克尔·拉森,他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数论学家,寻求建议。我正在尝试证明哥德巴赫猜想,但毫无进展,我说。我该怎么办?
你试过学习数学吗?他建议。
表面上看,这听起来是个明智的想法。然而,时间因素困扰着我。算一下,申请研究生院一年,两年研究生课程,再四年写论文——那是我生命中的七年。七年里会发生很多事情。如果怀尔斯和他的同类在我还在学校里磨蹭的时候就证明了所有剩下的东西怎么办?肯定有更快的方法。
也许,我想,一位创意专家可以帮我找到它。我打电话给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的认知心理学家大卫·珀金斯,他拥有数学博士学位。是什么导致了创意瓶颈?我问他。
珀金斯告诉我,它们可能有两种不同的原因。一种是个人原因——比如焦虑,当你害怕自己可能无法解决问题时,或者动机从其他领域转移了。有时人们表现不佳是因为他们试图逃避某种情况,或者报复某人,他们通过损害自己的表现来达到目的。焦虑会产生自我实现的预言:人们开始担心自己能否解决问题,并开始相信自己不能,然后他们当然就不能,这证实了他们的信念。临床医生称之为自我封闭系统。
珀金斯继续说,第二种是问题本身的原因。创意情境可能导致人们遇到困难,不是因为他们处于某种低谷,而是因为问题确实很难。他描述了四种可能的创意困难:荒野问题,即可能性太多,以至于难以在其中导航并找到好的解决方案;高原问题,即你处于某个位置,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峡谷问题,当你在不自知的限制中原地打转,你需要走出峡谷,因为真正的解决方案在附近的另一个峡谷中;以及绿洲问题,当你 clinging to a partial solution but to reach a real solution you have to abandon it。
我想,珀金斯一定穿着磨损的登山靴。我看到自己迷失在他的风景中,在但丁地狱第七圈的某个地方。有出路吗?我问。他说,头脑风暴对峡谷问题和绿洲陷阱非常有效。对于荒野困难,解决一个更小版本的问题可能会有帮助。对于高原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彻底研究你试图回答的问题,探索其所有方面。
这听起来又可疑地像学校了。我赶紧谢谢珀金斯,在他提出博士项目之前,我就去了当地的灵修自助书店。他们肯定不会让我学习。你能推荐什么来帮助我克服创作瓶颈吗?我问那个全身紫色衣服的店员。
最好的办法是接触你内在的艺术家,也许联系你的精神向导,她真诚地告诉我。
我指的是更像是书或录音带。
她找到几本,收了我的钱,把收据递给我。找零:4.17美元,上面写着。勤勉地对待现实。善待所有人。少说多做。好建议,我想,但是怎么做呢?而且它不应该实践它所宣扬的吗?
希望这些磁带能有更完整的说明,我效仿希拉里·克林顿,求助于心理学家珍·休斯顿,或者珍·休斯顿博士,正如她在书封上自称的那样。休斯顿在六月给克林顿夫人带来了糟糕的一周,当时有报道称她一直在鼓励第一夫人与埃莉诺·罗斯福和甘地进行想象对话;评论家们认为这些人物过于优柔寡断,无法提供适当的指导。
休斯顿对时间的感知有些弹性。正如她在她的有声磁带《唤醒创造力》中所解释的,在短短几分钟的时钟时间里,你会发现自己拥有——哦——很多分钟、几小时,有些甚至几周,甚至几个月,似乎是内在体验,去探索人类心灵中广阔……未开发的宝藏……一首通常需要数小时练习的贝多芬奏鸣曲,可以在五分钟内通过加速的心理过程练习,你将从这种状态中醒来,感觉自己练习了数小时,并且在演奏上显示出显著的进步。(要是有人早点告诉我哥哥,就能省去我们一家人听了那么长时间的《致爱丽丝》了!)所以,让我们开始吧。
我们开始躺下,闭上眼睛。慢慢地,珍博士那迷人的声音将我进一步引入加速心智过程的领域。深呼吸……想象空气升入你的大脑并为其注入能量,她低语道。一分钟过去了,然后是一小时。三天过去了。我希望我能想到带午餐。我开始怀疑我是否完全关掉了炉子上的所有炉头。遵循休斯顿的建议,我轻轻地按压我的手掌,闭上眼睛。我看到了灯光,然后是一些形状,最终它们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红绿相间的鹦鹉。我想,这一定是我的精神向导。
你好,它说。
你好,我回答。
你好,它说。
你好,我回答。
你好,它说。
你是谁?我问。
你是谁?它问。
我是波莉,我说。
我是波莉,它回答。它歪着头,用一只黄色的眼睛看着我,收缩着瞳孔,好像在眨眼。
你是我的精神向导吗?我问。
波莉盯着我看了很久,也许几周,瞳孔交替收缩和扩张。最后它又开口了:你闻到煤气味了吗?
我停下磁带,匆匆去检查炉子。四个炉头都关着。我坐回书桌,再次削尖铅笔。仍然一无所获,于是我回到音响旁,播放了鲍勃·格里斯沃尔德的《发展你的创造力》。盒子上写着:保证100%可听。像珍·休斯顿博士一样,格里斯沃尔德也想让我有节奏地呼吸。(他说放松的呼吸比紧张的呼吸更深更慢,通过改变呼吸,你可以把情绪从焦虑变为平静。)不建议在开车时听这盘磁带,因为它会让你闭上眼睛,深度放松,他警告说。催眠的钢琴声伴随着他缓慢的声音,他解释着如何做。起初,波莉也跟着哼唱,还加了一些听起来像《致爱丽丝》的小花样,但渐渐地,这只鸟安静了下来。我瞥了一眼,看到它单腿站立,头藏在翅膀下。一种深深的平静感笼罩着我;我感到紧张消退;很快,我和波莉一样,处于一个绝佳的状态,可以从伊丽莎白·欧文·罗斯的《如何在睡梦中写作以及其他惊人的方式来提升你的创造力》中获益。
在她的书中,罗斯引用了一位又一位诗人——伏尔泰、斯温伯恩、但丁、歌德、弥尔顿、布莱克——他们简直是在梦中创作出了不朽的诗篇。而且,并非只有作家才能在闭着眼睛、微张着嘴、枕头上留着一道细细的口水痕迹时获得深刻的见解。罗斯提到了像苯的发现者化学家弗里德里希·凯库勒和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这样的科学家。
她建议通过冥想练习来驾驭你自己的梦想力量,比如这个:首先,像珍博士那样给你的大脑充气。接下来,想象你自己正在煮咖啡。你将水倒入壶中,量好所需的咖啡量,放入滤纸,然后把咖啡壶放在炉子上……默念十遍:“我的文章/故事/书就像咖啡。所有必要的成分都在我的潜意识中酝酿……”如果你在睡前做这个练习,就直接睡着。
很快我就开始做梦了。
我在满月下沿着一条路疾驰。我走的每一步都让我陷入严重的危险,但我不能离开它,否则我永远也无法到达目的地。我正在吟唱一首韵歌,一个咒语来保护我免受潜伏的恐怖。这首韵歌是唯一能让我安全的东西。不知何故,我知道它不仅是一个强大的护身符,也是一部杰作的种子——一首伟大的诗歌或一项发明,一些能让我名利双收,并给各地人们带来希望的东西。我一遍又一遍地吟唱着它,以抵御道路的威胁,并将其安全地带过睡眠之门,进入清醒的世界。
带着胜利的感觉,我睁开眼睛,大声念出我的咒语:袜子和鞋子!袜子和鞋子!
睡梦中写作就到此为止吧。我把剩下的咖啡倒进杯子里,派我的精神向导去买甜甜圈。然后我打开格里斯沃尔德的快速播放。在你右脑半球,你可以接触到大量的才能和能力,而你大脑的这一部分几乎完全未被开发,他以最快的速度喋喋不休地说。
那会是我的问题吗?我一半的大脑是不是就这样像个肿块一样闲置着?翻阅我在书店买的东西,我一遍又一遍地看到关于未开发的大脑潜力的概念。我们的陈旧、狭隘的大脑和教育观念,让多少脑力付诸东流!这个数字无疑是可怕的,珍博士哀叹道。《无限可能:释放你自己,创造你真正想要的生活!》一书中,路易丝·L·海叹息道:“你知道,他们告诉我们只使用了大脑的10%。我的问题是,那另外90%是用来做什么的?”
那也是我一直想知道的。实际上,我听说10%这个数字只适用于选举年,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认知心理学家乔纳森·金在我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回答道。如果你在听脱口秀电台,这个数字还会更高。你没有录音吧?但每个人都会问我“10%问题”。他解释说,似乎没有人知道这个数字最初是从哪里来的,而且对于任何神经科学家来说,它是否具有意义也不清楚。这肯定不是你大脑皮层功能总量的10%,因为其中大约50%几乎只用于视觉。但这也有点误导。我的意思是,如果你看《辛普森一家》时比我听贝多芬时用的大脑更多,你会觉得我很厉害吗?大脑的听觉处理区域只占我们最喜欢器官的区区4%到5%。当然,金继续说,如果你能把它变成某种竞赛,也许你可以通过增加一些其他活动来追上我——同时爬楼梯、敲击手指和嚼口香糖。那也能锻炼你的运动皮层。但如果你转过头开始读窗外的广告牌,使用视觉和语言区域,我可就完蛋了。
那么,那10%指的是别的东西吗?比如同一时间活跃的脑细胞总数?
这可能更接近事实,因为不到50%的脑细胞是互相发送信息的神经元。其余的都是各种类型的神经胶质细胞,它们做着各种重要但无聊的事情。特别是,它们提供包裹着轴突(神经细胞的长臂)的髓鞘,并帮助防止电信号衰减。
髓鞘,金说,大部分是脂肪。给大脑充氧并不会让它变得更瘦,这是一件好事:没有人想要瘦弱的许旺细胞。无论如何,增加同一时间放电的神经元总数并不会让你思考得更好,即使它不是癫痫的发作原因。让一个神经元一直放电,肯定不如让它在正确的时间放电有用。
那你的右脑半球是不是被闲置了呢?
哦,不。不是右脑半球的问题,金呻吟道。嗯,右脑半球擅长把握大局的说法有点道理。粗略地说,左脑半球看到更多细节;右脑半球将它们整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意义。所以当你只是向窗外看时,你就使用了右脑半球,即使你认为自己并没有特别“有创意”或“有灵性”或其他什么。
我向窗外望去,我的左半球能够辨认出200多块砖头,而我的右半球则将它们识别为隔壁建筑的墙壁。波莉落在窗台上,手里拿着一盒全麦薄饼。
甜甜圈呢?我问。
波莉想要饼干,那只鸟回答道,递给我找零和收据,上面写着,总计:3.21美元。低买高卖。既不借钱,也不借钱给人。
我再次坐到我的书桌前。
我的精神向导发出了削铅笔的声音。
没必要挖苦我,我说,伸手去拿另一盘磁带。我的手落在马克·H·麦考马克(Mark H. McCormack)的《110%的解决方案》(The 110% $olution [原文如此])上。盒子上写着:连100%都不够。你必须学会如何付出额外的10%。我想,对于任何能理解那种数学的人来说,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应该轻而易举。然而,仔细阅读小字,我得知这盘磁带是缩略版。还剩多少?只剩100%?(八块钱,波莉插嘴道。)我连打开都没打开就把它扔了。
根据我尝试的下一盘磁带《女性创造力之书》的作者兼旁白C·黛安·伊利(C. Diane Ealy)的说法,像我这样的障碍可能源于社会将她所描述的整体螺旋式女性创造过程强行纳入男性线性模式。解决方案是什么?走到镜子前,看着自己的眼睛,大声宣布:“我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人。我喜欢以多种方式进行创造。”多说几次。
我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人。我喜欢以多种方式进行创造,我说。我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人。我喜欢以多种方式进行创造。我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人。我喜欢以多种方式进行创造。
虽然我可能很有创造力,但我发现自己离证明舒尔曼第一定理从未如此之近。此外,我想,我为什么要仅仅因为我是女性而回避逻辑呢?居里夫人没有;伟大的数学家埃米·诺特也没有。哈佛商学院的心理学家特蕾莎·阿马比尔也同样表示怀疑。我打电话给她时,她告诉我,在过去的20年里,我对创造力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我根本没有发现任何持续的性别差异,无论是在创造过程还是在创造产出的质量上。
即使男性和女性以不同的风格解决问题,我们仍然面临问题本身的相同类别困难。如果你不能在办公桌前坐足够长的时间来决定你面对的是峡谷问题还是高原问题怎么办?如果你不停地起身去听磁带或打电话给专家怎么办?大卫·珀金斯告诉我,这明确表明是个人问题。也许存在一些焦虑或转移。也许你不够投入。许多研究人员认为投入甚至比才能更重要。
承诺?我从哪里得到它?解决方案原来是我尝试的最后一盘磁带,茱莉亚·卡梅伦的《艺术家的道路》。卡梅伦没有简单的答案:没有在睡梦中写作,没有不触碰琴键就能学会弹钢琴。她说,创意表达是真实的工作,而且需要很长时间。
卡梅伦抨击了那些阻碍人们加入艺术家俱乐部的神话。她坚持认为,你不需要穿黑色才能成为艺术家。你不需要住在巴黎,不需要喝酒,也不需要在阁楼里独自挨饿。我们有一个信念系统,认为艺术家是独狼。没有任何东西支持这一点。例如,印象派画家们一起吃午餐——那就是他们所画的。
困扰有创意的人的一件事是卡梅伦称之为“审查者”的内在批评家。把它想象成你小学时认识的最坏的恶霸,但要聪明得多,她说。
我把鹦鹉抱在手臂上,再次坐到我的书桌前。听着,波莉,我需要跟你好好谈谈,我说。你是我的精神向导吗?还是你是审查者?你是什么,鸟?
我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人,波莉说。我喜欢以多种方式进行创造。
好吧,我相信你的话。我就坐在这里,拿着我的笔记本。我不会再削铅笔,也不会再听磁带了。我只会专注,也许写几个方程之类的。它们可能是不好的方程,但我会一直写下去,直到你告诉我更好的事情要做。所以,开始吧。启发我。
当我勾勒莫比乌斯带并计算其表面积的公式时,波莉开始唱歌。
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从没想过新娘头纱会是我的泪谷。
嘘,你分散我的注意力了,我说。我正在努力计算莫比乌斯带的周长。那只鸟跳到我的耳边,唱得更响亮了一些。那曲调有点像《致爱丽丝》。
我想你把她抱过了门槛。
你一定把妈妈的戒指给了她。
我想你发誓的时候我不在场。
我想你从未对我许诺过什么。
波莉重复了一遍副歌,然后沉默了。
就这样?我说。就这些?一首乡村歌曲?没有定理?甚至没有治打嗝的办法?
你是审查者吗?我的缪斯问道。
但是波莉,我抗议道,一首乡村歌曲?这太令人尴尬了!
鹦鹉把它那明亮的黄眼睛转向我,带着严厉的同情说:“袜子和鞋子。”
好吧,精神向导。你赢了。灵感是无法抗拒的。你只需接受降临的一切,继续走在那条危险的道路上,用你的歌声保护自己。向你致敬,快乐的精灵!有人知道纳什维尔的好经纪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