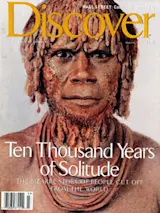我记得去上大学的时候。我紧张又兴奋,以至于提前一周就开始拉肚子。如果他们录取我错了怎么办?如果我一个朋友都交不到怎么办?这些真的会成为我生命中最美好的几年吗?我晕头转向地把行李装上灰狗巴士,偷偷地把一瓶高岭土(Kaopectate)塞进我的背包。
实际上,我的肠胃之所以如此不安,是完全有道理的,因为等待着我的大一生活充满了重大事件:顿悟到我永远无法理解光合作用,应该放弃生物学专业(我转修生物人类学);在食堂里看着四年紫色的酸奶和波利尼西亚无肉丸子时,意识到我妈妈是一位了不起的厨师;我上的第一堂政治正确课——我学会了现在我周围都是女性,而不是女孩;无限愉快的发现,有些女性现在偶尔愿意和我说话;惊叹于年长的男生如何巧妙地将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和巴克明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的参考文献融入随意交谈中;发现高中时有效的笑话在这里同样有效时的得意;每天晚上与室友争论开窗还是关窗的平静仪式。
成长,然后离开。去上大学,去参战,去城市工作,去新的世界安家——家再也不会一样了,有时甚至再也见不到家了。这种成熟事件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不仅对我们人类至关重要,对我们许多灵长类亲戚也是如此。成长和离开的过程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充满兴奋、发现和挑战。
一些灵长类动物,如猩猩,过着独居生活,只在偶尔交配时相遇。但普通的灵长类群体是极其社会化的,无论是一群生活在山区雨林中的十几只大猩猩,一群生活在印度村庄边缘的20只叶猴,还是一群生活在非洲草原上的100只狒狒。在这样的群体中,幼崽出生在一个充满亲戚、朋友和对手的世界里,被阴谋、背叛、约会和英勇事迹所包围——这些都是小镇八卦的必备元素。对于学习如何信任他人、了解规则以及物种特有的餐桌礼仪的孩子来说,这真是令人兴奋的事情。
大多数年轻的灵长类动物以这种方式有效地社会化,家园似乎一直都很温馨。然后,不可避免地,许多幼崽必须离开群体,独自闯荡。这是由遗传和进化驱动的一个简单事实:如果所有成员都留下来,在那里成熟和繁殖,如果它们的后代也留下来,它们的后代的后代也留下来,那么最终所有人都会变得非常亲近。你就会遇到经典的近亲繁殖问题——很多长相奇特的幼崽,有六根手指和两条尾巴(以及更严重的遗传问题)。
因此,几乎所有社会性灵长类动物都进化出了青少年从一个群体迁徙到另一个群体的机制。并非所有青少年都必须离开。只要一个性别的所有青少年都去别处发展,近亲繁殖问题通常就能解决;另一个性别的成员可以留在家里,与迁入群体的新成员交配。在黑猩猩和大猩猩中,通常是雌性离开去新的群体,而雄性则与它们的母亲留在家里。但在大多数旧大陆猴子——狒狒、猕猴、叶猴——中,则是雄性进行迁徙。为什么一个物种中是一个性别迁徙,而另一个物种中却不是,这是一个完全的谜团,正是这种谜团让灵长类动物学家们争论不休。
这种青少年迁徙模式解决了近亲繁殖的幽灵。但仅仅把它看作是对进化问题的解决方案,未免过于机械化。你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那些是真实的动物,正在经历艰难的过程。观察起来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每天,在灵长类动物的世界里,某个年轻而害怕的个体收拾行李,离开妈妈和所有它认识的人,走向未知。
我最熟悉的迁徙模式是东非大草原上的狒狒。两群狒狒在中午时分在某种自然边界(例如一条河流)相遇。在这种情况下,狒狒惯常的做法是,两群的雄性会进行各种攻击性展示,发出叫声和吼叫,它们无疑希望这能表现出极大的威胁。最终,所有狒狒都感到厌倦,然后回去吃东西和休息,无视河对岸的闯入者。突然,你发现那个幼崽——你群中的某个青少年。它站在河边,完全被吸引住了。新狒狒,一大群!它朝它们跑了五步,又跑了四步回来,在它群的其他成员中寻找,看为什么没有人被这些陌生人迷住。经过漫长的思考,它小心翼翼地穿过河流,坐在另一边河岸的边缘,只要有任何新狒狒朝它看一眼,它就会惊慌失措地跑回来。
一周后,当两群狒狒再次相遇时,那只幼崽重复了同样的模式。只不过这次它整个下午都坐在新狒狒群的边缘。在下一次相遇时,它会跟着它们走一小段距离,直到焦虑感变得太强,它才转身返回。最终,在一个勇敢的夜晚,它留在了它们那里。它可能会再犹豫一段时间,甚至最终选择第三个狒狒群,但它已经开始了向成年期的过渡。
那真是一段糟糕的经历——一段痛苦、孤独、边缘化的生活阶段。没有新生周,没有新来的同伴抱团取暖,用虚张声势掩盖他们的紧张。只有一个年轻的狒狒,独自一人在新群体边缘,没有人关心它。实际上,这并不完全正确——新群体中常常会有一些成员非常关注它,表现出灵长类动物中最不讨人喜欢的行为,也最让人想起它们人类表亲的行为。假设你是这个群体中等级较低的成员:也许是一个在你刚迁徙后一年左右的弱小幼崽,或者是一个正在衰老的雄性。你大部分时间都在打架中失败,被人推来推去,食物被等级更高的个体抢走。你有一长串不满,却无能为力。当然,群体中有些幼崽你可以成功地欺负,但如果它们是迁徙前的年龄,它们的母亲——也许还有它们的父亲和整个大家族——会像一吨砖头一样向你袭来。然后突然,就像天赐的礼物一样,一个更弱小的新幼崽出现了:一个可以发泄的对象。(在黑猩猩中,雌性进行迁徙,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当地的雌性对生活在群体边缘的新来的雌性会表现出残忍的攻击性。)
然而,这只是迁徙动物问题的开始。作为我对狒狒疾病模式研究的一部分,当我麻醉并检查迁徙雄性时,我发现这些年轻的动物身上寄生虫丛生。不再有人给它们梳理毛发,坐下来细致地清洁它们的毛,一半是为了卫生,一半是为了友谊。如果没有人对梳理刚迁徙来的动物感兴趣,那么肯定没有人对更亲密的事情感兴趣——简而言之,那是一个充满自慰的时期。年轻的雄性遭受着被认定为灵长类书呆子的所有屈辱。
它们也极易受到攻击。如果捕食者袭击,迁徙的动物——通常一开始就处于边缘和暴露的位置——不太可能识别群体的信号,也没有人可以依靠来保护自己。在我第一次在非洲进行研究时,我就目睹了这样一件事。那只不幸的动物对我的群体来说是如此之新,以至于它只有一个编号273,而不是名字。群体在午后的炎热中漫步,沿着一条干涸的河床下降,遭遇了不幸:一只半睡的狮子。恐慌随之而来,狮子苏醒时,动物们四散奔逃——而雄性273号则茫然地站在那里,非常显眼。它受了重伤,并以一种悲怆的行为,爬行了数英里,回到它以前的家园群体,死在它母亲身边。
简而言之,迁徙期是灵长类动物生命中最危险、最痛苦的时期之一。然而,几乎不可思议的是,生活会变得更好。有一天,一个年轻的雌性会坐在我们的迁徙雄性旁边,短暂地为它梳理毛发。某个下午,所有狒狒都饥饿地涌向一棵结果实的树,年长的年轻雄性忘记了赶走新来者。某个早上,年轻的雄性和一个成年雄性互相打招呼(在雄性狒狒中,这包括互相拉扯生殖器,如果我见过的话,这是一种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社交姿态)。而总有一天,不可避免地,一个受惊的新迁徙雄性会出现,我们的英雄,也许会永远感到羞耻,沉溺于欺负阶梯上比自己低的人的攻击性快感。
在一个渐进的同化过程中,这只迁徙的动物交到了朋友,找到了盟友,并交配,在群体中的等级也逐渐上升。这可能需要数年时间。这就是为什么霍布斯(Hobbes)是如此非凡的野兽。
三年前,我和妻子在肯尼亚安博塞利国家公园的一个狒狒群里度过了一个夏天,那是一个由芝加哥大学行为生物学家珍妮·奥特曼和斯图尔特·奥特曼运营的研究地点。我研究狒狒的等级与个性之间的关系,它们的身体如何应对压力,以及它们会患上哪些与压力相关的疾病。为了获取生理数据——例如血样以衡量动物的应激激素水平、免疫系统功能等——你必须借助一个小型铝制吹管和装有药物的飞镖,麻醉狒狒几个小时。将飞镖装满适量的麻醉剂,走到狒狒旁边,瞄准,然后吹,五分钟后它就睡着了。当然,事情没那么简单——你只能在早上射飞镖(以控制昼夜节律对动物激素的影响)。你必须确保周围没有捕食者来撕碎它,并且你必须确保它在昏迷前不会爬树。最重要的是,你必须在其他狒狒不注意的时候射飞镖并将其从群体中移开,这样才不会惊扰它们并破坏它们对科学家的习惯。所以,基本上,我用我的大学教育所做的事情,就是在灌木丛中悄悄地跟踪一群狒狒,等待它们都看向别处的那一刻,这样我就可以把飞镖射到某个狒狒的屁股上。
那大约是这个季节过半的时候。我们刚刚开始认识我们狒狒群里的狒狒(以一位已故的母系长者命名为“胡克群”),并逐渐熟悉它们的日常生活。每天晚上它们都在它们最喜欢的一片树林里睡觉;每天早上它们起床,在撒满了亿万年前附近的乞力马扎罗山喷发出的火山岩的开阔稀树草原上觅食。那是旱季,这意味着狒狒必须比平时走更多的路才能找到食物和水,但两者仍然充足,而且狒狒群有时间在下午的炎热中在阴凉处休息。在雄性狒狒的社会等级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一个名叫鲁托(Ruto)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他几年前加入了这个群体,并相对迅速地升入高位。第二位是一只名叫肥仔(Fatso)的雄性,他不幸在几年前迁入群体时是个圆滚滚的青少年,并被一位冷酷的研究员起了这个名字。他现在已经不胖了。现在他是一只肌肉发达的壮年雄性,是鲁托最明显的竞争对手,尽管仍然明显处于下属地位。那对狒狒群来说是一个相当平静的时期;邮件定期送达,火车准时运行。
然后,一天早上我们发现狒狒群完全混乱了。说所有狒狒都非常焦躁不安,这并非拟人化。来了一只新的迁徙雄性,而且不是那种怯生生地在边缘徘徊的。它在群体中央,大吵大闹——恐吓、追逐、殴打所有它看到的一切。这只邪恶、粗暴的动物很快就被命名为霍布斯(Hobbes)(以纪念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他将人类的生活描述为孤独、贫穷、肮脏、粗暴和短暂)。
这在狒狒中极其罕见,但并非闻所未闻。在这种情况下,迁徙的雄性通常是一只体型大、肌肉发达、令人生畏的幼崽。也许它比平均七岁的迁徙雄性更年长,或者这可能是它的第二次迁徙,它从第一次迁徙中获得了信心。也许它是它旧群体中高等级雌性的儿子,从小就被培养得自大傲慢。无论如何,具有这些特征的罕见动物会像卡车一样冲进来。而且它通常能逍遥法外一段时间。只要它不断施压,居住的雄性在鼓起勇气对抗它之前还需要一段时间。没有人认识它;因此没有人知道,率先挑战这个好斗的疯子是否会带来致命的伤害。
这就是霍布斯的风格。受惊的雄性们无助地站在一旁。肥仔发现自己还有各种各样的差事要跑到别处。鲁托躲在雌性后面。没有人愿意站出来。霍布斯在一周内就升到了群体中的第一位。
尽管霍布斯突然崛起,但他的成功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他仍然是一个相对缺乏经验的幼崽,最终其中一只体型较大的雄性肯定会让他知道自己的斤两。霍布斯大约有一个月的逍遥时光。此时他做了一件残忍暴力但却具有某种冷酷进化意义的事情。他开始选择性地攻击怀孕的雌性。他殴打并残害它们,导致四分之三的雌性在几天内流产。
在进化背景下,动物行为的一大俗套是动物为了物种的利益而行动。这种观点在20世纪60年代就被否定了,但仍然渗透在类似《狂野王国》版本的动物行为中。更准确的观点是,动物通常以最大化自身繁殖和近亲繁殖的方式行事。这有助于解释在某些情况下非凡的利他主义和自我牺牲行为,以及在另一些情况下令人作呕的攻击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霍布斯的攻击才有意义。如果那些雌性完成怀孕并抚养后代,它们在两年内不太可能再次交配——谁知道霍布斯届时会在哪里。相反,他通过骚扰雌性使其流产,而它们在几周后再次排卵。尽管雌性狒狒在与谁交配方面有发言权,但在像霍布斯这样强硬的个体面前,它们几乎没有选择:几周之内,霍布斯,仍然是群体中的主导雄性,与那三只雌性中的两只交配。(这并不是说霍布斯阅读了关于进化、动物行为和灵长类产科的教科书,并深思熟虑了这一策略。这里的措辞是方便的简称,更准确的说法是他的行为模式几乎肯定是一种无意识的、进化的行为。)
碰巧的是,霍布斯的出现——就在我们已经为我们的研究射击并测试了大约一半的动物之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我们可以比较在他的骚动性迁徙前后,这个群体的生理状况。在一项最近与珍妮·奥特曼和苏珊·阿尔伯茨共同发表的研究中,我记录了一个并不令人惊讶的事实:霍布斯正在给这些动物带来巨大的压力。它们血液中的皮质醇(也称为氢化可的松,是压力期间最可靠分泌的激素之一)水平显著升高。同时,它们的白细胞或淋巴细胞(免疫系统的哨兵细胞,保护身体免受感染)数量显著下降——这是另一个高度可靠的压力指标。这些压力反应指标在那些受到霍布斯最多困扰的动物身上最为明显。未受骚扰的雌性循环淋巴细胞数量是那些在最初两周内被攻击五次的贫穷雌性的三倍。
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为什么不是每一个新迁徙的雄性都尝试像霍布斯那样大胆成功的举动?首先,大多数迁徙的雄性在七岁的典型迁徙年龄时体型太小,连瞪羚都吓不倒,更何况是一只80磅重的成年雄性狒狒。(霍布斯异乎寻常地重达70磅。)大多数雄性没有这种不愉快所需的个性。此外,这是一种高风险策略,像霍布斯这样的个体很有可能在生命早期就遭受致残的伤害。
但还有一个原因,直到后来才变得明显。一天早上,当霍布斯专注于接下来要骚扰谁而没有注意到我们时,我设法将一支飞镖射进了他的臀部。几个月后,在实验室检查他的血样时,我们发现霍布斯体内的皮质醇水平在群体中是最高的,淋巴细胞数量极低,不到群体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当时坐在一旁的鲁托和肥仔,淋巴细胞数量分别是霍布斯的三倍和六倍。)这只年轻的狒狒自己也经历着巨大的应激反应,甚至比他正在骚扰的雌性还要大,当然也比我研究过的其他温顺的迁徙雄性要大。换句话说,每天12小时做一个混蛋并不轻松——这样的情况持续几个月很可能会对生理造成影响。
作为后记,霍布斯并没有保住他的位置。不到五个月,他就被推翻,在等级制度中降至第三位。在狒狒群中待了三年后,他消失在夕阳中,迁徙到未知的地方,去别的狒狒群碰碰运气。
所有这些都再次证实,迁徙对青少年来说是糟糕的——无论他们是选择缓慢被接受的普通书呆子,还是像霍布斯这样试图通过风暴征服群体的稀有动物。无论哪种方式,这都是一场磨难,年轻的动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令人惊奇的是,它们仍然继续这样做。迁徙可能解决了种群的近亲繁殖问题;但这对个体有什么好处呢?
青少年迁徙是许多社会性哺乳动物的特征,不限于灵长类动物,其机制可能有所不同。有时迁徙可能源于同性竞争——一个花哨的说法,指青少年被更强大的同性竞争者驱逐出群体。例如,在瞪羚和黑斑羚等物种中,你就会看到这种情况。核心社会群体由一只繁殖雄性、大量雌性及其后代组成。在任何特定时间点,这些雄性后代中有些可能正在进入青春期。但由于繁殖雄性通常不会长时间保持其不稳定的地位,他可能不是这些青春期雄性的父亲。他不会将它们视为成年的儿子,而是视为没有血缘关系的、正在成为繁殖竞争者的雄性。在它们第一次出现青春期迹象时,他会暴力地将它们赶出群体。
然而,在灵长类动物中,被迫分散几乎从未发生过。关键是,这些青少年选择离开——尽管这种举动看起来很疯狂。毕竟,它们生活在一个被家人和朋友包围的群体中。它们熟悉自己的地盘,知道一年中什么时候哪些树结果,当地的捕食者往往潜伏在哪里。然而,它们离开了这些舒适的家园,去忍受寄生虫、捕食者和孤独。为什么呢?为了生活在对待它们糟糕的陌生人中间。从个体动物的角度来看,这说不通。行为主义理论更正式地说明了这一点:动物,包括人类,倾向于做那些能获得奖励的事情,而不倾向于做那些会受到惩罚的事情。然而,它们却离开了舒适、有回报的世界,去远方遭受大量的打击。此外,动物往往讨厌新奇。把一只老鼠放进一个新笼子里,给它一种新的喂食模式,它就会表现出应激反应。然而,这里的年轻灵长类动物却为了新奇而冒着生命危险。旧大陆猴子已知一生中迁徙多达五次,或旅行近40英里到一个新的群体。为什么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个体都想这样做呢?
我不知道迁徙为何发生,但它显然根深蒂固。人类,部分因为他们的饮食适应性强,是地球上分布最广的哺乳动物,几乎栖息在这个星球的每一个荒凉角落。在我们的灵长类亲戚中,那些饮食最不挑剔的,如狒狒,也是地球上分布最广的动物之一(非洲狒狒的栖息地从沙漠到雨林,从山区到稀树草原)。不可避免地,总有人必须是第一个踏足这些新世界的人,一个以重大方式迁徙的个体。而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年轻的个体做到了这一点。
这种对风险和新奇的热爱似乎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所有灵长类物种的幼崽最有可能死于事故,做着愚蠢的事情,而它们的年长者则抱怨着他们早就告诉过它们。这也是为什么幼崽最有可能发现真正新颖非凡的事物,无论是在物理领域还是智力领域。当日本雪猴发现用海水洗食物这种新颖做法时,是一个幼崽这样做的,而她的玩伴们学会了这种适应;几乎没有年长的动物这样做。当达尔文关于进化的思想在19世纪中期席卷学术界时,正是新一代、崭露头角的科学家们以最大的热情拥抱了他的思想。
你不需要远找其他例子。想想近乎青少年的数学家们彻底改变了他们的领域,或者年轻的毕加索和斯特拉文斯基激发了二十世纪的文化。想想青少年不可避免地、不可抗拒地想开快车,或者尝试一些新的、即兴的、注定会摔断脖子的运动,或者兴奋地冲向他们的长辈们发动的任何愚蠢战争。想想无数的年轻人离开他们的家,也许是充满贫困或压迫的家,但仍然是他们的家,去寻找新世界。
灵长类动物(无论人类与否)进化成功的部分原因在于,我们是一群相当聪明的动物。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拇指以特别巧妙和有利的方式运作,而且我们对食物的适应性比大多数动物都强。但我们的灵长类本质不仅仅是抽象推理、灵巧的拇指和杂食性饮食。我们成功的另一个关键一定与这种自愿迁徙过程有关,这种在青春期左右产生“骚动”的灵长类遗产。自愿分散是如何进化的?个体基因、激素和神经递质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它们踏上征途?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确实知道,追随这种冲动是灵长类动物最深刻的行为之一。一只年轻的雄性狒狒痴迷地站在河边;一只年轻的雌性黑猩猩伸长脖子,试图瞥见隔壁山谷的黑猩猩。新动物,一大群!去他妈的逻辑和明智的行为,去他妈的传统和尊重长辈,去他妈的这个沉闷的小镇,去他妈的你胃里那团恐惧。好奇心、兴奋、冒险——对新奇的渴望是我们整个分类阶层共同拥有的,某种从根本上说有些古怪、鲁莽而又丰富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