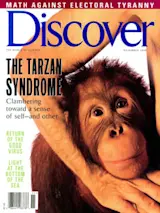动画电影《奇幻森林》中,一只名叫路易王的猩猩正是以这样一段切分音式的哀叹开场。路易王正在向他最近(尽管是强行)交上朋友的人类幼崽毛克利倾诉他对人类的羡慕之情。他解释道:“噢比嘟,我想变成你的样子/和你一样走路/也和你一样说话……”
在路易斯安那州西南的新伊比利亚研究中心,人类和猿类之间的关系则远没有那么融洽。某些青春期的黑猩猩不会对来访的人类高歌一曲,而是会满嘴含水,然后像水龙头一样用力地从门牙缝里喷向来访者的脸、胸膛或笔记本。伴随着水流而来的,还有大量嚼了一半的食物和唾沫。噢比嘟。这就是我们对你的看法。
“布兰迪,别这样。不,停下。快停下。卡拉,你也是。伙计们,别闹了。”这些命令来自该中心比较行为生物学实验室主任丹尼尔·波维内利,他穿着一件熨烫平整的白衬衫,站在黑猩猩铁链围栏的“唾液射程”之内。他和一小队饲养员从小将这七只猿类养大,但这些动物不理他,继续着它们热情的欢迎仪式。“大约四到五岁时,它们开始意识到自己可以远距离控制人们的行为,”波维内D利一边躲避着又一波水弹攻击,一边说道。
“我过去还能让它们停下来。现在我连吓唬它们都做不到了。”
很难想象波维内利能吓唬住谁。这位身材瘦长、头发淡黄的32岁年轻人,看起来自己也刚脱离青春期不久。他一边描述,或者更常见的是,一边模仿着他在十年猿类认知研究中观察到的行为。波维内利对行为本身不感兴趣,但他总是在寻找能揭示他研究对象内心世界的线索。他与新伊比利亚的黑猩猩进行了数十项实验,探索它们的大脑是如何表征世界的。在此过程中,他发现了人类与黑猩猩心智之间一些出乎意料甚至违背常识的差异。
波维内利的研究探讨了猿类如何——或者说是否——思考自己和其他生命。动物行为研究者长期以来一直怀疑,某些非人灵长类动物可能与人类共享一个对我们物种至关重要的特质,就像走路和说话一样:自我意识,即认识到自身存在的心智品质。正是自我意识,让像毛克利和路易王这样开化的个体能够理解“我”和“想要”这类抽象概念;在人类心灵中,自我意识与对他者心智生活的意识相结合,催生了同情、骄傲、尴尬、内疚、嫉妒和欺骗等抽象概念。
研究人员还曾假设,猿类像人类一样,也具备对他者心智生活某种程度的意识——它们对“像你一样”意味着什么有所了解。这一假设塑造了主流的灵长类智力模型,该模型认为,由自我和他者意识所驱动的复杂社会互动,推动了人类及其最近的系统发育亲属心智敏锐度的进化。这种社会性理论在灵长类认知研究领域已占据主导地位超过十年。
但波维内利的研究让他对这一模型提出了挑战,并提出了一个关于自我意识进化起源的全新激进理论——一个会让路易王感到自豪的理论。波维内利相信,自我意识起源的关键不在于备受赞誉的黑猩猩的社会行为,而在于独来独往、难以捉摸的猩猩的移动行为。他认为自我概念的萌芽并非源于群居生活的压力,而是源于穿越树梢的危险。1995年,波维内利和波多黎各大学医学院的体质人类学家约翰·坎特将这一构想阐述为他们称之为“攀爬假说”的理论。他们的论证精妙而深奥,融合了哲学、心理学、进化生物学和体质人类学的元素。然而,其主要论点建立在一个观察之上:猩猩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是“摇摆之王”。
四月一个闷热的星期六,波维内利将一面三英尺见方的镜子拖进黑猩猩的围栏,让他的猿类们有机会大约一年来第一次端详自己。反应各不相同。所有黑猩猩都对新来的“客人”感到兴奋,但有些似乎比其他同伴更明白这个新来者到底是谁。阿波罗发出呼叫声并做出佯攻动作,试图与镜中的自己玩耍。布兰迪则注视着镜子,重复着一系列不寻常的手势,显然被那个能预知她一举一动的同类模仿者迷住了。
而这群猩猩中的爱因斯坦——梅根,则在镜子前表演了一系列令人感到诡异而熟悉的行为。她张大嘴巴,从牙齿里剔出食物,拉下下眼睑检查眼睛上的一个斑点,还尝试做了一连串夸张的面部表情。然后,梅根摆出一个不太常见、在其他灵长类动物身上可能会被认为不雅的姿势,利用镜子仔细观察自己的私处。她用一根手指戳了戳,然后饶有兴致地闻了闻那根手指。
“这是典型的自我探索行为——把屁股紧贴在镜子上,这样它们就能看到,嗯,平时看不到的身体部位,”波维内利说。“它们只有在有镜子的时候才会这样做——摆出那种奇怪的姿势,摆弄生殖器。”
波维内利和其他研究人员认为,在镜子前的自我探索行为表明猿类认出了镜中的自己。他们推断,一个动物要认出自己,就必须有一种自我感——某种形式的自我意识,无论多么初级。因此,他们认为,镜中自我认知可以作为衡量非人类物种自我意识的一个指标。
这一推理思路的构建者是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的心理学家戈登·盖洛普,他在20世纪60年代末设计了一种衡量自我认知的标准方法,称为“标记测试”。测试中,趁黑猩猩被麻醉时,在其眉骨和对侧耳朵上涂上鲜红色的染料标记。这种染料无味无刺激,所以黑猩猩闻不到也感觉不到;没有镜子的帮助,它也看不到这些标记。当这只猿类醒来后,它有机会审视自己的新面貌。
“当它们在镜子里看到自己时,会大吃一惊,”盖洛普说。“然后它们会触摸被染色的区域,接着闻并看接触过标记的手指。这就是自我认知的基本测试。”盖洛普说,黑猩猩触摸标记然后检查手指是决定性的证据,因为它表明这些动物知道它们在镜子里看到的血红色斑点不是在某个不幸的同类身上,而是在它们自己毛茸茸的身体上。
自从盖洛普开创这一程序以来,研究人员已经对数十种动物进行了标记测试,包括猫、狗、大象和20多种猴子。到目前为止,唯一通过测试的只有大型猿类:黑猩猩、猩猩和一只大猩猩(著名的可可)。即使是这个精英群体的成员,自我认知也非一蹴而就。它们需要长时间接触镜子——从几分钟到几天不等,因个体而异——然后才开始表现出自我探索行为。
当黑猩猩第一次遇到自己的倒影时,它们的行为很像在面对另一只黑猩猩。阿波罗的嬉戏性爆发是这类社交反应的典型表现。然而,大多数黑猩猩很快就会放弃这种策略,像布兰迪一样,开始一边专注地看着镜中的自己,一边做一些简单、重复的动作,比如左右摇摆。波维内利认为,在这个阶段,这些动物可能正在理解自己的行为与镜中那个陌生者行为之间的联系;它们可能明白是自己在引起或控制对方的行为。当它们最终领悟到镜中影像与自己等同后,它们就会像梅根一样,将注意力转向自己的身体。
波维内利说,在某种意义上,这些黑猩猩可能正在重演某个猿-人祖先产生自我意识的进化戏剧。在这场戏剧中,其他物种从未超越第一幕。猴子,像许多动物一样,似乎明白镜子的工作原理;但它们无法解开自己倒影的谜团。例如,1978年,盖洛普将一对猕猴引入镜子,从那以后镜子就一直放在它们的笼子里。如果猴子在镜子里瞥见一个人的影像,它们会立刻转身直接面对那个人。但每只猴子仍然会像对待入侵的猕猴一样,威胁自己的镜像。
“这并不是说它们无法对镜像信息做出反应——当镜像适用于自身以外的物体时,它们显然能察觉到这种双重性,”盖洛普说。“但当它们看到自己时,就完全不知所措了。”
波维内利在青少年时期发现了盖洛普的研究,当时他正在为一次高中辩论复印《美国科学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他复印了那篇文章的最后一页,同时也复印了盖洛普一篇文章的第一页;他在家读了盖洛普论文的开头,然后回到图书馆读完了全文。
“我当时大概十五六岁吧,开始读这些关于黑猩猩的东西,”波维内利说。“那会儿猿类语言实验正火,我也被‘黑猩猩是毛茸茸的人类小孩’这种时代思潮吸引了。”
当时的观点将猴子、猿类和人类的认知能力置于一个连续体上,物种间的差异被描绘为程度问题而非种类问题。圈养的大猩猩可可在20世纪70年代初学习美国手语的成就,极大地强化了这一观点。而在20世纪80年代初,当年轻的波维内利开始大量阅读关于黑猩猩认知的文献时,灵长类研究人员开始记录猴子和猿类之间可与复杂人类行为相媲美的社会互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互动涉及明显的欺骗行为——例如,向同伴隐藏食物、为分散攻击者注意力而“狼来了”式地喊叫,以及隐瞒不正当的性行为。
这种背叛、小心眼和政治手腕似乎在我们最近的亲戚——黑猩猩的社会中达到了顶峰。盖洛普的自我认知研究为这些观察提供了概念框架。很容易想象,如果你一心想捉弄你的同伴,那么敏锐的自我意识——包括计划自己行动并预测其后果的能力——会派上大用场。此外,许多灵长类研究人员认为,黑猩猩社会群体中复杂的欺骗行为清楚地表明,这些动物不仅理解自己的动机和意图,也理解他人的。盖洛普曾推测,自我认知不仅意味着自我意识,还意味着对他者心理状态的洞察,即一种被称为“共情”的能力。
能否设计出像标记测试探测自我意识那样,来衡量灵长类动物共情能力的测试?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波维内利。它成为他在耶鲁大学的博士论文题目,也是他后来在新伊比利亚中心工作的主要焦点。管理该灵长类中心的西南路易斯安那大学在1991年聘请了这位新晋博士来建立一个研究项目;波维内利还成立了该大学的儿童研究中心,在那里他进行的实验与他的灵长类研究相平行——实际上是在比较猿类和儿童的智慧。通过比较这两个物种在认知任务上的表现,波维内利希望阐明区分人类与猩猩科动物的心智特征。
在人类中,自我意识和对他者的意识在一个心理学家称之为“心智理论”的认知特征中密不可分。这个高深的名词描述了这样一种倾向:我们倾向于假设其他人——也包括宠物,甚至有时是无生命的物体——和我们一样,也体验着欲望、意图和信念。我们利用关于这些主观体验的假设来解释行为(如,狗在门口叫是因为它想出去)、预测行为(如,他不会打电话,因为他生我的气了)以及判断行为(如,这次杀人是自卫,不是谋杀)。是的,人类也利用他们关于他人心智的理论来进行操纵和欺骗。
在幼儿中,这种将自我和他人视为有意识、有心智的主体的概念似乎是同步发展的。“我们认为,心智理论技能在孩子18到24个月大的时候开始出现,”波维内利说。“那时你会看到他们第一次理解欲望、指称和注意力。那也是孩子们第一次在镜子里认出自己的年龄。”
例如,能够通过标记测试的儿童,显然理解那些需要“他者”概念的非语言交流惯例。他们明白“指”是一种指称性手势——一种旨在无形地将两个或多个主体与空间中的一个物体联系起来的手势。他们也认识到,一个人的目光方向表明了其注意力的指向。
波维内利决定,人类认知发展的这些标志可以作为测试灵长类动物共情能力模型的典范。比如说,黑猩猩能否理解人类“指”和“凝视”背后的意图?他设计了一系列实验,得出了有趣的结果。在一个测试中,一只黑猩猩必须从两个倒扣的杯子中选择一个,以找到下面的食物。一位实验者通过指向其中一个杯子来提供线索。起初,猿类似乎能学会如何解读这个手势;经过几十次试验后,它们几乎每次都能选对杯子。但进一步的实验表明,黑猩猩并非根据手指的方向来获取线索,而是选择离实验者手最近的杯子。如果实验者将指向的手放在离两个杯子等距的位置,黑猩猩就会随机选择。它们似乎无法学会单独理解“指”的意义。
在另一项实验中,波维内利试图确定黑猩猩追踪他人目光的能力是否反映了它们对他人视角的有意识理解。这次,黑猩猩必须选择两个盒子中的哪一个藏有食物。一位实验者凝视着两个容器中间的一个点。一个木制隔板挡住了实验者的一个盒子,黑猩猩的任务是判断出他可能在凝视哪个盒子。孩子们知道要选择隔板前面的那个盒子。但黑猩猩,尽管它们清楚地注意到了实验者目光的方向,却倾向于选择隔板后面的盒子,其频率几乎和选择前面的盒子一样高。
“它们会跟随你的目光,但没有证据表明它们将你的视觉理解为一种注意力的心理状态,”波维内利说。另一项实验证实了这一点:如果让黑猩猩在两名实验者之间选择,它们会同样频繁地向一个头上戴着水桶的人——一个不仅看起来很傻而且显然看不见它们恳求的人——乞讨食物,就像它们会向一个肩膀上扛着水桶的人乞讨一样。
为什么一种在实验室里如此擅长学习的动物,在这些实验中却对提示毫无反应?波维内利承认探测另一物种心智的困难。在这种非传统的实验设计中,究竟是谁在测试谁并不总是很清楚。但到目前为止,他的实验结果表明,黑猩猩并不理解他人的意图或观点——尽管从拟人化的角度解读它们的社会行为可能会得出相反的结论。
与盖洛普关于猿类共情的看法相反,黑猩猩可能生活在一个包含主观“我”的概念,但不包含“你”的认知领域。波维内利说,关于黑猩猩欺骗的轶事记载,可以不用援引共情能力来解释——并且鉴于他的研究,也应该这样解释。他补充说,黑猩猩天生就对社会情境和线索极其敏感;它们是操纵行为的专家——就像在围栏里朝你吐口水一样。
但是,虽然欺骗和操纵显示出一种强大的、专门化的智能,但它们未必意味着拥有心智理论。一只黑猩猩可以通过看着人类躲避水弹而获得廉价的快感,却不必知道(或关心)人类为什么会那样反应——不必理解穿着被口水溅湿的衬衫、拿着一团湿纸浆当记事本进行采访的尴尬、烦恼和不适。在波维内利看来,黑猩猩可能是最纯粹意义上的自我中心。
波维内利对自我中心黑猩猩的描绘,重新提出了灵长类智力如何进化的问题。如果他的数据准确地反映了猿类的感知能力——他并未排除这种可能性不存在——那么猿类与人类之间存在着一道深刻的认知鸿沟。“从进化的角度看,自我概念和普遍的心智理论之间可能存在脱节,”他说。“换句话说,在理解他人之前,先有了对自我的理解。”
“也许黑猩猩对自己心智的理论相当不错,即它们能思考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什么上,想要什么,诸如此类。但也许它们根本不理解他人的这种品质。而也许人类,由于某种原因,将对自我和对他人的理解融合在了一起。”
波维内利的发现并没有完全驳斥社会性理论;相反,它们使其显得不那么相关。很容易想象,应对灵长类社会等级制度的压力——例如,躲避占主导地位雄性的愤怒——可能促进了某些灵长类动物智力的某些方面。然而,波维内利指出,社会压力本身并没有任何因素会驱动自我意识的萌芽。毕竟,猴子有相当复杂的社会生活,但它们在标记测试中失败了。另一方面,猩猩是灵长类中最孤独的物种之一,却能轻松通过测试。
“从来没有人解释过,为什么社会性会与自我概念的这种系统发育断裂有任何关系,”波维内利说。事实上,对于原始的自我感是如何在大型猿类和人类的共同祖先中进化而来的,根本没有任何解释——直到波维内利进入了印尼的丛林。
1989年和1991年,波维内利与约翰·坎特在苏门答腊北部的雨林中度过了一个野外考察季,记录树栖灵长类动物的活动。坎特当时正在研究猴子、长臂猿和猩猩的运动方式,为其关于灵长类肌肉骨骼系统进化的研究服务。尽管这类研究并非波维内利本人的兴趣领域,但他渴望获得野外经验;特别是,他期待观察在圈养环境中稀少的猩猩。
灵长类动物学界的说法是,这些体型巨大、独来独往、行动缓慢的猿类,即使不比它们爱好交际的系统发育表亲——黑猩猩更聪明,也至少同样聪明。然而,波维内利开始思考,如果猩猩的社会生活不是其聪慧的原因,那么是什么力量在起作用呢?冒着蝎子、水蛭和温热的民丹啤酒的威胁,他和坎特想出了一种方法,不仅解释了猩猩的智力,也解释了黑猩猩和人类的自我意识。“攀爬假说”就此诞生。
这个理论笨拙的名字来源于猩猩运动方式中一种同样笨拙的独特活动。根据坎特的定义,攀爬是猩猩用来在树与树之间移动的一种缓慢、审慎的导航方式。坎特坚称,攀爬与奔跑、跳跃和摆荡等其他灵长类动物典型的、更具自动化和重复性的运动方式截然不同。根据他的观察,攀爬是猩猩在树梢间穿行时偏爱的方法。
“当一只猩猩在树上移动时,”坎特说,“听起来就像一场小龙卷风穿过树冠——树枝来回摇摆,相互摩擦,有些还会折断。如果你仔细观察,常常会看到你以为是动物停下来在做决定的情景。它开始做某件事,停下,暂停,然后——不管它是否像困惑的人类一样环顾四周——它会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在树梢间穿行时,有很多事情会让猩猩停下来思考。成年雄性猩猩的体重可达180磅以上;树干和树枝在它们的重压下会大幅弯曲,坠落可能是致命的。尽管存在这些风险,苏门答腊猩猩却极少在地面上行走。它们像行动迟缓的杂技演员一样从一棵树爬到另一棵树,利用其髋关节和肩关节超凡的灵活性将体重分散到多个支撑点上。看到一只猩猩一手抓着木质藤蔓,另一只手抓着树枝,一只脚抵着树干,而另一只脚伸向附近的树枝,这种情况并不少见。通过来回移动体重,猩猩可以随心所欲地弯曲树木,使其摇向邻近的树,从而帮助通行。
所有这些技巧都没有逃过波维内利的眼睛。在熟悉猩猩运动方式的同时,他也在钻研让·皮亚杰的著作。这位瑞士心理学家曾将儿童自我概念的萌芽描述为源于感觉运动系统的“不足”或他所说的“失败”。在皮亚杰的理论中,这个系统支配着18个月左右或更小婴儿的重复性、看似本能的动作。皮亚杰认为,在此年龄之前,儿童没有意识到是自己在引发自己的行为。但随着儿童心智生活变得更加复杂,这些行为也变得更加雄心勃勃,有些行为不可避免地无法达到预期的结果。面对这些失败,儿童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和意图——简而言之,他们变得有自我意识。大约在两岁左右,他们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学会控制和计划自己行为的结果。
“当我们到了野外,开始讨论攀爬时,”波维内利说,“我突然意识到,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就是同一回事。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攀爬就是感觉运动系统的失败。”
在波维内利和坎特的假说中,攀爬代表了人类、黑猩猩、猩猩和大猩猩的共同祖先的一种具有自我意识的移动方式。像猩猩一样,这个祖先可能生活在树上,体重至少是最大树栖猴子的三倍。由感觉运动系统编写的攀爬程序——以猴子运动方式中有限的重复性动作为例——很可能会让这个祖先失败,就像它们会让今天的猩猩失败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失败意味着从30英尺或更高的地方直通森林地面。波维内利和坎特说,从几十英尺的高度脸朝下摔上几百万年,你迟早会进化出弄清楚哪里出了错的能力。而弄清楚这一点就意味着将自我构想为一个因果主体:理解树枝折断和随后的坠落行为是由自己笨拙施展的体重造成的。
这两位合著者写道,一旦这种个人认同感和主体感出现,“对那个客体(自我)的理解就可以几乎无限地被阐述和扩展。”
正是这种对自我作为因果主体的萌芽意识,波维内利在他黑猩猩镜前滑稽动作中看到了。镜子让猿类有机会观察到自己行为的直接后果:“那是我造成的。”当一只猿类明白它造成了镜中自己的所有一切时,自我认知就发生了:“我就是那个。”
对猴子来说,似乎没有“我”的存在。波维内利和坎特断言,对于猴子的祖先来说,树与树之间的穿行从未危险到需要进化出一种专门的认知应对机制。由于这些祖先体重较轻,坠落可能不常见,也并非特别有害。
“猴子跳到树枝末端,当树枝在它们身下弯曲时,它们就紧紧抓住,”波维内利说。“这是将环境的反应融入自己行为,与主动利用自己行为来计划如何改变环境以解决特定问题之间的区别。要成为一只猴子,你不需要有自我感。”
然而,在阐述了猴子和猿类之间的这种区别之后,波维内利强调,他对猿类自我意识的主张仍然相当谨慎。
“这绝不是说,‘天哪,我是一只猩猩。我是一只猩猩,天哪,我出生17年了,我还在这里,还在树上爬。我的命运会是怎样?’”波维内利说。“我们只是认为,多种因素的结合推动了一种将自我客体化能力的进化——他说,这是走向自我发现之路的第一步。”
撇开限定条件不谈,波维内利和坎特很清楚,他们自己也正处在一个相当脆弱的“枝头”上。“攀爬假说”是波维内利迄今为止最具推测性的研究,并且已经引来了其他裸猿(指人类)不少的嘲笑。
“我们几乎不知道自我意识是什么,更不用说它是如何产生的了,”亚特兰大耶基斯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的动物行为学家弗兰斯·德瓦尔说。“我个人并不信服这个论点。”德瓦尔认为,几种南美蜘蛛猴的攀爬行为可能与猩猩的攀爬一样复杂和经过深思熟虑。“我不认为猩猩做的任何事情是这些猴子做不到的。”德瓦尔也反对如此狭隘地定义自我意识。“我认为自我意识是一个可能从鱼类延续到人类的连续体,”他说。“镜子测试在某种程度上触及了它的一个更高层次。但我无法想象这是一个全有或全无的现象。”
“对于那些对攀爬假说极度怀疑的人,我是这样说的,”波维内利说。“我说,好吧,没问题。但这里有一个真正的问题。镜中自我认知仅限于大型猿类-人类谱系。目前还没有其他任何提案能解释为什么会这样。”
他补充说,但这并不意味着攀爬假说就是对的。
事实上,就连猿类镜中自我认知的说法近来也受到了抨击。哈佛大学的认知神经科学家马克·豪泽使用了一种改良版的标记测试,在狨猴身上引发了异常行为,他说这可以被视为自我认知的迹象。“我想对实际情况保持一种不可知论的态度,”豪泽说。但他表示,他的观察对“镜中自我认知是自我意识的可靠标志”这一长期存在的观念提出了质疑。
波维内利说,他和盖洛普曾试图在狨猴身上复制豪泽的研究,但至今没有成功。但他第一个承认,无论是在自我认知研究还是灵长类动物的自我概念上,他都没有最终的定论。
“这个问题看起来很简单,你知道吗?一面镜子,一只猴子……一面镜子,一只黑猩猩……但是,要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还需要三十年的研究工作。”
“任何认为自己对此有定论的人——”波维内利停顿了一下,动用了自己的心智理论——“我认为他们简直是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