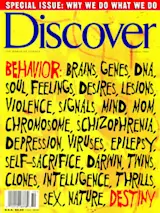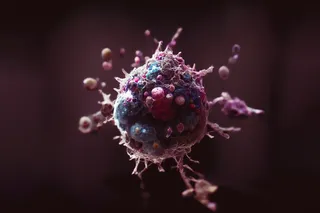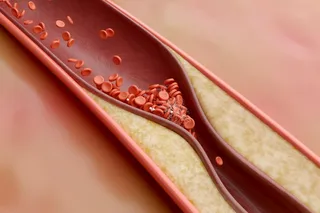我最先注意到卡尔·比克斯比(Carl Bixby)那双40岁的双手,这对我来说有些奇怪,因为我通常会立刻被病人眼中的情绪所吸引:抑郁症的向下凝视、躁狂症的狂乱瞥视、精神病的高度警觉。但他的双手,从他红色法兰绒衬衫袖子里伸出来,吸引了我的注意。它们对于他本人来说太大了,尽管他本人也很高大。厚厚的胼胝体像猫垫一样突出,遍布着缝隙,边缘沾满了油污。新鲜的划痕上沾着干涸的血迹,许多旧伤疤也留下了痕迹。我想,它们是一双强健的手,磨损得很好,而不是耗损殆尽。我想,如果你溺水了,你会祈祷这双手来抓住你。它们毫无脆弱之处。你可以用力抓住。就在我确信自己要仔细观察他的脸时,他却再次将我的注意力拉回到他那双了不起的手上,他拍了两下膝盖,预示着他即将要说的话。
他说:“我完了。”他的双手举到头顶。“这里。我的大脑。里面有些东西坏了。”他粗厚的手指梳理着他那浓密但修剪整齐的红褐色胡须。他突然看起来悲痛欲绝。
从来没有哪个病人曾直接抱怨过自己的大脑。无论大脑化学物质或解剖结构紊乱对产生精神症状有什么作用,通常对生病身体部位的看法——就像“我的腿疼!”一样——普遍不存在。一个人可能会觉得自己受伤了,世界可能会显得陌生、古怪或充满敌意,但大脑,在它自身的病理学掩盖下,几乎总是逃脱了比模糊怀疑更进一步的评判。
我第一次直视他的眼睛。当我们对视时,房间似乎在我们周围收紧——不,是他在瞪着我,他的目光锁住我的,不肯放开。我注意到他几乎不眨眼。他向前倾身坐在椅子上,仿佛想看我有什么话要说。
“你说你大脑坏了?”我问道。
“我猜是齿轮卡住了。”他用一根手指指了指自己的头顶,然后让双手放松地搭在膝盖上。“卡住了。肯定是,因为我现在工作跟不上了。老板就要解雇我了。”
“你做什么工作的?”
“我在铁路公司工作。”他说,仍然锁定我的目光。他一次都没移开视线。“我是个机械师。我负责照顾火车——引擎有什么问题,我都会修。当然,预防胜于治疗。我把那些宝贝保养得像赛车一样,擦油上蜡。”
“这有什么问题?你老板为什么要解雇你?我心里已经有了怀疑。评估刚开始五分钟,我就被卡尔那股强烈的目光压得喘不过气来。几乎让我感到幽闭恐惧。如果他一整天都待在这里,可能会让人难以忍受。”
“我干了十年,做得很好。”他告诉我。“比好还好。我是公司里排名前十的机械师之一。然后,十一个月前——大概是去年十一月,或者十二月初——一切都开始改变了。”
卡尔解释说,这些变化让他感觉很棒。他发现自己越来越被他负责的火车所吸引。与引擎的吸引力相比,他的社交生活和爱好都显得苍白无力。他可以愉快地工作12或14个小时,有时甚至通宵,精心调整一个气缸或追踪一个细微振动的来源。
起初,他的主管对他惊人的热情和能力印象深刻。他把更棘手的问题交给他,他从没感到困惑或不知所措。卡尔更加努力地工作,不计代价。他的女朋友不止一次地怀疑他是不是爱上了别人。
“没有别的女人。”卡尔向我发誓。“我爱上了那些车。尤其是老款的。我可以听一辆车在轨道上行驶的声音,就知道哪个气缸有问题。我能感觉到。你明白吗?”
我明白了——并且告诉他了。我感觉我整个人都沉浸在句子是否恰当的思考中。有时,我对写作的热情,对文字节奏的热爱,让我放弃了一切,但我也因此而快乐地忙碌到深夜。
但卡尔的激情,我看得出,已经开始越界成为一种痴迷。“我特意找了个房间,就在火车进站前的换轨处上面。”他继续说道。“它们在那儿减速换轨,然后再次加速。所以我能听到刹车声、轮子声、变速箱的声音——总之就是一切——我当初搬到那里就是因为这个。如果有什么不对劲,我可以看看外面,记下火车编号。我告诉你,即使在睡觉时,我也在关注那些火车。”
主管注意到卡尔要修理的火车列表越来越长。他告诉卡尔,引擎并不真的需要修得完美。齿轮可以稍微松动一点。气缸不必以音乐般的精确度运转。即使是偶尔吱吱作响的刹车也是可以接受的。他不想让卡尔花三天时间去完善一辆引擎,而有几十辆引擎需要维修。
“他说那点振动没关系。”卡尔向我抱怨。“嗯,对他来说可能没关系,但对我来说,关系太大了。对他来说,也许当个机械师只是份工作。对我来说,这更像是一种宗教。”他瘫坐在座位上。“但我也能理解他的想法。他要操心整条铁路,而不仅仅是一辆火车。所以我才来这里。我觉得我有点失控了。我想保住我的工作。也想留住我的女朋友。她们是我仅有的。”
我曾一度想沉溺于卡尔生活中的诗意——一个被引擎迷住的男人,几乎融入了他的技艺。他的爱中存在非理性,但也充满了巨大的奉献精神和不可否认的美。在一个倾向于贬低劳动价值、忽视技艺重要性的电脑时代,我内心的一部分想鼓励卡尔不惜一切代价追求他的热爱。我选择精神病学并非为了劝人放弃激情。也许他可以在铁路博物馆工作,而不是在通勤铁路。我设想他成为东方快车上的常驻工程师。一个人。一辆火车。完美的结合。
当我认识到卡尔可能生病了,真的“坏了”,这让我有些失望。我曾经治疗过另一个男人,一位诗人,他好几个月都在为一个诗句的完美而卡壳,结果却发现他患有癫痫。引起癫痫的电风暴可能发生在任何大脑区域,并可能导致各种各样的症状,包括戏剧性的肌肉痉挛和抽搐,也就是全面的强直-阵挛发作。但显然有些癫痫患者,比如那位诗人——我猜卡尔也是——只表现出性格上的改变。
轻微的癫痫发作会导致对那些原本不会引起如此关注的任务产生近乎宗教般的奉献。当癫痫发作发生在大脑的颞叶时,尤其如此。颞叶是两块楔形的组织,夹在额叶和枕叶之间,大约在颅骨中线的位置。颞叶包含边缘系统的一部分,而边缘系统是包含大脑最重要的情感回路的一系列大脑结构。
尽管研究结果存在争议,但研究人员指出,一些颞叶癫痫患者具有共同的特征,包括对哲学问题的过度关注、倾向于过度写作、极度的宗教情感、性欲改变(通常是减退),以及一种令人讨厌的、固执的、强迫性的特质,称为粘滞性。
精神病学家也曾怀疑,一种无法检测到的癫痫发作活动水平是否是躁狂症的核心,躁狂症是一种以看似无穷的精力、对睡眠和食物的漠不关心、膨大的自我形象,有时还有欣快感为特征的精神疾病。除了天然存在的锂盐——其作用机制未知——以外,如丙戊酸和卡马西平这样的抗惊厥药物是主要的治疗方法。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患有癫痫,描述了他发作前感受到的情感:“你们这些健康的人,无法想象我们癫痫病人在发作前一秒所感受到的幸福……。我不知道这种幸福是持续几秒、几小时还是几个月,但请相信我,我不会用它来交换生活中带来的任何快乐。”
其他人则报告说听到了美妙的音乐,重温了童年记忆,或者看到了上帝的光辉幻象。
那么,癫痫本身总是疾病吗?如果我们能找出每一个病例并加以治疗,我们是否会失去哲学家、烈士和伟大艺术家为社会做出的贡献?是否在某些情况下,大脑中异常的电放电会带来收益?我会劝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或梵高这样的艺术家追求更全面、不那么专注的追求吗?
我对颞叶癫痫可能是导致卡尔对工作产生如此强烈迷恋的原因的怀疑,在他报告说大约一年前从火车平台上摔下来晕过去之后,变得更加强烈。头部受伤,导致脑组织损伤,会触发癫痫失控的电回路。
我见到了卡尔和他女朋友。她是一位三十多岁的裁缝助理。她用双手捧着卡尔的一只手,几乎和他一样认真地听我解释进行脑电图(EEG)检查的益处,脑电图是一种大脑活动记录。脑电图使用一系列敏感的粘贴电极,通常贴在头皮或鼻腔内,以显示异常的电放电。“如果他有这个——这个癫痫问题——并且接受治疗,他还会对火车失去所有兴趣吗?”她问道。“他还会是修火车最好的吗?”她转向卡尔。“因为,卡尔,如果他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会变成那样,你就不应该再去想那个测试了,我们现在就走。我们会想别的办法的。听到了吗?”
看到她对我病人如此深情,愿意将自己置于我病人(如果我无法让他恢复如初)之后,我的喉咙哽咽了。我想,这种奉献背后的神经回路是什么?用合适的设备,我们会在相爱的人的脑电图上看到微小的癫痫波吗?
“从我所了解的情况来看,卡尔的问题始于他的头部受伤。”我停顿了一下。这个词“问题”似乎不太合适。“如果癫痫发作是从那时开始的,那么正确的药物可能会让他恢复正常,而不是不如正常。”我举起自己的双手。“我无法确定如果他服用药物会发生什么。”我承认。“如果他觉得没用,他随时可以以后决定不吃。”
“我们自己来解决。”卡尔说。“没必要不看,就怕找到什么。”他的目光锁住我。“如果我的齿轮坏了,我想把它修好,而且要彻底修好。”
“即使这意味着你会失去一些对工作的热情?”我追问道。
“你可以让一辆火车在轨道上飞驰,但如果它没有刹车,那也没什么用。我现在不能让自己停下来。那不对。我想保住我的工作,也想留住我的女朋友。”
卡尔接受了脑电图检查。正如我所怀疑的那样,他的脑电图显示他一侧颞叶有异常放电。
卡尔似乎对结果感到释然。他抬起头,好像要检查自己的大脑。
“我们怎么解决?”
我告诉他,我会建议他开始服用卡马西平,这是一种抗惊厥药物。
“嗯……。”他沉思着。他十指交叉,捏断了他那巨大的指关节。“最好给它调整一下。”
卡马西平在血液中的浓度需要达到一定范围才能起作用。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们调整了卡尔的剂量,直到他的水平达到治疗范围。不到四周,他的主管就评论说,卡尔又开始跟上维修量了。六周内,工作完成了——而且没有过度。
“我得谢谢你。”卡尔告诉我。我注意到和他坐在同一个房间里感觉更轻松了。他看着我,而不是透过我。“我回到正轨了。”他眨了眨眼说。
回到正轨。他大脑的癫痫发作消失了。这是真的。但我认为,卡尔身上还有另一部分,他自己诊断出自己的生活又恢复了正常,恢复了平衡。另一个病人可能会用尽全力反抗我的药物。我将成为他最大热情的敌人。我想,灵魂中有什么指南针,能告诉一个人他的生活是他想要的,他正以正确的速度、正确的方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