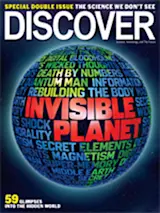1758年,瑞典分类学家卡尔·林奈将我们物种命名为“智人”(Homo sapiens),意为“明智的人”。我们是否真的名副其实,这是一个公开争论的问题。如果林奈想站得更稳,他本可以称我们为“巨脑人”(Homo megalencephalus),意为“拥有巨大脑的人”。
无论我们如何明智地使用大脑,不可否认的是,它确实非同寻常地大。一般人脑的平均重量约为三磅,即1350克。我们最近的近亲黑猩猩,大脑重量不到我们的三分之一——仅384克。如果比较大脑与身体的相对大小,我们的大脑则更为惊人。
通常来说,体型较大的哺乳动物往往也拥有较大的大脑。如果您知道哺乳动物的体重,就可以相当准确地猜测出它的大脑有多大。据科学家所知,这条规则源于身体越大,就需要越多的神经元来控制它。但这条大脑与身体的比例规则并非完美。有些物种稍有偏离。有些则偏离很多。我们人类是特别杰出的规则打破者。如果我们是普通的哺乳动物,我们的大脑只有现在实际大小的六分之一。
竞争性的理论试图解释大脑的价值。心理学家、牛津大学的罗宾·邓巴(Robin Dunbar)倡导的一种观点是,复杂的社会生活需要大脑(pdf)。一只大脑相对较大的狒狒可以建立十几个联盟,同时对几个对手怀恨在心。人类则维持着更多、更复杂的关系。
管理社交网络可以带来显著的好处:当发生冲突时,有朋友在背后支持是很重要的。但要时刻关注自己的社交生活需要付出努力。邓巴和他的同事发现,当人们必须思考他人的想法时,回答问题的速度会更慢。一个问题越需要“读心术”,它激活大脑的程度就越高。
来自西班牙巴塞罗那陆地生态与应用林业研究中心(Center for Terrestrial Ecology and Applied Forestries)的丹尼尔·索尔(Daniel Sol)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研究了动物引入新栖息地的情况。通过比较成功的和不成功的入侵者,他发现,在鸟类和哺乳动物中,大脑较大的物种比大脑较小的物种更有可能成功(pdf)。这项研究表明,大脑较大的物种更擅长解决问题,这转化为更高的生存机会。
邓巴和索尔都有可能是部分正确的。但无论争论如何解决,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仍然存在:如果大脑很大如此有用,为什么它们相对罕见?答案是,自然界中没有免费的午餐——而就大脑而言,代价可能是巨大的。事实上,科学家们正在发现,许多人类生物学已经重新组织自身以应对超大脑的负担。
1995年,当时在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莱斯利·艾埃洛(Leslie Aiello)和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Liverpool John Moores University)的彼得·惠勒(Peter Wheeler)提出了大脑稀少性最初的可能原因。他们指出,神经元食欲非常旺盛。它们需要大量能量来产生电压脉冲和释放神经递质。它们从氧气和食物(主要是葡萄糖)中获取能量。一个三磅重的人脑消耗的卡路里是三磅肌肉的20倍。
我们一刻也不能忽视这种需求。几分钟缺氧可能不会对我们的肌肉造成太多损害,但会不可逆地损害大脑。大脑还需要持续的食物供应。您每天摄入的卡路里中有25%都用于为大脑供能。对于刚出生的婴儿,其身体小巧,大脑相对较大且生长迅速,这一比例会跃升至87%。
600多万年前,我们祖先的大脑并没有施加如此残酷的需求。我们的祖先身高只相当于一只黑猩猩,大脑大小也与黑猩猩相似。在接下来的400万年里,我们祖先的大脑一直很小。然后,大约在180万年前,
进化了。我们属的第一个与我们相似的成员,直立人(H. erectus)身高与现代人相当,大脑重量约为900克。五十万年前,我们祖先的大脑开始再次增长;20万年前,它们终于达到了与今天智人大脑大致相同的重量。
艾埃洛和惠勒指出,大脑尺寸的这种戏剧性增加似乎需要代谢的戏剧性增加——就像给房子增加空调系统会增加电费一样。然而,按比例计算,人类燃烧的卡路里与其它灵长类动物相同。艾埃洛和惠勒认为,不知何故,我们的祖先找到了平衡能源预算的方法。随着大脑的扩展,他们可能缩小了其他器官。
科学家们比较了人类和其他灵长类动物的器官大小。相对而言,我们肝脏的大小与狒狒的肝脏差不多。我们的心脏与大猩猩的心脏相当。但我们的肠道却萎缩了。它们在我们这个体型的灵长类动物中,仅占预期大小的60%。肠道细胞也需要大量能量,因为它们神经支配丰富。失去如此大一部分肠道,可以让我们祖先弥补大脑额外能量需求的很大一部分。
艾埃洛和惠勒将他们的想法命名为“昂贵组织假说”(expensive tissue hypothesis)。为了验证它,他们比较了一系列灵长类物种的大脑和肠道大小(pdf)。他们发现,一个灵长类动物的大脑相对于该物种的整体体型越大,肠道就越小。这种持续的权衡表明,缩减我们的肠道对于大脑的超大化至关重要。
然后,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的生物人类学家威廉·伦纳德(William Leonard)对昂贵组织假说进行了新的检验。伦纳德没有将大脑和肠道大小在不同灵长类物种之间进行关联,而是决定对所有哺乳动物进行研究。他发现,除了灵长类动物之外,大脑大小和肠道大小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关联。
这表明,灵长类动物群体内部的肠道萎缩现象可能过于微妙,无法完全解释我们大脑的增长。还必须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伦纳德说,这个因素就是饮食。在研究了灵长类物种的饮食并统计了摄入食物的数量和质量后,伦纳德发现在大脑更发达的物种中,饮食从低能量的树皮和树叶转向了高能量的种子、块茎和肉类。随着大脑与身体比例的增加,可以推测,更密集的卡路里提供了所需的额外燃料。
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的进化生物学家格雷格·雷(Greg Wray)正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寻找大脑之谜:人类基因组。一种被称为SLC2A1的基因,与为大脑供能有关,它构建了一种用于将葡萄糖从血管转运到细胞中的蛋白质。这对大脑的健康至关重要。减少大脑中转运蛋白数量的突变会导致癫痫和学习障碍等疾病。如果SLC2A1基因的一个副本完全失效,后果是灾难性的:大脑的发育只达到正常大小的一部分。如果两个基因副本都无效,胎儿会直接死亡。
雷和他的同事比较了人类和其他动物的SLC2A1。他们发现,我们的祖先在这个基因中获得了异常多的突变。这种突变累积的最佳解释是,SLC2A1在我们自己的谱系中经历了自然选择,而新的突变提高了我们的繁殖成功率。有趣的是,杜克大学的团队发现,这些突变并没有改变葡萄糖转运体的形状。相反,它们改变了控制SLC2A1基因开启和关闭的DNA片段。
雷推测,这些突变改变了人脑中葡萄糖转运体的总数。为了检验他的理论,他查看了人类脑组织切片。为了制造葡萄糖转运体,细胞必须首先复制SLC2A1基因作为模板。雷发现,在人脑中,SLC2A1的拷贝数是黑猩猩大脑的2.5到3倍,这表明葡萄糖转运体的数量也更多。
然后他查看了将糖分输送到肌肉的葡萄糖转运体。这些肌肉转运体的基因,称为SLC2A4,在人类中也经历了自然选择,但方向相反。我们肌肉中的葡萄糖转运体比黑猩猩的肌肉少。雷的结果支持这样的观点:我们的祖先进化出了额外的分子泵,将糖分输送到大脑,同时通过减少肌肉的转运体来“饿死”肌肉。
成为“巨脑人”(Homo megalencephalus)的过程绝非简单。进化不仅要缩小我们的肠道并改变我们的饮食。它还必须进行基因工程。
卡尔·齐默(Carl Zimmer)是一位屡获殊荣的生物学作家,也是《纠缠的银行:进化导论》(The Tangled Bank: An Introduction to Evolution)等书籍的作者。他的博客“The Loom”运行在blogs.discover magazine.com/lo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