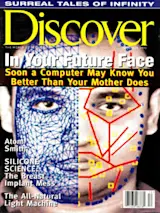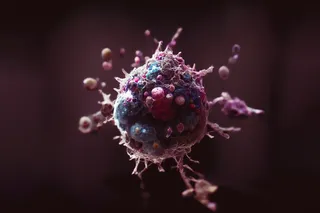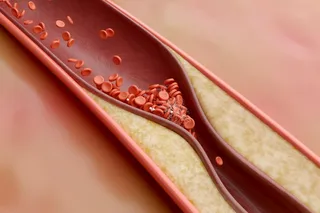三年前,当帕梅拉·约翰逊(Pamela Johnson)的案件在休斯顿开庭审理时,这位 46 岁的女性刚刚取出了她的第三套硅胶乳房植入物。第一套从 1976 年持续到 1989 年,当时她向整形外科医生抱怨说她的乳房变硬了,原因显然是植入物周围形成了疤痕组织。外科医生进行了一种名为“闭合式包膜切开术”的治疗,也就是说,他挤压了约翰逊的乳房,希望通过这种手法能打破疤痕组织。然而,这却导致她的左侧植入物破裂。面对后来新闻报道中描述的“一塌糊涂”的状况,他进行了一次部分乳房切除术,并用第二对植入物替换了旧的。约翰逊觉得新的植入物在美学上不尽人意,于是咨询了另一位外科医生,该医生于 1989 年 11 月为她植入了第三对。尽管她抱怨有慢性疲劳、盗汗、脱发和头痛,约翰逊还是将它们保留到了 1992 年 6 月。在医生们暗示她的病痛是由她体内的硅胶引起后,约翰逊取出了第三对植入物,并起诉了医疗工程公司(Medical Engineering Corporation),该公司是百时美施贵宝(Bristol-Myers Squibb)的子公司,生产了她的前两套植入物。她的律师是约翰·奥奎因(John O'Quinn),休斯顿一位传奇的原告律师。当时,奥奎因手上大约有 800 起植入物案件正在处理中。
由于审判的关键在于与硅胶相关的诊断是否具有科学合法性,奥奎因聘请了包括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中心的病理学家尼尔·科索夫斯基(Nir Kossovsky)在内的几位专家证人,来作证说明硅胶可能对人体免疫系统造成的严重破坏。陪审员后来说,科索夫斯基的证词在他们的裁决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们判给约翰逊 2500 万美元,其中 2000 万美元为惩罚性赔偿金。约翰逊案是针对植入物制造商的第二起数百万美元的和解案。第三起发生在 1994 年:针对 3M 公司的 4000 万美元判决。在这三起案件中,科索夫斯基关于硅胶有害影响的专家证词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1994 年春,以道康宁公司(Dow Corning Corporation)为首的一批美国植入物制造商同意支付 42 亿美元,赔偿给那些认为自己的植入物对她们造成了伤害的女性。然而,即使是这笔天文数字的和解金,很快也显得可能不够,其中 10 亿美元将归律师所有,其余部分由 44 万名原告分摊。还有数千名原告选择了退出和解,希望独立对抗植入物制造商。去年五月,道康宁公司试图通过申请破产来阻止财务上的大出血。1995 年 9 月,该协议破裂,关于新和解方案的谈判重新开始。
在整个争议过程中,科索夫斯基在法庭上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他曾担任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顾问委员会的顾问,该委员会 1992 年的听证会促成了暂停使用植入物的决定,他对硅胶免疫学的观点不仅被本杂志引用,还被《科学》、《纽约时报》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等刊物引用。奥奎因的律师事务所称他为“硅胶生物特性领域的世界高级权威”。对于一位在风湿病学或免疫学——这两个与争议核心相关的科学学科——均未获得专业认证的病理学家来说,这是一份令人印象深刻的资历。
事实上,科索夫斯基作为专家证人的名声,主要建立在一个仍然缺乏科学证据支持的理论之上,以及一种科索夫斯基声称可以检测硅胶诱发疾病的测试方法上,尽管最近的研究发现甚至没有证据表明这种疾病存在。来自哈佛大学、梅奥诊所及其他地方的多项流行病学研究证据表明,尽管植入物中的硅胶可能会在体内引起局部问题,但没有证据表明它会造成全身性的伤害。一些最权威的科学机构——包括美国医学会、美国整形与重建外科学会、FDA 通用与整形外科设备顾问小组,以及加拿大、英国和法国政府委托成立的委员会——都同意这一评估。虽然现在完全否定硅胶植入物与疾病之间的联系可能为时过早,但用英国医疗器械局的话来说,“证据的天平显然正向着这样的结论倾斜”。
科索夫斯基在法庭上的主张与科学证据之间的鸿沟表明,主流科学与法律体系已经分道扬镳,这并不罕见。好的科学需要时间才能得出可靠的判断,而法院为了实现实际的正义,则渴望迅速确定有罪或无罪。针对植入物制造商的案件之所以胜诉,并非基于科学证据的力度,而是基于原告的痛苦、制造商对明确证明其产品安全的明显冷漠,以及原告方专家愿意以在法庭外的科学界看来非常不科学的确定性来陈述他们的观点。科索夫斯基不是唯一一个卷入硅胶争议法律层面的研究人员,但他是最引人注目和最有影响力的之一;此外,他已成为一个专业知识存疑的专家证人的典型。
根据科索夫斯基的说法,他与硅胶的接触始于 1981 年,当时他作为芝加哥大学的一名二年级医学生,阅读了道康宁公司一份长达二十四卷的关于硅胶的报告。这种材料被认为是植入人体的理想设备材料,因为它似乎是化学惰性的——不会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因此研究人员得出结论,即使在活体生物中埋藏数十年,它也不会造成太大伤害。正如科索夫斯基所说,道康宁报告的执行摘要提出了这一论点,但其余的二十四卷中包含了一些证据,表明硅胶在患者和动物体内引起了炎症甚至淋巴瘤。他说:“这有点对不上号。它不是结论性的。它只是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这也促使科索夫斯基与他的导师,一位名叫约翰·赫格斯(John Heggers)的微生物学家和免疫学家,在豚鼠身上进行了一些关于硅胶的实验。科索夫斯基说,他们在 1983 年发表的研究表明,在豚鼠体内,硅胶可以诱发对其自身血液蛋白的敏感性。他推测,这种敏感性可能是一个可能导致自身免疫性疾病——即像类风湿性关节炎这样,免疫系统失控并攻击身体自身组织的疾病——过程的第一步。
1984 年至 1987 年间,科索夫斯基在康奈尔大学医学中心接受病理学培训,然后转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在那里他将他对硅胶的推测扩展为一个关于其对免疫系统影响的理论。他的理论依赖于硅胶分子众所周知的粘性。他解释说,一旦硅胶从植入物中泄漏出来,它就会被身体的蛋白质包裹,就像一颗樱桃蘸入巧克力后会立刻被巧克力包裹一样。他说,这改变了蛋白质的结构,这些蛋白质通常是被称为氨基酸的化学构建块构成的长而复杂的盘绕和打结的链条。他说,硅胶会解开或“变性”这些蛋白质,改变它们的形状:“这是一种基本的表面化学的生物物理现象。”
接着,科索夫斯基涉足了免疫学领域。当身体发现内部有病毒或细菌等不熟悉的物质时,免疫系统会产生称为抗体的防御分子,并派出它们执行搜索和摧毁任务。这些被称为抗原的入侵者带有分子标记,使抗体能够识别它们。免疫系统通常会为每种特定的抗原产生特定的抗体。科索夫斯基假设,一旦硅胶使组织或血液蛋白质变性,免疫系统将不再认识到这些蛋白质属于身体,并会产生抗体来攻击它们。这些抗体随后可能会错误地攻击原始的蛋白质,结果就是自身免疫性疾病。
研究人员后来说,科索夫斯基的理论不应被轻易否定,当然也值得进行检验。但科索夫斯基是否曾充分地做到这一点,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在 1980 年代后期,越来越多将硅胶植入物与自身免疫性疾病——特别是类风湿性关节炎、狼疮和硬皮病——联系起来的轶事报告引起了媒体的关注。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执行编辑玛西娅·安吉尔(Marcia Angell)的话说,所有人都同意,当植入物破裂,或者当它们周围形成的疤痕组织硬化和收缩时,乳房植入物的局部影响可能“相当可怕”。更具争议的是全身性影响。身体作为一个整体对硅胶有何反应?硅胶的存在是否会导致疾病——特别是自身免疫性疾病?声称会引起疾病的报告来自那些在植入植入物后才患上这些疾病的女性,尽管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尚未确定。正如安吉尔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一篇社论中所解释的那样,虽然这些轶事报告引人注目,但许多女性即使从未有过植入物,也会患上自身免疫性疾病。因此,她写道,“这种假定的关联非常难以评估”。
当 FDA 在 1992 年呼吁暂停使用硅胶植入物时,并非因为它们已被证明不安全,而是因为缺乏证据来证明它们是否安全。制造商也没有积累足够的证据来说明乳房植入物能持续多久,或者它们泄漏或破裂的频率有多高。尽管如此,那些没有密切关注的人——这意味着大多数美国公众和大部分媒体——将 FDA 的决定理解为植入物确实是危险的。
当流行病学家开始寻找数据以确定有植入物的女性是否比没有植入物的女性更频繁地患有自身免疫性疾病时,实验室研究人员则在寻找证据,证明硅胶和人体免疫系统是不健康的组合。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命题。硅胶,一种主要由硅和氧组成的简单分子,渗透在我们的文化中,也可能渗透在我们的身体里。例如,大多数抗酸剂使用硅酮作为填充剂,一些早餐麦片也是如此。Norplant 避孕设备也涂有硅胶。甚至腋下除臭剂也含有硅胶,这可能会通过皮肤吸收。华盛顿大学的生物工程师巴迪·拉特纳(Buddy Ratner)说:“我们简直被这东西包围了。”
科索夫斯基在 1990 年被引入这一领域,当时他接到一个妇女权益组织的电话,请求他查看一些有植入物且有健康问题的女性的乳腺组织切片。对科索夫斯基来说,这些切片显示了一系列模式,从大量的硅胶和炎症到相对轻微的生物反应,这表明了对植入物的各种局部反应。
不过,这些切片仅仅是个开始。在一个新闻通讯中,该倡导组织将科索夫斯基的名字印在了他以前的导师约翰·赫格斯(John Heggers)的名字旁边,赫格斯当时正在收集有植入物女性的血样。科索夫斯基说:“血样开始向我涌来。来自全国各地认为她们在为某项研究寄送血液的女性。所以我打电话给约翰。我说,‘我收到了血样。’我把它们寄下去。这种情况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转寄血液的费用开始变得相当昂贵。”
最终,赫格斯说他的血样够了,让科索夫斯基保留剩下的——来自数百名有乳房植入物并声称患有各种未指明疾病的女性的样本。科索夫斯基认为这是一个检验他关于对硅胶的免疫反应假设的绝佳机会。他推断,如果硅胶使这些女性的血液和组织蛋白变性,那么她们应该有针对硅胶变性蛋白的抗体,并且这些抗体应该是可以检测到的。他说:“他所要做的就是设计出合适的检测方法,就像艾滋病病毒测试或任何其他测试一样。”
他发明的检测方法是 ELISA 测试,研究人员称这种测试看似简单易用,但正确解读可能极其困难。起始设备包括一个由聚苯乙烯塑料制成的盘子,称为 ELISA 孔。像硅胶一样,聚苯乙烯能紧紧吸附接触到它的蛋白质。ELISA 的第一步是用你想要寻找抗体的特定抗原包被这个孔。抗原会粘在聚苯乙烯上。然后你加入血清——血液中去除细胞后剩下的液体成分。如果血清中有针对你的抗原的特异性抗体,它们会附着在抗原上,而抗原则粘在聚苯乙烯上。然后你洗去多余的血清,如果幸运的话,剩下的就是你正在寻找的抗体,它们附着在抗原上,而抗原当然也粘在聚苯乙烯上。
这是一个简化的描述,看起来很直接。但在 ELISA 孔中的情况可能会变得非常棘手。例如,如果你没有用你的抗原完全包被你的聚苯乙烯,那么血液中所有的抗体——无论它们是针对你的抗原还是其他物质的——都会粘在聚苯乙烯上,因为几乎任何东西都会粘在聚苯乙烯上。所以当你在测试结束时发现抗体,这并不意味着你找到了你正在寻找的特定抗体。这意味着你搞砸了程序。此外,测试给出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是”或“否”,而是一个高度主观的数值范围。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免疫学家诺埃尔·罗斯(Noel Rose)的话来说,这些数值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进行测试的技术人员、温度、湿度以及许多难以估量的因素。你得到的绝对值每天都在变化;所以你不会比较不同日子的测试,只会比较由同一位技术人员在同一块板上、在同一天进行的血清样本。ELISA 测试必须极其小心地进行,即使是有多年经验的研究人员也必须质疑他们是否正确解释了他们的结果。
然而,科索夫斯基却表现得好像 ELISA 测试相对简单。他亲自培训本科生志愿者进行测试。学生们用硅胶包被 ELISA 孔,然后加入人体血液和组织中常见的蛋白质,如胶原蛋白和纤维蛋白原,期望硅胶会使它们变性。然后,他们测试了科索夫斯基保存的 249 份血样,将血清倒入孔中,看它是否有会与推测已变性的蛋白质结合的抗体。
此时,即使 ELISA 显示存在这些抗体,科索夫斯基仍然不知道它们是否是植入物女性所特有的。也许所有女性都有这样的抗体。或者也许所有患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女性,即使没有植入物,也有。或者也许所有接受过大手术的女性,而植入手术当然是大手术。事实上,女性可能因为很多原因产生变性蛋白质——例如,感染可能会导致这种情况,植入物周围的局部炎症或手术后的疤痕组织也可能。像类风湿性关节炎这样的疾病可能会导致错误折叠的蛋白质在血液中漂浮,即使在没有植入物的人群中也是如此。因此,科索夫斯基必须测试来自健康和生病的、有植入物和没有植入物的女性的血液,以确定有植入物和症状的女性是否不仅有这些变性蛋白质的抗体,而且是唯一拥有这些抗体的人(或者至少比其他组别拥有更多)。只有这样,他才能得出一些科学结论。
因此,为了进行他必要的比较中的第一次,科索夫斯基在 1991 年 10 月收集了 47 名没有植入物的健康女性的血样。几个月后,他联系上了加利福尼亚州拉霍亚斯克里普斯研究所(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自身免疫性疾病中心的研究人员,他们对他的测试和理论很感兴趣。他们同意将患有确诊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女性的血液寄给他,以便他用他的检测方法进行测试。1992 年 3 月,他收到了 40 名未植入假体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女性、10 名没有植入物的健康女性以及 11 名有植入物并患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女性的血样。斯克里普斯研究所寄送的血样是“盲样”,这意味着科索夫斯基不知道哪个血样来自哪位女性。他必须用他的测试对样本进行检测,并将结果发送给斯克里普斯,由斯克里普斯来揭示编码。然后研究人员就会知道科索夫斯基的测试是否能揭示出有植入物且有自身免疫性疾病症状的女性含有针对变性蛋白质的抗体,或者至少比其他女性拥有更多的这类抗体。
四月,科索夫斯基寄出了他的测试结果,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揭示了编码。科索夫斯基的测试未能区分患有自身免疫性疾病并有植入物的女性与患有自身免疫性疾病但没有植入物的女性。虽然它也许能判断哪些女性患有自身免疫性疾病,但它无法说明这些疾病是否由硅胶乳房植入物引起。而对于这个有限的目的来说,它是没有必要的——已经有许多可用的测试可以做到这一点。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的风湿病学家罗伯特·福克斯(Robert Fox)说,研究人员将结果写信告知了科索夫斯基,并认为至少就斯克里普斯而言,这件事到此为止了。
但两年后,即 1994 年,该研究所开始接到来自患者、医生甚至一家大学诊所的电话,询问关于科索夫斯基的测试,显然是认为斯克里普斯已经验证了该测试或者正在提供这项服务。福克斯认为这种误解来自科索夫斯基,于是又给他写了两封信,重申他的测试无法区分与硅胶相关的疾病,并要求他不要再提及斯克里普斯诊所的患者数据。福克斯说,他给科索夫斯基的两封信是一种绅士的方式,解释该测试并不能检测科索夫斯基想要检测的东西。福克斯说:“由于他没有回应我发送给他的数据,我以为他已经明白我的意思了。”
福克斯还对科索夫斯基 1992 年 4 月的测试结果进行了统计学上的重新分析。他在 1994 年写给斯克里普斯研究所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整形外科医生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的一封信中描述了重新分析的结果,米勒当时是美国整形外科学会的主席。福克斯写道,分析不仅未能提供证据表明科索夫斯基的检测能够检测出与硅胶植入物相关的自身免疫性,而且科索夫斯基为他自己的健康未植入女性获得的 ELISA 值与他为斯克里普斯的健康未植入女性获得的值存在显著差异。这意味着科索夫斯基的研究存在根本性问题。如果测试运行得当,所有健康女性的结果应该是一致的,无论她们来自哪里。换句话说,福克斯写道,“整个 ELISA 必须被视为无效并重新进行。”
但科索夫斯基有不同的看法。他似乎甚至在与斯克里普斯研究所开始合作之前就相信自己的测试——这意味着在他有机会对任何确诊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进行测试,并将这些结果与植入患者的结果进行比较之前。早在 1991 年,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场审判中,他就对硅胶的免疫反应作证,帮助原告赢得了对道康宁公司的 700 万美元判决。他说,他对这件事的看法部分基于他研究的初步发现。
至于斯克里普斯的批评,科索夫斯基说,让斯克里普斯合作的目的不是为了让那里的研究人员告诉他他的测试是否有效,而是为了他能将他测试过的所有女性,包括斯克里普斯的病人,分成几组——有植入物的女性、健康对照组和没有植入物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女性。然后,当他们揭示编码时,他可以做自己的分析。至于福克斯的来信,科索夫斯基说,“他给我寄了一大包东西,一封非常奇怪、语无伦次的信,我完全看不懂。”
当他在 1992 年底起草一篇关于他工作的论文时,他拒绝了斯克里普斯的分析,并提供了自己的分析。他将斯克里普斯的 40 名自身免疫病患者中的 39 名与他的 249 名生病的、有植入物的女性以及他的 47 名健康的、没有植入物的女性进行了比较。然后他报告说,249 名有植入物的女性中有 9 名在他的 ELISA 测试中得分如此之高——高于其他任何人——以至于她们体内必定有非自然数量的针对变性蛋白的抗体,这暗示她们肯定患有与硅胶相关的疾病。这种疾病是什么,科索夫斯基无法说明。他后来说,除了发烧和脚痛的发生率更高之外,这 9 名女性的症状与另外 240 名植入女性的症状几乎没有区别,后者的 ELISA 测试结果并不特别高。
科索夫斯基的论文在 1993 年发表于同行评审的《应用生物材料杂志》之前,至少被三家科学期刊拒绝,而科索夫斯基是该杂志的编辑委员会成员。读过这篇论文的研究人员评论说,它存在多处错误,包括 ELISA 检测的几个缺陷,以及一个明显而突出的问题——科索夫斯基推断出其戏剧性结论所依据的受试者数量。
问题很简单。科索夫斯基报告说,他 249 名有植入物的女性中,有 9 人的 ELISA 分数显著高于 47 名健康女性或 39 名自身免疫性疾病女性的平均分。但那 9 名女性只占他测试的所有植入女性的不到 4%。如果实际上他的 ELISA 测试是无意义的呢?那么他可能会预期所有女性中有 4% 的人得分同样高。因为他的两个比较组的女性人数相对较少,所以其中 4% 的人数将少于每组两人。在如此小的数字下,他得到零而不是一或二,并不特别令人惊讶。当各组人数不均时,解释结果需要极其谨慎。
例如,想象一下,科索夫斯基决定检验一个与免疫系统完全无关的理论——比如说,身高——来判断一名女性是否患有硅胶引起的疾病。女性越高,她的乳房植入物引起自身免疫问题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是这样,很容易想象 249 名有植入物的女性中,有 9 名可能比 47 名无植入物女性或 39 名自身免疫患者中的任何一个都高,仅仅因为植入物组的女性人数比另外两组多得多。只有当科索夫斯基比较了足够大的、数量大致相等的女性群体——比如说,三组各 249 人——他才能得出结论,说 9 个最高分都来自有植入物的女性可能在某种医学意义上是有意义的。当然,如果有大量植入物女性,比如 50 人或更多,得分高于其他任何人,那么即使在不均衡的比较中,这也将是令人信服的。
许多读过科索夫斯基论文的科学家认为,科索夫斯基有一个有趣的假设,但他的论文中没有任何东西让他们相信它是对的,更不用说他的测试是有效的了。爱荷华大学免疫学家约翰·巴特勒(John Butler)说:“他把结论建立在假设本身之上。当你有一个假设时,你必须做非常彻底的实验来检验它。但他似乎把拥有假设等同于拥有数据。对于检测至关重要的细节缺失到这种程度,以至于当他得出最终结论时,作为一名科学家,我已经失去了兴趣。”英国医疗器械局审查了科索夫斯基的研究并得出结论,“不可能从这项工作中得出任何明确的结论。”……科索夫斯基认为这些批评过于极端。他后来解释说,这篇论文不应该被看得那么严肃;它只是说“这里有些非常奇怪的事情,暗示着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
尽管如此,科索夫斯基凭借一篇已发表的论文和通过加州大学提交的专利申请,在匹兹堡创立了 SBI 实验室,以推广一种名为 Detecsil(意为检测硅胶)的血液测试。他在公司的合伙人是他的妻子贝丝·布兰迪吉(Beth Brandegee)和他的父亲拉姆·科索夫斯基(Ram Kossowsky,父子俩的姓氏拼写不同)。
到 1994 年 3 月,SBI 正在宣传 Detecsil,称其为“受试者是否对硅胶产生免疫反应的明确答案”。在《Trial》这本面向原告律师的杂志上的一则广告写道:“代理与硅胶相关的诉讼客户?请考虑:Detecsil 测试可以确认个人是否已对与硅胶相关的蛋白质产生免疫反应。Detecsil 为那些研究高危人群中硅胶免疫反应的人提供了宝贵的答案……”
根据 SBI 的说法,这些“高风险人群”不仅包括估计有 100 万接受硅胶乳房植入的女性,还包括任何拥有硅胶假体或职业性接触硅胶的人,甚至是通过内衬有硅胶的皮下注射器注射胰岛素的糖尿病患者。在 Detecsil 测试中得分高的人将被告知他们对硅胶有免疫反应——言下之意,他们有一个很好的诉讼理由。想要进行测试的人被指示将血液和 350 美元寄给 SBI。这种测试的潜在利润显而易见。如果 Detecsil 对 100 万植入女性有价值,更不用说其他高风险人群,那么 SBI 实验室有望获得数亿美元的业务。(然而,科索夫斯基说,截至 1995 年 9 月,他和他的妻子都没有从实验室的运营中获得任何利润。)
然而,推广这项测试给科索夫斯基和他的家人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没有逃过 FDA 的注意。因为 SBI 是将血液测试作为一种服务而不是可以购买的试剂盒来提供的,所以 FDA 对其的监管控制很小。但是,该机构可以坚持要求测试的广告必须真实。
1994 年 7 月,FDA 通知 SBI,尽管其宣传材料中包含了“仅供研究使用”的警告,但这与声称 Detecsil 是诊断工具的说法相矛盾。例如,“Detecsil 是第一种也是唯一一种检测对因硅胶受损的身体蛋白质产生免疫反应的测试”这一说法,似乎暗示了某种诊断。在一封给 SBI 的信中,FDA 警告说,在 Detecsil 被证明具有诊断能力之前,这种宣传是误导性的,SBI 正在违反联邦法规。
这种概念上的两难境地导致了一些同样令人困惑的澄清尝试。例如,在法庭证词中,科索夫斯基必须准确描述他的测试能为那些支付 350 美元看结果的女性做什么,而他却不能声称它可以诊断任何疾病。科索夫斯基承认,该测试无法确定某人是否生病。那么它能做什么呢?科索夫斯基后来解释说,它是一个“研究工具”和“法律工具”。
法律工具?
他解释说:“目前,在这个日益严重的硅胶烂摊子中,最大的问题之一是如何识别那些确实有硅胶诱导反应证据的患者,并将他们与那些可能因为任何原因患有硬皮病并有植入物的患者,以及那些声称自己有各种症状但实际上什么问题都没有的患者区分开来。”但是,这再次似乎暗示了一种诊断测试。这一切都非常令人困惑。无论如何,去年五月,SBI 实验室申请 FDA 批准 Detecsil 作为一种医疗设备,并在不久之后暂停了该测试的销售。
或许,科索夫斯基的法庭证词所揭示的其研究中最令人困惑的方面,是他原始数据的状况。研究人员喜欢将日志和实验室记录保存多年,有时甚至是无限期保存,以便支持他们发表的主张。但当植入物制造商的律师传唤科索夫斯基交出他的数据,希望能弄清楚他的测试时,他给他们的不过是他论文的草稿和其中的图表——没有实验记录本或原始数据。在 1994 年 6 月的一次取证中,科索夫斯基解释说,他的大部分数据,也许是全部,都在一次洛杉矶地震中丢失了。
科索夫斯基说,数据堆在他办公室的地板上。地震期间,“一些喝了一半的咖啡杯或水杯或其混合物,其中一些可能已经长出了微生物物种,以及一些其他也放在桌子边缘和地板上的大堆附近并且很湿很恶心的液体容器。结果,他找了两个大垃圾桶,扔掉了所有看起来恶心或不是特别重要的东西。”
其中一位律师问道:“你知道吗,你是否看过一张纸,然后说‘这是最近发表的一项研究的数据,即使湿了我也应该保留’?”
科索夫斯基回答说:“这个念头从未在我脑海中闪过。”
1995 年 3 月,科索夫斯基宣布他有了一些新数据,他在匹兹堡的 SBI 完成了一项基于血液样本的研究。他在由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主办的一次会议上报告了结果,声称 Detecsil 可以极其准确地区分有乳房植入物和症状的患者与各种对照组。然而,数据似乎和以前一样不均衡:这次科索夫斯基比较了 310 名有植入物和未指明疾病的女性,与 173 名没有植入物的健康女性,88 名没有植入物但诊断出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女性,以及只有 11 名有植入物但没有症状的女性。科索夫斯基说,Detecsil 测试完全基于这些新数据,而不是 1993 年论文中包含的数据,尽管他无法解释为什么公司在开始汇编新数据前几个月就已经在宣传 Detecsil。(一份宣传册甚至声称“Detecsil 硅胶敏感性测试是基于十多年来对硅胶乳房植入物研究收集的数据”,这与他的说法相矛盾。)
会议后不久,SBI 开始发送新闻通讯,引用科索夫斯基的话说,他的新研究构成了“迄今为止将硅胶与免疫疾病联系起来的最强有力的人类数据”。根据 SBI 的说法,预计至少有 20 万名乳房植入女性将显示出硅胶与疾病之间的联系。通过他们的营销攻势,科索夫斯基和 SBI 似乎在努力反驳那些显示没有证据表明硅胶诱发免疫性疾病的流行病学研究的积累,其中最新的一项于六月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这项研究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项:一项为期 14 年、涉及 87,501 名护士的研究,其中 876 人有硅胶植入物。由哈佛大学流行病学家格雷厄姆·科尔迪茨(Graham Colditz)领导的研究人员发现,硅胶乳房植入物与自身免疫性疾病之间没有关联。科索夫斯基声称,也许硅胶引起了某种未知的疾病,其特征不是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常见症状,而是一系列症状的集合,如口干、脱发、疲劳和睡眠障碍。但哈佛的研究也没有显示任何证据支持这一论点。
当然,科索夫斯基坚持认为他的研究是正确的,而流行病学研究是有限的。他解释说,那些研究没有寻找正确的症状或疾病。“我感觉自己有点像伽利略,”他说。“地球仍在转动。”
最后,我们为什么要关心科索夫斯基是另一个伽利略,还是只是一个销售着一种测试和专业知识的人,而这些东西充其量也只是意义可疑?毕竟,总会有研究人员提出无法证实的说法,甚至有研究人员通过这种说法赚钱。但许多其他科学家担心这种说法如何影响科学和公众。在我们的社会中,科学家因其职业而具有权威性。公众相信他们的话,并把他们置于崇高的地位。但是,罗伯特·福克斯说,就像那些说服女性乳房植入物会改善她们生活的整形外科医生一样,提出未经证实的说法的研究人员不值得公众信任。福克斯说:“有乳房植入物并伴有疲劳、关节问题和其他定义不清症状的女性需要明白,医生们与她们一样,对我们未能理解她们的症状感到沮丧。然而,让他们使用一个控制不善的实验室测试,从而对自身免疫系统失衡产生恐惧,这对他们并没有任何有益的服务。”
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的斯蒂芬·米勒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尽管他特意指出,他担忧的是所有未经证实的理论的推广,而不仅仅是科索夫斯基的。“这个问题非常令人不安,”米勒说,“对病人来说也非常不安。我们大多数人花了大量时间与那些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应该恐慌的事情而恐慌的人在一起。这些人吓坏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一只鸡在尖叫天要塌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