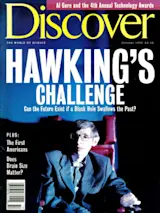几年前在女权主义圈子里流传着一个笑话,开头是这样的问题:你知道为什么女人不能学数学吗?答案既需要语言也需要手势。因为,开玩笑的人会说,她们一生都被教导说这个(这时她会把拇指和食指分开大约三英寸的距离)是六英寸!这个笑话嘲笑了那些认为性能力是大小问题的人,以及那些认为女人不能学数学的人。在我的朋友中,这些想法都是可笑的,但在过去两年中,两者都被训练有素的科学家提出——而且不仅仅是在鸡尾酒时间。它们在声誉良好的科学期刊上发表并进行了辩论。
在几篇文章中,西安大略大学心理学家J. Phillipe Rushton宣称不同种族有不同的大脑和阴茎尺寸,引起了轩然大波。他坚持认为,随着大脑尺寸的减小,阴茎尺寸会增加。他得出结论,大脑较大的种族更聪明,但性抑制也更强,而大脑较小的种族则没那么聪明,但像兔子一样交配。去年,在一项新研究中,他重复了他关于大脑尺寸的观点,并增加了一个新的转折——他说,在每个种族内部,女性的大脑都比男性小。Rushton的加拿大同事C. Davison Ankney也加入了进来,他重新审视了从克利夫兰1200多具尸体中获取的数据,这些数据显示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大脑尺寸没有显著差异。Ankney声称分析有误。他说,如果正确地进行分析,尺寸差异就会变得明显且有意义——女性的大脑更小。
在这样一个以种族划分、传统性别角色迅速变化的文化中,这样的想法必然会引发争议。有趣的是,Rushton和Ankney提出的观点与19世纪的观点惊人地相似——那是性政治和种族政治另一个剧烈动荡的时期——当时许多著名科学家相信男性和女性之间以及不同种族之间存在大脑大小差异。但这些想法的当前版本有一个引人入胜的时代特色。19世纪的科学家将欧洲裔排在第一位,亚洲人第二,非洲人最后。Rushton交换了亚洲人和欧洲人的位置,这一举动与一种新现象非常吻合:北美新亚洲移民的孩子在学校表现非常出色,而日本和中国的学生在数学成绩测试中远胜于美国人。
去年,Rushton的文章在小型期刊《智力》上发表后,这个话题溢出到了《自然》杂志的版面,《自然》是世界上阅读最广泛的科学期刊之一。《自然》的编辑约翰·马多克斯认为,期刊只有在符合特别高的证据标准时,才应该发表这种具有社会颠覆性的内容,他认为Rushton的研究未能达到这一标准。随后在读者来信版上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一些科学家站在加拿大科学家一边;另一些则攻击他们或其他写信人。经过五个月,分歧仍存,编辑们突然结束了这场辩论。
争论点是什么?Rushton和Ankney提出的观点引发了如此多的问题,以至于不知从何说起。首先,当然,人们想知道他们是否正确。如果他们是正确的,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越大越好吗?大脑越大的人就越聪明吗?不幸的是,这些不仅仅是学术问题——它们对教育和社会政策都有影响。仅仅三年前,哈佛心理学家理查德·赫恩斯坦就曾提出,非洲裔美国人之所以处于美国社会经济阶梯的较低层,可能是因为平均天赋差异,而“领先开始”和积极行动等项目充其量只是误导,最坏的情况是完全浪费时间和金钱。至于女性,安克尼写道,她们较小的大脑是由于空间和数学能力不发达造成的。一些科学家受这种粗糙的大脑运作观点的启发,认为鉴于科学思维的数学性质,更多的男孩而不是女孩会成为成功的研究人员,这是很自然的。
这些想法的潜在影响使得我们更有必要仔细审视其基础——即大脑尺寸是如何实际测量的。大脑测量者采用了三种方法之一:死后称量新鲜或保存的大脑,用芥菜籽或铅弹填充空颅骨然后测量填充物的体积以估计颅容量,或者将头部形状的外部测量值转换为颅容量的估计值。每种技术都存在争议。例如,1849年,费城医生塞缪尔·乔治·莫顿发表了623个人类颅骨的颅容量测量数据。他报告说,亚洲人和白种人的颅容量相同,而非洲人的大脑略小(小4立方英寸)。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当哈佛古生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重新审查莫顿的数据时,他发现莫顿可能在无意中篡改了他的测量结果。其中包括,莫顿出于我们只能猜测的原因,从非洲人群中排除了特别大的大脑,从欧洲人群中排除了特别小的大脑。古尔德对莫顿测量值的重新计算,考虑到这些因素,显示没有真正的尺寸差异。
颅容量不仅难以测量,其与实际大脑尺寸的关系也不确定。毕竟,颅骨内部除了大脑还有更多东西。这个珍贵的器官被结缔组织和充满液体的脑膜所包裹。换句话说,颅容量可能反映的是大脑保护层而非灰质的差异。
你可以通过称量整个大脑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前提是你能够拿到它们。19世纪末,科学家们成立了协会,鼓励有知识和社会成就的人将他们的“思考帽”遗赠给科学。记录显示,例如,1906年,约有70位受过教育、行为规范的人承诺将他们的大脑捐献给康奈尔大脑协会。诗人沃尔特·惠特曼将他的大脑遗赠给了美国人体测量学会。后来,一位粗心的实验室助理不慎将其摔落,未能收集剩余部分并保存下来以传后世——这让哥伦比亚大学解剖学家爱德华·安东尼·斯皮茨卡大为愤慨。1906年,斯皮茨卡统计了130多名已故白人男性的大脑重量,得出结论,美国人和加拿大人的大脑最大,英国人次之,德国人和奥地利人最小。在杰出男性中,数学家的大脑最大,其次是行动派——军事、政府和政治领袖。艺术家和哲学家的大脑相对较小。(20世纪初的科学家们每当将大脑大小与成就联系起来时,总是发现科学家拥有最大的大脑之一,这似乎不仅仅是巧合。)
然而,斯皮茨卡在计算中并未考虑身体大小,莫顿也没有。众所周知,身体较大的人拥有较大的身体部位。然而,早期大脑大小研究中使用的许多非洲人,包括莫顿的研究,都比与他们进行比较的北欧人小得多。有些人将此称为“大象问题”。大象的大脑比人类大得多,但尽管大象很聪明,没有人认为它们比人类更聪明。假设一个种族群体平均而言比另一个种族群体拥有更大的大脑:这仅仅是因为他们身体较大,还是有更复杂的情况发生?类似的问题也适用于女性和男性大脑之间的比较。例如,如果女性平均比男性矮约10%,那么她们的平均大脑大小比男性小约10%,这可能并不令人惊讶。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假设您有充足的新鲜尸体,最简单的方法是将它们的大脑尺寸除以某种身体尺寸标准,例如身高或体重——也就是说,求一个比率。但是您应该选择哪个标准呢?用大脑尺寸除以体重通常会使女性的比率更高(每体重的大脑更大)。但如果用大脑尺寸除以身高,男性则往往会领先。在19世纪,科学家们努力寻找大脑和身体尺寸之间的有意义关系。他们用大脑尺寸除以身高、体重、肌肉质量、心脏大小或股骨长度。这些方法都受到了挑战,有些被废弃(有时是因为它们不支持欧洲男性比女性或非洲裔人更聪明、因此大脑更大的预设观念)。即使是幸存的方法也仍然存在争议。
事实上,当代关于女性和男性大脑大小的争论仍然围绕着他们的体型差异。首先,解剖学家们对大脑大小的绝对差异存在分歧;估计范围从10%到17%。此外,一些研究人员认为,校正体型后,大脑大小的差异就会消失。安克尼声称这些研究人员使用了不当的统计检验,而《自然》杂志的一些通讯员则认为安克尼的统计数据完全不靠谱——简而言之,这场辩论在这一问题上是火药味十足,却鲜有真知灼见。
至于鲁斯顿1992年那项备受争议的研究,它放弃了直接测量大脑,转而采用19世纪末英国生物统计学家爱丽丝·李和卡尔·皮尔逊(现代统计学的创始人之一)开发的统计公式。这些公式旨在根据颅骨高度、宽度和长度的外部测量值来计算脑容量。为了让大家了解这些计算有多么神秘,这里是他们为男性制定的公式:脑容量等于0.000337乘以头长(减去颅骨周围的脂肪和皮肤厚度)乘以头宽(减去脂肪和皮肤)乘以头高(减去脂肪和皮肤)加上406.01。数字0.000337和406.01没有理论依据;它们只是用来使公式产生可验证结果的修正因子。为了测量女性颅骨大小,李和皮尔逊在同一公式中引入了不同的修正因子。
1898年,李和皮尔逊测量了参加都柏林解剖学会会议的科学家们的头部。他们假定他们遇到的解剖学家智力相似,但他们的测量结果显示颅骨大小存在很大差异。此外,他们发现一些女大学生拥有比一些男解剖学家更大的颅骨。这让他们确信:女学生不可能比男科学家更聪明;因此颅骨大小不能反映智力。然而,Rushton尽管使用了他们的统计方法,但仍认为大脑大小与智力相关。Ankney也持此观点。(对于20世纪初英国女大学生的大脑尺寸,他们有何看法,则不得而知。)
哥伦比亚大学的先驱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也研究了颅骨尺寸。他的研究结果给鲁斯顿带来了另一个问题。从1910年到1916年,博厄斯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表明平均身高、面部和颅骨形状等种族特征——这些都被普遍认为是不可改变的遗传特征——会随着环境而变化。他报告说,在美国出生的儿童的头部大小和形状(以及颅容量)与他们欧洲出生的移民父母有显著差异。例如,在美国出生的波西米亚人的头部比他们的父母更短更窄。另一方面,在美国出生的西西里人的头部比他们的父母更短更宽,而美国出生的犹太人的头部比他们的父母更长更窄。颅骨形状不仅随着不同环境(可能包括不同饮食等因素)而变化,而且这些变化在世界各地不同地区的人群中也各不相同。博厄斯里程碑式的研究使“固定种族类型”的整个概念陷入混乱。然而,鲁斯顿在他的《智力》文章中正是坚持这一观念。
鲁斯顿不为所动,他将李和皮尔逊的公式应用于军队例行对新兵进行帽子和战斗头盔尺寸测量的外部头部数据。他获得了6000多名新兵的数据,并按性别、种族和军衔进行了分析。根据鲁斯顿的分析,男性的颅容量大于女性,军官的颅容量大于入伍新兵。他按降序排列了各族裔的颅容量:亚洲人、白人、黑人。
为了确定新兵属于哪个种族,鲁斯顿使用了新兵的自我描述。但这引出了另一个问题,不仅对鲁斯顿,对任何涉及种族的研究都如此。首先,被称为亚洲人、白人或黑人的人群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比较一下高大白皙的北欧人和矮小黝黑的意大利人。或者娇小的俾格米人和高大的瓦图西人。外部外观的变异性在基因层面也有体现,种族内部的变异性几乎与种族之间的变异性一样大。此外,曾经地理上相互隔离的人群之间存在大量混血。我们只需看看我们称之为黑人的美国公民的横截面,就能看到这个问题。我的黑人朋友从深棕色皮肤的人到几乎和我一样白的人(我的祖先来自中欧的犹太人)都有。他们都出于历史和政治原因将自己认定为黑人,但快速一瞥就会发现这个称谓并不能代表生物学上的统一性。事实上,哈佛遗传学家理查德·列万丁得出结论,广泛的种族分类没有真正的生物学意义。如果他是对的,那么鲁斯顿对军队数据的解释就只是一个幻觉。
但让我们姑且相信Rushton的论点。你是否认同他的结论,归根结底是一个如何解释他的数字的问题。例如,黑人女兵的平均颅容量为1260立方厘米,平均体重为62.2公斤。将颅容量除以体重,得到比率为20.3。对黑人男兵进行同样的计算,得到比率为18.5。总的来说,女性每公斤体重的大脑空腔比男性大。使用这个比率,黑人和白人没有差异,而亚洲人的颅容量可能略大。但Rushton忠实于他19世纪的科学祖先,没有进行这个计算(我用他的数据进行了计算)。相反,他发明了一个有效的计算方法——我认为这符合他的先入之见。他估计女性体重中约有20%是脂肪,而男性只有10%;因此,他没有直接将颅容量除以体重,而是首先从女性体重中减去20%,但只从男性体重中减去10%。(为什么这样做是有效的,我不得而知,但他成功了。)使用他新的、调整后的体重挽救了局面。男性每调整后的体重拥有更大的大脑。
但是,无论你选择哪种衡量标准,根本问题仍然存在:大小真的重要吗?大脑大小可能因多种原因而异。例如,患有脑积水(脑部积水)的儿童拥有巨大的、充满液体的脑部,其中大量的神经组织已经不可逆转地受损。这些儿童中的一些患有智力缺陷。在这种情况下,显然越大越不好。
更常见的情况如何?1987年,德国解剖学家赫伯特·豪格发现,女性大脑皮层每立方毫米的神经元(神经细胞)比男性多4000个。豪格得出结论,即使女性大脑较小,女性和男性拥有的神经元总数是相同的。换句话说,女性只是将所有神经元都塞进了更小的空间。尽管这些数据令人着迷,但它们仍然没有告诉我们神经功能方面的信息。例如,我们不知道这些细胞的连接和效率如何。神经细胞会发出线状突起,可以与其他神经细胞连接,将信号从一个细胞传递到下一个细胞。一个神经细胞可能与10个其他细胞相互作用,也可能与50个其他细胞连接。连接越复杂,一组神经元能执行的活动就越复杂。一个拥有许多神经元但相互连接较少的大脑,其执行复杂活动的能力可能不如其更小但连接更紧密的对应物。重要的不一定是大小,而是你如何利用你的设备。
你可以在鲁斯顿的作品中找到许多其他值得批评的地方(正如《自然》杂志的通讯员所做的那样),但这并非重点。对我而言,清楚的是没有答案。通过操纵统计数据,双方的科学家都可以为自己的先入之见辩护。这是一场社会争论,而非科学争论。生物学上的身体已成为关于政治体的辩论的载体。无论在19世纪还是今天,关于大脑大小的说法都是社会政策斗争中的武器。那些相信我们的社会对所有生活在其中的人都是公平公正的人认为,精英会脱颖而出。如果某个群体——非洲裔美国人或女性——处于底层,那么其成员就一定不是精英,改变社会结构如果不是不可能,也是不明智的。相反,那些相信机会均等尚未实现的人认为,至少有一些白人男性之所以位居顶端,是因为他们是白人男性,而不是因为他们更有能力。如果白人男性的特权是问题所在,那么就存在问题。真正的问题不再是谁的大脑更大,而是为什么在机会均等的土地上,我们仍然存在社会不平等?我们能做些什么来改变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