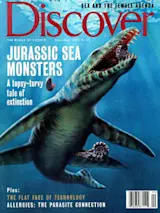第一幕:光线昏暗的卧室;一位英俊的男子躺在床上。一位穿着睡衣的漂亮年轻女子走进来。她的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一枚闪耀的结婚钻戒;右手紧握着一张蓝色的小纸条。她弯下腰,亲吻男子的耳朵。
她:亲爱的!时候到了!
第二幕:相同的卧室,相同的夫妻,正在做爱;细节被昏暗的灯光遮挡。镜头转向一只戴着相同结婚钻戒的优雅之手翻动日历。
第三幕:相同的夫妻,幸福地抱着微笑的婴儿。
他:亲爱的!我真高兴排卵试纸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是最佳时机!
最后一帧:特写相同的优雅之手,紧握着相同的蓝色小纸条。说明文字:排卵试纸。家用尿液测试,检测排卵。
如果狒狒能理解我们的电视广告,它们会觉得这则广告特别好笑。无论是雄性还是雌性狒狒,都不需要荷尔蒙测试盒来检测雌性的排卵期,因为那是她的卵巢唯一释放卵子并可以受精的时候。相反,雌性狒狒阴道周围的皮肤会肿胀并变成鲜亮的粉红色。她会散发出一种独特的气味。如果一个迟钝的雄性仍然不明白,她还会蹲在他面前,展示她的臀部。大多数其他雌性动物也类似,通过同样大胆的视觉信号、气味或行为来广告排卵期。
我们认为臀部鲜粉色的雌性狒狒很奇怪。然而,实际上,我们人类才是奇怪的——我们几乎检测不到的排卵使我们成为哺乳动物世界中的少数。诚然,许多其他灵长类动物——包括猴子、猿和我们自己——也隐藏排卵。然而,即使在灵长类动物中,狒狒式的广告仍然是主流做法。相比之下,人类雄性无法检测到伴侣何时可以受精;直到现代科学时代,女性自己也无法检测到。
我们持续的性行为也很不寻常,这是我们隐藏排卵的直接后果。大多数其他动物的性行为仅限于排卵期前后短暂的发情期。在发情期,一只雌性狒狒会从一个月的性禁欲中恢复过来,交配多达100次。一只雌性巴巴利猕猴平均每17分钟交配一次,至少一次向其群体中的每只成年雄性提供性服务。一夫一妻制的长臂猿夫妇会好几年没有性生活,直到雌性断奶其最近的幼崽并再次发情。雌性一旦怀孕,长臂猿就会恢复禁欲。
然而,我们人类在一个月的任何一天都可以进行性行为。因此,大多数人类的性交都涉及到当时无法受孕的女性。我们不仅在周期的错误时间发生性行为,而且在怀孕期间和绝经后,当我们确定无法受精时,我们仍然继续发生性行为。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人类性行为似乎是巨大的精力浪费。毕竟,大多数其他动物在交配努力上都明智地吝啬,原因很简单——性是昂贵的。数数看:对于雄性来说,精子生产的代谢成本很高,以至于精子数量少的变异蠕虫比正常产生精子的蠕虫寿命更长。性会占用原本可以用于寻找食物的时间。在性行为本身中,紧密拥抱的伴侣面临被捕食者或敌人突袭杀死的风险。最后,雄性之间为争夺雌性而进行的战斗常常导致雌性以及雄性受到严重伤害。
那么,为什么人类女性不像大多数其他动物那样,发出明确的排卵信号,让我们将性行为限制在对我们有益的时候呢?
现在,您可能已经认为我是象牙塔科学家不必要地寻找问题来解释的典型例子。我能听到几百万人在抗议,“没有什么问题需要解释,除了贾雷德·戴蒙德为什么这么笨。你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一直做爱吗?当然是因为好玩!”不幸的是,这个答案不足以让科学家满意。人类隐蔽的排卵和持续的性接受能力必然是出于充分的理由而进化的,而且这些理由超越了“好玩”。动物在交配时,从它们全神贯注的样子来看,似乎也在享受乐趣。对于智人这个具有独特自我意识的物种来说,一个像人类女性一样聪明和有意识的雌性竟然对自己的排卵一无所知,而像牛一样笨的雌性动物却能意识到,这尤其自相矛盾。
在推测我们隐蔽排卵的原因时,科学家们倾向于关注我们另一个不寻常的特征:我们婴儿的无助状态,这使得多年的父母照护成为必要。大多数哺乳动物的幼崽一旦断奶,就能开始自己觅食,并很快变得完全独立。因此,大多数雌性哺乳动物能够并且确实在没有父亲任何帮助的情况下抚养幼崽,母亲在交配后就再也不会见到父亲。然而,对于人类来说,大多数食物是通过复杂的技术获得的,这远远超出了幼儿的灵巧性或心智能力。结果,我们的孩子在断奶后十年以上都必须有人给他们带食物,而这项工作由两个父母来做比一个父母要容易得多。即使在今天,单身母亲独自抚养孩子也很困难。对于我们的史前祖先来说,无疑要困难得多。
试想一下,一位刚刚受精的排卵期穴居女性所面临的困境。在许多其他哺乳动物物种中,雄性会迅速离开,寻找另一位排卵期雌性。然而,对于穴居女性来说,这将严重危及她孩子的生存。如果那个男人留下,她会过得更好。但她能做什么呢?她绝妙的解决方案:一直保持性接受能力!只要他想要,就和他交配,让他满意!这样一来,他就会留在身边,不需要寻找新的性伴侣,甚至会分享他每天捕获的肉食。
这基本上就是以前在人类学家中——反正是在男性人类学家中——流行的理论。可惜的是,这个理论有很多漏洞,因为有许多雄性动物不需要这样的性贿赂就能留在配偶和后代身边。我已经提到过,长臂猿似乎是忠贞不渝的典范,它们可以数年没有性生活。雄性鸣禽在喂养雏鸟方面与配偶勤勉合作,尽管受精后性行为就停止了。即使是拥有多只雌性后宫的雄性大猩猩,每年也只有几次性交机会,因为它们的配偶通常在哺乳期或非发情期。显然,这些雌性不必提供持续性交的诱惑。
但我们人类夫妻与其他动物物种中禁欲的夫妻之间存在一个关键区别。长臂猿、大多数鸣禽和大猩猩分散在各地,每对或每个后宫都占据着各自独立的领地。这意味着它们很少有机会遇到潜在的婚外性伴侣。传统人类社会最独特的特征也许在于,它由生活在其他伴侣群中的已婚夫妻组成,我们必须与他们合作。父母必须合作多年才能抚养他们无助的孩子,尽管他们经常受到附近其他有生育能力的成年人的诱惑。婚外性导致的婚姻破裂,及其对育儿中父母合作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在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不知何故,我们进化出了隐蔽排卵和持续的性接受能力,以使我们独特的婚姻、共同育儿和通奸诱惑的结合成为可能。这种结合是如何运作的?
十几种新理论已经作为可能的解释出现。在众多可能性中,两种理论——“父亲在家理论”和“多父理论”——被认为是最可信的。然而,它们几乎是相反的。
“父亲在家理论”由密歇根大学生物学家理查德·亚历山大和研究生凯瑟琳·努南提出。为了理解它,想象一下如果女性像臀部鲜粉色的雌性狒狒那样广告排卵,婚姻生活会是怎样的。丈夫会准确无误地识别出妻子排卵的那一天。在那一天,他会呆在家里,勤奋地做爱,以便让她受精并传承自己的基因。在所有其他日子,他会从妻子苍白的臀部意识到与她做爱是徒劳的。他反而会四处游荡,寻找其他没有防备的粉色女士,这样他就可以传承更多的基因。他会放心地让妻子呆在家里,因为他知道她对男人没有性接受能力,无论如何也无法受精。
这些被广告的排卵结果会很糟糕。父亲不会在家帮忙抚养孩子,母亲也无法独自完成这项工作,婴儿会成批死亡。这对母亲和父亲都不利,因为他们都无法成功传播自己的基因。
现在,让我们设想一个相反的情景,丈夫对妻子的受孕日一无所知。如果他想有很大的机会让她受孕,他就必须尽可能多地呆在家里,和她做爱。他留在身边的另一个动机是保护她免受其他男人的侵扰,因为在他离开的任何一天,她都可能受孕。此外,他现在外出游荡的理由也少了,因为他无法识别其他女性何时受孕。令人欣慰的结果是:父亲留在身边并分担育儿工作,婴儿得以存活。这对母亲和父亲都有好处,他们现在成功地传播了他们的基因。实际上,双方都受益:女性通过招募一个积极的共同父母;男性因为确信他正在抚养的孩子确实携带他的基因而获得信心。
与“父亲在家理论”竞争的是“多父理论”,由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人类学家莎拉·赫迪提出。人类学家早就认识到杀婴在许多人类社会中曾经很常见。然而,直到赫迪和其他人的田野研究,动物学家才意识到杀婴在其他动物中也经常发生。杀婴尤其可能由雄性针对从未与他们交配过的雌性的后代实施——例如,由取代了常住雄性并获得了其后宫的入侵雄性实施。篡位者知道被杀死的婴儿不是他自己的。(当然,动物不会有意识地进行如此微妙的推理;它们是本能地这样进化的。)现在已记录到杀婴的物种包括我们最亲近的动物亲戚,黑猩猩和大猩猩,此外还有从狮子到非洲野狗的各种其他物种。
自然,杀婴行为令我们感到恐惧。但仔细思考,人们会发现凶手获得了可怕的基因优势。只要雌性哺乳婴儿,她就不太可能排卵。通过杀死婴儿,凶手终止了母亲的哺乳期,并刺激她恢复发情周期。在大多数情况下,凶手会继续使悲伤的母亲受精,然后她会生下一个带有凶手自己基因的婴儿。
杀婴对这些动物母亲来说是一个严重的进化问题,她们失去了对被谋杀后代的基因投资。如果雌性只有短暂、显著的排卵期,这个问题似乎会更加恶化。一个优势雄性可以轻易地在那段时间独占她。所有其他雄性因此都会知道由此产生的婴儿是他们的竞争对手所生的,他们将毫不犹豫地杀死这个婴儿。
然而,假设雌性有隐蔽的排卵和持续的性接受能力。她可以利用这些优势与许多雄性交配——即使她必须偷偷摸摸地进行,在她的伴侣不注意的时候。(顺便说一句,赫迪认为,人类女性重复性高潮的能力可能已经进化,以提供她这样做的进一步动机。)
根据赫迪的设想,没有一个雄性可以确定自己的父权,但许多雄性都意识到自己可能是母亲婴儿的父亲。如果这样一个雄性后来成功地赶走了母亲的伴侣并接管了她,他会避免杀死她的婴儿,因为那可能是他自己的。他甚至可能在保护和其他形式的父爱方面帮助婴儿。母亲隐蔽的排卵也将有助于减少其群体内雄性之间的争斗,因为任何一次交配都不太可能导致受孕,因此不再值得争夺。
简而言之,亚历山大和努南认为隐蔽排卵能够明确父子关系并加强一夫一妻制,而赫迪则认为它混淆了父子关系并有效地瓦解了一夫一妻制。哪种理论是正确的呢?
为了找到答案,我们转向比较方法,这是一种进化生物学家经常使用的技术。通过比较灵长类物种,我们可以了解哪些交配习惯是隐蔽排卵物种所共有的,而哪些是公开排卵物种所没有的。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每个物种的生殖生物学都代表了自然界在隐蔽排卵的利弊方面所进行的实验结果。
这项比较最近由瑞典生物学家 Birgitta Sillén-Tullberg 和 Anders Møller 进行。他们首先列出了68种高等灵长类动物(猴子和猿)的排卵可见迹象。他们发现,有些物种,包括狒狒和我们的近亲黑猩猩,会显著地广告排卵。另一些物种,包括我们的近亲大猩猩,则表现出轻微的迹象。但近一半的物种,像人类一样,缺乏可见迹象。这些物种包括非洲绿猴、狨猴和蜘蛛猴,以及一种猿类,猩猩。因此,虽然隐蔽排卵在一般哺乳动物中仍然是例外,但在高等灵长类动物中却占有相当大的少数。
接下来,将这68个物种根据它们的交配系统进行分类。有些物种,包括狨猴和长臂猿,被发现是实行一夫一妻制。更多的物种,例如大猩猩,拥有由单一成年雄性控制的雌性后宫。人类在这两个类别中都有代表,一些社会是常规的一夫一妻制,另一些则拥有女性后宫。但大多数高等灵长类物种,包括黑猩猩,都实行滥交制度,雌性通常与多个雄性交往并交配。
Sillén-Tullberg 和 Møller 随后研究了排卵期信号的明显程度是否与特定的交配系统存在任何关联。基于我们两个相互竞争理论的简单解读,如果“父亲在家理论”是正确的,那么隐蔽排卵应该是实行一夫一妻制物种的特征;如果“多父理论”成立,那么隐蔽排卵应该是实行滥交制物种的特征。事实上,几乎所有分析过的一夫一妻制灵长类物种都被证明具有隐蔽排卵。没有一个一夫一妻制灵长类物种拥有大胆的排卵期广告,这种广告主要局限于滥交物种。这似乎是对“父亲在家理论”的有力支持。
但预测与理论的契合度只有一半,因为反向关联并不成立。是的,大多数一夫一妻制物种都有隐蔽排卵,然而,永久苍白的臀部反过来并不能保证一夫一妻制。在32种隐藏排卵的物种中,有22种不是一夫一妻制,而是滥交或生活在后宫中。所以,无论最初是什么导致了隐蔽排卵的进化,它显然可以在各种交配系统下维持。
同样,虽然大多数有明显排卵期广告的物种都是滥交的,但滥交并不需要每月展示一次鲜粉色的臀部。事实上,大多数滥交的灵长类动物要么有隐蔽排卵,要么只有轻微的迹象。拥有后宫的物种可以有任何类型的排卵信号:不可见的、轻微可见的或明显的。
这些复杂性提醒我们,隐蔽排卵会根据其所共存的特定交配系统而发挥不同的功能。为了识别这些功能变化,Sillén-Tullberg 和 Møller 想到了一个好主意,那就是研究现存灵长类物种的家谱。他们的基本原理是,一些现代物种之间亲缘关系非常近,因此可能源自一个共同的近期祖先,但在交配系统或排卵信号强度方面存在差异。这意味着最近的进化变化,两位研究人员希望识别这些变化发生的节点。
以下是推理如何运作的例子。DNA比较表明,人类、黑猩猩和大猩猩在遗传上仍有约98%相同。测量这些基因变化积累的速度,加上对有年代的猿类和原始人类化石的发现,表明人类、黑猩猩和大猩猩都源于大约900万年前生活的一个祖先缺失环节。然而,这三个现代后代现在却表现出所有三种排卵信号类型:人类的隐蔽排卵,大猩猩的轻微信号,黑猩猩的显著广告。这意味着这三个后代中只有一个可能与缺失环节相似,而其他两个必然已经进化出不同的信号。
解决问题的一个强烈线索是,许多现存的原始灵长类物种——如眼镜猴和狐猴——都有轻微的排卵迹象。那么,最简单的解释是,缺失环节从一个原始祖先那里继承了轻微的迹象,而大猩猩又从缺失环节那里原封不动地继承了它们的轻微迹象。然而,在过去的900万年里,人类肯定已经失去了那些轻微的迹象,从而发展出我们目前的隐蔽排卵,而黑猩猩则进化出了更明显的迹象。
同样的推理也可以应用于灵长类家谱的其他分支,以推断其他已灭绝祖先的排卵信号及其后代的后续变化。事实证明,信号转换在灵长类历史中非常普遍。大胆的广告出现了多次独立起源(包括黑猩猩的例子);隐蔽排卵也出现了许多独立起源(包括人类和猩猩);并且排卵的轻微迹象也多次重新出现,无论是从隐蔽排卵(如某些吼猴)还是从大胆的广告(如许多猕猴)。
好的,这就是我们如何推断排卵信号的过去变化。现在,当我们把注意力转向交配系统时,我们可以使用完全相同的程序。我们再次发现,人类和黑猩猩朝着相反的方向进化,就像它们在排卵信号方面所做的那样。对现存原始灵长类行为的研究表明,6000万年前的祖先灵长类动物是滥交的,而我们900万年前的缺失环节已经转向了单一雄性后宫。然而,如果我们观察今天的人类、黑猩猩和大猩猩,我们会发现所有三种交配系统都有代表。因此,大猩猩可能只是保留了它们的缺失环节祖先的后宫,而黑猩猩则必须重新发明了滥交,人类则发明了一夫一妻制。
总的来说,一夫一妻制似乎在高等灵长类动物中独立进化了许多次:在我们人类、长臂猿和许多猴子群体中。后宫制似乎也进化了许多次,包括在缺失环节中。黑猩猩和少数猴子显然在它们的近亲祖先放弃滥交转向后宫制之后,重新发明了滥交。
因此,Sillén-Tullberg 和 Møller 已经重构了遥远过去许多灵长类动物可能共存的交配系统类型和排卵信号。现在,我们终于可以把所有这些信息整合起来,检验在我们家谱中每次隐蔽排卵进化时的交配系统是什么。
我们学到了什么呢?在考虑那些确实有排卵信号,后来又失去这些信号并进化出隐蔽排卵的祖先物种时,只有一个是一夫一妻制。其余的都是滥交或实行后宫制——其中一个物种就是从实行后宫制的缺失环节进化而来的人类祖先。因此我们得出结论,滥交或后宫制,而非一夫一妻制,是与隐蔽排卵相关的交配系统。这个结论与赫迪的“多父理论”预测一致。它与“父亲在家理论”不符。
但我们也可以问一个相反的问题:在我们家谱中每次一夫一妻制进化时,普遍存在的排卵信号是什么?我们发现,一夫一妻制从未在排卵期有明显广告的物种中进化。相反,一夫一妻制通常出现在已经有隐蔽排卵的物种中,有时也出现在有轻微排卵信号的物种中。这个结论与亚历山大和努南的“父亲在家理论”的预测一致。
这两个看似相反的结论如何调和呢?回想一下,Sillén-Tullberg 和 Møller 发现今天几乎所有实行一夫一妻制的灵长类动物都有隐蔽排卵。这个结果必然分两步发生。首先,隐蔽排卵出现在滥交或实行后宫制的物种中。然后,在隐蔽排卵已经存在的情况下,该物种转向了一夫一妻制。
或许,到了现在,您会觉得我们的性历史令人困惑。我们从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开始,它应该有一个简单的答案:我们为什么隐藏排卵,并且在一个月的任何一天都能发生性行为?然而,您得到的不是一个简单的答案,而是被告知答案更加复杂,涉及两个步骤。
归根结底,隐蔽排卵在灵长类动物的进化史中反复改变甚至逆转了其功能。也就是说,“父亲在家”和“多父”这两种解释都是有效的,但它们在我们的进化史上作用于不同的时期。隐蔽排卵产生于我们的祖先仍然滥交或生活在后宫制的时代。在这样的时期,它让祖先女性将她的性服务分配给许多雄性,其中没有一个能确信自己是她孩子的父亲,但每个人都知道他可能是。结果,那些潜在的杀婴雄性都不想伤害婴儿,有些甚至可能保护或帮助喂养它。一旦女性为了这个目的进化出了隐蔽排卵,她便利用它来挑选一个好男人,诱使或强迫他与她一起在家,并让他为她的孩子提供大量帮助。
回想起来,我们不应该对这种功能转变感到惊讶。这种转变在进化生物学中非常常见。自然选择不像工程师有意识地设计新产品那样,直线地朝着一个遥远的既定目标前进。相反,动物身上某个具有一种特征的功能,也开始服务于其他功能,因此被修改,甚至可能失去原始功能。结果是类似适应的频繁再创造,以及生物进化过程中功能的频繁丧失、转变甚至逆转。
最常见的例子之一涉及脊椎动物的肢体。祖先鱼类的鳍用于游泳,进化成了祖先爬行动物、鸟类和哺乳动物的腿,用于在陆地上奔跑或跳跃。某些祖先哺乳动物和爬行-鸟类的前腿分别进化成了蝙蝠和现代鸟类的翅膀,用于飞行。鸟类的翅膀和哺乳动物的腿随后又分别独立进化成了企鹅和鲸鱼的鳍状肢,从而恢复了游泳功能,有效地重新发明了鱼类的鳍。至少有两组鱼类后代独立失去了它们的肢体,变成了蛇和无腿蜥蜴。基本上以同样的方式,生殖生物学的特征——例如隐蔽排卵、明显广告排卵、一夫一妻制、后宫制和滥交——反复改变功能并被转化、重新发明或失去。
下次你为了乐趣而做爱时,想想这一切吧。很可能是在排卵周期的非受孕期,并且你正在享受持久一夫一妻制关系的安全感。此时,思考一下你的幸福是如何被你的生理特征奇妙地实现的,而这些特征正是你遥远的祖先所特有的,他们注定要生活在后宫或滥交之中。讽刺的是,那些可怜的祖先只在罕见的排卵日发生性行为,那时他们履行了受精的生物冲动,但由于迫切需要迅速的结果,他们被剥夺了悠闲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