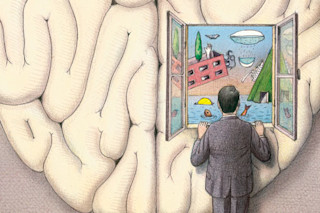玛丽莲·梦露和简·拉塞尔出现在格劳曼中国剧院外,在湿水泥上写下她们的名字,并留下她们的手印和高跟鞋印。她们跪下,肘部枕着一个天鹅绒枕头,用花体字写下“绅士爱美人”,然后是她们的签名和日期,6-26-53。但是,那些观看当天事件的人是如何在大脑的软水泥中,用神经元和突触刻下记忆痕迹,铭记下这些细节的呢?这些记忆是在哪里以及如何被写入的?拼写出颜色、气味和声音等丰富回忆的分子字母又是什么?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寻找,最近终于找到了答案,说来也巧,就在距离格劳曼八英里远的地方。虽然不在任何旅游地图上,但这个发现的地点可以从好莱坞大道向西前往日落大道,轻松抵达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校园。在那里,坐落着世界上神经科学研究设施最密集的区域之一的Gonda (Goldschmied) 神经科学和遗传学研究中心。而坐在大楼一楼餐厅“突触咖啡馆”的一张桌子旁,正是那位比任何人都想象的更接近于找到大脑中记忆写入位置的神经科学家。
那个地点,也就是特定记忆的物理基质,在脑研究中长期以来被称为记忆痕迹(engram)。几十年来,科学教条一直断言记忆痕迹只存在于庞大的连接网络中,并非存在于特定地点,而是分布在广泛穿梭于大脑的神经网络中。然而,一系列开创性的研究表明,可以将特定记忆诱导到特定神经元中,至少在小鼠中是如此。如果这些神经元被杀死或暂时失活,记忆就会消失。如果这些神经元被重新激活,记忆就会恢复。这些研究也开始解释大脑如何以及为何将每段记忆分配给特定的细胞群,以及它是如何将它们连接并组织起来的——这是普鲁斯特笔下那块引发记忆洪流的传奇甜点玛德琳的气味,通过何种物理方式引发对往事的回忆。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综合学习与记忆中心联席主任、神经生物学家Alcino Silva说:“这太令人惊奇了。在过去的一百年里,科学家们一直在大脑中寻找记忆痕迹。我们现在已经对记忆以及记忆如何形成有了足够的了解,以至于我们真的能够找到记忆痕迹,并且通过找到它,我们可以操控它。”
这项工作让人想起电影《暖暖内含光》。但与电影中金·凯瑞和凯特·温丝莱特饰演的角色完全抹去彼此记忆不同,西尔瓦和其他参与记忆痕迹操纵的研究人员认为,他们无法完全清除记忆的每一个片段,而只能清除某些部分。西尔瓦和他的同事们针对所有哺乳动物中储存恐惧记忆的杏仁形区域——杏仁体——已经证明,他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小鼠对某种音调的恐惧反应,这种音调是动物之前学会与不愉快的电刺激相关联的。小鼠是否仍然记得听到过这种声音尚不确定,但动物明显不再记得它所学到的教训——即这种特殊的音调是受到电击的前奏。
这一发现的意义为治疗人类记忆障碍带来了希望。一方面,它指明了选择性靶向那些承载着创伤性事件记忆的神经元的方法,这些事件使人们陷入困境。你无法摆脱的那个暴力袭击?使杏仁体中与此相关的神经元失活,你可能仍然记得袭击,但能从无法承受的恐惧阴影中解脱出来。据估计,每年有3.5%的美国成年人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一种有效的新疗法将标志着精神健康领域的一个里程碑。
虽然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记忆力过好,但患有阿尔茨海默病和其他形式痴呆症的人则面临相反的问题。正如西尔瓦和其他研究记忆痕迹的人已经证明能够删除记忆一样,他们也表明能够强化记忆。去年七月,西尔瓦的同事,多伦多大学病童医院的神经生物学家Sheena Josselyn报告称,她的实验室改善了培育出来具有阿尔茨海默病等效病症的小鼠的记忆力。她利用同样有效于创建和清除恐惧的工具,增强了整个大脑区域——海马体,已知海马体对形成长期记忆至关重要。
西尔瓦提出了一个他承认是“科幻小说式”的想法,他想知道治疗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医生是否“可以将记忆引导到大脑中仍保持强健的区域。特别是在神经退行性疾病中,大脑有些部分是健康的,有些则不然。如果我们找到策略将记忆导向那些仍然完好无损的部分,我们也许能够延长功能。”
通过颠覆长期以来对记忆的认知,西尔瓦和乔斯林从科幻小说的领域中开创了对记忆的新观点,在科幻小说中,个体记忆痕迹长期以来一直被主流科学家视为神经学上的独角兽和不明飞行物。
“记忆痕迹”(engram)一词由德国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西蒙于1904年在其著作《记忆》(The Mneme)中创造。西蒙断言,记忆在大脑中物理体现的巨大难题在于,普通的物体只在受到力作用时才对其做出反应,而神经系统却以某种方式被永久改变,能够在多年后对很久以前的刺激表现出独特的反应。例如,一个婴儿抓住狗的尾巴并被咬伤:咬痕会愈合,但关于不要抓住狗尾巴的痛苦教训却依然存在。这种学习能力构成了西蒙所说的“记忆”(mneme),他借用了希腊记忆女神的名字。这种能力的实际结果就是他所说的“记忆痕迹”(engram),即“由刺激造成的这种永久性变化”。如果可以将“记忆”(mneme)视为西蒙对生物硬盘的概念,那么“记忆痕迹”(engram)就是写入其中的信息字节(或者,在那个婴儿的例子中,就是被咬的“咬痕”)。
然而,寻找记忆痕迹比命名它要困难得多。1950年,著名神经学家卡尔·拉什利(Karl Lashley)在一篇题为《寻找记忆痕迹》的著名论文中描述了他详尽的努力。在长达30年的数百次实验中,拉什利训练实验室动物进行日常记忆任务,例如打开一个有闩锁的盒子,然后仔细地对它们的大脑进行小的外科损伤,以观察效果。他发现,大脑中的任何一个单一的切口都无法完全消除大鼠对迷宫路径的记忆。即使是两三个切口也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事实上,他有时可以切除大脑的整个部分,动物仍然会记住,比如说,黑色地砖和电击之间的联系。他能找到的唯一一致的效果是,动物的整体记忆能力与被破坏的神经元数量成正比下降:脑细胞损失越多,所有记忆都越弱。
“大脑的所有细胞都在不断活跃,并通过某种代数求和参与到每一个活动中。没有专门为特殊记忆保留的特殊细胞,”拉什利写道。“有限的区域可能对特定活动的学习或保留至关重要,但在这些区域内,各部分的功能是等效的。记忆痕迹分布在整个区域。”
拉什利关于记忆普遍编码但没有特定位置的观点,在三十多年间占据主导地位。然后,它在一眨眼之间就被推翻了——确切地说,是在兔子的眨眼之间。现为南加州大学心理学、生物科学和神经科学荣誉教授的理查德·汤普森,训练兔子进行所谓的瞬目条件反射,即音乐声与吹向眼睛的一股气流配对。(巴甫洛夫条件反射101:气流是“非条件”刺激,因为它不需要任何实验条件就能产生行为反应——眨眼。音调是“条件”刺激,只有当它与气流配对时,动物才会学会将两者联系起来,产生后来被称为“条件反应”的反应:对单独的音调产生的反射性眨眼,这是通过实验条件产生的。)
在1984年发表于《科学》杂志的一篇里程碑式论文中,汤普森证明,在训练兔子后,他通过手术切除了间位核(小脑的一部分,位于大脑底部附近)的数百个神经元,这些动物就不再对音调做出眨眼反应。
汤普森发现的意义很清楚:他找到了一个编码气流、音调和眨眼之间关联的记忆痕迹,首次表明破坏特定的一组神经元可以消除特定的记忆。“关键在于,”汤普森告诉我,“记忆是局部化的。眨眼条件反射存储在小脑特定区域的少量细胞中。”
但汤普森仍在思索。间位核的现象仅仅是拉什利法则的一个例外吗?那些细胞中发生了什么变化才使它们能够充当记忆痕迹?既然如此,为什么是这些特定的细胞,而不是附近的其他细胞,被征用作存储功能呢?回答这些问题需要等待更年轻一代的神经科学家。
“我妻子说我记忆力选择性很强——我只记得美好的事情。”阿尔西诺·席尔瓦在突触咖啡馆吃午餐时笑着说,他经常这样做,店里总是供应玛德琳。阿尔西诺出生于葡萄牙,在安哥拉度过童年,看起来像演员比尔·默里的西班牙裔同父异母兄弟,散发着幽默和活力,这与他在楼上进行的崇高工作形成轻松的反差。在他的记忆中,即使是父亲带他在安哥拉丛林中打猎,期间遭到反殖民叛军袭击,也是一段美好的时光。
“我大约8岁的时候,”他说。“叛军用哨声包围了我们。我父亲把我妹妹和我用厚毯子裹起来,准备把我们扔出行驶中的车辆,这样即使叛军追上吉普车,我们也不会被俘虏。然后,我们偶然遇到一个葡萄牙正规军营地,叛军就消失了。但我并不认为那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对我来说,那是一次伟大的冒险。我对安哥拉只有最美好的回忆。”在革命爆发后搬回葡萄牙,席尔瓦在16岁时决定要去美国上大学,因为,他笑着说,“那里是科学最好的地方——而且是我能去的最远的地方。”
西尔瓦仍然珍藏着宝贵的记忆,最终于1989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师从诺贝尔奖得主利根川进,担任博士后。在那里,他研究突触,即神经元之间的间隙,突触被认为是细胞层面的记忆存储部位。事实上,由于成年大脑中绝大多数神经元早已丧失分裂和增殖的能力,记忆只有通过现有神经元扩张,生长出更多与通过更多突触连接到其他神经元的枝杈,才能被刻入神经网络中。突触的不断变化的海洋就像一种计算机代码,允许信息以不同方式存储在其空间内。西尔瓦决定研究记忆,寻求其根源的细胞机制,因为他想不到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了。“记忆并非我们的一切,但几乎是,”他说。“我们是我们所获得的所有记忆的集合。我们的每一段记忆都改变着我们是谁。”
到1992年,西尔瓦在纽约冷泉港实验室获得第一个职位时,哥伦比亚大学的神经科学家埃里克·坎德尔(他将因该领域的工作获得诺贝尔奖)已在探索之中。为了追踪记忆的分子基础,坎德尔使用海蛞蝓加州海兔,这是一种神经结构简单的生物,只含有大约2万个神经元,其中许多都相当大。(人类大脑估计有1000亿个神经元。)坎德尔的巧妙策略是追踪海蛞蝓受到电击时产生的分子级联反应。根据电击的性质,它的鳃会以某种方式移动,并形成短时或长时记忆。例如,对海蛞蝓进行一次短暂的刺激脉冲,会导致其鳃收缩数分钟。这种短暂的反射总是由于被刺激神经元释放神经递质血清素引起的。血清素简单地穿过突触,暂时改变靶细胞膜中的蛋白质,导致信使化学物质(如环磷酸腺苷,CAMP)的产生。
五次相同的刺激导致了长期反应,海蛞蝓的鳃收缩了数周。在这里,细胞大量产生一种名为蛋白激酶A的蛋白质,这促使了另一种类似分子——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的产生。这两种分子共同进入细胞核,激活了第三种生物分子——CAMP响应元件结合蛋白(CREB)。坎德尔发现,CREB通过与细胞核中的DNA结合,然后开启产生大量参与记忆的蛋白质的基因,即使没有进一步的刺激,这些蛋白质也会产生。长期记忆,体现在鳃的长时间屈曲和海蛞蝓的神经结构中,是整个化学过程的最终结果。到1991年,CREB也被证明对果蝇的长期记忆形成至关重要。
西尔瓦解释说:“CREB是调控细胞内许多基因表达的‘总指挥’。当CREB被激活时,它会启动许多其他蛋白质的制造,这些蛋白质对各种事物都至关重要,其中之一就是记忆。”
1994年,西尔瓦迈出了下一步,首次证明CREB对于哺乳动物(在此例中是小鼠)维持长期记忆也是必不可少的。西尔瓦的研究表明,培育出CREB功能失调的小鼠,无法记住前一天已经学会了如何通过水迷宫,或者之前曾被放入一个特殊笼子里并受到轻微电击。如果没有功能正常的CREB,它们就如同昨天才出生一般。
“CREB改变了神经元放电的容易程度,”西尔瓦说。“当记忆准备存储时,神经元拥有的CREB越多,它就越有可能进入长期记忆模式。它使神经元更加警觉。”
西尔瓦在哺乳动物身上证明了CREB的作用后,全球数百名其他研究人员迅速加入了破解记忆过程的行列。其中之一就是年轻的博士后研究员希娜·乔斯林(Sheena Josselyn),她是一位身材娇小、红发、来自俄亥俄州的女性,对杰瑞·宋飞和汤姆·克鲁斯等流行文化偶像充满热情。(她最近发表在《精神病学与神经科学杂志》上的一篇论文同时引用了夏奇拉的畅销歌曲《Hips Don’t Lie》和史蒂文·西格尔电影《死亡标记》的片名。)
在1990年代后期,乔斯林在耶鲁大学神经科学家迈克尔·戴维斯的实验室工作时,决定观察如果不是通过移除CREB来减弱动物的记忆,而是通过添加额外的CREB来增强记忆会发生什么。
挑战在于如何偷偷地注入CREB。幸运的是,乔斯林的同事,在隔壁工作的另一位博士后比尔·卡尔莱森(Bill Carlezon,现于哈佛大学从事神经科学研究)已经开发出一种巧妙的策略,用额外的CREB来“掺杂”神经元。他的诀窍是将编码CREB的基因插入到一种疱疹病毒的变种中,这种病毒可以感染神经元而不会扩散到附近的细胞。换句话说,这种病毒充当了完美的特洛伊木马,将CREB滑入细胞之门。
乔斯林借鉴卡莱森的技术,将载有CREB基因的病毒直接注射到实验鼠大脑的杏仁核侧部——这是所有哺乳动物杏仁核中作为“恐惧中心”的区域。大鼠从手术中恢复后,乔斯林使用标准的巴甫洛夫条件反射训练了被治疗的大鼠和未被治疗的对照组,让它们将光与轻微不愉快的足部电击联系起来。一旦训练完成,每当它们看到光时,它们就会表现出夸张的惊吓反应,高高跳起。为了稀释这种效果,乔斯林使用了一种所谓的弱训练技术,即将训练课程密集安排,中间没有休息时间,这种方法此前已被证明只能产生微弱的记忆。弱训练后,CREB增强的大鼠在看到光后,跳得比正常大鼠高出五倍。
乔斯林当时意识到,CREB不仅对正常的长期记忆必不可少;它还可以作为记忆增强剂。
但乔斯林的数据存在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在她所针对的杏仁核侧部,只有15%的神经元被携带额外CREB的疱疹病毒感染。如此少量的神经元如何能产生如此显著的记忆增强呢?她论文的一位同行审稿人认为这种不一致性过于明显,以至于他质疑结果是否可靠,并敦促她投稿的期刊拒绝发表。
此后不久,即将把实验室从冷泉港搬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阿尔西诺·席尔瓦顺道拜访了乔斯林的导师。这种不期而至的拜访是他为了促进与该领域领先同事合作而养成的习惯。席尔瓦说:“今天的神经科学全是关于联系的。”
那次访问期间,三人坐下来探讨如何解释数据中的差异。西尔瓦认为,“问题”实际上可能是一个机会:一个如何利用CREB作为工具,不仅增强或抑制记忆,还能探索每段新记忆精确位置的线索——找到记忆痕迹。也许这么多年以后,真的有可能在大脑中找到记忆的真实轨迹。也许只有一小部分神经元参与记忆形成才是必要的。也许记忆形成是一种竞争性运动。CREB可能在招募那些幸运地构成我们记忆基础的神经元中发挥关键作用。
到2001年乔斯林的研究发表时,她已经接受了邀请,与她的丈夫,同样是神经科学博士后的保罗·弗兰克兰一起加入西尔瓦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团队。
在那里,乔斯林与西尔瓦构思了一项巧妙而精密的实验,以验证他们关于记忆形成的“神经元竞争”理论。首先,他们决定使用一种经过基因改造、CREB水平非常低的小鼠,这样注射额外CREB到杏仁体中产生的任何行为效应都会非常明显。然后,乔斯林和西尔瓦对乔斯林在耶鲁大学使用的疱疹病毒技术进行了改进。这次他们不仅将CREB基因添加到病毒中,还插入了绿色荧光蛋白基因。这样,任何由于感染病毒而获得额外CREB的神经元,在显微镜下也会方便地发光。
但是,为了确切知道是否只有那些拥有额外 CREB 的神经元——而且仅仅是这些神经元——存储了记忆痕迹,研究人员还藏着另一个绝招:一种方法来显示哪些神经元在回忆记忆时活跃过。
那个技巧很难实现。首先,乔斯林和西尔瓦把小鼠放进一个笼子里,每当它们听到一个音调时,就会受到电击。小鼠表现出预期的条件反射,每当它们听到这个音调时,就会因恐惧而僵住——尽管此时已经停止了电击。接下来,研究人员在小鼠听到音调并因恐惧而僵住后的五分钟内将其处死。为什么要五分钟?因为记忆一旦形成,在神经元内部,产生一种名为Arc(活动调节细胞骨架相关蛋白)的蛋白质的RNA片段就会被激活,持续时间恰好是五分钟。换句话说,在神经元内部检测到Arc,就表明在动物死亡前不到五分钟内,一段记忆刚刚在其中被激活。为了检测Arc的存在,科学家们使用了荧光标记技术,就像他们对CREB所做的那样。
好的,他们已经给小鼠的杏仁体注射了额外的 CREB,教会它们识别在受到电击时听到的音调,再次播放音调看它们是否僵住,然后立即镇静并处死它们。接下来,科学家们取出小鼠的大脑,分离出杏仁体,将其切成薄片,然后放在玻璃载玻片上。
在显微镜下,得到的杏仁核切片像圣诞树一样闪闪发光:吸收了额外CREB的呈绿色,Arc阳性的呈红色。虽然红色和绿色并不完全重叠,但乔斯林和西尔瓦确实发现,发出红色荧光(Arc活跃)的神经元比其邻居发出绿色荧光(CREB阳性)的可能性高3到10倍。这说得通,对吧?当棒球运动员服用类固醇时,他们会打出更多本垒打。CREB,本质上是一种记忆兴奋剂,就像神经元的类固醇一样。
但这正是事情变得异常之处。想象一下,如果本垒打王巴里·邦兹、亚历克斯·罗德里格斯和萨米·索萨涉嫌使用类固醇并开始表现更好,而他们没有服用类固醇的队友实际上开始表现得更差。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正是神经元竞技场上发生的事情:没有因CREB而发绿光的神经元,其因Arc而发红光的可能性,大约是富含CREB的同类神经元的十二分之一,这意味着它们根本没有参与记忆痕迹的形成。
西尔瓦和乔斯林最终得出结论,神经元之间的记忆存储是一个零和游戏。CREB 通过提高拥有者和非拥有者之间的对比度来帮助形成记忆,而不是通过使所有神经元更强壮。
“成功还不够;别人也必须失败,”乔斯林引用戈尔·维达尔的话说。
乔斯林碰巧喜欢汤姆·克鲁斯。“他的电影《危险事业》改变了我的生活,”她说。乔斯林穿着运动鞋和一件褪色的俄亥俄州立大学T恤,坐在多伦多大学病童医院的小办公室里,她的办公室斜对着她丈夫的办公室。(去吃你的心吧,克鲁斯先生。)2003年7月,他们一起离开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前往多伦多,在那里他们各自拥有了自己的实验室,并被任命为神经科学助理教授。现在她办公室门旁立着一根“节礼日柱”,她在12月用它来举办办公室派对,庆祝《宋飞正传》中描绘的虚构的世俗节日。
乔斯林说,当他们到达多伦多时,她和弗兰克兰合作进行了一项研究,旨在对富含CREB的记忆痕迹进行下一步操作:将其杀死。他们认为,如果含有额外CREB的神经元对于维持记忆确实至关重要,那么消除这些神经元也应该消除记忆。但是,与汤普森在1980年代通过手术切除的间位核中的神经元不同,那15%富含CREB的神经元并没有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可以用手术刀靶向的区域。相反,它们均匀地分散在杏仁体周围。挑战在于:如何在不破坏周围神经元的情况下杀死它们。
为此,乔斯林和弗兰克兰寻找除了CREB之外,还可以添加到疱疹病毒中的物质,这种物质最终会导致受感染的神经元死亡。最终,他们的一位合作者,神经生物学家史蒂文·库什纳,了解了一种利用白喉毒素选择性杀死神经元的新技术。小鼠天生不携带允许毒素进入神经元的受体,但猴子携带。通过将白喉受体的猿猴基因添加到同时携带CREB基因的疱疹病毒中,科学家们现在拥有了一种只杀死那些同时含有额外CREB和毒素受体的神经元的方法。
以白喉作为他们的“定时炸弹”,团队再次对小鼠进行听觉恐惧条件反射训练。一如既往,注射了携带CREB基因(以及毒素受体)病毒的动物学习得更好,表现出比没有注射的动物更多的恐惧。正如预期的那样,当这对夫妻研究团队给小鼠注射白喉毒素,选择性地杀死那些同时含有额外CREB和毒素受体的神经元时,小鼠在听到音调时不再僵住。乔斯林和弗兰克兰成功地引发了选择性遗忘——这一历史性发现使他们离找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治疗方法又近了一步。
一年半后,乔斯林在神经科学学会年度大会上,与西尔瓦共同主持的“记忆机制”研讨会上,介绍了这些及其他发现。座无虚席的人群,包括数百名神经科学家,对他们可能最终拥有比谈话疗法更好的工具来治疗数百万因创伤记忆而致残的退伍军人和其他人这一想法感到兴奋不已。一扇门已经打开:恐惧的记忆痕迹已被找到。它被CREB强化,又被白喉毒素清除——现在,一条通往人类实际治疗的道路正在招手。
就连席尔瓦和乔斯林都不认为人类受试者会很快接受注射含白喉毒素的CREB。“这是一项非常有趣的工作,但对于临床治疗患者并不实用,”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的神经科学家丹尼斯·帕雷说,他也在研究药理学方法来操控恐惧记忆。“这些是你在人类身上无法进行的实验操作。”
西尔瓦对此表示赞同,但他对将他与乔斯林的研究转化为有效治疗的前景仍保持谨慎乐观。“我们无法修复我们不理解的东西,”他说。“长期以来,我们对记忆在大脑中的物理表现,也就是记忆痕迹,一无所知。我们现在知道CREB在决定记忆去向方面发挥作用。我们可以操控CREB,将记忆导入特定的细胞。”
小鼠对单一恐惧事件的记忆是一回事;人类记忆的复杂联想,由密集的神经元连接网络驱动,则是另一回事。“我们正在研究一种非常简单、基本的记忆,”乔斯林承认。“对于小鼠,你不能问它们,‘你还记得我们昨天把你放进的那个笼子吗?’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观察它们的行为,看它们是否学到了什么。更复杂的记忆,比如对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件的回忆,存储在大脑的许多不同区域。但即使是为了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我们也不想完全消除记忆,只想消除让你因恐惧而致残的那部分。而这部分来自杏仁体。”
因此,卡尔·拉什利关于记忆存在于分布式网络中的信念仍然存在且运转良好;西尔瓦和乔斯林并未推翻它,只是对其进行了补充,表明某些记忆的某些部分确实存在于离散的神经元中。
至于将CREB作为记忆增强剂的实际应用,乔斯林正在探索——但持谨慎态度。早在20世纪90年代,当CREB研究刚刚起步时,一家名为“记忆制药”的公司投入数百万美元,致力于开发一种能延长CREB作用的药丸。但这家公司,以及其他押宝于所谓“智能药丸”的公司,都没有取得什么好结果。
乔斯林说:“人们原以为现在市面上会有这种药丸了。公司成立又倒闭,试图找到这种药丸。这个领域在初期曾欣喜若狂。结果证明,记忆真的很难强化,尤其是在人类身上。”
然而,谨慎的进展正在取得。乔斯林迄今为止最令人兴奋的发现,发表于去年七月《神经精神药理学》的研究,涉及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小鼠。当她的团队使用基因工程疱疹病毒将CREB注射到动物的海马体中时,这些小鼠恢复了学习能力。
类似的程序能否用于将CREB输送到人类大脑中?“这有可能,”乔斯林说。“原理是存在的,但我们需要更精细的工具。疱疹病毒可能不是人类的好选择。但我们做这一切并非只是为了提高小鼠的学习能力。我们想弄清楚人类是如何学习和记忆的,以及当他们无法做到时我们如何帮助他们。”
对于我这中年人的大脑来说,突破越快越好。在洛杉矶与席尔瓦会面结束时,他提出送我到车边。然而,讽刺的是,我竟然想不起自己把车停在了哪里,某个地下停车场的后街。席尔瓦下定决心要帮忙,他陪着我沿着韦斯特伍德广场寻找,经过塞梅尔神经科学与人类行为研究所,经过里德神经病学研究中心,经过艾哈曼森神经生物学实验室——这些地方对我来说都没半点用处。再往前走,我们就会走到格劳曼剧院前,在那里,玛丽莲和简的手印比我的记忆保持得好多了。
就这样,我们像两只迷失在迷宫中的老鼠一样,在街上行走,记者和世界上顶尖的记忆研究者之一,他努力帮助我回忆。
丹·赫尔利是《糖尿病崛起:一种罕见疾病如何演变为现代流行病及其应对之道》一书的作者。他住在新泽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