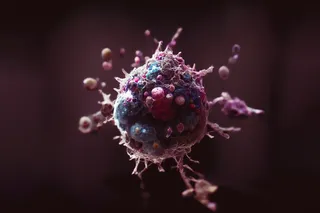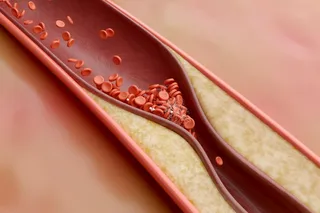图片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提供。唐纳德·亨德森在炭疽病开始侵入邮政系统很久之前就开始担心生物战争。作为乔治·布什的科学顾问以及克林顿政府的高级卫生官员,他亲身了解了我们国家的脆弱性。1995 年,他继续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进行生物恐怖研究,并担任该校的平民生物防御研究中心主任。如今,亨德森已成为新成立的联邦公共卫生防御办公室主任,该办公室将协调全国应对健康紧急情况的行动。在霍普金斯大学的办公室里,他与《Discover》杂志记者 Rabiya S. Tuma 分享了他的见解。
是什么让您早期就关注生物恐怖主义?1995 年之前,生物恐怖主义被认为是不可能发生的。然后发生了三件事。首先,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释放了沙林毒气。人们发现他们一直在研究炭疽病和肉毒杆菌毒素,并试图在东京市中心空气中播撒炭疽病。与此同时,萨达姆·侯赛因的女婿叛逃,并带回了显示伊拉克细菌战项目规模惊人的文件。但真正令人担忧的事件是发现了苏联生物武器项目的规模。其规模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涉及 6 万人在 50 个不同的实验室工作。其规模可与他们的核计划相媲美。
自那时以来,我们的生物袭击防御能力有所提高吗?最晚到 1998 年,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在该领域没有人负责。同样,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也没有相关计划,没有人负责,也没有拨款。现在,CDC 确实有生物防御计划,NIH 也有一个专门的研究项目。所以我们有所改进,但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的薄弱环节在哪里?我们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非常薄弱。我们依赖它每天 24 小时、每周 7 天正常运转——就像消防部门一样——所以如果有人报告了非常奇怪的事情,公共卫生部门应该能够迅速介入并进行确认、诊断、检测其他病例并制定控制措施。但几十年来,我们任由基础设施恶化。而且,有很多事情可以加速研究过程,这样当我们发现一种生物制剂时,我们就能非常迅速地开发出抗生素或抗病毒药物或疫苗。这些药物也将有助于应对自然传染病,特别是新兴传染病。
什么会成为一种特别有效的生物武器?显然,理论上几乎任何引起感染的病原体都可以用作武器。但以普通流感为例,我们每两三年就会发生一次疫情;虽然有很多人生病,其中一些人死亡,但城市仍然在运转。我们研究了那些比其他病原体更具破坏性的病原体,无论是由于它们造成的死亡,还是由于它们传播恐慌的能力。我们确定了六个主要候选病原体:天花、炭疽病、鼠疫、肉毒杆菌毒素、兔热病(一种引起发热的疾病)和出血热(一种病毒性出血性疾病,包括埃博拉)。
您曾为消灭天花而奋斗,但现在人们却将其列为潜在武器。这是怎么发生的?我非常、非常痛恨苏联。1959 年,苏联向世界卫生大会提议,由世界卫生组织负责消灭天花。在该计划期间,俄罗斯政府每年提供 2500 万剂高质量的疫苗。他们对自己能在消灭计划中发挥重要作用感到非常自豪。1980 年,我们在大会上宣布天花已被消灭。我们说服各国政府和实验室销毁他们的储存,他们也这样做了——将储存转移到美国和俄罗斯的两个地点之一。然后,从 1994 年到 1995 年,俄罗斯人在做什么变得显而易见:他们一直在武器化天花。与我共事的人对此一无所知;是军方在推动武器化计划。
恐怖分子在商场或棒球场造成大范围感染有多难?我们的一些同事一再表示,识别出致命病原体、获取它、培养它、将其制成合适的形态并进行播撒有多么困难。但我敢打赌,你可以造成很多麻烦,造成数万人伤亡并非不可能。而且,谁能说恐怖组织买不到已经准备好并可供使用的生物武器材料呢?毕竟,那些驾驶飞机撞击世界贸易中心的恐怖分子,并不需要知道如何建造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