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迪丝·博恩博士决定不哭。
在1956年这个秋天的下午,她七年的单独监禁突然结束了。在监狱大门外,匈牙利革命的最后零星枪声在布达佩斯的街道上回荡。在大门内,博恩走出监狱的前门,进入院子里令人眼花缭乱的阳光中。她68岁,身材矮胖,患有关节炎。
博恩于1889年出生在布达佩斯,事实证明她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尽管不听话。她想成为像她父亲一样的律师,但这个职业对女性是关闭的。她的选择是女教师或医生;她接受了后者。
她毕业后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于是她去了一家军事医院工作。也许是在那里,目睹了下层人民的苦难,她的共产主义同情心萌芽了:她看着一个不识字的罗马尼亚士兵,战前是一名牧羊人,他在窗边哭了几天,抱着一只破碎的手臂,担心着他失散的孩子们。他只是众多破碎的人中的一个。
战后,博恩在英格兰致力于政治工作长达16年,正是这种外国联系在她1949年返回共产主义布达佩斯时引起了当局的怀疑。在她返回英格兰的途中,秘密警察在机场拦住了她。
在总部内,一个身材苗条的男人现身,衣着考究,举止得体。他把她带进一间小办公室,告诉她他们知道她是一名间谍,是英国特工处的特工。“除非你告诉我们你的指示是什么,否则你不能离开这栋大楼。”
博恩回答说:“既然如此,我大概会死在这里,因为我不是特工处的特工。”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她七年零五十八天的单独监禁——是恐怖电影的素材。她被关在肮脏、冰冷的牢房里;墙壁要么滴着水,要么长满了真菌。她通常处于半饥饿状态,除了与警卫对峙时,总是被隔离。二十三名训练不足的警官对她进行侮辱和威胁的审讯——有一次长达60小时。有六个月的时间,她完全陷入黑暗。

(图片来源:María Victoria Heredia Reyes/Unsplash)
María Victoria Heredia Reyes/Unsplash
然而,她的囚禁者没有得到任何虚假供词,也没有求饶;他们唯一的收获是她傲慢回答的记录。对博恩来说,在偶尔见到狱警时惹恼他们成了一种消遣。
但是博恩最非凡的策略并非她戏弄囚禁者的方式,而是她掌控自我的方式——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理智。从那个被迫的虚空中,她缓慢而稳定地为自己建立了一个无法被摧毁或剥夺的内在世界。首先,她背诵诗歌,将她烂熟于心的诗句翻译成她的六种语言。然后她开始创作自己的打油诗。其中一首,是在那六个月没有光线的时候创作的,赞美了她心智“黑暗中诞生的魔杖”的救赎力量。
受到她在托尔斯泰故事中记得的一个囚犯的启发,博恩在想象中漫步于她去过的所有城市。她在巴黎、罗马、佛罗伦萨和米兰的街道上漫步;她参观了柏林的蒂尔加滕和维也纳的莫扎特故居。后来,当她的脚在床边的水泥地上磨出一条窄窄的凹痕时,她心里想着回伦敦的旅程。她每天走一定的距离,并心记她停下来的地方。她完成了四次旅行,每次到达海峡时都会停下来,因为她觉得游泳太冷了。
博恩的警卫被激怒了,但她证明自己擅长独处。他们将她与世界隔绝,而她则施展这种艺术,选择平静而非疯狂,慰藉而非绝望,独处而非囚禁。博恩非但没有被摧毁,反而从监狱中走出来,用她的话说,“变得更睿智,充满希望。”
我觉得她的故事很了不起。随着我对她对待单独监禁的态度——以及她忍受它的无底能力——越来越熟悉,我感到一种羡慕之情悄悄涌上心头。我当然不是羡慕她的处境。但我羡慕她的才能。即使是读她的故事所需的几个小时独处对我来说也很难忍受。
如何独处。以及为什么。
我心想,这其中一定有门道。一种特定的实践,或炼金术,能将寂寞转化为独处,将空虚的日子转化为空白的画布。一种失落的小技艺,年复一年,在未来的苍白光线下逐渐消逝。
思想上的冲击
“对不起,朱莉,但这是事实——人们对‘独自思考’感到‘恐惧’,”我说,“我读过一项研究,受试者宁愿给自己‘电击’也不愿独自思考。”
那是2015年的夏天,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半空置的校园里花团锦簇。朱莉——我在校园里偶然遇到的一个老朋友——怀疑地瞥了我一眼,说她完全能够独自思考。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她走出玫瑰园去寻找咖啡因。我对着植物们怒目而视。

(图片来源:Agsandrew/Shutterstock)
Agsandrew/Shutterstock
这项研究是真实的。它于2014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作者是弗吉尼亚大学教授蒂莫西·D·威尔逊和他的团队。他们的研究表明,如果我们独自一人,大多数人在六到十五分钟后就会开始失去理智。电击是可以接受的,尽管疼痛,因为任何东西——任何东西——都比人类大脑在无人干扰时开始做的事情要好。
我们是这样认为的。
事实上,在没有对抗性外部刺激(嗡嗡作响的电话、吱吱作响的人群)的情况下,大脑会做什么呢?它会做白日梦。我故意让它听起来很温和。“白日梦”是一个如此柔和的词。然而它指的是一种我们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学会像对待不雅思想一样压制的心境。也许我们压制它是因为害怕白日梦与“游手好闲”的罪过有关。至少从中世纪开始,就一直存在一场反对懒惰的持续运动,懒惰被认为是万恶之源。
如今,在我过去做白日梦的那些间隙时间,比如公交车上、淋浴时或散步时,我被一种罪恶感和悄悄的绝望所困扰——一种恐慌的需求,要阻止我的思绪独自游荡太久。大脑必须得到利用。
我来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是为了探究白日梦的重要性以及原因。该校是认知神经科学思维实验室的所在地,他们的专长之一是“无方向性思维过程”,这是白日梦和心智漫游的行话。
他们的研究由志愿者提供支持,这些志愿者在白日梦期间接受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脑部扫描。今天的大脑——我们称她为海莉——到了,并被立即问及体内是否有金属(MRI机器,除其他外,是极其强大的磁铁)。她报告说自己没有金属,于是得到了一对耳塞——事情将会变得异常嘈杂。
海莉被安置在滑动床上,技术人员将一个“鸟笼”戴在她头上。实际上是这个鸟笼进行扫描。她现在被滑入的巨大灰色甜甜圈只是为了产生一个均匀的磁场;鸟笼绘制的是大脑偏离该磁场的情况。
当技术人员打开扫描仪时,声音震耳欲聋。最终,她的思绪习惯了噪音,并做了任何没有新刺激的思绪都会做的事情——它开始游荡。她的白日梦时刻被绘制出来,数据需要六个小时来处理。然后,砰:一幅用电蓝色和红色描绘的白日梦画像。
意想不到
最终,这些图像只能给我们一个非常粗略的白日梦者思维状态的 ধারণা(概念)。尽管90分钟的会话花费了900美元,但它产生的是一张儿童画,一个试图表现860亿个神经元舞蹈的粗浅尝试。(如果我给你看一张被迷住的人或受惊的人的脑部扫描图,你又能真正了解爱情或恐惧多少呢?)一位头发蓬松的博士生马特·迪克森这样向我描述:“你知道,这就像我们得到了某物的遥远快照——它是真实的,但很模糊。在这张图中,我们每两秒钟看到大脑中发生的事情,但大脑实际上每百分之一毫秒都在变化。”
我们确实得到了一些有启发性的暗示。我们现在知道,当大脑停止关注外部世界但保持清醒和警觉时(换句话说,当它开始做白日梦时),它会激活一种叫做默认模式网络(DMN)的东西。默认模式绝非昏迷体验。南加州大学的玛丽·海伦·伊莫迪诺-杨领导的一项关于DMN的研究综述发现,当我们直接关注事物时,一种特定的神经处理方式会被抑制,而当大脑切换到默认模式时,它就会出现。这种做白日梦的DMN活动处理个人记忆并导致身份形成。

(图片来源:Agsandrew/Shutterstock)
Agsandrew/Shutterstock
白日梦构成了一系列强烈而异质的大脑功能。然而,这种勤奋的活动在意识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进行着。我们的思想(有时是真正“伟大”的思想)在我们没有预料或理解的情况下出现。它们是突如其来的。白日梦可以是漫无目的的幻想、复杂的计划或创造性思想的产生。但是,无论其用途如何,其产物都是不请自来的。你可以称之为一种非自主过程,就像心脏的跳动。
当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实验室的创始人卡琳娜·克里斯托夫还是学生时,研究自发思想和心智漫游并不受待见。她仍然认为她的同行的工作对它抱有偏见:“我们的文化在所有事情上都高度重视控制,”她告诉我。缺乏控制被认为是低劣的,因此失控的思维变得可疑。
又是那些游手好闲的手。
不加审查
克里斯托夫是一位身材娇小的女士,目光平静,与她有条不紊的声音相得益彰——这种自信使她受益匪浅。即使在本科阶段,她的兴趣也与同龄人不同。当他们想研究分析思维时,她更喜欢给人们“洞察力问题”——没有明确答案的问题——需要一个“顿悟时刻”才能解决。例如,克里斯托夫可能会给参与者一个装有蜡球的玻璃管,然后递给参与者一堆物品,告诉她在不打破玻璃的情况下取出蜡。参与者必须通过找到回形针或废纸片的新用途来“顿悟”出一个答案。克里斯托夫喜欢观察那些顿悟,她不需要核磁共振机就能看到。她告诉我:“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当人们走向解决方案时,完全缺乏传统的逻辑。”漫游的思维也能解决现实世界中的问题。
我们倾向于将解决问题视为朝着预定和必然的答案采取逻辑步骤。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掌握了事物的控制权。但克里斯托夫发现,人们解决她的洞察力问题,反而通过一种实际上非常诗意的联想过程。参与者得出的解决方案绝不能通过严格的逻辑推导出来。(字谜是洞察力问题的常见例子,例如,“sta4nce”是什么意思?答案:“for instance”。)克里斯托夫发现她周围几乎没有人对人类独创性的这个“黑暗”领域感兴趣。
“那是一片未知的领域,”她说。
在斯坦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在剑桥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后,克里斯托夫来到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并成立了她的实验室。当最初的脑部扫描数据涌入时,她把大脑想象成一个依靠对立力量运作的肌肉系统。例如,要弯曲手臂,你弯曲一块肌肉,同时放松另一块——伸直手臂则需要相反的操作。同样,克里斯托夫对一个调适良好的大脑的新愿景包括专注力和意识流之间的相互作用。过度锻炼其中一个或另一个都会损害整个系统的功能。她告诉我:“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总是被鼓励练习专注,但我们却不被鼓励进行我们在独处时体验到的广泛的思维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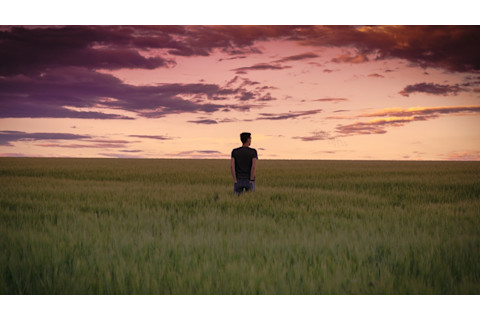
(图片来源:Maxim Smith/Unsplash)
Maxim Smith/Unsplash
给予足够的独处和时间,思维会进入默认模式,并浏览起初看起来完全随机的联系。它以一种我们可能永远不会选择娱乐的好奇心和开放性来探索问题。但这种随机性至关重要。克里斯托夫说:“漫游思维的力量,恰恰在于它不审查任何事物。它可以建立你原本永远不会建立的联系。”
白日梦是一个内在的创造性过程,她说,因为白日梦者对奇特的新选择持开放态度。通过这种独自思考的方式,揭示了在更大文化中尚不存在的新见解和方法。相比之下,分析性思维,逻辑思维,都是关于排除和批判思想,这样大脑才能成为一个精准的手术激光。我们的学校训练我们使用的有意识的分析性思维方式,总是压制白日梦思维可能尝试的奇特或不受欢迎的想法。
“分析性思维非常适合在定义明确的问题中权衡选择,”克里斯托夫说。但这种力量也是它的弱点。“分析性思维与灵感背道而驰,”她补充道。
孤独的天才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著名地注意到了大脑中职责的这种分离。他认为,白日梦思维连接事物的能力,实际上是我们通往新思想的唯一途径。可以说,这就像一条装配线,知识和对话从一开始就源源不断地涌入,然后在后续阶段,是一段寂静和白日梦。工厂的这两端对于生产关键产品——洞察力——都是必不可少的。
艾萨克·牛顿几乎完全在隔离中从事自己的研究。孤独的童年让他在剑桥度过了一段不满意的时光,那里仍然教授着荒谬的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但随后,在1665年,瘟疫袭击了剑桥——这也许是那场灾难中唯一美好的事情——牛顿被迫退隐到他家在伍尔索普的农舍。正是在那里,在被迫离开大学社区的情况下,牛顿发现了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正是在那里,在一个花园里,而不是在一个演讲厅里,他看到一个苹果落下,并思考为什么。
爱因斯坦和牛顿等物理学家是我们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们特别清楚孤独对深入思考的意义。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研究员费利西蒂·梅勒批评新一代高级研究机构,认为它们强调合作和社交氛围,却牺牲了这种独自沉思。诺贝尔奖得主、大型强子对撞机的教父彼得·希格斯支持梅勒的观点,称他开创性的工作在今天是不可能完成的,因为他1960年代享受的宁静和独处已经消失。我们只能想象,过早的分享可能会如何削弱统一场理论,或者扭曲伽马射线暴起源的解释。
对于机构如此,对于个人亦是如此。我们每天都能证明,独处的时刻能让游离、不集中的思绪获得灵感。和别人一样,我更好的想法总是在清晨,甚至在床上,世界还没给我带来任何噪音或烦恼之前,就冒出来了。洗澡时,一个新奇的想法可能会击中我。这就像大脑被允许拥有它的天才时刻,然后我们笨拙、官僚化的“思维观念”才打上领带,碍手碍脚。
当我们继续谈论这一切时,克里斯托夫转向了令人惊讶的哲学层面:“如果我们的生活方式有时让我们感到空虚,”她告诉我,“那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被放任自流,我们不允许自己仔细思考事情。我们被剥夺了那种心智漫游可以产生的意义感和幸福感。”长时间凝视雨水打湿的窗户,可能与快速眼动睡眠一样,是巩固我们思想的关键。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备受赞誉的心理学教授艾莉森·戈普尼克将这一概念推向了更深层次。她认为,我们从“顿悟时刻”获得的愉悦感,相当于思维的性高潮。性高潮的愉悦,毕竟只是我们身体用来确保我们繁衍后代的一种激励性伎俩;同样,“顿悟”的愉悦可能也内置在我们的DNA中,以确保我们更多地了解世界。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鼓舞的想法。如果我们的进化是为了从新鲜联系形成的时刻获得巨大的愉悦,那么让我们的思维漫游就不再是一种有罪的放纵——它对我们的成功和生存至关重要。
我们的蓝图要求如此。
摘自Michael Harris的《Solitude》。版权所有 © 2017 作者,经圣马丁出版社许可转载。
[本文最初以“让你的思想漫游”为题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