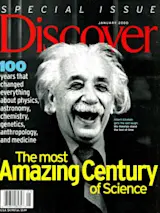1979年,我刚进入普林斯顿大学读研究生时,一位高年级学生警告我,在数学系会遇到很多奇怪的人物。他说,其中最奇怪的是一个幽灵般的人物,人称纳什。接下来的几周里,我偶尔会看到纳什穿着破旧的外套和鲜红的运动鞋在走廊里蹒跚而行,或者独自坐在食堂里,眼神呆滞地望着远方。但我最强烈地感受到他的存在,是他晚上在黑板上写的那些毫无意义的信息。这些信息通常以数学方程的形式出现,但它们与数学的关系,就像猫在钢琴上乱走与音乐的关系一样。
有一天,一群学生下课后围着一位教授聊天,有人问起了这个神秘人物。教授压低声音告诉我们,纳什曾经是约翰·纳什,是普林斯顿大学有史以来最优秀的数学学生群体中最耀眼的人物。在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约翰·纳什的发现——纳什均衡、纳什嵌入定理——至今仍被同行们每天使用,尽管他们避开纳什本人。但后来,不知怎的,他失去了对现实的把握。他开始相信自己收到了来自外太空的信息,并且有人对他进行了巨大的隐秘阴谋。
现在,在约翰·纳什被数学界“遗失”四十年后,数学本身可能掌握着治疗精神分裂症的关键,这种精神疾病曾将他的思想困住。一种新的形状分析方法,称为形态计量学,可能使医生能够在精神分裂症患者失去与现实的联系之前,判断他们大脑中发生了哪些变化。形态计量学也为胎儿酒精综合征和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提供了线索,并提高了脑外科医生规划精细手术路径的能力。在大脑研究中,未来的形状,字面上就是形状。
密歇根大学的统计学家弗雷德·布克斯坦(Fred Bookstein)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将形态计量学发展成一门定量科学。他说,这个基本思想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纪德国艺术家阿尔布雷希特·丢勒(Albrecht Dürer)的作品。也许是受到透视几何学最新发现的启发,丢勒尝试在他的肖像画中的面部上画上网格线。通过移动线条,同时保持面部的特征相对于网格在相同位置,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面部,将粗犷的额头变成倾斜的额头,将虚弱的下巴变成方下巴。
布克斯坦对丢勒主题的现代变体——四张小小的趣味屋脸——从他办公室外面的公告板上向下凝视。一张是布克斯坦的照片,看起来像比利·克里斯托尔(Billy Crystal)的严肃版本;另外三张是“非弗雷德”(not-Freds)——根据第一张照片生成的电脑漫画。为了制作漫画,布克斯坦首先将他的照片扫描到电脑中。然后,他在脸上的13个“地标点”上附上一个网格,例如额头顶部和耳朵尖。完成后,他只需移动几个地标点,从而迫使网格变形弯曲,就像一块薄金属板附着在上面一样。事实证明,工程师们多年来一直在使用这种“薄板样条”(thin-plate splines)。但正是布克斯坦意识到,这些复合图像是表示形态计量学家所谓的“形状空间”变化的完美方式——并且可以检测大大小小的形状差异。
形状是一个令人惊讶地难以捉摸的概念。诚然,人类在辨别形状细微差异方面拥有非凡的能力。否则,就不可能在拥挤的地铁站里认出朋友,或者快速区分时尚的裙子和过时的裙子。但描述形状差异总是会遇到问题。以海马体为例,它是大脑中与长期记忆形成相关的一个区域。对布克斯坦来说,它像一个“卷轴,一本部分展开的《妥拉》”。与我交谈的另一位神经科学家说,它“基本上看起来像一把茶匙”。而为它命名的人体解剖学家则认为它像一匹海马(hippocampus在拉丁语中意为“海马”)。
现代科学需要比这更精确地描述形状。“形态计量学为你提供了一种谈论形状的语言,”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吉姆·罗尔夫(Jim Rohlf)说。罗尔夫是形态计量学分析最广泛使用的计算机程序集的作者。“你可以说这种形状像那种形状,只是这里扩张了,那里压缩了。”即便如此,罗尔夫说,形态计量学不仅仅是漂亮的图片。它还有一个统计理论核心,解释了为什么薄板样条是表示形状空间差异的最佳方式。
布克斯坦的办公桌里藏着一张“非弗雷德”的照片,它比其他照片更能说明形状的细微变化会带来多大的不同。他办公室外公告板上的“非弗雷德”们看起来都像是可爱的大傻瓜,而这张照片上的却令人毛骨悚然。他没有傻笑,而是扁平、略带嘲讽的嘴唇;他没有圆鼓鼓、梨形的脸,而是宽大的鼻子和令人不安的宽眼距。布克斯坦把这张照片留在身边,也许是为了提醒自己正常与异常之间那微小的距离。对于局外人来说,它也令人毛骨悚然地回荡着一个事件,正是这个事件激发了布克斯坦将形态计量学应用于精神分裂症的个人动力。
1980年,布克斯坦的一个侄子“听到脑海中的声音”,从大学回家后试图杀害他的父母。幸运的是,他被诊断出患有精神分裂症并及时服药,避免了一场悲剧。但他的治疗漫长而缓慢,即使是今天,他对自己生命中某些年份发生的事情也没有记忆。
布克斯坦后来了解到,他侄子的故事出人意料地典型。尽管精神分裂症患者并不特别倾向于暴力,但他们中的许多人会听到幻听、产生幻觉,或患有夸大妄想、被害妄想,或两者兼有。一位康复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称她在精神病院的经历是“旋转门”,许多其他人甚至在精神病发作间歇期也无法与人交往。据估计,大约10%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会自杀。然而,尽管症状剧烈,精神分裂症通常会悄然袭击受害者。目前尚未确定精神分裂症的单一病因,大多数精神分裂症患者直到青少年晚期或二十岁出头才会首次“精神病发作”。此外,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大脑形状与正常人并没有任何一致的变化——至少肉眼是看不出来的。
形态计量学登场了。大约五年前,受到侄子不幸遭遇的刺激,布克斯坦研究了14名精神分裂症患者和14名非精神分裂症志愿者(或称“对照组”)的大脑扫描图,这些扫描图由他的同事约翰·德夸多收集。他给每个大脑标记了13个关键点,将这些关键点转换为形状,并取了平均值。
乍一看,很难区分正常形状的平均大脑图像和精神分裂症患者平均大脑图像。但当布克斯坦使用薄板样条比较正常人与精神分裂症患者时,差异就显而易见了。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胼胝体后部的一个小三角形区域似乎肿胀了,胼胝体是大脑皮层两侧所有通信的中央导管——就像大自然抓住了一些关键点并将它们推开以创造一个漫画。由于胼胝体的形状在健康人中几乎没有变化,即使是这种轻微的肿胀也具有统计学意义。
“我真的想看看我是否能以某种方式帮助那些患上精神分裂症的人,”布克斯坦指着肿胀的胼胝体说。“如果这个模式是正确的,它将使我能够在[他们第一次精神病发作]之前找出谁将患上这种病。”如果医生知道哪些患者表现出精神分裂症的迹象,他们可以尝试提前开药。至少,患者可以得到建议,避免饮酒和成瘾药物,这些都会使疾病复杂化。
布克斯坦关于精神分裂症的研究仍然领先于主流思想。话又说回来,他的思维总是比别人快一点。“我有点神童,”他实事求是地指出。11岁时,他自学了图书馆里的代数。14岁时,他赢得了全州数学竞赛,15岁时进入密歇根大学。他三年就读完了大学,然后去哈佛大学攻读数学研究生。
他似乎准备进入数学的最高境界。但在哈佛,这位自学成才的数学天才突然发现自己再也不能随意发挥自己的解法了。“我坚持了大约四周,就意识到这行不通,”布克斯坦说。“我将成为一名糟糕的数学家。”他转攻社会学,但情况也好不了多少。他所有的研究想法要么过于雄心勃勃,要么过于离谱。他笑着回忆起当他提交一份利用广义相对论数学测量社会变革的提案时,他的论文委员会的想法:“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我们知道这不是社会学。请找点别的事情做吧。”
工作了几年后,布克斯坦听说密歇根大学有一个针对有奇思妙想的古怪学者的项目。在200名申请者中,他是被选中的七人之一。回到安娜堡,他们仍然记得八年前的那个神童。1974年布克斯坦回到那里时,他带着一个典型的宏伟计划——要提出一个数学上正确的形状理论。
如今,和布克斯坦交谈仍然是一次紧张的经历,尽管他说自从他和妻子伊迪丝一起经营民宿以来,他已经放松了很多。“他讲课时,信息传输速度非常快,”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古生物学家、自称新形态计量学“促进者”的莱斯利·马库斯(Leslie Marcus)说。“就像嘴里塞了一根消防水带。”确实,布克斯坦说话很快——句子组织得天衣无缝,仿佛在引用书中的段落——打字速度甚至更快。看着他在电脑工作站上操作一个三维大脑图像,足以让人眩晕。
这种令人望而生畏的风格,以及形态计量学背后高深的数学,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医生们迟迟不采用他的技术。“形状测量有什么阻碍?它是一个更难的概念,”哈佛医学院形态计量学分析中心的神经科学家大卫·肯尼迪(David Kennedy)说。“如果我说海马体的体积是13立方厘米,我们都知道我的意思。如果我谈论球谐函数或薄板样条,临床医生就不明白这在生物学上有什么意义。”
由于磁共振成像(MRI)为大脑研究提供了窗口,精神分裂症研究领域如今蓬勃发展。但许多研究人员并未意识到他们需要全新的形状理论来解释MRI扫描所揭示的信息。大多数研究人员,像肯尼迪一样,仍然偏爱研究体积。“老实说,体积测量做得相当不错,”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神经科学家保罗·汤普森(Paul Thompson)说。除其他外,研究人员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海马体通常较小,而一些脑室(大脑中央充满脑脊液的四个腔室)则较大。
逐一测量
形状分析的一些用途听起来令人不安地熟悉。毕竟,在19世纪,颅相学家发表了大量文章和书籍,声称证明了“低劣”种族的大脑比“理想”的大脑更小或形状不同。(那个理想,恰好与研究人员的种族和国籍相同。)时代变了吗?还是形态计量学仅仅是带着MRI扫描仪的颅骨测量学?
根据布克斯坦的说法,现代形态计量学——以及所有统计学——完整性的真正保证在于严格遵守某些防范偏见的措施。这就是几乎任何科学论文中都能找到,但很少在大众媒体中报道的细则。
一项现代常规预防措施,是百年前从未实践过的,被称为“盲法”。例如,在他的研究中,比较了胎儿酒精综合征患者的大脑与正常大脑,图像经过编码,因此布克斯坦在标记地标点时不知道哪些患者患有该综合征。如果布克斯坦知道,他的偏见可能会导致他得出错误的结论。“我真的希望综合征患者的胼胝体更窄,”他说,因为这可能导致一种新的疾病诊断测试。相反,他发现患有该综合征的患者大脑与正常人的差异方式各不相同。有些人胼胝体更窄,有些人更宽,但很少有正常宽度。在这种情况下,盲法使布克斯坦看到了真相。
但这些发现也令人困惑地前后不一。四分之三已发表的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脑室扩大;四分之一没有。四分之三发现海马体较小;四分之一没有。“在精神分裂症患者和对照组之间,对于每个成像(和神经病理学)参数,都存在显著重叠,”牛津精神病学家保罗·哈里森(Paul Harrison)在去年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因此……精神分裂症不能通过脑部扫描或显微镜诊断。”
形态计量学也许能提供答案,它已经赢得了一些信徒。例如,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凯斯西储大学,精神病学家彼得·巴克利(Peter Buckley)利用布克斯坦的方法表明,男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大脑的脑室在形状和大小上都与正常大脑不同。但布克斯坦仍然担心他的初步研究未能引起足够的关注。“我发现自己,出乎意料的是,51岁时仍然像研究生一样激进,”他叹息道。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在其他领域发现了他的技术的应用。马库斯运营着一个讨论邮件列表,现在有400多名订阅者,罗尔夫和布克斯坦在维也纳、巴黎、托斯卡纳、台湾等地举办了研讨会。由于其对微小差异的敏感性,形态计量学在物种分类中特别有用。生物学家利用布克斯坦的方法研究了各种动物:蝙蝠、鱼类、蠓虫、老鼠、珊瑚、鼩鼱,甚至蛲虫。
或许更重要的是,脑外科医生现在在手术室中使用形状科学,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在为到底在哪里进行切割而苦恼。大脑是一个极其神秘、精致且可塑的器官。切错部位,患者可能会失去她的周边视力,或者失去她的针线活能力,或者理解英语的能力。因此,越来越多的脑外科医生依赖于CT和MRI扫描仪生成的三维计算机图像来规划手术,甚至在手术过程中观察他们正在做什么。体积扫描使他们能够以毫米级的精度观察大脑的内部结构,并通过小切口进行手术,而不是打开大块颅骨。
然而,这项新技术也带来了一些只有复杂的形状分析才能解决的问题。大脑的某个部分可能以惊人的细节呈现,但它的功能是什么?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一种称为“大脑扭曲”的技术来回答,其中大脑中的地标点被映射(通过薄板样条或类似的变换)到“大脑图谱”上对应的点。这告诉计算机患者的大脑几何结构与通用大脑有何不同,并允许识别功能区域的边界,例如视觉皮层。当外科医生进入手术室时,他会在电脑显示器上看到一个巨大的彩色显示屏,就像一本针对该患者大脑的兰德麦克纳利指南。
如今,让布克斯坦最兴奋的发现是可能用于胎儿酒精综合征的检测方法。这种疾病在某些方面与精神分裂症处于精神疾病谱系的两端。胎儿酒精综合征在婴儿期就立刻开始影响患者的生活。它的发病率约为精神分裂症的一半,影响着近100万美国人,而且同样难以诊断。许多母亲不愿承认自己在怀孕期间大量饮酒。另一些人则无法照顾自己的孩子,并将其送养。然后,第一个意识到孩子有问题的人是养父母,他们对生母的饮酒史一无所知。如果有一种方法能够始终如一地诊断胎儿酒精综合征,即使不知道孩子在子宫内是否接触过酒精,许多这些不知情的受害者也能得到他们所需的专业帮助和倡导。
患有胎儿酒精综合征的儿童眼睑缩短,额头狭窄,人中缺失(上唇和鼻子之间的褶皱)。但患有较轻型综合征,即胎儿酒精影响的儿童,可能不具备这些典型的面部特征。“这些孩子很多都没有被诊断出来,然后他们开始表现得越来越奇怪,”发现该综合征的研究小组的成员安·斯特赖斯古斯(Ann Streissguth)说。“他们的父母不知道他们有什么问题。”
虽然患有胎儿酒精综合征和胎儿酒精效应的人很少智力迟钝(至少根据智商测试),但他们难以排除干扰。他们常常无法应对新情况或新任务。斯特赖斯古斯的一位更成功的患者在一家餐馆找到了一份稳定的洗碗工工作,并且一直做得很好,直到他被要求代替收银员。“他最终把家具扔了,不得不被束缚带到医院,”她说。随着他们进入成年期,问题只会变得更糟。60%的胎儿酒精综合征和胎儿酒精效应患者辍学、被停学或被开除。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进了监狱。
再一次,胼胝体的形状可能提供答案。在患有这两种综合征的人中,胼胝体要么比正常人宽得多,要么窄得多。布克斯坦说,当胚胎在子宫内接触酒精时,“有一个过程基本上失控了。”这就像大自然在瞄准正确的形状,但瞄准的准确性不如往常。
对儿童进行胎儿酒精综合征或精神分裂症的早期症状检测,或追踪疾病在大脑中的发展,并非易事。MRI扫描复杂、昂贵且有些令人望而生畏,并且需要父母的特别许可。然而,当应用于成人时,布克斯坦的方法已经是一个强大的工具。在一项正在审查以待发表的研究中,布克斯坦和斯特赖斯古斯检查了45名成年男性的行为测试和脑部扫描结果,其中30名患有胎儿酒精综合征或胎儿酒精效应,其余未患。尽管布克斯坦和斯特赖斯古斯从未见过这些患者,但他们除了一个例外,都猜对了诊断结果。
在布克斯坦的领域,如此具体的成果非常罕见,以至于几乎令人怀疑。大多数数学家对晦涩难懂感到一种反常的自豪,对他们的工作与日常生活无关感到顽固的自豪。“我们将需要数百万年才能获得任何理解,”匈牙利理论家保罗·埃尔德什说。“即便如此,它也不会是完全的理解,因为我们面对的是无限。”但是形状理论,在布克斯坦手中,是数学的具象化:它不仅为精神疾病提供了新的视角,还可能改变医生的诊断或他决定在哪里切开一个活体大脑的决定。
“回首往事,我认为数学对我最大的吸引力是审美,”布克斯坦说,“但这并不是理由。理由是它偶尔能让世界变得有意义,而且是以非常意想不到的方式。”至于精神分裂症,他承认这种疾病如此复杂和多方面,一个真正的诊断测试可能还需要20年。然而,这种测试一旦出现,可能植根于布克斯坦的工作,这有一种诗意的公正。像约翰·纳什一样,布克斯坦是一个局外人,一个敢于“跳出固有思维”的自学者,他挑战了大多数专家认为无法解决的问题。
值得吗?布克斯坦显然会说是的。但纳什可能要三思。如果他服用了药物来预防精神分裂症,他的生活会轻松得多。但同样的药物也可能削弱了他数学天才的莽撞锐气。“你就会失去纳什嵌入定理,”布克斯坦指出,而其他人可能会获得199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诺贝尔奖值得30年的疯狂吗?对于任何在纳什与自己心灵漫长而黯淡的斗争中见过他的人来说,答案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