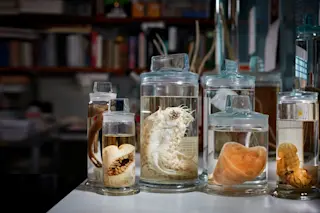你听说过《国家地理》本周与 TEDx 联合举办的关于物种复原的大型活动吗?不是濒危物种——而是已经灭绝的物种,比如猛犸象。我对这个想法有喜忧参半的感受。抽象地说,我觉得它很酷。正如我在 2006 年《Audubon》杂志上发表的一篇书评中所写的那样,有机会恢复我们进化遗产中失去的部分,这令人兴奋。但生态学家和保护主义者似乎意见不一。其中一群人在 2005 年《Nature》杂志上的一篇评论中表达了他们的热情;而另一些人,如著名的保护生物学家Stuart Pimm,则强烈反对“灭绝复活”的提议。在本周《National Geographic》网站上的一篇文章中,他讨论了一系列不容忽视的可能问题。在一个资源和注意力有限的世界里,我倾向于支持 Pimm 的观点,他写道:
幻想重新获得已灭绝的物种总是很诱人。这是一种幻想,即“真正”的科学家——那些穿着白大褂的人——正使用带有旋钮和数字读数的精密仪器来拯救地球免受人类过度行为的影响。在这种幻想中,不存在我所处世界所特有的与人、政治和经济之间复杂的互动。也不存在关于栖息地破坏的现实世界以及不断增长的人口与野生动物生存之间的固有冲突。为什么要担心濒危物种?我们可以保留它们的 DNA,以后再把它们放归野外。
Pimm 提出的棘手问题与之前在涉及狼、黑足鼬、黑豹和山猫的争议性濒危物种重新引入项目中所争论的问题相似。(很久以前,我曾写过其中一项关于后者的努力。)其中一些物种的重新引入是成功的,有些则不太成功。但它们都充满了挑战,而《Revive & Restore》倡议提出的潜在已灭绝物种的回归,无疑会将这些挑战放大一千倍。Frank Swain 在《ScienceBlogs》上撰文,提供了一个更宏观的视角(我也有同感),探讨“灭绝复活”想法背后可能存在的更深层次的动机。
“保护”这个词有点尴尬,因为它唤起了两个愚蠢的想法。一,自然环境具有某种前人类伊甸园的状态,应该维持(甚至在面对非人类影响时也应该保存)。对恢复失去物种的痴迷是这种保护态度的标志。但动物不是你可以放回环境中的拼图——世界已经改变,并且通常不再有适合那种动物的生存空间。
其次,这种形式的保护把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幻想成是它们偏离了“自然”状态。不存在人类对抗自然环境,只有环境。当人类活动影响到环境时,生活在那里的居民很少愿意打包离开,以便让它恢复到以前的状态。我们是地球上的主导物种。我们将竭尽所能地开发利用它。没有什么能改变这一点,但我们可以选择我们想生活的世界。这意味着保护将不得不关于平衡对环境的竞争性需求——包括人类和非人类的需求。《Revive and Restore》的筛选过程之一是,物种“应该能够承担它们在旧栖息地中的旧生态角色”。有些动物和人类确实可能无法和平共处,我们需要接受这一点。
他还呼应了 Pimm 表达的担忧。
最后,如果我们能复活物种,这会不会削弱保护现有物种的努力?抓住一些 DNA,让动物灭绝,然后在你拥有十万英亩农田或一个小加勒比岛屿来玩耍时再把它们带回来。事实上,如果我们正在将生物多样性减少到大体型光鲜动物的现有遗传物质,为什么还要让它们活着呢?如果基因是它们的本质,只要存在完整的 DNA 样本,它们不就同样是“灭绝复活”了吗?装在冰箱里的动物园。为什么不将其渲染成生物分子二进制呢?芯片上的老虎。最终,如果我们能让环境“复活”,那么维持它健康的动力又在哪里?
这些都是明天将在斯图尔特·布兰德的“长远基金会”组织的关于“灭绝复活”的全天会议上激烈辩论的问题。还有另一个问题也值得讨论,那就是我们(潜在地)为谁做这件事的哲学问题?是为了我们杀死掉的物种,比如塔斯马尼亚虎和旅鸽,还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自己的救赎,正如 Cynthia Mills 在 21 世纪初的《Conservation》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思考的那样。无论如何,她认为,克隆已灭绝物种“可能是保护的圣杯,也可能是最终的愚蠢”。我猜我们会知道的。********* 还有一些值得一看的文章:“复活生态学的承诺与陷阱”,作者:Brian Switek,以及“复活森林”,作者:Carl Zimmer(都在《Phenomena》博客上)。另请参阅《Scientific American》上的 Ferris Jabr 的文章“克隆能拯救濒危动物吗?”。

[塔斯马尼亚虎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的照片(1904 年),来源 Wikimedia Comm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