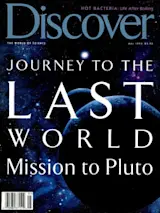迈克·亚当斯可能是北美唯一一个能够使煤渣砖墙倒塌的微生物研究者。他不喜欢你把它们与普通生命混淆。“让我称它们为有机体,”他说。“它们不是真正的细菌。”但它们确实有一些令人讨厌的习性,毫无疑问是它们恶劣环境的产物。它们大多数最初来自海底的温泉——壮观的冒烟、富含硫磺的大锅,在那里,受压的水从火山喷口射出,温度高达700华氏度(371摄氏度)。
当你走进这些坚韧的小生物生长的房间时,一扇厚重的金属门“砰”地一声关上。煤渣砖墙和普通的混凝土地面增添了地堡般的氛围。孵化罐——一个全新的120加仑发酵罐,漆成蓝色——看起来足以承受深海潜水。微生物生长时,没有人靠近它。一束电线从孵化器连接到隔壁一个密封的计算机控制室。这个控制室对面的墙壁设计成在压力下会爆裂。“一切都是防爆的,”亚当斯说。
“我们研究的大多数有机体都是分解者,它们产生氢,”他解释说。它们以硫磺为食,释放出硫化氢,这使得发酵罐散发出令人愉悦的腐烂鸡蛋的气味,就像一箱又一箱的臭鸡蛋。作为额外的好处,它们还会释放出一些与兴登堡号飞艇中充斥的相同的爆炸性气体。但亚当斯说这只是一个次要的考虑。
然而,他的微生物对热的渴望是一个主要考虑因素。这些生物喜欢在沸水中煮沸。这使它们与所有其他生命不同。在212华氏度下,构成我们——以及我们所知的所有生命——的分子会分解。DNA会解体,蛋白质会在几秒钟内坍塌成一堆缠结的粘稠物。我们依赖沸水的致命效率来净化食物和消毒医疗器械。然而,亚当斯可以永远煮沸他的生物。它们不仅能在高温下生存,而且在其中茁壮成长。这使它们生长和繁殖。事实上,许多类型认为212华氏度有点温和。更热的水浴,比如说在压力锅中达到220华氏度左右,会按摩它们的分子,使其肽充满活力,并使它们更渴望繁殖。
乔治亚大学的生物化学家亚当斯想知道它们这种不可能的生命是如何可能的。“这些是全新的生物,”他坚持说。“它们有望彻底改变关于生命起源和化学的观念。很明显,要在这种极端温度下生长,它们不可能与所有其他生物做完全相同的事情,所以它们一定在做一些不同的事情。它们也做了很多相同的事情,我们还不太明白它们是如何做到的。”
当亚当斯称这些生物是“新”的,他只是指它们对科学来说是新的。他真正想说的是,它们可能非常古老。事实上,他相信它们是我们所知最古老的生命形式,与年轻、炽热的星球上出现的第一个单细胞生物密切相关。如果这个理论(最初由伊利诺伊大学微生物学家卡尔·沃伊斯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是正确的,那么这些微生物内部的化学反应指向了生命的原始化学反应——一种在212华氏度以上效果最好的化学反应。
“传统上,亚当斯说,那些能在高温下生长的生物一直被认为是某种程度上适应了高温的普通生物。新理论将原有观念彻底颠覆,如果你仔细想想,这有点戏剧性。我们才是适应者。”
在适应较冷环境的过程中,我们这种生命可能已经转向了生物学温度刻度的低端。如果略高于98华氏度(对我们来说是正常温度)实际上是偏冷的,如果212华氏度更接近舒适,那么上限是多少?这些生物体内部的化学可以给我们一个更好的概念。它也可以暗示生命可能在宇宙中其他地方演化:不一定是在像地球一样的行星上。
目前,亚当斯对其他行星的猜测不多。他正在培育的地球生物已经够奇异了。他对这些奇异生物的追寻始于1981年新泽西州的埃克森美孚研究中心。亚当斯于1979年在伦敦大学获得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并在普渡大学短暂工作后,来到了埃克森美孚。他当时正在研究一种细菌酶,氢化酶,它可以将氢从水分子中分离出来。埃克森美孚显然希望这种强大的酶可能对炼油有用;亚当斯只是想了解它是如何工作的。然而,1986年,埃克森美孚削减了生物学基础研究,亚当斯决定离开。
他去了乔治亚大学,在那里他开始寻找代谢氢的微生物。如果它们能够代谢氢,它们就会有一种像氢化酶一样的酶。查阅文献后,他发现了一位名叫卡尔·斯泰特(Karl Stetter)的德国微生物学家的几篇报告。1982年,斯泰特发现了第一批在212华氏度以上温度下茁壮成长的生物,它们存在于西西里岛海岸附近的浅层温泉中。后来,他和其他研究人员开始在海底深达三英里的喷口中发现它们。生物学家此前已知一些细菌可以在黄石公园等地的温泉中存活,水温可达190华氏度。这些温泉居民被称为嗜热生物,意为喜热生物。然而,新发现的这些生物超出了嗜热生物的范围——它们是超嗜热生物。
亚当斯说:“我看到了这些生物,但没有生物化学研究。时机刚刚好。没有人从它们身上纯化出任何酶;没有人对它们了解。而且它们代谢氢。所以我心想,‘好吧,见鬼,它们不可能那么难培养,即使它们在这些极端温度下生长。’”他从德国的一个培养物收藏库订购了两种,它们都生长了。“嗯,事后看来,它们长得不是很好,”亚当斯回忆道,“但我们可以收集细胞。”尽管他已经阅读了关于它们的报告,亚当斯仍然对它们看似不可能的化学性质感到震惊。这些生物确实含有氢化酶——一种超高温版本。“我们可以把它们打开,然后测量212华氏度下的氢化酶活性。据我所知,那是从超嗜热生物中纯化出的第一种酶。”
酶是生物体内的“驱动者和推手”,是强大的蛋白质,它们将其他分子聚集在一起,产生生命必需的化学反应。亚当斯决定让酶引导他穿越212华氏度以上生命体的奇异领域,一个充满奇异物种的景观,超越了传统地图上已知的世界。亚当斯认为,通过跟踪酶,他会发现这些生物是如何真正工作的。
从微生物中分离酶的第一步是打开一团细胞。你可以用压机压碎它们,用另一种酶裂解它们的细胞壁,或者用声波将它们震碎。然后进行离心。在19,000 g的作用下离心一小时后,细胞壁碎片会像铅一样沉淀在试管底部。细胞内的酶仍溶解在顶部溶液中。为了将它们分离出来,你需要将溶液倒入一个装满材料的柱子中,这些材料对于相对较大的酶分子来说很难穿透。较大或较粘的分子——那些带较高电荷的分子,倾向于粘附在过滤介质上——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到达底部。这项工作通常是繁琐的,需要多次数小时的运行才能纯化那些不愿分离的类似酶。每当有酶流出时,都必须有人在场,而且柱子不分昼夜。
亚当斯说:“纯化其中一种酶时,在其中一个柱子上,我们偶然发现了一种鲜红色的分子。于是我对一个学生说,‘你为什么不去纯化它,看看它是什么呢?’因为它呈红色,我的想法是它可能是一种含金属的化合物,比如血红素。血红素是一种含有铁原子的分子,它是红细胞中血红蛋白蛋白质的重要组成部分。铁能迅速吸收溶解的氧气,这种结合呈现红色。亚当斯对金属非常感兴趣。他说,金属让世界运转。就像铁与血红蛋白一样,金属通常赋予酶加速反应的能力。亚当斯和他的学生分析了这种酶中的金属,他们确实发现了一些铁。他们还发现了其他东西。‘瞧,’亚当斯说,‘有钨。’”
对亚当斯来说,钨令人兴奋之处在于它在普通生命中的稀缺性——此前只从活生物体中分离出一种含钨酶。现在,亚当斯和他的同事们在这条分子拆解线上开始左右发现钨。他们能培养的五种生物中的每一种都含有含钨酶,而且这些酶与研究人员以前见过的任何东西都不相似。它们似乎属于一系列未知的化学反应,这些生物体利用这些反应分解糖和蛋白质以获取能量,并在过程中产生氢气。亚当斯的研究团队发现,当他们给这些生物喂食钨时,它能刺激它们的生长。
虽然以钨为基础的代谢方式使这些生物与普通生命区别开来,但额外的酶纯化显示,这些生物也含有传统的含铁等金属的酶,而且它们似乎能够同时使用两种代谢途径。钨在整个体系中扮演什么角色尚不清楚。它是更古老的、在更高温度下效果更好的化学反应的一部分吗?传统的酶是为了应对较低温度而后来进化出来的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它们在高温下没有像我们的酶那样分解呢?是时候深入挖掘了,从化学层面——分子间的反应——深入到分子本身的层面。“对我来说,”亚当斯说,“我们似乎需要回答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是什么让分子稳定?”
当蛋白质沸腾时,它会变得不稳定。它会分解,然后就会下沉——或者,专业地说,它会沉淀。亚当斯说,蛋白质的本质在于它必须溶解在溶液中。你甚至可以说,水是其结构的一部分。微小的水分子在热能的作用下颤动,悬浮着构成蛋白质的长链氨基酸。在适宜温度的水中,这些链状分子像毛线球一样扭曲和折叠。过热的水会剧烈颤动,并不断敲击折叠的链,直到蛋白质解开,与其他正在解开的蛋白质缠结,并从溶液中沉淀出来。室温下的蛋清是丰富的毛线球溶液。煮熟的蛋清则是凌乱、凝胶状的一堆毛线。
为什么超高温蛋白质不像蛋清一样被煮熟呢?亚当斯能做出的最佳猜测是,它们的链比我们的有更多的交联——在链紧密盘绕的地方有微弱的化学键。这些相互作用可能阻止它们在热水中解开。可能的交联数量取决于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这决定了链如何自身折叠。
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亚当斯转向了一种名为红球菌素的蛋白质。“红球菌素的好处在于它是一种非常小的蛋白质,”他说。“它含有53个氨基酸。这种蛋白质已经从大约十几种常规生物中分离出来,并且其结构在它们之中已经得到了很好的确定。所以我们从一种高温生物中分离了红球菌素,并用三种不同的技术确定了它的结构——X射线晶体学、磁共振成像和计算机建模。去年,它们都得出了基本相同的结构。”
常规的红蛋白由一根长链组成,缠绕成一个球状。这根链包含三个区域,称为β折叠,当酶折叠时它们彼此相邻排列,并保持整个结构的稳定。“中间的β折叠有一端有点伸出来,”亚当斯说,“随风飘动。”
超高温版本的红蛋白是不同的。中间β折叠的末端缺少一个氨基酸;它没有从分子中伸出来。“我们的假设是,”亚当斯说,“如果你将常规蛋白质加热,一端会因热运动而开始晃动,最终它会脱落并解开结构。松散的一端会拉动中间的β折叠,分子就会散架。在超高温蛋白质中,脆弱的末端更短,更靠近整个结构。所以它不会晃动,而且这个球状结构也更难解开。”
亚当斯说:“有一点让我们有点惊讶的是,这些红球菌素的结构是多么接近。没有发生重大的、全面的变化。常规版和超高温版足够相似,可以执行相同的化学反应。在宏观层面上,它们或多或少是相同的三维结构,但存在一些关键差异。”亚当斯认为,同样微小的结构变化可以稳定嗜热微生物中其他看似常规的分子。“我认为,很明显,所涉及的机制对每种蛋白质来说都是独特的,而且这些相当微小的变化发生在蛋白质的关键点上。”这个假说似乎打破了这些生物的神秘感。它们对热的显著抵抗力归结为一个微不足道的适应。但亚当斯说,“从蛋白质结构微小变化可以导致稳定性巨大变化的观点来看,这并非微不足道。”
当然,他补充道,我倾向于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他坚信,耐热蛋白质从未通过适应更高温度而变得更稳定。相反,像我们这样的蛋白质在适应更冷的环境时变得不那么稳定。随着地球冷却,它们别无选择。在60华氏度(目前地球表面的平均温度)下,紧密交联的蛋白质变得僵硬,基本上被冻结。僵硬的酶无法参与化学反应,因为它不够灵活,无法靠近其他分子并影响它们。通过去除交联,酶变得足够灵活,可以在更冷的温度下发生反应。然而,这些相同的适应使它们变得过于脆弱,无法在更高温度下生存。
亚当斯说,这告诉我们一些关于这些蛋白质的进化史。如果你接受这个简单的方案,紧密结合的蛋白质往往更古老,而蓬乱的蛋白质更年轻。迟早,一个不断进化、不断解开的蛋白质可能会分裂成单独的分子。每个分子都可以在更复杂的化学反应链中发展出专门的作用。这个想法解释了亚当斯在某些在高温下发挥作用的酶中发现的一种模式:其中一些酶比你在高等生物中发现的酶简单得多,或者似乎是它们的祖先。例如,一种名为丙酮酸氧化还原酶的耐热酶结合了我们自身较冷化学反应中由单独分子承担的几种功能。这就像代谢途径需要在高温下紧凑,就像耐热蛋白质本身一样。在分子水平上,这是生物学的“大爆炸”:你回顾的时间越远,生命的化学反应就越热、越紧凑。
亚当斯将他迄今为止破译的拼图碎片融入到生命的历史概述中。它始于耐热生物,正如沃伊斯所声称的那样。随着环境冷却,蛋白质脱落交联以保持松散和功能。同时,大多数生物将钨换成了另一种元素钼,钼现在在所有其他生物中都很常见,并且可能在更冷的温度下或与不同营养物质一起效果更好。钨可能更适合在更高温度下进行化学反应,例如涉及氢和硫的反应。保留钨的生物变成了超嗜热生物。其他生物进化成了今天植物和大多数其他生命形式的祖先,从蚯蚓到我们。
这是一种合理的化学理论——但这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证明。“我一直提醒自己,”亚当斯说,“不要太认真对待这些。这个领域的想法一直在变化,因为超高温生命中的化学反应通常比最初想象的更复杂——毕竟,它已经进化了数十亿年。这些不是简单的生物,”亚当斯指出,“它们进行的化学反应和细菌一样复杂。但无论细节如何变化,将一切联系在一起的理论——沃伊斯关于生命从热到冷进化的宏大图景——至今都没有让亚当斯失望。我把它作为一个框架,在需要的时候,为我们的结构数据或对钨的依赖提供一个依据。它仍然在领域中受到挑战,但证据越来越多。”
来自红球菌素的证据尤其引人注目。如果超高温版本中一个微小的结构变化——一个使一端稍微软化的变化——真的能让分子在60华氏度而非212华氏度下发挥作用,那么如果那一端稍微收紧一点会发生什么?同样微小的变化,让分子进一步收紧,能让它在接近300华氏度(亚当斯新孵化器上的最高设置)下发挥作用吗?更广泛的变化又会怎样呢?事实上,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地球上仍然存在着在远高于300华氏度的温度下生长的生物。
现在回想起来很容易看出,212华氏度是一个武断的屏障:海平面、一个大气压下水的沸点。在海下三英里,压力高于300个大气压。那里有一些生活在超高温喷口中的微生物,我们根本无法靠近。“我们还没有开发出分离它们的工具,”亚当斯说。那些能进入实验室的,很可能是化学性质最接近我们的。更古老、更耐热的生物仍然存在吗?亚当斯认为没有理由不相信。“我们还没有足够努力地寻找它们,”他说。“为什么直到1982年才有人发现一种能在沸水中生长的微生物?以前没有人寻找过。我认为很快就会有相当大的突破,”他补充道。“这确实令人难以置信,因为20年前,如果你问最高温度限制是什么,我肯定我们会说它必须低于212华氏度。谁知道20年后会是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