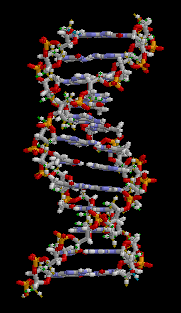
我想,关于保守派与杏仁核、自由派与前扣带皮层(ACC)的近期博文,还不够引起争议。那么,为什么不进一步讨论将我们的政治观点与基因联系起来的最新研究呢?我在此推荐以下论文:Peter K. Hatemi 等人(有很长的名单),《自由派和保守派政治态度的全基因组分析》,近期发表(2011年)在《政治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s)上。论文的PDF可以在这里找到。以下是摘要
认为社会行为和政治偏好的传播纯粹是文化性的观点,在过去的40年中,通过对成年双胞胎及其亲属的大规模研究、收养研究以及分开抚养的双胞胎的综合证据,一再受到挑战。利用大家系数据的方差分量和路径模型分析量化了遗传对政治态度的整体影响,但很少有研究试图定位解释政治偏好遗传力估计的基因组部分。在这里,我们报告了对13,000名受访者的保守-自由派态度的首次全基因组分析,其DNA是在与一项50项社会政治态度问卷调查同时收集的。我们确定了几个显著的连锁峰值,并讨论了潜在的候选基因。
所使用的技术,“全基因组连锁”,作者称其曾用于定位与乳腺癌相关的BRACA1和BRACA2基因……基本上,所有受试者(13,201名)都完成了上述政治态度问卷调查并提供了血液样本。然后,试图寻找染色体上多态性——即,这些区域因人而异——并且这种变异与政治观点相关的区域。令人惊讶的结果——对于我们任何一个停下来思考我们与生俱来的基因和成年后的政治态度之间巨大距离的人来说——是发现了三个“显著”相关(其中一个达到了最严格的标准)的区域,以及一个“提示性”相关的区域。(所有这些技术细节都在论文中。)这可能意味着什么?嗯,正如作者所写:
我们确定了四个感兴趣的区域,其中一个符合最严格的标准,我们的发现与预期一致,如果保守-自由派变异的遗传成分类似于任何其他多基因人类性状,那么亲属之间的遗传相似性只能可靠地分解为大量具有小效应的基因的作用,这些基因通常无法通过连锁来识别。
换句话说,没有单一基因直接决定我们的政治观点——没有“自由派”或“保守派”基因——但可能存在基因组合协同作用,以某种方式使我们倾向于具有特定的政治倾向,这可能通过影响我们的大脑,进而影响我们的个性和社会行为。事实上,研究中发现的最有希望的基因区域都与“NMDA和谷氨酸相关受体”有关。作者忍不住在此推测:
思维组织、信息处理、抽象思维能力、学习和表现与NMDA阻滞有关。对于政治意识形态尤其感兴趣的是NMDA与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试(WCST)表现之间的关系。WCST是一项神经心理学测试,用于评估在不断变化的强化时程面前表现出灵活性的能力。根据定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都与在变化的世界面前的态度灵活性息息相关。
这些是高度探索性的结果。科学家们甚至不能肯定地说他们确定了影响我们政治观点的单一基因通路。但与此同时,全基因组的“撒网式”搜索并没有空手而归。他们捕获了一些肯定会受到进一步研究的东西。大局是什么?作者再次表示:
找到一个可能暗示特定基因标记的显著连锁区域,并不意味着某个特定基因决定了某个特定行为。我们的结果也不主张基因的作用比环境的作用更大。当然不是这样。相反,我们是从一个非常复杂过程的两端开始的:一端是DNA,接近构成生物体最基本物质的某个地方;另一端是表现出来的复杂行为(政治意识形态)。行为是一个人作为人类所经历的所有输入和输出的最终产物,在一个人的一生(例如,青春期、更年期等)中与复杂多变的环境相互作用。我们才刚刚开始理解这两者之间发生了什么,这使得这一研究领域令人兴奋,同时也告诫我们要谨慎。我们尚未能准确描绘基因如何影响大脑过程和生物机制,而这些机制又与我们的成长经历、社会生活、个人经历、天气、饮食等相互作用,并部分表现为保守-自由派取向,这种理解正是全基因组分析对政治学有价值且必要的原因。人类行为源于基因、社会化和环境刺激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通过进化框架(Dobzhansky 1973)内化的个体发育神经生物学过程而产生。就数据而言,一种包含遗传影响(无论大小)的理论和方法,能够解释仅靠环境模型无法解释的保守-自由派取向的某些部分。
我真的觉得这很神奇。但是,如果这就是目前的科学结论,那就只有一件事可做:进行更多的科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