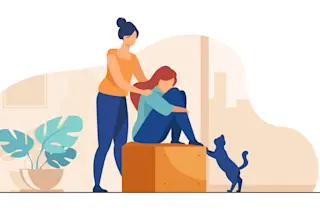死亡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安乐死会惹人厌烦。无论您在这场辩论的哪一方,您都陷入了人类痛苦的困境和知情自主自由选择的顽石之间。安乐死实际上是在争论不要死于自然原因。长久以来,我们一直认为死亡只有在自然发生或明显意外的情况下才是可以接受的。除此之外的任何情况都被视为谋杀、过失杀人或战争。不仅是上帝,我们人类也已经确立了禁止自杀的准则。正如丹尼尔·布洛克所指出的,“自愿积极安乐死”既不自然,也并非明显意外。因此,我们本能地将其归类为道德上错误的行为。许多人不去试图找出这种本能的根源,也不去调查自愿积极安乐死是否真的违反了道德,反而利用由此产生的模糊界限作为反对选择死亡的充分理由。《纽约时报》的罗斯·多萨特(Ross Douthat)认为,杰克“死亡博士”克沃基恩(Jack “Dr. Death” Kevorkian)为那些痛苦中的人们提供帮助,创造了一个道德上的滑坡。
一旦我们允许这种权利存在,那么限制其仅限于临终者死亡的论点充其量也显得武断。我们都在一天天地走向死亡:绝症患者真的占据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道德范畴吗?癌症患者的痛苦并不一定比多发性硬化症、瘫痪或躁郁症患者更难以忍受的、更不确定的痛苦。而且并非所有难以忍受的痛苦都是医学上的:如果一个在与帕金森氏症的斗争中失败的男人可以要求获得医生协助自杀的解脱,那么为什么一个遭受重创的鳏夫,或一个失去了唯一孩子的父母不行?
请注意,多萨特并不认为帕金森氏症是一种医学疾病。但更重要的是——多萨特的论点是,我们不知道痛苦到何种程度才能使选择死亡在道德上变得可以接受。痛苦的程度是错误的标准。除了承受痛苦者本人,没有人能定义它,而且它也永远无法被真正地传达。这里面临的风险不仅是临终者自由和知情的选择,还有我们对“死于自然原因”的理解。那么,我们如何确定选择死亡的人是头脑清醒、拥有所有必要信息且未受胁迫的情况下做出这一决定的呢?值得庆幸的是,特里·普拉切特爵士(Sir Terry Pratchett)有一个建议。
因此,我和其他人曾建议建立一种严格的、非侵略性的法庭,在辅助死亡发生之前充分了解案件事实。这可能会让一些人,包括我自己,感到有些不安,因为它暗示政府有权告诉人们是否可以生或死。但即便如此,政府也不能回避确保弱者得到保护的责任,我们必须尊重这一点。那些反对辅助死亡的人似乎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这些支持它的人并没有认真地思考过这个问题,这让我感到非常痛苦。事实上,这正是我论点的核心。法庭的成员将为社会和申请人(这个可怕的词)的利益行事,以确保他们头脑清醒、信息灵通、目的坚定,患有危及生命且无法治愈的疾病,并且不受第三方的影响。这需要比我更明智的头脑——尽管我敢说,找到这些人应该很容易——来决定如何组建这样的法庭。但我建议应该有一名律师,一位在家族事务方面有专业知识、善于识别某人真正意图的律师,并且能够识别是否存在外部压力。还应该有一名在处理严重长期疾病复杂性方面经验丰富的医生。我还建议法庭的所有成员都应年满 45 岁,到那时他们可能已经获得了稀有的智慧,因为在这种法庭中,智慧和同情心应该与法律并存。法庭还必须对那些出于理性人认为微不足道或短暂的痛苦原因而寻求死亡的人进行制衡。我敢说,相当多的人曾因后来觉得非常小的事情而考虑过死亡。如果我们想生活在一个可以允许“体面地提前死亡”的世界里,那么必须经过深思熟虑才能允许。
多萨特试图从人类经验的多样性中构建一个滑坡论证。普拉切特拥抱了这种多样性,并试图建立一个道德机制来处理死亡带来的不适。但死亡还有一个第二个问题。如果我不想死于自然原因呢?如果我想活很长时间,比如一万年呢?有趣的是,那些不想让我如愿以偿地死去的人,也 *不* 希望我活得比“应该”活得更长。利用技术寿命超越统计平均寿命,就是违反了某些其他价值观,比如在面对死亡时的谦卑,或者类似的陈词滥调。生物保守主义作家,如莱昂·卡斯(Leon Kass)和弗朗西斯·福山(Frances Fukuyama),一再认为,死亡是赋予人类生命价值的一部分。但这里有个转折。如果你生病了,我们会给你注射化学物质,把你固定在你的医疗计划勉强支付的任何机器上,但不要活得超过平均水平。正如多萨特在上面所说:“我们都在一天天地走向死亡。”在这里我们有什么选择?同样,“自然”的严酷道德观又露出了它们丑陋的嘴脸。自然死亡的概念将我们束缚在悖论的枷锁中。围绕死亡做出选择似乎违反了我们都无意识同意的自然法。我们没有人知道我们的终点何时到来,但不要试图太早死去,也不要试图活得太久。死亡,似乎是一个对我们来说太重要的决定。就像许多反增强论证一样,答案也过于熟悉:最关键的选择——那些影响我们基本基因密码、我们拥有什么样的孩子以及我们如何死亡的选择——应该留给命运。在很大程度上,超人类主义就是对造成死亡悖论的心态的反对。死于自然原因并不好,只是没有人为此负责。但在一个如此多的死亡是出于故意、恶意和毫无意义的世界里,死于自然原因不仅可以看作是一种解脱,甚至是一种恩赐。因此,我们已经开始珍视和看重那些仅仅是道德上中性的必要事物。当另一个人违背我们的意愿选择我们的死亡时,这是一种道德错误。死于自然原因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我们别无选择。但它并不在道德上是好的。自主、自愿地选择何时死亡,这才是道德上的善。没有理由必须遵守决定我们死亡日期的生物构成和环境的条件。如果技术能够让我们在多年的痛苦面前止步,或者在不幸的温和离世后再多活 20 年,为什么不呢?对自然死亡的迷恋不应该让我们在生命质量和寿命上被劫持。
在凯尔的个人博客上关注他
、脸书
和推特上关注他。
患者图片由
José Goulão 通过 Flickr 知识共享(许可)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