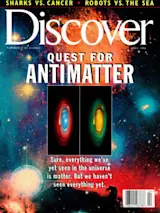是不是只有我怀念苏联?在我看来,如果你想寻找一场一流的、A级的、有趣的战争,冷战是无与伦比的。
冷战时期之所以成为世界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有很多原因,但最重要的可能是参与其中的历史人物。厌倦了过去十年全球冲突的美国人,在1952年选择了低调而令人安心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作为他们的领导人。这位前将军深受民众爱戴,以至于人们通过佩戴写着“我喜欢艾克”(I LIKE IKE)的竞选徽章来表达对他的支持——这是一种比1990年代更复杂的情感表达方式(比如“我想我喜欢艾克”;“我不确定我是否准备好承诺支持艾克”;“我与艾克处于一种共生关系”)。苏联同样热衷于自己的领导人,选择了富有魅力的尼基塔·赫鲁晓夫作为其总理。赫鲁晓夫是一位鼓舞人心的政治演说家,也许他最出名的事迹是在联合国上脱下鞋子在桌子上敲打,从而通过用共产主义的系带牛津鞋取代长期以来令人恐惧的法西斯主义的军靴,瞬间缓和了世界紧张局势。
那个时代的语言和那个时代的人一样戏剧化。正是在冷战时期,美国出现了麦卡锡主义,这是一场大胆的政治运动,勇敢的政府调查人员在那里斗争,以保护国家免受泽罗·莫斯特尔(Zero Mostel)、伯尔·艾夫斯(Burl Ives)和吉普赛·罗斯·李(Gypsy Rose Lee)的侵害。也正是在冷战时期,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如今传奇般的厨房辩论中与赫鲁晓夫对峙,并以“我不是厨师!”这句令人难忘的宣言战胜了苏联领导人。最重要的是,正是在冷战时期,国家才开始担心其各种——且不祥——的差距。
与1990年代那些更关注磨白牛仔裤®和宽松卡其裤®而非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的“差距”不同,1950年代的“差距”性质更为严重。近一代人以来,忧心忡忡的美国人听到了关于导弹差距、准备差距和部队差距的黑暗警告。如今,根据新解密的档案,美国情报界似乎也关注着一种完全不同的“差距”:一种真正令人恐惧、完全严肃的“心灵差距”。据去年披露,在冷战的最后20年里,美国花费了2000万美元研究超感官知觉和其他心灵现象,试图确定超自然界的力量是否能被自然界中的间谍专家利用。
在一个政府官员们曾考虑过用除《出版商的清扫》优惠券之外的一切来平衡联邦预算的赤字意识时代,花纳税钱研究心灵意识的想法似乎确实是浪费,但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认为他们有他们的理由。多年来,自称的预言家们一再被私人侦探和当地警察局要求协助调查各种罪案,从绑架到银行抢劫。如果同样的超感官侦探能力可以用来定位莫斯科附近的导弹基地或中国境内的部队调动,美国就能在国际情报游戏中获得一个有利优势。唉,联邦资助的占卜术二十年未能找到任何近似具体的东西;然而,争论仍在继续,少数顽固的研究人员仍在为这项工作辩护,而绝大多数主流科学家则坚持认为,大多数超感官现象与其说是知觉的问题,不如说是欺骗的问题。
中央情报局(CIA)于1973年开始涉足心灵现象领域。从一开始,就有人质疑这是否是个好主意。毕竟,就在十多年前,CIA还策划了“猪湾事件®”入侵,这是一次闪电般的行动,派出了受过机构训练的特工队伍前往古巴,袭击该岛南部的海滩,在那里扑腾几分钟,然后——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就扬长而去。当时认为,这会让菲德尔·卡斯特罗立即放下武器,向美国当局投降。出乎意料的是,这并没有发生。但CIA的声誉依然良好,该机构继续探索超感官领域。
CIA资助的研究首先在加州门洛帕克的斯坦福研究所(SRI)进行,后来在附近一家私有的科学应用国际公司进行。甚至在研究开始之前,CIA的科学家们就知道他们的工作任重道远。大多数普通人在某个时候都曾测试过自己的超感官能力,比如猜测一副牌中抽出的哪张牌,或者另一个人心中想的是哪个数字(从一到十)。然而,对于CIA来说,他们不太可能遇到一个第三世界独裁者抛出“我正在想阿富汗和赞比亚之间的边境战争……”这样的线索,所以他们的方法必须更微妙一些。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统计学家杰西卡·尤茨(Jessica Utts)参与了一些实验,她表示,CIA的研究以多种方式进行,但所有研究都有相同的目标:确定志愿者在一项涉及非常规感官的实验中能够表现得多好。
必须指出的是,尤茨不仅是一位统计学家,也是一位超心理学倡导者。超心理学这个词,当然来自希腊语“para”,意为“接近”,加上“psychology”,意为,嗯,心理学,合起来的意思是“是不是该找个好心理医生了?”但尽管超心理学声誉可疑,尤茨坚持认为它是一门真正的科学,她和其他政府研究人员在心灵现象研究中采用的方法表面上似乎支持了这一说法。
一般来说,CIA的ESP工作涉及选择一张视频或照片,其中包含一个人、地方或物品,将独立的志愿者隔离在另一个房间,然后让他们尝试确定图像是什么。在一些试验中,第二名志愿者被告知看着图像,集中注意力,并尝试将其传输给接收者;在另一些试验中,接收者则独自进行。尤茨说,在所有情况下,我们都试图发现被试者能否以大于偶然因素所能解释的频率确定正确的图像。
实验结果是由正在研究的现象还是由简单的数学随机性引起的问题至关重要,它取决于所谓的“统计显著性”。为了计算统计显著性,调查人员将包括样本量、每个被试者的试验次数、每次试验可能的正确答案数量、半粘性介质中的声速,以及埃迪·穆雷(Eddie Murray)在1983赛季的击球率(.306,111次打点,左右开弓)在内的多个变量结合起来,得出一个单一的数值答案。如果小于0.05——意味着如果仅凭偶然因素,只有不到5%的可能性会出现这些结果——则认为该研究具有统计显著性;如果大于0.05,则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对于尤茨和其他ESP研究人员来说,CIA研究的总体统计显著性似乎令人印象深刻。她说,在20年研究的头15年里,共进行了154项独立实验,包含26,000次试验。在这些实验中,被试者正确识别目标图像的频率足以使统计显著性数字仅为0.00000000000000000001——这意味着如果结果纯粹是偶然的,你只会遇到一次这样的结果(在10^20次尝试中)。如果你相信你观察到的结果,这些研究就导出了心灵能力存在的结论。
但是,你真的能相信你观察到的结果吗?几个世纪以来,巡回推销员用他们所谓的“心灵感应”能力迷惑观众,结果却不过是心灵上的“蛇油”。在美国西部,来访的预言家经常骑马进城,公开表演,在表演中他们似乎能读懂陌生观众的心思。最终,眼尖的镇民开始注意到一些细微的线索,表明所谓的预言家叫来的志愿者根本不是陌生人——例如,他们称呼他为“爸爸”。这通常会导致快速的“涂抹和羽毛”(tarring and feathering)惩罚,很快,大多数巡回推销员的职位就空缺了。在1990年代,超感官欺骗的可能性并不比1890年代小,一些研究人员认为,这正是CIA研究中发生的事情。
俄勒冈大学心理学家雷·海曼(Ray Hyman)说:“我发现任何人声称这些研究证明了ESP的存在都令人难以置信。即使你假设这些发现代表了与偶然性的真正统计偏差,那离证明你拥有心灵现象的证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海曼是心灵研究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之一,他认为政府的工作存在许多问题,其中最不为人知的就是参与这项工作的人员。他说:“一方面,我和杰西卡·尤茨没有任何问题。她是一位称职的统计学家,但她也是超心理学协会的成员。他指出,超心理学家致力于证明ESP的存在,他们的偏见不可能不影响他们的结果。”
尤茨对此表示异议,这并不令人意外。她坚持认为,她分析的研究是按照最严格的科学方法进行的:试验通常是双盲的,实验者和被试者都不知道选择了哪个图像;被试者在研究开始前与实验者互不认识;实验者选择志愿者时,有时会刻意选择那些最不具心灵倾向的人。
尤茨说,在研究早期的一组试验中,我们正在寻找可能愿意担任被试者的斯坦福大学员工,我们得知一位特别怀疑的人一直在告诉同事我们的工作是多么的荒谬。经过测试,我们认为他非常适合我们的需求,事实证明也是如此。在一项试验中,他描述看到一个像树一样的目标图像,但那棵树几乎完全是灰色的,顶部呈蘑菇状。我们为他选择的图像是一段核爆炸的视频。
其他试验也同样让尤茨信服。在一项实验中,研究人员派一名被试者在SRI大楼100英里半径的范围内开车,而另一名被试者则在实验室里尝试确定汽车的位置。几乎立刻,接收者开始描述一片起伏的山丘景观,前景有一个螺旋桨状结构,用于产生能量。后来有人透露,当时,传输者志愿者正经过加州北部的滚山风力发电场。在另一项试验中,实验者选择了位于西弗吉尼亚州的一个绝密地下情报设施作为目标图像。两名志愿者几乎毫不费力地开始描述该综合体的外观和位置,甚至还识别出该地点使用的一些代码词。
尽管这些轶事结果对CIA来说似乎很有趣,但主流研究人员坚持认为它们什么都不是的证据。当然,一名志愿者成功地识别出了滚山风力发电场,但在加利福尼亚州,研究人员试图利用除了猪肉以外的一切来生产廉价、可持续的能源,这真的有那么难吗?当然,另外两名被试者识别出了西弗吉尼亚州的绝密情报设施,但是,这个设施不是由同一个机构运营的吗?该机构雇佣了双重间谍奥尔德里奇·艾姆斯(Aldrich Ames)近20年,直到高级政府审计员最终注意到,一辆捷豹、一栋价值64万美元的房子和格罗兹尼附近的一栋夏季别墅实际上并不包含在该机构的退休套餐中?如果连那都能从机构的漏洞中溜走,那么西弗吉尼亚州的地址就不能吗?
海曼说:“这项研究进行了20年,并且一直被列为机密。没有任何比秘密进行工作更能引起人们对其可信度的质疑了。假设研究人员的方法存在缺陷?假设有关目标图像的信息不知何故传给了被试者?提供对研究结果的访问权限,并允许其他人尝试复制你的结果,这是最基本的研究协议。”
尽管受到主流科学界的批评,超心理学家们却毫不在意,并且已经开始着手工作的下一步:不仅确定研究中哪些被试是真正的预言家,而且确定他们是如何获得这些非凡能力的。对于大多数街头算命先生来说,ESP的起源一直是个谜,最好的解释与穿着花卉沙笼裙、名字叫玛ダム·罗莎(Madame Rosa)以及接受大多数主要信用卡有关。对于CIA的研究,超心理学家们正在寻找更科学的东西,尤茨认为他们可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她说:“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大脑中存在某种探测器,能够感知变化——视觉场的变化,思想场的变化——从而提供关于人们或物体的信息,而这些信息通常是看不见的。有趣的是,我们发现目标图像的变化越多——例如,颜色或形状越多——被试者表现得越好,这表明他们确实是对变化做出反应。”
当然,虽然算命先生可能对思想场的变化做出反应,但CIA必须对政治场的变化做出反应。随着华盛顿的预算制定者们密切关注国家的银行账户,CIA最近找到了海曼和尤茨,请他们评估超心理学研究,以帮助该机构决定是否将有限的资金用于其他地方。当一个有能力颠覆外国政权、发动秘密战争并收集国内麻烦制造者信息的机构请求进行绩效评估时,大多数人会发现很难完全坦率(“伙计们,研究很棒。真的。要不要再来一杯?”)。然而,海曼并不犹豫地告诉CIA他的想法。
他说:“尽管工作了20年,但超心理学家未能提出一个解释心灵现象为何存在的积极理论。相反,他们提出了一个消极理论,只是接受研究的统计结果,并询问除了ESP之外,还有什么可以解释它们。这不是证明,而是争论。”
这显然是一个不足以说服CIA的争论。在这次评估之后不久,该机构官员决定停止资助这些研究。经过反思,很难不同意他们的决定。在一个地缘政治风险如此之高的世界里,美国真的想处于依赖卡纳克(Carnac the Magnificent)这样的人物来挑战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吗?(他猜中了我的身高、体重和出生日期!我不得不放弃科威特。)即使是最敏感的巫师,也能取代最不敏感的卫星来精确定位敌方潜艇的位置吗?(我看到一张水……)国务院谈判代表在打“中国牌”时,是否不得不记得在将其放回牌组前向观众展示?在这些问题得到解答之前,CIA最好还是避开超自然领域——以免政府情报本身变得更加自相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