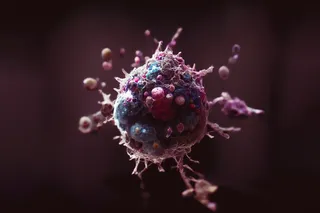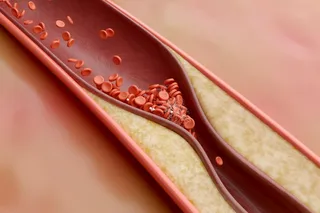1994年2月19日晚上8点15分左右,医护人员将一名年轻女子推入南加州河滨市综合医院的急诊室。他们穿过两套双层玻璃门,向左转,将她停在一个标有“创伤一室”的小帘子隔间里。这名女子身穿短裤和T恤,神志清醒,但对问题的回答只有简短且有时语无伦次的只言片语。她呼吸浅而快。她的心跳太快,以至于心室在泵血前无法充满血液,导致血压急剧下降。当晚在创伤室协助工作的呼吸治疗师莫琳·韦尔奇回忆说,她唯一不寻常的地方是她的年龄。韦尔奇说,大多数出现这种症状的急诊室病人都是老年人。而这名女子,据医护人员报告,年仅31岁,患有宫颈癌。她的名字叫格洛丽亚·拉米雷斯。
围在拉米雷斯身边的医护人员给她注射了一系列速效药物,这是针对她病情的标准治疗方案:安定、咪达唑仑和阿提凡用来镇静,以及利多卡因和溴苄胺等药物来抑制她异常的心跳。与此同时,韦尔奇用一个Ambu-bag(一种足球大小的橡胶气囊,连接到一个覆盖在病人鼻子和嘴巴上的塑料面罩,作为口对口人工呼吸的卫生替代品)将空气强行送入拉米雷斯的肺部。当发现拉米雷斯对治疗反应不佳时,工作人员试图用电击除颤。他们脱掉她的上衣,将带垫的电极按在她胸前;就在那时,有几个人看到拉米雷斯的身体上覆盖着一层油光,还有人注意到一种果味、蒜味的气味,他们认为是她嘴里发出的。
为了抽血化验,一位名叫苏珊·凯恩的注册护士用酒精擦拭了拉米雷斯的右臂,插入导管,并连接了注射器。就在这时,急诊室紧张而有序的常规开始被打乱。当注射器充满血液时,凯恩注意到血液中有一股化学气味。凯恩把注射器递给韦尔奇,并俯身靠近垂死的女子,试图追查气味的来源。韦尔奇闻了闻注射器,也闻到了一些东西:我以为会是化疗的味道,就像人们服用某些药物时血液发出的腐臭味。但韦尔奇说,闻起来像氨水味。她把注射器递给了一位名叫朱莉·戈尔琴斯基的住院医生,她注意到血液中漂浮着不寻常的马尼拉纸颜色的颗粒——这一观察得到了负责急诊室的医生温贝托·奥乔亚的证实,他当时正在帮助治疗拉米雷斯。
凯恩转向创伤室的门口,身体摇晃了一下。“抓住她!”有人喊道。奥乔亚冲向凯恩,扶住了她,并轻轻地将她瘫软的身体引导到地板上。凯恩说她的脸在灼烧,她被放在担架上带离了创伤一室。戈尔琴斯基也开始感到恶心。她抱怨自己头晕,离开了创伤室,坐在一张护士的办公桌前。一名工作人员问戈尔琴斯基是否还好,但没等她回答,她就瘫倒在地。她现在是河滨急诊室工作人员中第二个被担架抬离创伤室的人。戈尔琴斯基间歇性地抽搐;她会一次又一次地停止呼吸几秒钟,然后呼吸几下,再停止呼吸——这种情况被称为呼吸暂停。与此同时,在创伤一室,韦尔奇成为第三个倒下的人。“我记得听到有人尖叫,”韦尔奇说。“当我醒来时,我无法控制四肢的活动。”
那个超现实的夜晚让河滨综合医院在接下来的几周里登上了报纸和电视新闻的头条,一个人的身体释放出有毒气体的可怕可能性抓住了公众的想象力。这也引发了法医史上最广泛的调查之一——来自十个地方、州和联邦机构的医学侦探调查了数十种潜在的罪魁祸首,从有毒的下水道气体到群体性歇斯底里。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嫌疑都已排除,只有一个非同寻常的假设:一个研究团队认为,一系列化学反应可能基本上将格洛丽亚·拉米雷斯的身体变成了一个神经毒气罐。
韦尔奇倒下后,其他几名工作人员也开始说他们感到不适,医院管理人员宣布进入内部紧急状态。奥乔亚命令工作人员将所有急诊室病人疏散到医院外的停车场。一小队人马留下来帮助他拼命抢救拉米雷斯的生命。她的血压持续下降,脉搏越来越微弱。奥乔亚和其他三个人反复进行电击和药物治疗,但他们稳定拉米雷斯的努力失败了。晚上8点50分,奥乔亚宣布她死亡。两名工作人员将尸体移至创伤一室旁边的一个隔离前厅。
在外面,停车场里,医院工作人员在昏黄的硫磺灯光下治疗病人和生病的同事。由于担心受影响的工作人员是被有毒化学物质击倒的,他们被剥得只剩下内衣,衣服被捆进塑料袋里。戈尔琴斯基继续出现震颤和呼吸暂停。凯恩挥舞着手臂踢着腿,她的脸仍然在灼烧。与此同时,一名职业护士萨莉·巴尔德拉斯,曾返回室内帮助将拉米雷斯的尸体抬入隔离室,她开始干呕,并感到皮肤有灼烧感。很快,她的情况变得非常糟糕,也被放在了担架上。
总共有37名急诊室工作人员中的23人至少出现了一种症状。其中五人住院过夜。巴尔德拉斯在为期十天的住院期间经历了呼吸暂停的发作。病情最严重的戈尔琴斯基在重症监护室待了两周,除了呼吸暂停,她还患有肝炎、胰腺炎和缺血性坏死,这是一种骨组织因缺血而开始死亡的疾病。在她的病例中,缺血性坏死侵袭了她的膝盖,使她几个月都得拄着拐杖。俄勒冈州立大学的临床毒理学家谢尔登·瓦格纳说:“能造成这一切的,得是一种非常非常强效的毒素。”
最先到达现场的是河滨县危险品处理小组,大约在晚上11点到达医院。危险品处理小组正在寻找确凿的证据——可能仍潜伏在急诊室空气中的某种挥发性有毒物质。他们搜寻了多种有毒化学品,包括硫化氢(也称为下水道气体),这是一种阴险的毒物,闻起来像臭鸡蛋,在高浓度下一两口就能致人死亡;还有光气,一种具有双重身份的气体——一方面,它是制备许多有机化学品时合法的成分,另一方面,它是一种可怕的化学战武器,会撕裂肺部毛细血管,使受害者溺毙于血液中。令医院管理人员松了一口气的是,危险品处理小组在急诊室没有检测到这些化学物质。
然而,危险品处理小组没有找到任何嫌疑物,这对于河滨县验尸官办公室来说并非好事,他们的病理学家现在面临着一项令人不安的任务:在对拉米雷斯的尸体进行尸检时,完全不知道尸体中潜藏着什么——可能是一种逃逸的病原体、一种有毒化学物质,或者什么都没有。为了万无一失,他们穿上密闭的太空服,进入一个密封的检查室对尸体进行处理。90分钟后,他们带着血液和组织样本以及从尸袋和装尸体的铝箱中抽取的空气样本出来。
验尸官办公室对随后几天的分析一直守口如瓶。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尸检几天后,河滨县验尸官仍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并开始寻求帮助。
其中一个咨询小组是一个名为法医科学中心的神秘机构,位于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利弗莫尔位于旧金山东部约60英里处,其根源可追溯到二战后不久开始的核武器建设。但在过去十年中,随着核武器生产的减少,利弗莫尔及其兄弟实验室试图寻找一个更适合后冷战世界的身份。这一目标促使法医中心于1990年成立,该中心是一个信息交换所,允许州和联邦执法法医团队向利弗莫尔及其他能源部实验室的科学家寻求高科技援助。
法医中心在三月初接手了拉米雷斯的案件,当时萨克拉门托的一位犯罪学家让河滨县验尸官办公室联系上了该中心的副主任帕特·格兰特。3月25日,经过一些初步讨论后,该办公室正式请求利弗莫尔的帮助,并将尸检样本用干冰运送到实验室。
“我们在那个月的最后一天开会,以确定我们确切的行动计划,”该中心主任布莱恩·安德森说。他们制定的计划很直接:分析拉米雷斯器官(包括心脏、肝脏、肺、大脑和肾脏)的血液、胆汁和组织中的化合物,包括有机物和无机物。团队还将检查是否有任何气体从样本中挥发到顶部空间,即样本与容器顶部之间的空气层。
安德森怀疑顶部空间很可能是有毒气体的藏身之处——尤其是在装有胆汁的容器中,胆汁是肝脏分泌的黄色液体,毒物常常在此浓缩。但当他将胆汁加热到体温以提取其中可能潜藏的气体时,他只发现了氮气、氧气、二氧化碳和氩气——都是空气的正常成分。“我希望能看到一种化学物质,某种能把大家都击倒的小分子,但那里什么也没出现,”他说。
接下来,安德森使用一种名为计算机引导的组合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的强大工具分析了样本。程序如下:首先,安德森将一滴准备好的样本注入色谱仪。这滴含有数百种化学物质的样本被汽化并送入色谱柱,在其中缓慢加热至570度。随着蒸汽温度升高,化学物质开始沿色谱柱迁移,并根据其电荷和蒸气压进行分离。安德森测量了它们的浓度,然后将蒸汽送入质谱室,该室用电子轰击化学物质。“电子将分子打碎成各种碎片,”安德森说。这种独特的破碎模式,每种物质都不同,被称为质谱。
通过研究质谱,安德森推断出了拉米雷斯临死前体内循环的多种化合物的身份;其中包括利多卡因、泰诺、可待因和Tigan(一种止吐药)。安德森还发现了大量的碳氢化合物,这些化学物质是从无菌塑料容器中渗入样本的。“医务人员认为无菌是没有细菌,而不是没有化学物质,”安德森说。“所以他们使用的产品是超级干净和消毒过的,但上面覆盖着化学物质。”一个训练有素的法医眼光可以迅速排除这种误导性信号。
忽略了这些误导性信息,安德森发现了一些有趣的异常现象。其中一个是未识别的胺,一种氨的衍生物,可能与急诊室中注意到的氨味有关。国家职业安全与健康研究所的调查也发现了这种胺,并提出它可能是一个罪魁祸首,尽管它在尸检样本中的含量微乎其微。安德森的团队对这种胺有更可能的解释:他们认为它是在拉米雷斯的身体分解止吐药Tigan时形成的。
第二个奇特的发现是烟酰胺——一种像光气一样具有双重性格的化合物。它是一种对人体健康至关重要的B族维生素,但它也常被混入像甲基苯丙胺这样的非法药物中。由于烟酰胺相对便宜且能引起欣快感,毒贩可以用它来稀释他们昂贵的毒品,从而获得更大的利润。“对于一个病得很重的人来说,服用这种化合物很不寻常,”安德森说。
第三个奇怪的化学信号既不能归为琐碎也无法确定其重要性:二甲基砜。二甲基砜是由一个硫原子、两个碳原子、六个氢原子和两个氧原子组成的分子。它被制造用作工业溶剂,但有时也在我们体内由含硫的氨基酸自然产生。被肝脏分解后,二甲基砜在体内的半衰期不到三天,所以健康人体内从未有可测量的量。但在拉米雷斯的血液和组织中,却有每毫升数十微克的浓度,大约是样本中可待因含量的三倍。“在谜团的这个阶段,我们看到的唯一不寻常的东西就是二甲基砜,”安德森说。
但二甲基砜本身不可能击倒一个急诊室,所以当安德森于4月12日飞往河滨向验尸官汇报时,他的结论是他没有发现任何看起来像毒物的东西。安德森回忆说,验尸官办公室焦急地提问,希望能找到确凿的证据,但他坚持认为,拉米雷斯似乎只是服用了大量的可待因和泰诺,这两种药物在大量、持续服用时会损害肝脏。他还强调了那些引起他兴趣的发现:可能引起氨味的胺、烟酰胺和二甲基砜。“显然发生了一些不寻常的事情,但没有任何事情可能导致拉米雷斯的死亡或急诊室的症状,”安德森说。他感到很沮丧。“我记得当时在想,‘我怎么花了这么多时间却什么也没找到?’”
河滨县验尸官办公室也觉得他们已经走到了尽头。在4月29日公布尸检结果的新闻发布会上,验尸官斯科蒂·希尔宣布,拉米雷斯死于由其宫颈癌引起的肾衰竭引发的心律失常。希尔说,对她死亡的调查已经结束。至于医院工作人员的疾病以及这可能与拉米雷斯有何关联,希尔总结道,“详尽的毒理学研究未能确定任何可能导致她死亡的外部有毒物质。”
尽管拉米雷斯死亡的案卷现在正式关闭,但医院工作人员中爆发的疾病仍然没有解释。县卫生部门求助于加州卫生与公共服务部,该部门指派了两名顶尖科学家——安娜·玛丽亚·奥索里奥医生和克尔斯滕·沃勒医生负责此案。他们采访了2月19日在急诊室工作的34名医院工作人员。奥索里奥和沃勒使用一份标准化的问卷发现,那些出现严重症状,如失去意识、呼吸短促和肌肉痉挛的人,往往有一些共同点。也许不足为奇的是,那些在拉米雷斯两英尺范围内工作并处理过她静脉输液管的人风险很高。但其他与严重症状相关的因素似乎与烟雾释放的情景不符:调查发现,受影响的往往是女性而不是男性,以及那些当晚没吃晚饭的人,而不是那些吃饱了的人。
这些发现,再加上尸检结果、危险品分析以及受影响医院工作人员无异常的血液检测结果,导致卫生部门于9月2日发布了一份官方报告。结论是:医院工作人员很可能经历了一次群体性心因性疾病的爆发,可能是由一种气味引发的。换句话说,他们是被压力和焦虑击倒的。为了支持这一群体性歇斯底里理论,奥索里奥和沃勒引用了缺乏毒物证据以及女性更容易出现严重症状的事实,这两点都是群体性歇斯底里的典型标志。此外,他们指出,在救护车上治疗拉米雷斯的两名护理人员都没有生病——尽管空间狭小,而且他们在开始静脉输液后接触了她的皮肤和一些血液。然而,奥索里奥和沃勒并未排除某种物质毒害了直接在拉米雷斯上方工作的急诊室工作人员的可能性。
卫生部门的报告引发了又一轮新闻报道;这些报道以戈尔琴斯基和她的律师、医生拉塞尔·库斯曼为主角,他们谴责了群体性歇斯底里的结论。此时,戈尔琴斯基已对河滨综合医院、验尸官办公室和其他几方提起诉讼,索赔600万美元。一份暗示戈尔琴斯基经历心身症状的报告在法庭上对她肯定不利。“这份报告可能基于政治或无知,但它不是基于科学,”库斯曼告诉《纽约时报》。“这些都是专业的急诊室工作人员。他们不会因为一次心脏病发作而变得歇斯底里。”
这份州报告也激怒了其他一些急诊室工作人员,包括韦尔奇。她坚信,那天晚上她和任何其他人都没有参与群体性歇斯底里。她希望有人能更仔细地审视这个案子,在她看来,利弗莫尔是所有相关实验室中唯一没有既得利益的。韦尔奇给利弗莫尔的安德森打电话,恳求他再看一看。为了吸引他重新回到这个案子,她寄给了他一份她收集的资料剪贴簿,包括新闻报道、河滨县验尸官的报告、法律简报和毒理学报告。
安德森请他的副主任格兰特筛选这份文件。为了让格兰特回忆起这个案子,他还向他展示了自己的结果,包括他识别出的那些令人费解的化合物。安德森摊开一张带有气相色谱-质谱联用结果的纸,图表上的峰值类似于地震仪上的地震读数,并指向了二甲基砜的峰值。
格兰特有点犹豫。“我是一名核化学家,我的有机化学知识说实话微乎其微,”他说。格兰特把二甲基砜误认为是二甲基亚砜,或称DMSO——这两种化学物质的区别仅在于DMSO有一个氧原子,而不是两个。格兰特对DMSO更熟悉,因为,他说,“我以前当运动员的时候用过DMSO。”DMSO以凝胶形式在五金店作为重型脱脂剂出售,长期以来一直是运动员治疗肌肉和关节酸痛的民间疗法。安德森纠正他说,那个峰值是二甲基砜。格兰特直到几天后在飞往华盛顿特区参加商务会议的航班上才开始看韦尔奇的文件。“有很多我们以前没见过的东西,”他说。特别让他震惊的一件事是尸检报告中关于拉米雷斯身体大蒜味和油光来源的推测:DMSO。
DMSO有着一段曲折的历史。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一系列研究表明它具有显著的治疗能力,能缓解顽固性疼痛并减轻焦虑。但这种潜在的神奇药物的兴起突然停止了,因为动物试验表明,长期接触DMSO会改变眼睛的晶状体。由于担心DMSO药物可能会损害人们的视力,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于1965年命令公司停止该药物的临床试验。FDA后来放宽了这一政策,并于1978年批准了一种50%浓度的DMSO溶液作为治疗间质性膀胱炎的药物,这是一种以痛苦的尿路病变为特征的疾病,主要发生在女性身上。
与此同时,在过去的30年里,DMSO作为一种家庭疗法在地下流行起来。不仅格兰特用过,安德森也记得20世纪70年代他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担任药理学教授时DMSO的风靡。“体育系的每个人似乎都在用DMSO治疗伤病,”他回忆道。
它的使用也不仅限于运动员。“人们用它来治疗各种疾病,从关节炎到肌肉拉伤,”加州州流行病学家乔治·卢瑟福说。但考虑到其潜在的副作用,这是一种危险的疗法,因为在五金店随时可以买到的脱脂剂形式中,它的纯度高达99%。由于对日益增多的DMSO使用者感到担忧,FDA在1980年向医生发出警告:“劝告患者不要购买质量不明的DMSO并自行用药。”
然而,即使拉米雷斯为了减轻疼痛在身上涂抹了DMSO,即使它与氧气结合形成了安德森发现的二甲基砜,这仍然无法解释医院工作人员中爆发的疾病。格兰特决定更多地了解DMSO和二甲基砜,所以当他回到利弗莫尔时,他在《默克索引》中查找了这两种化合物,这是一本化学家的圣经,描述了超过10,000种化学品、药物和生物物质的特性。由于DMSO可以与氧气反应形成二甲基砜,格兰特开始思考当向该化学物质中添加氧气时还可能形成哪些其他化合物。在他正在阅读的同一页索引上,他找到了答案:硫酸二甲酯。“这真是 fortuitous(侥幸)的事情之一,”格兰特说。
在化学中,微小的变化有时会导致巨大的结果。向DMSO中添加一个氧原子,你得到二甲基砜——你将一种溶剂变成了另一种。但现在向二甲基砜(化学符号为(CH3)2SO2)中添加两个氧原子,你就得到了硫酸二甲酯((CH3)2SO4),一种真正有害的化学物质。索引解释说,硫酸二甲酯的蒸气会杀死暴露组织中的细胞,如眼睛、口腔和肺部。当被吸收到体内时,硫酸二甲酯会引起抽搐、谵妄、瘫痪、昏迷,并对肾脏、肝脏和心脏造成延迟性损害。在严重的情况下,蒸气会致命。像许多其他化学物质一样,硫酸二甲酯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工业界使用硫酸二甲酯将甲基基团附加到有机化学品上。但索引也说硫酸二甲酯是一种战争毒气。
终于找到了一种可能造成真正损害的化学物质。意识到硫酸二甲酯是他们迄今为止最好的线索,法医中心的化学家理查德·惠普尔和杰弗里·哈斯在成千上万篇关于这些化合物的论文中进行搜索。一份参考文献特别有启发性,如果有点恐怖的话——一份1987年发布的国防部机密文件,名为《化学战信息参考手册》。它报告说,暴露在每立方米空气中分散的半克硫酸二甲酯中十分钟就可以杀死一个人。(尽管硫酸二甲酯已被测试为神经毒气,但显然从未被制造用于战争。)
利弗莫尔团队从参考书以及工业界购买任何硫酸二甲酯时附带的安全说明书中,收集到了关于硫酸二甲酯暴露症状的详细信息。(一升液态硫酸二甲酯售价约为32美元。)医院工作人员经历的症状与硫酸二甲酯暴露的症状之间的匹配度惊人地一致。在工作人员报告的20种症状中,从昏厥到抽搐再到戈尔琴斯基的肝炎,只有一种——恶心和呕吐——不是硫酸二甲酯暴露的症状。“当症状匹配得如此好时——那是我们可能真的有所发现的第一个迹象,”格兰特说。
尽管如此,法医团队意识到,在向河滨县验尸官解释他们的理论之前,他们需要回答一些棘手的问题——并做一个重要的实验。尽管他们渴望继续推进,但他们不得不将拉米雷斯的案件在九月份剩下的时间里搁置一旁。利弗莫尔的科学家们一直在无偿地、在下班后和周末为这个案件工作,作为一项公共服务。现在,他们面临着在9月30日之前完成一份给支付他们账单的组织——美国能源部,利弗莫尔的上级机构——的技术报告的压力。
十月初,当利弗莫尔的科学家们再次着手处理拉米雷斯的案件时,他们首先必须确定她的身体是否可能产生硫酸二甲酯。安德森在拉米雷斯的血液和器官中发现了二甲基砜的证据,这表明她首先接触了DMSO。其他硫酸二甲酯的前体,如含硫氨基酸,可能无法产生足够多的化学物质来造成如此大的破坏。
研究人员想到了两种可以解释拉米雷斯如何接触到DMSO的情景。其一,拉米雷斯在皮肤上涂抹了一种含有苯环利定(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PCP或天使尘)溶解在DMSO载体基质中的乳膏(一种常见的吸食该药物的方式)。根据加州工业关系部工业卫生师塔姆·斯马尔斯蒂格八月份关于河滨事件的一份报告,河滨县验尸官办公室曾告诉该部门,但未详细说明,拉米雷斯的尸体有与使用苯环利定相符的迹象。这种情况可以解释安德森在拉米雷斯血液和组织中发现的烟酰胺的存在——它被混入PCP中以增加其量。但如果拉米雷斯服用了PCP,应该有人会发现药物本身的痕迹。没有人发现,所以利弗莫尔团队认为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
相反,利弗莫尔团队认为更可能的情况是,拉米雷斯为了缓解癌症的疼痛而在自己身上涂抹了DMSO。这可以解释工作人员观察到的油光和蒜味。拉米雷斯的家人此后否认她在去世前使用DMSO或PCP,但如果她确实为疼痛使用了DMSO凝胶,那将远非不寻常——据估计,三分之二的癌症患者会使用某种未经处方的家庭疗法来治疗他们的疾病。
当拉米雷斯(推测是因癌症相关的肾衰竭)昏倒并被送上救护车时,医护人员给她戴上了氧气面罩。研究人员推测,氧分子涌入她的血液,与她体内的DMSO结合,形成了高水平的二甲基砜。所需成分的浓度越高,化学反应的效率就越高;因此,有了这么多的氧气,没有DMSO未被转化。
现在,利弗莫尔团队需要弄清楚下一步:相对无害的二甲基砜是如何转化为极度有害的硫酸二甲酯的。“在这里,我们担心可能会遇到一个让整个理论破产的障碍,”格兰特说。
他们进行了一项实验,看看在正常体温下,血液中能积聚多少二甲基砜。他们将该化合物溶解在一种名为林格氏溶液的透明液体中,这种液体基本上是血液中除了红细胞以外的所有成分。“我们发现,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将它大量加载到林格氏溶液中,”格兰特说。(研究人员指出,尸检发现拉米雷斯有尿路堵塞。这可能会加剧二甲基砜的积聚,因为它无法从她的系统中排出。)
当他们将一小瓶充满二甲基砜的林格氏溶液冷却到室温(约70华氏度)时,他们看到了一个好迹象。“溶液变得过饱和,二甲基砜开始形成美丽的白色晶体,”与格兰特一起进行实验的惠普尔说。在真实的血液中,这些晶体可能呈现马尼拉纸的颜色。因此,这个过程可能产生了在医院注射器中观察到的晶体,特别是因为急诊室通常比大多数房间凉爽——大约66华氏度。
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但二甲基砜是如何转化为神经毒气硫酸二甲酯的呢?利弗莫尔的化学家们设想了一种尚未被观察到的反应:拉米雷斯血液中的一些二甲基砜分子分解了。原本的(CH3)2SO2变成了CH3、CH3和SO2。硫酸盐(SO4)在体内很常见,所以这两个CH3分子可能与它们结合形成了(CH3)2SO4——硫酸二甲酯。但在她温暖的血液中,硫酸二甲酯不稳定,很快分解成其烃类和硫酸盐成分。当时还没有足够量的神经毒气来伤害医护人员。
然而,当苏珊·凯恩在医院抽血时,较低的温度减缓了硫酸二甲酯的分解。相当数量的硫酸二甲酯在注射器中积聚,其中一些从血液中蒸发出来。这就是毒害急诊室工作人员的气体。硫酸二甲酯不易蒸发——《默克索引》列出其沸点为370华氏度。然而,根据格兰特和其他化学家的说法,在室温下仍会有一部分蒸发。二甲基砜的晶体也转变成了硫酸二甲酯并消失不见。最终,所有的硫酸二甲酯要么蒸发,要么在血液中分解回其组分。因此,那个夜晚恐怖的化学反应向调查人员隐藏了它的大部分痕迹。
“这真是一件非常聪明的侦探工作,”俄勒冈州立大学的毒理学家弗兰克·多斯特说。“在我看来,这需要大量的DMSO,但在她生命垂危的阶段,拉米雷斯可能真的超量使用了,”他说。河滨县验尸官办公室显然同意——它在去年十一月发布了利弗莫尔的报告,称其结论是医院工作人员症状的“可能原因”。
但这一理论也引起了其他科学家的强烈反对。几位有机化学家对DMSO一步步转变为空气中的硫酸二甲酯表示嗤之以鼻。“我相当怀疑,”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有机化学家汉斯·赖克说。赖克怀疑二甲基砜会在人体相对凉爽的环境中分解。“我曾用它作溶剂,温度至少高达300度,”他说。其他科学家则认为,医院工作人员的症状与一些意外接触硫酸二甲酯的工人的症状不符。“那东西就像催泪瓦斯,”新墨西哥大学的生理学家兼神经外科教授杰克·德拉托雷说。“当你接触到硫酸二甲酯蒸气时,首先发生的是它会让你流泪。”没有一个医院工作人员报告流泪或其他眼睛刺激。此外,硫酸二甲酯的许多其他已知影响通常需要几个小时才会出现,而医院的昏厥和其他症状在据称接触后几分钟就开始发生了。
利弗莫尔理论最严厉的批评者之一是一位在20世纪60年代初对DMSO进行了大量临床研究的科学家。斯坦利·雅各布,波特兰俄勒冈健康科学大学的医生和医学研究员,他怀疑从DMSO中不可能产生大量的可疑化学物质。事实上,雅各布说,利弗莫尔的科学家们根本不应该允许河滨县验尸官发布他们的报告。“这就像冷聚变那样的胡闹,只不过这个有可能伤害到人,”他说。他的办公室接到了几十个来自因间质性膀胱炎而接受DMSO治疗的忧心忡忡的女性的电话。“我只是告诉她们,硫酸二甲酯理论在化学上是不可能的,”雅各布说。
但其他科学家则为利弗莫尔辩护。华盛顿特区国家健康与医学博物馆馆长马克·米科齐就是其中之一。米科齐是一名法医病理学家,曾协助调查过数十起不寻常的死亡事件。他指出,法医调查常常找不到真正的确凿证据,但他们仍然可以得出有效的结论。“没有哪条线索能完美地解释一宗死亡,但当所有线索加在一起时,你会得到一个模式。有时这是一个我们从未见过的模式,”他说,比如河滨案。但尽管无法证明利弗莫托的设想,“我认为他们给了我们一份相当有趣和有分析性的报告,”他说。
安德森认为一些反对意见是可以避免的。“我们只是想要验尸官办公室的意见,而他们拿去就说,‘这就是答案。’这让我们措手不及。我们从来没说过这就是事实,只是说人们应该调查一下。而人们还是抓狂了。”
尽管如此,他认为这个假设是好的。“我在答录机上收到了化学家的留言,他们说这是一个不可能的结论,”安德森说。“但大多数人甚至没读过我们的报告,有些人听我解释了我们的假设后就改变了主意。”他指出,确实没有人做过实验来证明当二甲基砜分解并与体内的硫酸盐重新结合时会产生硫酸二甲酯。然而,化学家们曾多次发现,看似不可能的反应结果却是完全可能的。
安德森的团队将进行更多的实验,并再次检查拉米雷斯的血液;他们希望很快能将他们的初步报告变成一篇论文,提交给一份有同行评审的法医期刊。然后,多亏了河滨案的宣传,他们将毫无问题地从一个离奇故事转向另一个。他们被大量的电话和信件淹没,敦促他们彻查一系列谜团,从海湾战争综合症——一些参加波斯湾战争的美国士兵出现的症状——到婴儿猝死综合症。“人们感到沮丧,希望我们从化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些案件,”安德森说。
事件发生十四个月后,河滨案的遗留问题仍然奇特而模糊。如果安德森的团队是正确的,人们不禁要问这次爆发是否是独一无二的。目前,研究人员无法在医学文献中找到类似的中毒事件,也无法说明医院是否应该为未来的病例担忧。利弗莫尔的科学家们确实在他们的报告中提出了一个警示,建议医院应意识到这种化学反应在他们的急诊室中可能产生的后果。其他科学家则更坚信有必要采取行动。“这种情况很可能再次发生——DMSO并不少见,”洛马琳达大学医学院的微生物学家巴里·泰勒断言,他一直密切关注此案。
最终,河滨案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警告和一个谜题。警告是,人体可能是一个发生离奇——且可能致命——化学反应的地方。谜题是,如果利弗莫尔的调查人员是错的,那么1994年2月19日,在河滨急诊室到底发生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