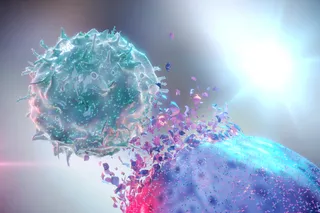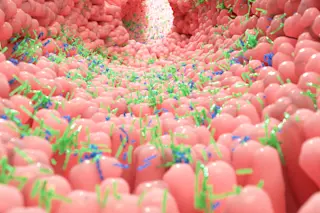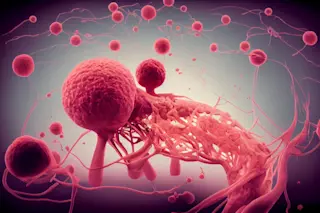张太太躺在急诊室里,拼命挣扎。她与晚期癌症、疼痛和绝望抗争,作为她的肿瘤科医生,我被叫去看她。她刚从台湾探望完父母回来,此刻正躺在绿帘后的担架上,儿子陪在她身边。她蜷着膝盖,双手交叉,闭着眼睛。当我向她问好,隔着磨损的病号服触碰她瘦弱的肩膀时,她转过身来,身体僵硬得不像她这个年纪。她努力想坐起来,努力想挤出微笑,努力想恢复她天生的那种礼貌和优雅。
但这种挣扎耗尽了她所有的力气。她痛苦地呻吟了一声,又无力地靠回了她身下的塑料枕头上。
“我做不到,”她只说了这几个字,“我做不到。”
张太太患有宫颈癌,而癌症正在吞噬她的生命。她还不到50岁,但因为癌症,她永远也无法达到这个年纪。她的人生——作为移民、妻子、母亲、服务员、女儿——充满了艰难。她曾克服了所有这些困难,但现在,她却在与那些她无法战胜的痛苦搏斗。我无法治愈她,只能让她感觉更舒适一些。
自从她大约两年半前第一次来看我——芝加哥库克县医院的妇科肿瘤医生——以来,已经过去了将近两年半。确诊时,她的癌症已经扩散到宫颈(阴道通往子宫的开口)之外,并侵入了周围的组织。尽管癌症已经晚期,但并非完全没有希望。我告诉了她生存的几率,并列出了她的治疗方案。起初,她恢复得很好。放疗缩小了她的肿瘤。随后,子宫切除术移除了残留的病变。两年半的时间里,她都很健康。每隔几个月,我都会在门诊检查她。我密切关注着她的生殖道中是否还有癌细胞。我还会询问她是否有新的疼痛、体重减轻、腿部肿胀或咳嗽——这些都是癌症复发的迹象。
在这些复诊期间,她向我讲述了她的成功与辛酸。她的儿子大学毕业,并开始攻读分子生物学研究生。她仍在一家中国餐馆工作,端茶倒水,送餐上桌。她照料、埋葬并哀悼了多年前与她一起从台湾移民过来的年迈的丈夫。她一直保持着她唐人街公寓的整洁。她一直抱着希望。
然后,她在工作时滑倒,伤了背。她吃了药店买的止痛药,也接受了中医草药师的药方,但背痛依然没有缓解。她儿子注意到了她一直试图忽视的脖子上的肿块,然后带她来看我。我摸到了那坚硬的肿块,并下令进行检查以确认我早已知道的事实:她的癌症复发了。一周后,我站在昏暗、有空调的放射科,看着张太太的CT扫描片,放射科医生指出了她脊柱沿线的恶性淋巴结。后来,一名外科医生将一根针插入张太太锁骨上方的肿瘤,吸出了组织碎片。
当这些细胞在显微镜下被检查时,它们与她宫颈中的恶性细胞无法区分。张太太的癌症发生了转移:癌细胞已经从阴道和骨盆的局部结构扩散开来,通过淋巴系统沿着脊柱向上,穿过心脏后方,最终到达了颈部。癌症在那里通常很容易被发现,因为它们会形成可见的肿瘤。
回到诊所,我向张太太和她儿子宣布了她的诊断。她双手交叠,低着头。他则站着,手搭在她的肩膀上。我告诉他们,她的癌症已无法治愈,已经扩散得太远,放疗或手术都无法控制。尽管如此,我们仍会努力减缓它的扩散。我看到她并不惊讶:我们之前曾谈过我怀疑癌症复发,而她也有同感。我说完后,她站起身,身高不到五英尺。她问道:“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开始交谈。照顾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需要大量的沟通。病人总会想知道为什么他们的治疗无效,即使有些人从未说出口。我知道概率和预后,但却永远不知道为什么治疗对一些人有效,而对另一些人却无效的谜团。我们对癌症的生物学特性和治疗机制仍然知之甚少。我只能握着张太太的手,告诉她我无能为力。我向她道歉。
然后,我们转向更实际的问题;我们讨论了她愿意为抵抗疾病付出多大的努力。我们的谈话方式是她从未有过的。以前,我能告诉她哪种治疗能给她最好的治愈机会。现在,我只能回顾她的治疗方案,让她自己选择最适合的。癌症治疗就是这样。在癌症治疗的早期阶段,通常会遵循基于科学研究制定的明确的算法。治疗过程常常很艰难,涉及痛苦的手术、令人虚弱的化疗或放疗——有时是它们的组合。但通常,一开始的目标是生存。医生会指导病人完成治疗,病人则要忍受。
然而,一旦治愈的希望破灭,就没有了算法,决策的重担就从医生转移到病人身上。重心从治愈转向生活质量,而生活质量的决定因素只有病人自己能判断。有些人会选择积极治疗,与疾病殊死搏斗,永不投降,不计代价(包括疾病、虚弱和痛苦)。有些人则选择立即放弃,不愿委屈自己,当力量耗尽,无法再维持他们珍视的尊严和身体完整性时,便听从死亡的安排。大多数人,就像张太太一样,会选择中间的道路,接受常规的抗癌治疗,如化疗和止痛药,直到不断升级的身体和情感代价变得难以承受。
五个月来,张太太接受了静脉注射化疗。虽然化疗无法根除她的癌症,但却能缩小导致她痛苦的肿瘤。化疗药物很强大:它们通过杀死快速分裂的细胞来起作用。但它们也有强大的副作用:由于大脑和胃肠道的相互作用引起的恶心,以及由于正常但快速分裂的红细胞耗尽而引起的贫血。张太太认为恶心可以忍受,贫血引起的虚弱也是值得的。她每三周接受一次化疗。六周内,她颈部的转移性癌症从鸡蛋大小缩小到一个坚硬的小珍珠,她的疼痛也随之减轻。
然而,五个月后,化疗无法摧毁的癌细胞对药物产生了耐药性。她脖子里癌变的淋巴结又开始增生。疼痛也随之复发。我提供了其他化疗方案:效果尚未充分验证的方案,需要更长的住院时间,会让她脱发,并削弱她的免疫力。她拒绝了。
“我还能活多久?”她问道。
“很少有像您这种情况的女性能活过一年,”我故意含糊其辞地回答。尽管她不理解我用英语解释,但她学分子生物学的儿子用普通话向她解释了化疗为何对不同女性在不同时间会失效:有些人几周内就会失效,有些人可以带惰性癌症生活一两年或三年,而大多数人在六个月左右就会死亡。
“我可以告诉你一百个女人会发生什么,”我告诉她,“有多少人会战胜困难活得更长,有多少人会早逝。但我永远无法预测任何个别病人,也就是您,会发生什么。”
我们没有谈论她的未来,而是专注于她当前的痛苦。疼痛是晚期癌症患者的常客,其原因尚不清楚。不断增长的肿瘤可能会压迫附近的神经,也可能引发局部炎症,这是身体对癌症的一种反应——也是一种无效的防御。麻醉剂是缓解癌症疼痛的关键。但它们带有污名,当我告诉张太太我将给她开吗啡时,我看到了她眼中的恐惧。
“我不会变成瘾君子,”她说。
“不,”我告诉她,“您将摆脱痛苦。我要求病人们把吗啡看作是一种工具。有些人滥用它,它会伤害他们。我们会用它来帮助您。”
我们开始使用速效和长效吗啡的组合,以减轻副作用并尽量减少药丸的数量。我加了泻药来对抗吗啡引起的便秘。不久之后,当我再次见到她时,她坐得更直了,看到我时还笑了。
“我要回台湾了,”她宣布,“我必须再见我的父母一面。我不指望您理解,但这是我的责任。”
“谁会陪您去?”我皱着眉头问道,“谁来照顾您?”
“我照顾我自己。我一直都是。即使在我丈夫去世前也是如此。”
我看了看她总是陪在她身边的儿子。他只是耸耸肩。
“我试图劝她打消这个念头,”他说,“我真拿她没办法。这是中国人的传统,孔子什么的。老一辈都那样。”
她瞪了他一眼。“我就是要去,”她说。我为她开了一张足够的药物处方,并希望海关人员不会为难她。
张太太不在的时候,我阅读了关于实验性治疗和替代疗法的文章,但没有发现任何能真正带来延长生命的希望的新方法。我意识到我喜欢上了张太太。我也意识到她不久将不久于人世。沉浸在诊所、病房和手术室的忙碌中,医生很少反思自己的病例。尤其是晚期病例——那些无法带来战胜疾病的情感回报的病例——尤其难以思考。然而,作为一名肿瘤科医生,我渐渐认识到,照顾临终病人是医生角色的核心部分,这一角色在现代技术能够征服某些疾病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数个世纪。接受这个角色很困难,因为它意味着接受死亡——不仅是病人的死亡,还有你自己的死亡。作为一名妇科肿瘤医生,我最初的训练是产科,在住院期间夜以继日地接生婴儿。也许正是目睹了生与死的循环,生命的延续和几代人的传承,才让我更容易面对张太太和我终将一同走向死亡的事实。想到张太太的生活,让我想到了我个人抱负的局限性和我成就的短暂性。当张太太两个月后返回时,她面对的是一个更加谦逊的医生。
她回来时斗志昂扬,直接从机场前往急诊室。我到达时,她正被疼痛折磨得死去活来。她儿子告诉我,在她回国前一周,她的药就用完了,而她之前无法负担更早的机票或者肿瘤科医生的费用。她几乎是在飞行中才勉强撑过来,癌症在她身上肆虐,飞机又在颠簸中摇晃。
我把她安排住进了医院。我的一位住院医生将液体吗啡通过静脉输液管推入。她的脸放松了下来。她的身体也放松了。她睡着了。
但她的身体已经对麻醉剂产生了耐受。控制她的疼痛需要大量的吗啡,以至于药物让她头晕。她看到了幻觉:童年的朋友,祖父母。我减少了剂量,并添加了其他药物。我使用了一种抗抑郁药,它改变了身体对疼痛的感知方式,减轻了痛苦和绝望感。我使用了抗炎药,以减轻身体对入侵性癌症的反应所引起的疼痛。我咨询了放射肿瘤医生,他们进行了短程X射线照射,以缩小她脊柱骨骼中的转移瘤,并暂时阻止其生长。我请来了一支专门从事门诊疼痛管理的麻醉师团队。他们开具了新的药物来阻断传递疼痛的神经。
我还请来了临终关怀护士。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临终关怀运动兴起,填补了常规医疗疗法留下的空白。临终关怀为临终病人提供了在家中,在亲人朋友的关爱中面对死亡的机会。曾经,这是一种常态,但现在大多数病人在医院里去世,他们的死亡往往被那些侵蚀他们残存生命质量的技术所拖延。临终关怀是一种许多人选择的替代方案。
但对张太太来说,这似乎并非一种可行的选择。尽管临终关怀是建立在同情心的基础上的——咨询、护士探访、便桶和特制床、药物——但它需要花费金钱。张太太几乎没有钱,而且作为一名勉强赚取最低工资的餐厅服务员,她没有健康保险。虽然她的儿子是公民,但她是一名合法外国居民,医院的社工发现,由于她一直以来都是现金交易、不上班,她不符合参加医疗保险(Medicare)的资格。县政府为她提供了门诊和住院治疗,就像几十年来为数百万移民提供的服务一样。但随着预算的缩减,为贫困人口提供临终关怀的资金却寥寥无几。临终关怀团队每周会来一次,但这对极其虚弱的张太太来说还不够。
“这不是问题,”在我一个下午在张太太床边概述了家庭护理的障碍后,她儿子告诉我。“我要退学。”
“不,”张太太说。她试图坐起来,努力想站起来,同时又想控制住自己的愤怒。“我是你母亲,我绝不允许。我宁愿一死了之,也不会让你毁掉你的梦想。”她无力地靠回枕头上。她问道:“毕竟,你认为我这辈子是为了什么?”
最终,他的牺牲没有必要。癌症迅速生长,堵塞了将尿液从肾脏输送到膀胱的管道。肾脏梗阻,张太太的肾脏衰竭了。
“我们可以放管子,”我提议,“这样可以缓解梗阻,争取时间。”
“时间来做什么?”张太太问道,她始终是个务实的人。“我儿子是个科学家。”她叹了口气。“我想看看我的孙子们。”她看了看她有些不好意思的儿子。“但是‘美国先生’(Mr. America)说他还没找到合适的女孩,所以我就走了。”
她陷入了昏迷,在儿子身边去世。在他去通知姑姑、叔叔、表亲、朋友和殡仪馆后,我进去看了看她。她的脸安详宁静。她终于超脱了她所有的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