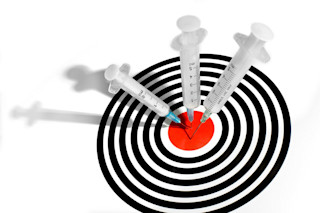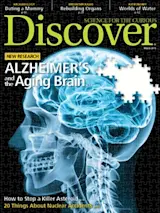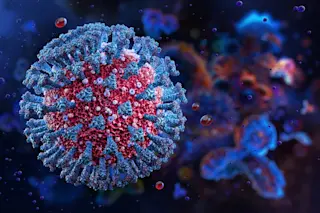回想起来,您不敢相信自己居然错过了:三天,相同的诊断。它们又浮现在您的脑海中:那个挂在椅子上的孩子,左臂扭曲;那个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男人,头颅像患有妥瑞氏症的人一样抽搐;那个30多岁的拉丁裔男人紧捂胸口。
那个孩子在一个拥挤不堪的周五晚上来了。
“医生,疼死我了。天哪,疼死我了,”他呻吟着,抱着左臂。这位20多岁的年轻人带着长岛口音,看起来像个初级营地辅导员。
明显的肩关节脱位。迅速出院。我先处理了他,后面还有三个病人。
“医生,您太棒了!”他喊道。“我该怎么办?我的肩膀一直脱位。要是那个瘾君子在救护车上没踢我该多好。”
“您是医务人员?”
“那个瘾君子毁了我的职业生涯。毁了我的肩袖。”
我同情地轻拍他,帮他脱下衬衫。他左肩上有一道手术疤——很可能是肩袖修复术。然后我看到了他肘部内侧的针孔。他注意到了我的惊讶。
“医生,是卫理公会医院的静脉注射团队。”他摇了摇头。“上周他们为了给我打药、复位我的肩膀,尝试了一次又一次。”
他的右手掌里出现了一部手机。“我哥哥是拉斯维加斯的麻醉师。我相信他很乐意就我的治疗与您进行咨询。”
“和我配合,我们不用药物就能做到,”我向他保证。“我们一分钟就能让您出院。”
“我听您的,医生。”他跳上担架。被自己的说服力所鼓舞,我开始摆弄他的手臂以复位脱臼。
“哎哟。快好了,医生。继续拉。我能忍受,”他呻吟道。
第二位病人——那位商人——在一位担心的护士的陪同下匆匆赶来。
“突然出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头痛,”她喊道。“头一直往一侧偏。会不会是癫痫发作!”
一瞬间,我想,那他为什么还紧抓着他的公文包?
他喊道:“老天,好疼啊,医生!我的头!”
他的头向右抽搐,缓慢地恢复原位,然后再次猛地一甩。这是局灶性癫痫吗?脑出血可以通过引发大脑某个区域向其控制的身体部位放电,从而诱发头痛和有节奏的抽搐。
唯一的其他线索是六周前的一次潜水旅行。这是潜水病晚期症状吗?无论如何,情况看起来很糟糕。
“先生,我们需要立即进行 CT 扫描,”我告诉他。
我转向我的护士梅,说:“给他注射安定和吗啡,然后送去做 CT。”安定,是安定片的同类药物,可以停止局灶性癫痫——如果那就是它的话——并让他放松以便进行 CT 扫描。吗啡,就是吗啡。
第一剂药物注射完毕。我们等了 10 分钟。
“头疼得厉害,医生,疼得厉害!”他嚎叫着。
“把吗啡和安定剂量翻倍,”我命令道。梅通过静脉注射了药物。 CT 扫描技师将他推走了。
第三位病人:“一位37岁的患者,胸痛。两年前曾心脏病发作。”布莱恩,我的医学生,在我们研究心电图时读出了分诊记录。
“现在不是心脏病发作,”我得出结论。“去看他吧。”
十五分钟后,布莱恩回来了。“37岁男性,两年前在波多黎各发生心肌梗死(MI)。植入了右冠状动脉支架。此后恢复良好。两小时前,他感到胸骨后剧烈疼痛,放射到左臂。三次服用硝酸甘油均无效。他还抱怨气短和冷汗。疼痛仍为10分中的9分。姿势或深呼吸均无变化。父亲45岁死于心脏病。”
“哇,这故事太完美了,”我评论道。一个怀疑开始形成。“他有他的支架卡吗?”介入心脏病专家总是给病人一张卡片,上面画有他们植入支架的冠状动脉。
“我没问,”布莱恩回答。
我拉他的胳膊时,长岛皱起了眉头,身体紧绷。“我听您的,医生,”他咕哝着。
我继续拉。骨头似乎咯嗒一声归位,但又开始滑出来。走廊里挤满了新病人。“休息一下,”我喘着气说。
那个孩子握紧了左手。“我觉得我的胳膊变蓝了!”
在我看来,胳膊看起来还好。“我马上回来,”我说。
十分钟后,我们的一位麻醉师走了进来。
“你在这里做什么?”我问。
“你有胳膊变蓝的病人吗?”
“嗯?你怎么知道?”
“他哥哥从拉斯维加斯给我打的电话。”
我惊呆了,心想:他抱怨了吗?我惹麻烦了吗?但随后我看到了一个机会。
“好吧,既然你来了,帮我给他镇静一下,我们就能复位了。”
他耸了耸肩。“当然。”
一位护士准备了麻醉剂和镇静剂的昏迷剂量。随着药物注入,那个孩子的眼睛变得迷离。他的肌肉放松了;肩膀滑回原位。
“好吧,快,我们固定住它,”我喊道。
当我们把胳膊滑入肩关节固定器时,长岛开始苏醒。然后他扭动了一下。肩膀又脱位了。我咒骂了一声。

(图片来源:Guy Shapira/Shutterstock)
Guy Shapira/Shutterstock
那位商人从 CT 室回来了。
“我做不了,”技术员道歉。“他太不配合了。”
这真是一场噩梦。但是潜水呢?我搜索了一个潜水信息中心并打了个电话。一个悠闲、饱经风霜的声音接了电话。
“六周后的神经系统并发症?哇,这倒是新鲜事。能给我患者的信息吗?”我向他汇报了情况。
“这里没有,”他道歉。“是的,潜水病确实会导致头痛和癫痫发作,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昏迷,但不会在六周后才出现。”没有帮助。
另一个想法:也许造影 CT 扫描能显示什么。当造影剂注入血液时,它会照亮脑动脉,从而更容易检测到出血。
那位商人的头还在有节奏地晃动。“哎哟,医生。疼痛又回来了。”
“好吧,这次我们增加他的药物剂量,”我告诉梅。“我们做造影 CT 扫描就完成了。”
梅停了下来,对这个“人肉节拍器”挥了挥手,给了我一个眼神。
“波多黎各,是吗?”我问。
“是的,医生,”那位年轻的心脏病患者礼貌地回答。“他们说我心脏病发作得很严重。”
“你碰巧有你的支架卡吗?”我问。
“啊,在我的钱包里,但我把它忘在家里了。”
我给他看粉红色的、光泽的 EKG,说:“好消息是,你没有心脏病发作。”
“哦,那太好了。”他用手捂住了胸骨左侧。
“那为什么这么疼?”
“我们再给你吃一次硝酸甘油。”
“我在家已经吃了三片了,医生!”
他夸张地皱着眉头。然后我问:“你在哪里接受治疗的?”
“波多黎各。我告诉过你了。”
“圣胡安?”
“嗯?嗯,是的,Centro Medico。”
“你有你医生的电话号码吗?”
他仍然揉着胸口,带着一种新的警惕看着我。“我告诉过你,我把钱包忘在家里了。加西亚医生。”
“好的,我们会给他打电话,”我迅速回答。
他可能以为 Centro Medico 的接线员不会说英语(更不用说 Garcia 是波多黎各版的 Smith 了)。他没想到的是,我是在圣胡安长大的。
两个电话解决了问题。布莱恩看着,然后说:“故事并没有那么完美,是吗?”护士过来了。“他想要止痛药。只是让你知道,他向你要硝酸甘油,但因为吗啡对我大喊大叫。”
我回到他身边,把手放在担架栏上,对我的病人说:“Centro Medico 没有叫加西亚的 the cardiologist。”
肩膀就是接不上。我绝望地给值班的骨科住院医生打了电话。
“听着,我其他的肩关节脱位都能接上,但这个不行,”我恳求道。“你能帮忙吗?”
长岛审视着住院医生、麻醉师、护士和我,然后带着一种懊恼的语气说:“对不起,给你们添麻烦了。”他露出了迷人的笑容。“我真的很感谢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
麻醉师准备了更多的吗啡和丙泊酚。当他将它们注入静脉时,长岛的脸又一次放松下来,露出幸福的表情。
在他昏迷期间,一位住院医生伸手摸了摸长岛的口袋,掏出了他的手机。他举起手机,给大家看。“最后一个拨打的号码是医院寻呼台。拉斯维加斯没有哥哥。”
梅什么也没说。
“先生,”我对那位商人说,“我们需要做一次腰椎穿刺。CT 扫描太模糊了。这是诊断脑出血的唯一方法。”
他第一次和我对视。“腰椎穿刺?不行。”
“那您必须自己签离院。”
“不做腰椎穿刺!”他尖叫道。
当他带着公文包离开,头还在不停晃动时,我心想:一个百万美元的诉讼就这样走了吗?
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医学界重新审视了疼痛处理。在绝症癌症患者饱受痛苦的故事的驱动下,后来又得到了主要是由制药公司资助的患者支持团体的推动,止痛从症状变成了热门话题。政府监管机构和医院董事会也加入了这一行列。现在,医生的报酬与患者满意度挂钩,迫使医生“先开药,后问诊”的压力是无情的。
可预见的结果是?2010年约有16500人死于处方止痛药过量。这比15年前高出三倍。止痛药处方量在10年内翻了三番。维柯丁,一种强效的止痛药,是该国销量第一的处方药。
美国——占世界人口的近5%——却消耗了全球80%的止痛药。
我的三位病人都有相同的诊断:寻求药物。对瘾君子来说,急诊科就是一个糖果店。不,甚至更好:编造一个戏剧性的故事,编个假名,你就能免费拿到东西。
那个长岛的孩子?他可以随意地让他的肩膀脱臼和复位。当我们给他看那份 damning 的通话记录——他冒充拉斯维加斯的医生打电话给医院寻呼台——他醒来后,一边大喊大叫一边踢打着离开了。作为回报,他后来还打电话给 911 报告称一名患者(他自己)在急诊室遭到虐待。那位商人?几周后,一家上城区的急诊室打来电话。一位担心的医生就一位潜水病人向我咨询。这次,那位热心的医生在周末组织了核磁共振成像团队,并让病人住进了重症监护室,然后才发现腰椎穿刺的挑战。现在,这位过于信任医生的医生正因浪费资源而受到医院的调查。
而我的圣胡安同胞呢?当他意识到没有加西亚医生就意味着没有吗啡时,他冲到走廊。“去你的!”他对着护士尖叫道。“我要见管理者!我要你们的名字!”
我站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勉强能躲过拳脚,直到安保人员赶到。失控的药物处方造成的死亡人数终于促使从缅因州到加利福尼亚州的各州采取行动,强制检查处方记录并开展教育宣传活动。但这场瘟疫远未结束。
治疗症状一直以来——而且将来也永远是——比诊断疾病更容易。阿片类药物的过度处方证明了临床推理这一精妙平衡的陀螺仪可以多么轻易地被外部议程所扰乱。在科学医学的开端,疼痛被视为诊断的重要线索,而不是患者满意度得分的驱动因素。
阿片类药物流行的解药是公正的思维。这是古老的疗法,这种临床判断,而且是有史以来最棒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