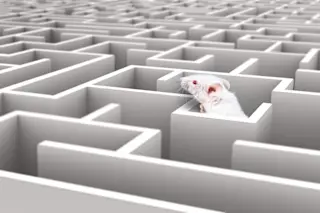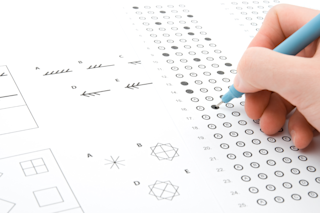自从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工作以来,我一直在考虑与Alex一起研究视觉错觉。2005年夏天,我与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Patrick Cavanagh合作,将这个想法付诸实践。人脑会欺骗我们很多,所以我们有时看到的东西并非其本来的样子。Patrick和我计划提出一个简单而深刻的问题:Alex是否真的像我们一样看到世界?也就是说,他的大脑是否和我们的大脑一样经历视觉错觉?
我设想这项工作是我与Alex旅程的下一个新视野,超越了命名物体、类别或数字。鸟类和人类大脑的进化分歧发生在约2.8亿年前。这是否意味着鸟类和哺乳动物的大脑在结构上如此不同,以至于它们的运作方式也截然不同?
直到2005年Erich Jarvis及其同事发表了一篇里程碑式的论文[pdf]之前,这个问题的答案一直是响亮的“是!”看看哺乳动物的大脑,你会对其巨大的大脑皮层上多重褶皱印象深刻。人们说,鸟类大脑没有这样的皮层。因此,它们的认知能力应该非常有限。这基本上是我在与Alex工作的三十年里一直面对的论点。它本不应该能够命名物体和类别,理解“更大”和“更小”、“相同”和“不同”,因为它是鸟类的大脑。但Alex确实做到了。我知道Alex证明了一个深刻的真理:大脑可能看起来不同,能力范围也可能由解剖学细节决定,但大脑和智力是自然界普遍共享的一种特质——能力有所不同,但基本构建块是相同的。
到千禧年之交,我的论点开始获得支持。这不仅仅是我与Alex的工作,也包括其他人的工作。动物被赋予了比以往允许的更高的智力程度。一个迹象是,我被邀请共同主持2002年美国科学促进会年会上的一个研讨会,题为“鸟类认知:当‘笨蛋’成为赞美时”。其前言如下:“本次研讨会表明,许多鸟类物种,尽管大脑结构缺乏大量皮层结构,进化历史也与人类大相径庭,但在各种认知任务上却能与人类媲美,有时甚至超越人类。”即使是五年前,这样的研讨会也很难获得批准。这便是进步。三年后Jarvis的论文实际上表明,鸟类和哺乳动物的大脑在结构上并没有那么大的区别。又一个进步。
当Patrick和我于2006年7月向国家科学基金会提交资助申请时,我们预计,至少在某些方面,Alex会像我们一样看待世界。我们没有等到收到资助的消息才开始一些初步工作。我们选择了一个广为人知的错觉作为第一个测试。你可能在心理学教科书和科普文章中见过它:两条等长的平行线,两端都有箭头,一条箭头的箭头向外,另一条箭头的箭头向内。尽管长度相同,但对人眼来说,箭头向内的线看起来更长。这就是错觉。我们不得不稍微修改测试,以便利用Alex的独特能力,我们改变了两条线的颜色,保持箭头是黑色的。然后我们问,“哪种颜色更大/更小?” Alex立刻、反复地选择了你或我都会选择的那一个。至少对于这个错觉,他是像我们一样看待世界的。这是一个非常有希望的进展。
到2007年6月,Patrick和我很有把握会获得资助,到8月底,我们得知资助将于9月1日(星期六)开始。我们有一年的资金。接下来的星期一,我们在哈佛大学William James Hall的七楼举办了一个派对来庆祝。我感到特别高兴,并欣慰地看到我的经济困境有所减轻。
不过,Alex本周有点低迷,但并无异常。前一个月鸟类得了一种感染,但现在它们都很好。兽医给它们都开了健康证明。周三下午,Adena Schachner和我以及Alex一起在实验室。她是哈佛大学心理学系的一名研究生,研究音乐能力的起源。我们觉得和Alex一起做些研究会很有趣。那天晚上,我们想看看哪些类型的音乐能吸引他。Adena播放了一些80年代的迪斯科音乐,Alex玩得很开心,随着节拍点头。Adena和我随着一些歌曲跳舞,Alex也跟着我们一起摇摆。下次,我们对自己说,我们会更认真地研究音乐。
第二天,星期四,Alex上午在和两位学生一起研究音素时兴趣不大。“Alex在这个任务中非常不合作。他转过身去了,”他们在Alex的工作日志中写道。到了下午,他更有兴趣了,这次是进行一个简单的任务:正确选择一个有坚果的彩色杯子。
晚上六点四十五分,和往常一样,辅助灯亮起,这表示我们还有几分钟时间收拾。然后主灯熄灭,是时候把鸟放回它们的笼子里了:Wart先,然后是Alex,最后是总是很不情愿的Griffin。
“你乖,我爱你,”Alex对我说。
“我也爱你,”我回答。
“你明天会来吗?”
“是的,”我说,“我明天会来。”
第二天早上,在我查看完电子邮件后,我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当我品味着咖啡浓郁的香气时,一个想法不时地闪过我的脑海,正如我朋友Jeannie曾经说过的:如果我1977年那天得到了一只不同的灰鹦鹉,Alex可能会在某人的空房间里度过一生,默默无闻,无人知晓。当然,我没有,但我们却拥有辉煌成就的历史,并准备好在我们的共同工作中踏上新的征程。而且我们拥有了所需的资源。我也允许自己享受这一切,一种自媒体实验室那个充满激情的日子以来一直难以获得的幸福、兴奋和安全感。是的!然后我回到了我的电脑。
在此期间,又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主题行只有一个词:“悲伤”。我的血液瞬间冻结,当我读完这条信息时。“我很遗憾地报告,今天早上何塞去打扫房间时,发现一只鹦鹉死在他的笼子里……不确定是哪只?……房间左后角。”发件人是K.C. Hayes,K.C. Hayes,布兰代斯大学动物护理设施的首席兽医。
我陷入了恐慌。不……不……不!房间左后角。那是Alex的笼子!我喘不过气来,拼命地压制着日益增长的恐惧。也许他把左右弄混了。也许他犯了个错误。也许不是Alex。不可能是Alex!即使我紧紧抓住那微弱的希望,一边匆忙抓起电话,我也知道K.C.没有犯错。我知道Alex已经死了。在我能够拨号之前,K.C.的第二封电子邮件就已出现在屏幕上。信息很简单。“恐怕是Alex。”
我联系上了K.C.,哭泣和痛苦让我几乎说不出话来。他告诉我,他把Alex裹在一块布里,放在走廊尽头的冷藏室里。我匆忙穿上牛仔裤和衬衫,跳上车。鉴于我的状态,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开车的。我打电话给Arlene Levin-Rowe [我们的实验室经理],因为我不想让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走进实验室。当我联系到她时,她正驾车驶向实验室下方的停车场。“Alex死了,Alex死了,”我哭喊着。“但也许,也许他们弄错了。也许不是Alex。请你去查查,Arlene。”我在说什么?我知道K.C.没有弄错。我知道Alex已经死了。
当我近一个小时后到达实验室时,Arlene和我紧紧拥抱,一起哭了很久。一阵阵的痛苦和绝望涌上心头,共享着难以置信的洪流。“Alex不可能死了,”Arlene抽泣着低语。“他活得比生命还精彩。”
我们知道必须带Alex去兽医那里做尸检。Karen Holmes,一位兽医,带着同情的拥抱迎接了我们。她带我们到告别室,我们把Alex,仍然裹着,仍然在笼子里,放在我们旁边的沙发上。Karen问我是否想最后看Alex一眼,但我没有。多年前,我曾见过我岳父躺在棺材里。很长一段时间,我无法摆脱他躺在那里、生命枯竭的画面。我那时就决定不再看死亡,即使我母亲去世了,我也坚持了这个决定。
我想记住昨晚我放进笼子里的Alex。Alex,充满生命和顽皮。Alex,他是我多年的朋友和同事。Alex,他让科学界惊叹,做了许多他本不该做的事情。现在他却在他本不该死的年纪去世了,比他预期的寿命提前了二十年。该死,Alex。
我想记住Alex最后对我说的话:“你乖,我爱你。”
我站起身,把手放在门上,低语道:“再见,小小的朋友。”
从科学角度讲,Alex教给我的、教给我们的最大的一课是,动物的心灵比绝大多数行为科学家相信的——或者更重要的是,甚至不承认可能有一点可能——要与人类的心灵更为相似。现在,我并不是说动物是拥有稍弱一些的思维能力的微型人类,尽管当Alex在实验室里踱步,对所有人都发号施令时,他确实像个羽毛版的拿破仑。然而,动物远非主流科学长期以来所认为的那样是无意识的自动装置。Alex教会我们,我们对动物心灵了解多少,以及还有多少东西需要去发现。这一见解具有深刻的哲学、社会学和实际意义。它影响着我们对智人(Homo sapiens)物种及其在自然界中地位的看法。
我们曾经认为只有人类会使用工具;事实并非如此,正如Jane Goodall发现她的黑猩猩使用树枝和树叶作为工具一样。好吧,只有人类会制造工具;再次不对,正如Goodall后来和其他人发现的那样。只有人类有语言;是的,但在非人类哺乳动物中也发现了语言的要素。每次非人类动物被发现做着原本是人类特有的事情时,“人类独一无二”学说的捍卫者都会改变标准。
最终,这些捍卫者承认,某些受珍视的人类认知能力的进化根源确实可以在非人类动物身上找到,但仅限于大脑较大的哺乳动物,特别是类人猿。通过Alex所做的事情,他教会我们,这也是不正确的。一种非灵长类、非哺乳动物,大脑只有核桃大小的生物,在沟通方面至少和黑猩猩一样能够学习。这种新的沟通渠道为Alex的心灵打开了一扇窗,向我和所有人揭示了那颗灰白羽毛小脑袋里复杂的、信息处理——思考——正在发生。
因此,一个广阔的动物认知世界存在于那里,不仅在非洲灰鹦鹉身上,也在其他生物身上。这是一个很大程度上未被科学开发的领域。显然,动物比我们想象的知道得更多,也比我们知道的想得更多。这基本上就是Alex(以及越来越多的研究项目)教会我们的。他教会我们,我们的虚荣心使我们对心灵的真正本质——无论是动物的还是人类的——视而不见;而比既定学说允许的要多得多的是关于动物心灵需要学习的。难怪Alex和我面临如此多的批评!
我们也面临着一阵阵的标准转移。他们说,鸟类学不会给物体贴标签。Alex学了。好吧,鸟类学不会泛化。Alex学了。好吧,但它们学不会概念。Alex学了。嗯,它们肯定不懂“相同”与“不同”的区别。Alex懂。如此等等。
Alex在教导这些怀疑论者关于动物心灵的范围,但他们是缓慢的、不情愿的学习者。
摘自《Alex与我:一位科学家和一只鹦鹉如何揭示了动物智能的隐藏世界——并在此过程中建立了深厚情谊》,作者Irene Pepperberg。版权©2008,Irene Pepperberg。经HarperCollins Publishers许可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