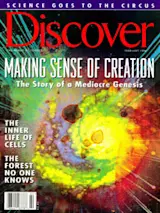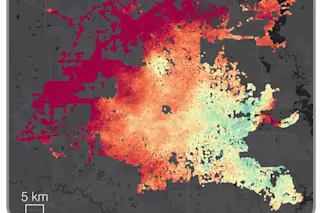夏季上班时,来自安大略省圭尔夫大学的和蔼可亲的46岁植物学家道格拉斯·拉森会徒步登上陡峭的悬崖,系上安全带,然后纵身跃入深渊。
他跳下的悬崖是尼亚加拉断崖的一部分,这是一道蜿蜒曲折的石灰岩和白云石墙,始于尼亚加拉瀑布附近,然后向北延伸,经过圭尔夫校区数英里,抵达伸入休伦湖的布鲁斯半岛;从那里,断崖绕过密歇根湖,向南延伸496英里,最终在芝加哥以北125英里处消失。断崖形成于4.5亿年前,曾经是古海的边缘,古海大约位于今天五大湖的位置,这使其对地质学家或古生物学家具有明显的吸引力。然而,它对植物学家感兴趣的原因是,在其古老、恶劣、不宜居住的表面上,是落基山脉以东最广阔、最未受干扰的原始森林。
拉森和他的同事们发现,这片森林是一个不同于地球水平部分生长的生态系统。它以东方白雪松为主,这种树在地面上只能活90年左右,但正如拉森发现的,在悬崖上却能活到1600年。断崖上的树木发育不良,扭曲变形,常常倒挂生长,是世界上生长最慢的植物之一。研究人员还发现,悬崖上其他奇怪的居民中,有生活在岩石内部的生物——这些生物通常在寒冷的南极平原或炎热的中东沙漠等地方发现。最重要的是,这片森林坐落在700万人口的工业化地区中央,它似乎可以提供2700多年前的气候模式记录,可能为全球变暖问题提供急需的答案。
难怪拉森,以及树木年轮学家皮特·凯利(拉森亲切地称他为“我的年轮专家”)以及由拉森的悬崖生态研究小组组成的各种研究生,愿意在夏天大部分时间都穿着头盔和安全带。事实上,拉森认为自己是个幸运儿。在从事悬崖工作之前,他曾花了十年时间研究地衣,但到了八十年代中期,这项研究的资金开始枯竭。拉森的转机出现在1985年秋天,当时一个名叫史蒂文·斯普林的固执研究生进入了他的生活,他正在寻找一个生态学研究项目作为硕士论文。
斯普林是一名休闲攀岩者,他经常爬上尼亚加拉断崖,这是安大略省南部平坦地貌中唯一一座像样的悬崖。他看到悬崖表面散落的树木,对它们感到好奇。他也礼貌地但坚决地拒绝研究地衣。“我相信他说过类似‘研究地衣你肯定疯了’的话,”拉森说。尽管如此,拉森还是不愿让斯普林如愿。“如果你是地衣专家,”拉森说,“就没有太多动力让你让别人独自去研究你专业之外的东西。让每个人都保持一致更容易。”
然而,就在斯普林表达自己偏好的时候,一位名叫尤特·马西斯-西尔斯的新博士后加入了拉森的实验室。她对生物如何在营养匮乏的边缘地区(如南极洲)生存感兴趣。不需要植物学家也知道悬崖是一个边缘环境,当另一位研究生也表示对边缘生物感兴趣时,他们集体的意见说服了拉森组建一个悬崖研究小组。
团队考察了安大略省北部的一些地点,但最终他们选择了断崖,尽管它有令人望而生畏的200英尺高的悬崖。“我们选择断崖是因为它离家很近,”拉森说。“你希望学生在附近;这样,如果他们搞砸了研究,把他们送回野外也不会很贵。”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他们开始研究以悬崖为家的植物群落,测量它们的死亡率和生产力。但直到1988年,他们才决定检查悬崖上占主导地位的白雪松的年龄。在大学生塞迪·纳什的帮助下,拉森开始在米尔顿镇附近进行测量,该镇位于圭尔夫东南,多伦多以西60英里处。研究人员系着绳索,倾斜着身体,从悬崖边伸出去,够到生长在峭壁正下方的雪松。如果一棵树死了,他们就直接锯下一片——拉森称这种样本为“饼干”。如果一棵树还活着,他们就从中钻取铅笔大小的木棒。
有了这些样本,他们可以测量并计算树木的年轮。每年,一棵树都会在它的树干上增加一个新的年轮;年轮的宽度显示了这棵树当年增加了多少木材到它的树干上,而年轮的总数则显示了树的年龄。在第三天外出时,拉森从一棵只有六英尺高、七英寸粗的扭曲小树上切下了一块“饼干”。令他困惑的是,竟然看不到任何年轮。
“我把它带回实验室,用细砂纸打磨,我勉强能辨认出像是年轮的东西,”拉森说。“然后我用我们用来抛光的更细的材料打磨它。”他把样本放在显微镜下,你瞧,那里有所有这些紧密排列的年轮。拉森开始计数。因为他不是树木年轮学家,他数得非常仔细。然后他又数了一遍,又一遍。每次,计数结果都一样:这棵小树活到了350岁高龄。
这是拉森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年龄。人们不仅认为白雪松寿命不到一个世纪,而且东北部几乎所有的原始森林都被认为早已被农民和伐木工人夷平了。在安大略省,今天存在的森林至少是第二代或第三代生长,最多不超过60年,也许70年。所以,一个植物学家在城市化的安大略省中部发现一棵在17世纪40年代发芽的白雪松,用拉森的话说,就像一个记者乘公共汽车发现猫王坐在旁边的座位上。
你必须明白:传统的观点,包括我自己的传统观点,是这个地区没有留下任何原始森林。所以,在一棵树里发现那么多树龄,而且是在你能看到多伦多市中心天际线的地方,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当我意识到我们发现了什么时,我差点——嗯,这么说吧,我简直是高兴得跳了起来。
几周后,又经过400多个样本的检测,拉森和纳什已经登记了许多古树,年龄最大的有700岁。大学发布拉森的发现新闻稿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媒体纷纷前来报道,据拉森说,其他研究人员开始抱怨。“人们在问,‘拉森到底在干什么?他是个地衣学家——就算他撞上一棵树,他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树。’”
拉森意识到他需要做两件事:他必须巩固自己的信誉,而且他必须查明自己是发现了一小片定居前的树林,还是一整片森林。他通过引入树木年轮学家凯利来做这两件事。在悬崖边的九个地点,拉森和凯利从悬崖顶部到基部的岩石碎屑(被称为塌积物)悬挂着涂有三英尺长黑白条纹的旧消防水带。他们沿着标记的长度计算雪松的数量,并采集样本进行测年。这本身就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虽然他们可以坐在较大的树上,但较小的树需要他们用脚抵住悬崖面,或者如果他们幸运的话,可以站在一个可以楔入靴子的岩架上。但即使在这里,也需要绳索和小心——狭窄的岩架可以成为脾气暴躁的山猫和打盹的蛇的平台。
将他们的研究结果与斯普林早期的工作相结合,他们意识到,在整个断崖沿线存在一个以前未知的完整古森林生态系统。生长在悬崖顶部、中部和底部的植物(如接骨木灌木、地衣和蕨类植物)的模式在断崖的整个长度上都保持相似。300到800年树龄的树木很常见,团队向北走得越远,树龄就越大。他们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活树是850岁,位于布鲁斯半岛的北岸。但研究人员发现,活雪松与他们发现的祖先相比,实际上是小巫见大巫。最古老的死树在死亡时竟然有1653岁。(同样令人震惊的是,通过放射性碳测年发现,这棵树在900年前,大约1082年就已死去。死去的雪松如何在潮湿的安大略气候中存活千年,仍然是个谜。)
凯利怀疑悬崖上还有850岁以上的活树,但他很难证明。测定活树年龄的部分问题,除了你在绳索上摇摇晃晃的明显困难之外,还在于很难一直钻到髓心——树木中心的组织。90%的断崖雪松不对称生长——如果你看一棵树干的横截面,你会看到的不是正常的圆形靶心图案,而是一种变形虫状的形状,髓心在一侧,远离中心,树干向不规则的裂片扩展。
拉森和凯利发现,这种奇特的生长模式是树木不寻常的“管道系统”造成的。与大多数树木的根系不同,东方白雪松的根系具有所谓的扇形水力通道。其他树木就像倒置的漏斗,所有来自广泛根系的水和养分混合并流遍整个树干。然而,在东方白雪松中,不同组的根系专门为树干的特定部分服务。当拉森的团队将悬崖上的雪松种子带到实验室并在花盆中种植时,这种效果得到了清晰的证明;后来他们将两种不同颜色的染料注入两根根系中。染料都沿着树木的长度传播,但从未混合,使树木看起来像一根带有垂直条纹的异样理发杆。“我系主任在染料注入后立即看到了这棵树,”拉森说,“他发誓我们是用毡尖笔画上这两种颜色的。它就显示得那么清晰。”
对于生长在悬崖边的生命,这种安排提供了一些优势。“这是一个聪明的系统,”拉森说。“如果一块岩石崩塌并切断一根根,那么只有连接到那根特定根的树干部分会死亡。一棵典型的悬崖树一生中会失去十次根,因为岩石会断裂脱落,或者大量的冬季冰会把根从岩石中扯出来。如果正常的根系以这种方式受损,整棵树都会受到影响;但有了它的扇形通道,东方白雪松可以隔离损伤并生存下来。”
尽管有如此进化的巧妙之处,但仍然很难理解这样一片与普通森林截然不同的森林是如何存在的。在拉森家乡的断崖上下生长着一片典型的落叶林,里面密密麻麻地生长着白蜡树、山毛榉、樱桃树和枫树。这些树扎根于肥沃厚实的有机土壤中,土壤上覆盖着积聚的枯叶、细枝、树枝、粪便和种子。上方有茂密的树冠,下方森林地面丰富的植物群中点缀着各种各样的动物——鸟类、松鼠、花栗鼠、青蛙、蛇、老鼠、蚂蚁、蜘蛛、蜈蚣、千足虫、蚯蚓、甲虫——成百上千大小不一的动物,啃食着,也被啃食着。
没有可与之媲美的垂直碎屑床来滋养雪松。这些树木零星地散布在悬崖面上,经受的温度波动比其他森林要极端得多。在夏季,当白云石和石灰石在阳光下烘烤时,它们会达到高达110华氏度的温度。在冬季,悬崖缺乏土壤提供的任何保护,甚至没有积雪的隔热作用,温度骤降至-20华氏度——更接近北极苔原的环境,而不是周围森林的温带气候。事实上,在悬崖上生长的25种左右的草本植物和蕨类植物中,有5种也在北极地区 thriving。
白雪松并非仅限于悬崖上的生活,但它们在平坦的地形上表现不佳。它们根本无法与更具攻击性的同类竞争。当森林重新占据一块被清理的土地时——比如农民废弃的田地——首先占据的树木是那些像野苹果和栓樱桃一样的树木,它们的种子很快被鸟类带到新的栖息地。后来,其他树木凭借其长期的优势而占据主导地位;例如,糖枫树拥有深厚的根系,可以有效地吸收土壤养分。山毛榉用它们的落叶覆盖地面,抑制其他树木的幼苗生长,同时从它们的根部发出新芽。
如果没有这些优势,雪松就会被降级到像岩石土壤或潮湿沼泽这样的边缘环境——甚至是悬崖。在这里,树木的扇形通道可能会给它们带来优势,而其他树木则存在某些弱点,可能会使栖息地不适合它们。“所有这些物种都有一些小小的个性缺陷,”拉森说。“枫树长得太大,会把自己从岩石中挤出来,就像弹簧从口袋里弹出来一样。相比之下,雪松可以保持小巧,因此它对环境的要求很少。雪松并没有专门适应悬崖。在更正常的栖息地种植悬崖边的雪松,它会像正常的雪松一样生长。”
在这些正常的栖息地,研究人员发现东方白雪松的平均寿命为90年,在此期间,树木平均生长到50英尺高。拉森怀疑,但尚未证明,这个年龄限制是结构性的。这些树因自身的成功而受苦;雪松是北美洲最弱和最轻的木材之一。所以,它们可能长得很快,然后倒下。(对于这样倒下的雪松来说,有一个安慰:如果倒下没有杀死这棵树,它的树枝可以穿透地面并长出新根,然后发出新芽。)
然而,在悬崖上,东方白雪松必须生长得慢得多。随着一些扇形通道的死亡和另一些通道的增大,树木扭曲成复杂的形状,坠落的岩石、挤压的冰块以及压倒性的重力阻碍了它们的进一步生长。即使是最古老的树,通常也只长到10英尺高和1英尺直径。20岁时,它们看起来像幼苗。一棵155年前出生的小树,身高不足4英寸,每年平均增加0.11克木材。这使其成为有史以来记录生长最慢的树。想象一下没有花盆的盆景。
这些树通过将根系深入溶蚀孔穴(杯状的微小凹陷,容纳着少量土壤和水分)来生存。最近,尤特·马西斯-西尔斯试图确定这些孔穴中水和养分供应的波动和不可靠性是否至少部分是雪松缓慢生长的原因。她在圭尔夫校区旁的一处废弃监狱采石场的50英尺高悬崖墙上搭建了工作场地。采石场悬崖上生长着一片雪松,它们在40年前,也就是最后一名罪犯挥舞大锤、采石场关闭时发芽。马西斯-西尔斯将医院用的静脉滴注袋挂在悬崖面上,并将管子伸入根系楔入的裂缝中。她将水和养分注入裂缝,让树木充分吸收。令人惊讶的是,丰富的食物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这些树根本不需要它。
“我们开始把悬崖想象成垂直沼泽,”拉森解释说。“它们似乎总是有足够的水。我们甚至在干旱期间用测量树干内部湿度的仪器测试了这些树,它们从未表现出缺水迹象。”
部分而言,雪松的顽强生命力或许可以解释为它们得到了悬崖生态系统中其他成员的帮助。研究人员发现,树木的根系被一张共生真菌网络渗透,这些真菌能够从岩石中收集磷和氮,并将其泵入树木。他们还发现岩石内部生活着一些生物,它们以一条深绿色的带状物出现在岩石表面下方。这种藻类和真菌的集合以前只在南极洲和中东沙漠等严酷环境中发现过,那里的生物很可能已经进化到生活在岩石内部,作为抵御外部恶劣条件的防御机制。断崖中的一些岩石结合藻类可以将氮转化为植物可以吸收的化合物。虽然藻类的普遍存在使得研究人员几乎可以肯定树木利用了它们的氮,但他们不知道树木是如何获取的。
悬崖森林究竟如何挑战所有生态规律,似乎还需要数年才能发现。但拉森和他的同事们已经开始从悬崖中收获科学成果:一份长达2700年的气候记录。许多因素都会导致树木生长波动:降雨、土壤养分、温度的变化。就悬崖森林而言,正如马西斯-西尔斯所展示的,水和养分的涨落对生长影响不大,这使得气候成为主要驱动力。“在树木年轮中,我们看到温度越低,生长越大;温度越高,生长越慢,”拉森说。在世界其他地区,研究人员正在研究树木年轮,以了解人类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之前气候如何变化,但大多数研究人员认为这在东北部是不可能的,因为所有老树都被砍伐了。然而,现在,悬崖雪松使得这种分析成为可能。
拉森的团队目前只有初步结果,但他们表明,虽然全球变暖正在发生,但其速度并未超过东北部过去经历过的早期变暖时期。这一发现并不与全球变暖可能造成的影响相矛盾,但它有助于将其建立在地球气候的实际历史之上。如果什么都没有,仅此一项可能就能让拉森、凯利和北方的微型森林名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