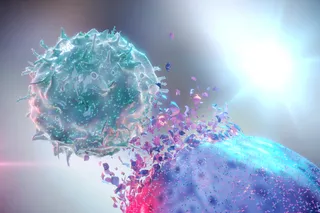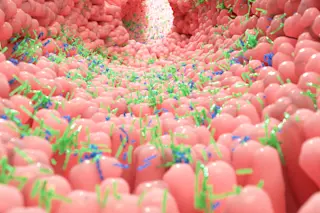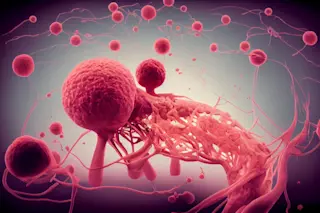六年前,在一个大型、正式的费城法庭上,内分泌学家乔尔·布林德手按《圣经》宣誓,站上证人席——从此告别了他默默无闻的科学生活。布林德是“基督新娘事工团”(Christ's Bride Ministries)的明星证人,该宗教团体曾在东北部各地利用广告牌声称堕胎会增加女性患乳腺癌的几率。负责该市地铁、公交和通勤铁路系统的宾夕法尼亚东南部交通管理局以科学上不健全为由拒绝了这些广告,整个事件最终闹上了法庭。
布林德在纽约市立大学巴鲁克学院教授人类生物学和内分泌学,他是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专家证人。这位瘦长的52岁老人,脸型瘦削,长得像马,职业生涯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生殖激素与人类疾病之间的联系。他擅长以耐心的方式解释科学,让普通人也能轻松理解。在那个温暖的六月早晨的证人席上,他揭示了一个即将发表在英国公共卫生杂志《流行病学与社区健康》(Epidemiology and Community Health)上的理论。
“怀孕几天后,女性卵巢中的黄体开始分泌大量激素,”布林德告诉拥挤的法庭。其中一种化学物质——雌激素——会促进乳房生长,为哺乳做准备。在首次怀孕的最初几个月,“乳房可能已经达到成年大小,但组织还相当原始。换句话说,它还没有专门用于产奶。它主要只是能够生长、增殖。”他补充说,在怀孕后期,生长开关会关闭,这些细胞会分化成成熟的、产奶的细胞。
“现在,原始细胞因为其生长程序,更有可能对致癌刺激敏感,”布林德说。如果一个女人堕胎,她的乳腺导管内会留下大量这些未成熟细胞,因此她将来更容易患癌症——布林德说,比从未堕胎的女人更容易患癌30%。
这位内分泌学家认为,这是一个可怕的事实,而医疗机构——包括国家癌症研究所、美国癌症协会和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在努力对公众隐瞒。在法庭上,“基督新娘”的律师之一詹姆斯·欧文斯试图暗示一场沉默的阴谋。“布林德博士,您认为为什么人工流产与乳腺癌之间的联系没有以警告那些选择流产的女性的形式在公共卫生部门广为宣传?”律师问道。“嗯,用一句常用的话来说,”布林德回答,“这似乎是政治不正确的。”
自从他在费城案件中作证以来——“基督新娘事工”是基于言论自由而非科学依据胜诉的——布林德将课外大约90%的时间都花在了调查和宣传堕胎与乳腺癌的联系上。他曾在亚利桑那州、佛罗里达州、马萨诸塞州、俄亥俄州、北达科他州、新罕布什尔州和阿拉斯加州的法院和州议会作证;他曾游说国会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并致函科学期刊。他的努力正在奏效:至少有18个州考虑立法要求诊所披露这种联系,密西西比州和蒙大拿州已经通过了此类措施。佛罗里达州在要求未成年女儿堕胎前通知父母的努力中援引了布林德的研究。反堕胎活动家利用布林德的声明来捍卫从马里兰州到加利福尼亚州的广告牌和电视广告宣传活动。最近,一位引用布林德研究的国会反堕胎议员说服国家癌症研究所淡化其长期以来关于女性终止妊娠几乎没有癌症风险的说法。
这张图景只有一个问题:绝大多数流行病学家说布林德的结论完全错误。他们说他基于不完整的数据进行了不健全的分析,并得出了与他自己支持生命权的观点相符的结论。他们说,流行病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群疾病的科学,是一门不精确的科学,要求从业者批判性地审视自己的工作,寻找可能影响结果的因素,只有在看到强有力且一致的证据时才得出结论。“不幸的是,谨慎是从事流行病学工作所必须的,”西雅图弗雷德·哈钦森癌症研究中心的Polly Newcomb说,“这是布林德无法做到的。他对堕胎与癌症之间的关联有着如此强烈的先入之见,以至于他根本无法批判性地评估数据。”
对于纽科姆和许多其他人来说,布林德的这场运动凸显了试图理解癌症等疾病起源所面临的挑战,因为这些疾病的发生不一定是从A到Z的直线关系。这场运动也警示了当政治驱动科学时会发生什么。对于试图理解科学争议的普通大众来说,它提醒了为什么研究本身很重要,而不仅仅是相信专家的言论。
10岁的乔尔·布林德在纽约劳雷尔顿长大时,就意识到自己想成为一名癌症研究员。20世纪60年代初,《生活》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细胞内部运作的文章,一个通过电子显微镜突然打开的世界。“他们说科学家会弄清楚细胞是如何运作的,最终他们将能够治愈癌症等等,”布林德回忆道。“我当时就决定,‘哇,这就是我想要的。’”甚至在获得纽约大学博士学位之前,他就发现自己正在研究性激素——特别是雄激素及其与痤疮的关系。最终,他开始研究血液中雌激素代谢物的水平,并将它们与恶性和良性乳腺疾病的发展联系起来。
1992年末的一天,布林德坐在宾夕法尼亚州马塔莫拉斯的餐桌前,阅读《科学新闻》,偶然发现一篇文章,声称怀孕的青春期女孩“似乎对后来的乳腺癌有一种内置的防御机制。”文章没有提及这些女孩是否必须分娩才能获得益处。布林德发现自己反复读了三遍文章,心想:“如果这个青少年终止了妊娠会发生什么?”他开始梳理纽约西奈山医学院的图书馆。尽管40年的相关研究结果不尽一致,但他坚信堕胎是乳腺癌的一个重要风险因素。他认为这在生理学上是说得通的:十多年前,生物学家何塞和伊尔玛·鲁索(当时在密歇根癌症基金会)通过让老鼠流产——使其留下未成熟的乳腺细胞——并暴露于有毒化学物质7,12-二甲基苯并(a)蒽,从而诱发了老鼠的乳腺癌。这种化学物质已知在从未分娩的老鼠中特别有效地产生乳腺癌。
读完这些文章,布林德几乎无法自持。他印了一些传单,标题是“女性有知情权”,然后带着妻子和9岁的女儿坐进他的道奇旅行车,开车去了华盛顿特区,在那里他试图与国会山上的立法者会面。布林德和家人坐在国会自助餐厅里,他看到了众议员理查德·格普哈特,便让女儿过去把传单递给他。布林德回忆说,当格普哈特试图走开时,小女孩恳求道:“不,你真的必须读一下这个。我爸爸说这很重要。堕胎会导致乳腺癌。”
布林德的同行告诉他,除非他在经过同行评审的期刊上发表自己的分析,否则他不会受到重视。于是他联系了两位同事,沃尔特·塞弗斯和琼·萨米-朗,他们都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医学院的内分泌学家,也是堕胎的反对者。由于他们都不是流行病学家,三人缺乏对现有研究进行严肃分析的训练。他们找到了该学院的生物统计学家弗农·钦奇利。“当我听到这个话题时,我的脑子里就响起了警报,”钦奇利说,他自称支持选择权。然而,他同意听取三人的意见,几次会面后,他决定加入他们的团队。
布林德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致力于挖掘将人工流产(与自然流产或流产相比)与乳腺癌联系起来的研究。他彻底地筛选了世界范围内多种语言的文献,这消除了钦奇利的许多疑虑。“我绝不会经历他所经历的折磨,”这位统计学家说。为了避免偏见的指责,研究人员决定纳入他们能找到的每一项相关研究——总共28项——尽管有些研究采用了过时的方法。“我们意识到,由于这是一个如此有争议的研究领域,最安全的做法就是最大限度地包容——把所有东西都包括进去,”布林德说。然后钦奇利将他们的数字输入计算机。
布林德在家时,他的传真机吐出了钦奇利分析的结果:堕胎女性患乳腺癌的几率似乎比未堕胎女性高30%。在生物统计学中,这被称为1.3的“相对风险”或“优势比”(风险为1.0表示没有危险)。由于有如此多的变量可能破坏数据,流行病学家对低于2.0的任何风险都持怀疑态度,除非它在不同研究中持续出现。(例如,国家癌症研究所的科学家曾声称漱口水使用者患口腔癌的几率高出50%。批评者后来表明,一旦酒精和烟草使用等其他变量得到适当控制,这种风险几乎消失了。)
在后来的会议中,钦奇利试图控制这三位支持生命权的科学家的热情。“作为一名统计学家,我有一些疑问,”他说,“我不认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但布林德仍然坚信他的结论,即堕胎与乳腺癌的关联已被证明。“当我们讨论结论时,他想发表最强烈的声明,”钦奇利回忆道,“我试图稍微缓和一下,但布林德博士对他的观点非常坚持。”
如果说钦奇利在宣布堕胎与乳腺癌之间存在联系时持谨慎态度,那么其他科学家——以及现在仍然如此——则对此不屑一顾。“在流行病学中,如果存在真正的关联,你期望会发现大多数研究都表现出某种一致性,”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癌症监测部门主任菲利斯·温戈说。当温戈为《癌症病因与控制》杂志查阅文献时,她发现结果千差万别。“有些研究显示风险略有增加,有些显示略有下降,还有些则显示两者都没有。这种缺乏一致性并不具说服力。”此外,她表示,1.3的相对风险——与吸烟和肺癌相关的20的相对风险相比——通常被认为太弱,无法得出明确结论。
研究人员得出的一个结论是,许多堕胎与癌症研究的设计不佳,导致其结果夸大了接受该手术女性所面临的风险。直到最近,大多数关于该主题的已发表论文都基于流行病学家称之为病例对照研究的方法。研究人员会找到一组病例——被诊断患有乳腺癌的女性——并询问她们是否在早年有过堕胎史。他们还会调查一组对照组——通过随机电话拨号或其他方法联系到的健康女性。科学家会调整年龄、生育史和家族健康史等变量,然后进行计算以确定堕胎的相对风险。
然而,流行病学家无法消除的一个变量是女性是否向研究人员承认她曾经堕胎——因为这种承认对许多人来说仍然是耻辱的来源。这正是结果最有可能出错的地方。相比之下,患者总是在寻找疾病的线索,因此“患有乳腺癌的女性会反省自己,非常可能深入回忆,并透露可能令人尴尬的事情,”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医学院妇产科、妇科和流行病学临床教授大卫·格莱姆斯说。“但是,一个没有患病、从社区中随机选出的女性,很不可能向一个敲门而来的匿名研究人员透露她曾在1992年堕胎。”流行病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应答偏倚,他们已经发现证据表明它可能污染堕胎与乳腺癌的研究。
布林德将应答偏倚斥为未经证实的假设,但其他人则找到了充足的证据。在瑞典,卡罗林斯卡学院的流行病学家布里特-玛丽·林德福斯-哈里斯利用该国全国性的合法堕胎登记制度。在一个发表在《美国流行病学杂志》上的项目中,林德福斯-哈里斯对堕胎和乳腺癌进行了一项病例对照研究,但有所不同:她查阅了政府记录,以查看参与者是否对自己的生育史说了实话。结果发现,她们中的许多人并没有。在829名女性中,有29人似乎谎报了堕胎史,其中绝大多数漏报来自对照组的健康女性。根据这些数字,林德福斯-哈里斯计算得出,“高达50%的观察到的风险增加可能由应答偏倚引起。”
五年后,即1996年,荷兰癌症研究所的马蒂·鲁克斯和弗洛拉·范·莱文提出了更具戏剧性的偏倚证据。这些流行病学家调查了该国两个地区的女性。在自由派的西部,鲁克斯和范·莱文发现了一个统计学上不显著的相对风险1.3——但在以罗马天主教为主的东南部,相对风险飙升至惊人的14.6。唯一合理的解释是:由于东南部保守的宗教价值观,那里的健康女性谎报了她们的堕胎史。“报告偏倚是一个真正的问题,”荷兰团队总结道。
1997年1月,布林德的分析在《流行病学与社区健康》发表三个月后,一位丹麦流行病学家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他的许多同事认为这篇论文使之前关于该主题的许多研究变得毫无意义。丹麦哥本哈根国家血清研究所的马德斯·梅尔比查阅了1935年至1978年间在该国出生的150万名女性的记录。与邻国瑞典一样,丹麦也记录所有堕胎;它还有一个国家癌症登记处。梅尔比将这两个数据库进行关联——结果发现相对风险为1.00。换句话说,接受堕胎的女性患乳腺癌的几率与未堕胎的女性完全相同。(梅尔比确实发现,在妊娠18周或更晚堕胎的女性,风险接近1.9,但这类手术很少见,且仅在紧急情况下进行。)由于如此庞大的人口基数且没有应答偏倚的机会,梅尔比的研究使许多科学家相信早期的病例对照研究受到了污染。“关于堕胎和乳腺癌的故事,基本上被这项最新研究画上了句号,”意大利米兰马里奥·内格里药理学研究所的流行病学家卡洛·拉·维基亚说。
“我认为梅尔比的研究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波士顿大学斯隆流行病学中心副主任林恩·罗森伯格说,“样本数量非常庞大。研究规模越大,统计效力越强,结果也越稳定。”
北美和西欧的公共卫生组织一直淡化终止妊娠的危险性,但去年夏天,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突然转变了立场。该研究所是联邦政府的一个研究机构,曾于3月发布一份情况说明书,称“现有科学证据表明,曾有引产或自然流产的女性患乳腺癌的风险与其他人相同。”2002年7月,众议院反堕胎核心小组联合主席克里斯托弗·史密斯致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汤米·汤普森,称该情况说明书“科学上不准确,误导公众”,之后该声明从该机构网站上撤下。特别是,史密斯批评该研究所未能引用布林德的研究,他称布林德的研究是堕胎与癌症之间联系的“唯一全面的综述和荟萃分析”。11月,该研究所表示已将该信息撤下“以审查其准确性”,并补充说史密斯的信是该决定中的“一个因素”。该研究所发布了一份临时声明,称数据“不一致”。其他可靠机构则对直接驳斥这种关联毫不避讳。“流行病学研究的结果令人放心,因为它们表明孕早期人工流产对女性晚年患乳腺癌的风险没有一致的影响,”世界卫生组织网站上2000年6月发布的一份情况说明书称。
这样的声明只会加剧布林德的努力。他称梅尔比的研究“糟糕透顶”,说这位丹麦流行病学家通过操纵数据“几乎违反了书中的每一条规则”。(布林德曾批评梅尔比调整研究参与者年龄的方式。其他流行病学家则表示梅尔比只是使用了适当的统计方法。斯隆流行病学中心的流行病学家朱莉·帕尔默曾作证说,在梅尔比的研究中,“同龄女性与同龄女性进行了比较。在流行病学研究中,尤其是涉及癌症的研究中,控制年龄是必然的。”)布林德对他最严厉的批评留给了国家癌症研究所等机构,这些机构直到最近的含糊其辞之前,近十年都在向公众保证堕胎似乎不会引发乳腺癌。布林德指责那里的科学家和工作人员从事“科学公正的流产”和“掩盖”真相的行为。他周游世界传播这一信息。在澳大利亚的一次演讲中,他指责国家癌症研究所“通过引用瑞典、荷兰和丹麦的错误分析来保护堕胎行业”。
在流行病学家马德斯·梅尔比看来,布林德的运动是科学客观性的失败。“我认为这是一种反堕胎角度的介入,这对于斯堪的纳维亚人来说是非常不寻常的,”梅尔比说,“在这里,我们希望非常客观地讨论科学,而不是宗教。”
“人类不是老鼠”
当乔尔·布林德试图将堕胎与乳腺癌联系起来时,他从何塞和伊尔玛·鲁索的研究开始。1978年,这对夫妇将49只雌性大鼠分成几组:一组是足月妊娠并分娩的,一组是堕胎的,还有一组是未交配的。然后他们将这些动物暴露于一种已知会导致雌性大鼠患癌的化学物质:7,12-二甲基苯并(a)蒽。结果,18只分娩的大鼠中有1只患上恶性肿瘤,9只堕胎的大鼠中有7只患上恶性肿瘤,22只未交配的处女大鼠中有15只患上恶性肿瘤。
鲁索夫妇在1980年8月的《美国病理学杂志》上撰文总结说,足月妊娠似乎能让雌性大鼠免受已知致癌物的侵害。他们指出,雌性大鼠出生时带有终末芽:乳腺导管末端呈球状的细胞群,这些细胞易患癌症。随着妊娠的进展,这些细胞分化成更成熟的结构,称为肺泡芽和小叶,为哺乳做准备。鲁索夫妇将大鼠与人类进行了类比:与大鼠一样,孕妇会经历荷尔蒙变化,刺激乳腺细胞的生长和随后的专业化,分化为泌乳细胞。“堕胎会中断这一过程,”他们补充道,“在乳腺中留下像在大鼠乳腺中观察到的未分化结构,这可能使乳腺再次易受癌变影响。”
耶鲁大学医学院生殖免疫学部门主任吉尔·莫尔直言不讳地说:“人类不是老鼠。”他说,人类和老鼠是根本不同的生物,并指出老鼠甚至没有乳房,因此,“老鼠没有乳腺癌。我们(使用)老鼠来理解基本的生物学过程。仅此而已。基本的生物学过程。”简而言之,莫尔说鲁索夫妇研究大鼠乳腺分化的基本过程是站得住脚的。但是,当他们或像布林德这样的人试图将这些过程推断到人类身上时,情况就变得不稳定了。
流行病学家表示,布林德未能建立堕胎与乳腺癌之间令人信服的联系。“流行病学研究的第一步是建立一个一致、可信的关联,然后你再看这个关联是否能得到生物学文献的支持,”美国癌症协会分析流行病学主任尤金妮亚·卡莱说。“堕胎与乳腺癌之间没有一致、可信的关联。所以,花费我们的时间去解释一个我们看不到的关联,这有点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