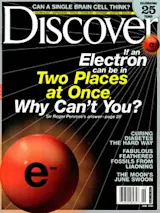有一个地方、一个角色,或者说一种心态,叫做 Tetazoo。这是“第三东区旅行动物园”(Third East Traveling Animal Zoo)的缩写,是麻省理工学院一间宿舍的名字。此刻,几名蓬头垢面的住户,包括22岁的萨姆·肯迪格,正以低技术的人力所能达到的最快速度,沿着教室走廊推动组合沙发,经过穿着实验服的教授和研究生,他们对此都视而不见。毕竟,这是令人惊叹的“神秘寻宝”(Mystery Hunt)周末——稍后会详细介绍——在这种时候,这种奇特的行为是正常的。在这所学院140年的历史中,这些走廊曾有59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30位宇航员走过,还有《杜立德医生》的作者休·洛夫廷、建筑师贝聿铭、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发明家雷蒙德·库兹韦尔、福特汽车公司高管威廉·C·福特、涉嫌“基地”组织特工的阿菲娅·西迪基,以及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汽车谈话”节目的主持人。据猜测,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也都不正常。在麻省理工学院,似乎没有人是正常的。
20世纪60年代,当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另一边的哈佛大学校园生活意味着抗议越南战争、吸食迷幻药和占领建筑时,反主流文化类型的人认为麻省理工学院是五角大楼的门面,那里的一群书呆子开发雷达、导弹和凝固汽油弹。这并非完全错误。但现在很清楚,这些书呆子赢得了那些文化战争:技术已经掌控了地球。
想想看。万维网于1994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诞生。同年,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生创办的公司创造了2320亿美元的价值,并在全球雇佣了100万人。现在,Treo手机和谷歌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都是书呆子。而且很有可能,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们此刻感兴趣的任何事物,都将在大约十年后再次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麻省理工学院的文化是一个肥沃的环境,地球上一些最优秀的创意人才不仅在此孕育思想,还在此探索如何应用这些思想。毕竟,技术的定义是“将知识应用于实际目的的科学”。
嗯,并非总是实用。就拿那些学生推着沙发四处走的“神秘寻宝”来说吧。山姆和他的团队把家具拖进教室,因为他们将在那里日夜生活好几天,以解开大约150个复杂的谜题。沙发就位后,他们又去执行其他任务,为寻宝活动囤积物资:搜罗电源插座和参考书(《牛津狄更斯读者伴侣》、《自行车纸牌游戏官方规则》、《指环王》),并储备大量垃圾食品(棉花糖、烧烤薯片、动物饼干、小黛比蛋糕、激浪汽水),这些将为他们周末的活动提供能量。校园附近星级超市的收银员们已经对“神秘寻宝”的抢购狂潮习以为常。他们曾扫描过整整一购物车的咖啡伴侣(点燃后能产生巨大的火花)或铝箔(用来包裹整个宿舍,包括墙壁、床、CD和书)。有一次,为了单色宴会,山姆只买橙色物品:奇多、多力多滋、胡萝卜、橙汁、奶酪花生酱饼干。
今年,26个独立的团队,人数从两人到超过100人不等,正在参加“神秘寻宝”。“我们主要感兴趣的是聚在一起,解决谜题,并享受乐趣,”萨姆说。但麻省理工学院学生所谓的乐趣,是将一个学期的大脑消耗性工作压缩在三天内完成。例如,每个谜题都从一个层面开始,比如填字游戏,然后进入另一个层面,比如用摩尔斯电码解释填字游戏的答案。最后一个层面结合了所有150多个答案,以创造一个整体的元谜题的解决方案,这使得获胜团队能够寻找到一个隐藏的圆形物体,比如1980年的印第安人头像一分钱硬币或两年前的CD-ROM。而所有这些课外努力的奖品是什么?更多的工作。获胜团队的奖励是允许他们花费数月时间设计下一年寻宝的谜题。
周五中午,比赛开始了。参赛者在网站上查看谜题,在打印件上计算,在黑板上画出数列,敲击笔记本电脑。“谁擅长历史?”有人喊道。“有没有人能识别这首MP3歌曲?”“如果你把通用产品码看作一个10维向量……”“谁擅长集合?”“给……做个字母谜。”“这里有没有人扑克很厉害?”“谁想读点莎士比亚?”萨姆研究一个缩写,一个数字7后面跟着字母串 J. B. F. S. S. C。“詹姆斯·邦德电影,主演肖恩·康纳利!”他欢呼道。“我怎么想到的?”答案是:科学家解决问题的方式——一步一步,运用智慧、灵感和坚韧的结合。参赛者必须擅长各种事物——盲文、密码学、Java、折纸、十六进制、旗语、整数序列、塔罗牌、地图阅读和普通话。
他们确实如此。今年大约1000名毕业生的SAT成绩是麻省理工学院历史上最高的:4%的学生获得了满分;语文平均分为711分,数学平均分为756分。这些孩子,其中一半是他们大多是公立高中毕业班的优秀学生,来自美国45个州和47个国家。对于这样的学生来说,来到校园发现其他与自己相似的人是一种启示。“我以前总有点像个独行侠,”19岁的阿曼达·塞博尔德说,她在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长大,父亲是医疗设备采购员,母亲是网上股票经纪人。在高中物理老师的启发下,她申请了麻省理工学院,并选择住在“刻板印象中的书呆子”随机堂(Random Hall),该宿舍最著名的或许是你可以点击学生设计的网站,查看浴室或洗衣机是否空闲。当阿曼达被问及她是否能记住她的房间号225时,她说:“当然——它是一个完全平方数。”当每个人都开始计算有多少个房间是完全平方数,并确定她的房间是二楼唯一的一个时,她就知道她来对地方了。
她的父母当然很担心:麻省理工学院的自杀率约为每年一起,而最近两起本科生自杀事件都发生在随机堂。2000年,伊丽莎白·申在她的房间和自己身上纵火,她的父母起诉麻省理工学院索赔2700万美元,声称学院本应告知他们女儿(法律上已成年)正在寻求精神科帮助,此案引起了全国关注。此案仍在诉讼中。
“这是一个很难的地方,”在学校工作了25年的招生主任玛丽莉·琼斯说。“麻省理工学院可能是一个你永远无法完全取悦的严厉的父母。”自杀事件发生后,琼斯回顾了申的申请,但没有发现女孩据说自高中以来一直挣扎的问题的任何痕迹。她的学业资格都是顶尖的。在20世纪80年代,男性和女性申请者的SAT数学成绩有10%到30%的差异。现在,琼斯说,“我们经常看到女生在所有科目中都得到800分。”当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他本人是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毕业生)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提出,男女在数学和科学方面的能力可能存在“内在差异”时,一位麻省理工学院的女教授愤然离席。麻省理工学院在最近任命神经科学家苏珊·霍克菲尔德为校长后占据了上风。女性教职员工也增加了,达到18%,2005届学生中43%是女性。琼斯希望招收那些不仅能在压力下生存,还能茁壮成长的男女学生。“麻省理工学院就像一所武士学校,”她说。“这些学生比大多数成年人更有勇气。”
工作既艰巨又无休止——正如他们在校园里常说的,“就像从消防水带里喝水一样”。“这比大多数人所经历的压力都要大,”阿曼达说,她像许多随机堂的居民一样,以她的用户名“vixen”而闻名。现在是一名留着紫色齐耳短发的大二学生,她说高年级学生帮助她度过了大一。作为一名电气工程-计算机科学专业(EECS,这是麻省理工学院充满缩写词的世界中众所周知的),阿曼达每周为宿舍烘焙一次巧克力曲奇饼干,现在也尽力确保新生吃好、睡好、洗澡。麻省理工学院词典中使用最多的缩写词可能就是IHTFP,根据工作量,它的意思可能是“我讨厌这个该死的地方”(I Hate This F---ing Place)或“我真的找到了天堂”(I Have Truly Found Paradise)。对许多人来说,两者都是真实的。学生的口头禅是“工作,朋友,睡觉:选两个。”唯一的休息时间是每年一月的独立活动期,那时孩子们可以参与特殊项目或多睡会儿。很少有人选择睡觉。
但回到Tetazoo的“神秘寻宝”总部:来自明尼苏达州的行星科学专业学生莎拉·纽曼正在解决一个逻辑谜题。她还通宵排练了The Who乐队的摇滚歌剧《Tommy》,这部歌剧的主角是一个弹球奇才,他是一个典型的书呆子——社交孤立,在某个单一领域天赋异禀。然而,莎拉并非如此。大多数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都参加课外活动,包括42项校队体育运动。莎拉的下唇被一个银色戒指分为两半,她刚刚放弃了划船队,加入了自行车队。她有着艺术学校的梦想,并在她的宿舍里精心绘制了苏斯博士的书和西斯廷教堂天花板的壁画。“这里有许多不同层次的书呆子,”她说。“这里有书呆子运动员,有埋头苦读的超级书呆子,也有真正有生活质量的书呆子。”
尽管如此,许多人认为他们需要一点修饰。因此,数百人参加了“魅力学校”,这是一个在学期之间独立活动期间举行的半认真的研讨会。在学生会,恰恰舞的乐声从交谊舞队的教学中飘出。在“成功着装”展位,一位老人向一个戴着锡克教头巾的孩子演示温莎结。在“餐桌礼仪咖啡馆”,一位亚洲学生(8%的学生是国际学生)询问如何握叉子。在“如何告诉别人他们不想听的事情”环节,室友问题通过角色扮演得到解决。
报名人数最多的“魅力学校”工作坊是“调情101”。是的,用校园幽默杂志《Voo Doo》的一篇讽刺文章的话来说,“爱情的难题是具有挑战性的。”一个女性比例失衡的班级集合了。“这是你们的第一个任务——出去找更多的男人,”社会哲学讲师李·珀尔曼说。然而,这里不是汤姆·沃尔夫笔下夏洛特·西蒙斯那种随便性爱的校园。这里的关系似乎要么是认真的,要么根本就没有——因为根本没有时间。因此,萨姆的女友斯蒂芬妮称之为“宿舍内婚”——倾向于与附近的人在一起。珀尔曼认为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不太可能发生一夜情,因为“麻省理工学院的女性不太容易受到男性认可的需求影响——她们的价值通过自己的成就得到认可。”与会者抱怨说,所有人都在谈论学术。“我遇到的女孩只谈量子物理,而且不洗澡,”一位男性说。一位漂亮的女孩打趣道:“这可能与机构本身有关。”珀尔曼说,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比他合作过的其他人更邋遢:“我认为睡眠不足导致了杂乱无章的程度升高。”尽管如此,大多数学生仍在校园内找到爱情,通常会发展成同居关系。
克里斯·霍夫曼,一名来自考艾岛的大一新生,计划主修航空航天学,他是被征召参加“调情101”的男生之一。他是一个英俊的孩子,眨眼的样子仿佛在适应隐形眼镜,身高5英尺4英寸。“高中时只有几个人比我矮,但在这里我没那么矮,”他说。“我这里很多朋友都快到法定侏儒的程度了。”“麻省理工学院符合书呆子的刻板印象——更小、更矮、更瘦、看起来更年轻,”文森特·陈说,他是一名EECS专业的学生,身高5英尺10英寸,觉得自己很高。他说,在划船队里,身高矮是显而易见的:“其他竞争对手都是高大的白人男性,然后就是麻省理工学院的队伍。我们确实很显眼。”
文森特和萨姆在进入麻省理工学院之前,曾在纽约市的亨特学院高中一起参加击剑队。一旦学生决定入学(麻省理工学院失去了一半以上也被哈佛或耶鲁录取的学生,但在加州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方面占据优势),他或她会在入学时选择一间宿舍,甚至是宿舍的哪个厅。作为大二学生,学生也可以选择兄弟会或姐妹会。萨姆和文森特以“预科新生”的身份去考察宿舍,并与一位住在东校区的老朋友住了几天。萨姆很喜欢;文森特“有点害怕”。
在东校区,宿舍楼有诸如Tetazoo、Putz和“东方之兽”(The Beast from the East)之类的名字。有些宿舍会用房费购买炸药。“你不能把这栋楼炸掉,”萨姆吹嘘道,“我们试过了!”Tetazoo里没有人吸烟(宿舍规定:除非你着火了,否则不准吸烟),而且大多数人都不怎么喝酒。没有人看电视。走廊破旧不堪,布满了壁画。房间是随心所欲的建筑项目。共享的猫咪在走廊里懒洋洋地躺着。无论白天黑夜,人们都可能在拆卸或组装东西。全校的就寝时间大约是凌晨5点,但在东校区,夜间时间更繁忙。许多麻省理工学院的“黑客”就源于此。
“黑客行为基本上就是非法闯入,”萨姆说。有时任务是探索一个未知的地下室或屋顶,但其他黑客行为则非常复杂。最显眼的目标之一是校园中心的巨大圆顶,那里曾发生过著名的事件:1994年的一天早上,一辆真人大小的校园警车出现在那里,里面坐着一个假人警察,旁边放着一盒甜甜圈。在其他场合,圆顶被改造成一个带螺旋桨的巨大小帽(1996年),缠绕着刻有《指环王》电影开头精灵文字的巨大戒指(2001年),还曾作为“小鹰号”全尺寸模型的底座,以纪念莱特兄弟飞行100周年(2003年)。登上圆顶需要躲避安全措施和一架20英尺的梯子。“我们尝试了八种方式——警报、锁——来阻止孩子们登上圆顶,”学生生活助理院长史蒂夫·伊默曼说,“我们为他们感到无比自豪——这是我们的一部分。同时,我们有明确的责任确保学生不会让自己或大学面临风险。”
“东校区的人更容易实施这类疯狂的项目,”文森特说,他像10%的毕业生一样,计划继续攻读医学院。“西校区的人可能会说,‘你为什么要浪费时间?’”他说,东校区的人“古怪”,措辞谨慎。“西校区的人离开校园后可能更容易融入。”两组人都用“正常”来形容西校区,东校区的人有些贬低,西校区的人有些防御性。“当你想到西校区,你会想到兄弟会派对、啤酒。当你想到东校区,你会想到火,”阿曼达说,她的随机堂在地理上属于西校区,但从亲近度上属于东校区。西校区是软技术、生物学和经济学;东校区是硬技术、数学和工程学。“Windows Me对我们的Linux,”萨姆的一位朋友说。西校区是星巴克星冰乐;东校区是激浪汽水。
文森特和他的弟弟杰森选择住在西校区的西蒙斯堂,这是一座被称为“霓虹海绵”的建筑杰作,于2002年开放。它有一个冥想室、一个健身房、供应珍珠奶茶的“乒乒茶”咖啡馆,以及Blu Dot设计师家具。难怪东校区的人认为弗兰克·盖里全新的斯塔塔中心也是浪费钱。“那是一座伟大的魔法城堡,”阿曼达的男朋友纳坦·克利弗严厉地说,“但麻省理工学院不需要一座魔法城堡。”萨姆似乎对斯塔塔中心缺乏直角感到个人冒犯;文森特则很欣赏它。
在“神秘寻宝”期间的凌晨2点30分,文森特和萨姆的路径短暂交汇。“他从某个派对回来,而我正在半夜测量东西,”萨姆说,他用攀爬绳从一点到另一点地测量,以解决一个谜题。然而,在麻省理工学院,“正常”是一个相对的术语——即使是西校区和兄弟会也是书呆子气的。西校区的人也有自己的几个“神秘寻宝”团队。而萨姆正在使用的测量单位叫做“斯穆特”(smoot),这个名字来源于Lambda Chi Alpha兄弟会的一名新生,他的身体在1958年被用来测量查尔斯河上横跨麻省理工学院附近的一座桥的距离。长度是364.4个斯穆特“和一只耳朵”。每年,这个兄弟会都会重新粉刷这些测量标记。奥利弗·斯穆特本人,讽刺的是,曾担任国际标准化组织主席两年。这就是麻省理工学院之后的生活。
米其林轮胎与碎石路的碰撞就发生在这里。一份使命宣言指出,麻省理工学院的建立是为了将科学应用于造福人类。在二战后的时代,许多毕业生将科学应用于军事力量。到了越南战争时期,甚至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也抗议“军事技术学院”。萨拉的麻省理工校友父母是在一次抗议活动中相识的。她的父亲,现在是一位神经科学教授,毕业时穿着一件抗议越南战争的标语。萨拉自己也在今年夏天回到以色列,通过计算机语言Java教导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青少年共存,以及在NASA实习之间挣扎。哪个对人类的利益更大呢?
反战行动促使麻省理工学院将德雷珀实验室(军事制导系统)剥离成为一个独立的实体。但该机构仍然雇佣了许多毕业生——其中许多人宁愿住在校园的储藏室里,也不愿离开。已故诺贝尔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热爱他在那里的学生时代,他指出了麻省理工学院的狭隘。“它为自己培养了一种精神,以至于每个成员都认为它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地方,”他写道,“这就像纽约人看待纽约的方式。”作为研究生,费曼当然将物理学应用于造福人类,通过在洛斯阿拉莫斯帮助研发了原子弹。
如今,当遥控设备在阿富汗执行任务并在火星表面巡逻时,即使是不关注新闻的极端极客们也意识到他们工作的伦理影响。萨姆的重点是微机电系统,他的名字出现在一篇名为“使用MEMS电准静态感应涡轮发电机发电”的论文上(他称其为“一个一英寸见方、四分之一英寸厚的燃气发电机”)。作为一名像67%的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生一样期望获得更高学位的毕业生,他需要赞助。他接受了林肯实验室的面试,但没有继续追求。“它过于专注于军事应用,”他说,“我更喜欢把炸东西当作爱好。”20岁的达蒙·范德·林德住在走廊对面,他也同意。“尤其是在伊拉克战争之后,我不想开发武器系统。”达蒙是一名物理学专业的学生,他通过在父亲的阿拉斯加鲑鱼捕捞船上工作来支付麻省理工学院的学费,他说他感兴趣的是“风力涡轮机或为第三世界开发的东西,这些都不会让你觉得自己是个坏人。”
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生追随金钱去了华尔街。在90年代,硅谷吸引了人才。但新千年的学生更加理想主义。他们被可持续技术和改善发展中国家医疗保健的方法所吸引。学院本身也一直在稳步进入生物技术领域。美国政府每年向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投入4.12亿美元,而如今,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投资是国防部的两倍。2003年,去非营利组织工作的毕业生人数(9%)几乎是去国防部门工作人数(5%)的两倍。“乐观、幸福、和平,”琼斯院长这样形容当今学生的兴趣。疾病的计算机模型、针对关节炎和糖尿病等自身免疫疾病的定制药物、新的给药方式、新的测试、癌症的治疗——“这些孩子无所不能,”伊默曼院长说,“我们提供实验室。”
萨姆的女友斯蒂芬妮,23岁,获得了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第一个硕士学位,现在正在攻读技术与政策专业的另一个学位。她刚从巴西回来,在那里她通过在亚马逊教授低成本水质检测和非电动制冷来练习葡萄牙语。她还学习了法语、西班牙语、俄语、德语和普通话。珍妮·胡的论文《用于高通量生物检测的微流控平台》是关于一种快速、廉价的基因检测技术。但22岁、在明尼阿波利斯长大的珍妮,她的父母是来自台湾的化学家,也帮助马里制造了一种低技术含量的划船发电机。她说:“我感兴趣的是帮助人们,而不仅仅是制造消费品。”她和她的男朋友丹尼·申,加拿大的医学研究员之子,都参与了Mayapedal,一个在危地马拉建造自行车动力机器的组织。22岁的丹尼是一个狂热的自行车手,他曾在不到两天的时间内从波士顿骑到纽约,他还与一个名为“自行车而非炸弹”的组织合作,并参与了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项目,该项目计划为非洲的医院制作发电机套件。他曾经齐脚高的黄色莫霍克发型,现在已被裱起来,装饰着Tetazoo的厨房墙壁。在完成他为学校和医院创造微型无线传感器的硕士学位项目后,他计划像他的英雄保罗·法默一样去医学院,法默在海地经营一家诊所。丹尼说:“我认为一个医生的衡量标准是看他是否能给病人带来和平、善良和安宁。”
到周日晚上,神秘狩猎进行到54.5小时,地板上满是疲惫倒下的人、压碎的Cheez-Its饼干和写满数字、字母、碳年代测定、五芒星的便利贴。电话响了。“狩猎结束了,”一位团队负责人宣布。“那谁赢了?”那些仍然清醒的人问道。“随机堂赢了。”笔记本电脑砰地合上,电源线拔掉,黑板擦干净。“我不吸尘——去年我吸过了。”“有没有人回第三东区,把沙发带走!”
课程很快就要开始了。又经历了一段模糊的失眠之夜后,2005届学生将毕业。如果说麻省理工学院是旧机器文化的灵魂,那么今天它培养的“书呆子”们,既有思想也有情感。多年来,毕业生们将知识应用于实践的用途已从权力转向财富,再转向对人类的爱——这是人与机器的结合。也许这些全面发展的极客们进入世界,恰逢其时。
一条名为“无限走廊”的通道连接着东校区和西校区。每年两次,在被称为“麻省理工学院巨石阵”的现象中,落日会穿过大学正门,直接照亮走廊。红色的光子源将大理石地板镀金,流淌过头顶平衡着球杆的杂耍者,为海啸救灾募捐的志愿者,正在学骑独轮车的女孩,纳米技术实验室的门口,以及在消防水管后面找到“神秘寻宝”硬币的藏匿处,成百上千的学生,或向东,或向西,追随着光明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