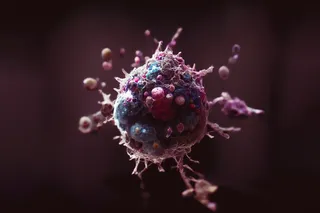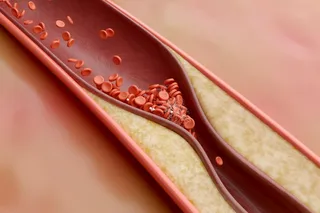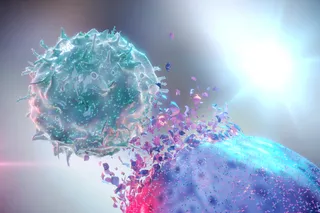在我们骨髓的深处,居住着我们血液的生命起源——造血干细胞。正是这些稀有且难以捉摸的多能细胞,孕育出了输送氧气的红细胞、帮助凝血的微小血小板,以及我们免疫系统中对抗疾病的白细胞。造血干细胞,正是我们血管中生命之河的源头。而欧文·维斯曼(Irving Weissman)发现了它们。
确切地说,维斯曼,一位斯坦福大学的免疫学家,以及他在1988年共同创立的位于加州帕洛阿尔托的生物技术公司SyStemix的合作者们,声称发现了一种极有希望的候选细胞。但他们并没有欺骗任何人。他们如此自信,以至于SyStemix不仅为发现这些细胞的工艺申请了专利,还为细胞本身申请了专利,实际上声称对这些生物实体拥有所有权。瑞士制药和化工巨头Sandoz Ltd.也如此自信,以至于以据报道的3.92亿美元收购了SyStemix 60%的股份,让55岁的维斯曼和他的股东们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
其潜在价值确实巨大。除了干细胞在基础研究中的重要性外,它们还有可能带来一系列突破性的医疗进展。通过赋予患者从头开始制造全新血液供应的能力——从而能够再生免疫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干细胞疗法可能带来治疗各种癌症的新方法,实现无需排斥反应抑制剂的骨髓移植,支持针对艾滋病和其他血液感染的强大策略,并提供基因工程的解毒剂来治疗各种遗传性疾病。难怪维斯曼引起了如此大的轰动。
然而,目前该领域没有任何一位先驱性研究人员使用维斯曼的配方来分离干细胞——当然,SyStemix的除外。无可争议的是,对干细胞的搜寻早于维斯曼,有些人认为即使没有他,这项研究也会顺利进行。虽然研究人员普遍认为维斯曼为这个以前鲜为人知的领域带来了知名度,但他们对于他科学贡献的价值却意见不一。有些人认为他的工作是关键性的,有些人认为它只是有用的,还有些人则认为它几乎无关紧要——正如维斯曼自己所说,将他视为一个江湖骗子。尽管维斯曼的专利存在争议,但关于干细胞究竟是什么以及如何才能最好地追踪它们,仍然存在持续的争论。干细胞先驱、维斯曼的竞争对手,纽约市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的马尔科姆·摩尔(Malcolm Moore)表示:“还没有人明确地分离出干细胞。有很多说法,但尚未被确定到我们可以说‘这就是干细胞’的程度。”
对造血干细胞的现代探索始于1945年原子弹在日本爆炸。研究人员很容易看出,强烈的辐射摧毁了血细胞,并且人们在暴露后几周内经常死亡。但是,在小鼠身上模拟这种暴露的研究人员很快意识到,通过将来自基因相同的供体的骨髓移植到受辐射的小鼠体内,可以预防这些致命的影响。注入的骨髓使受辐射的血液得以恢复;因此,研究人员推断,骨髓中一定含有能够再生其他血细胞的细胞,而成熟的血细胞则不具备这种能力。
在20世纪60年代,这些猜测变成了事实。加拿大安大略癌症研究所(Ontario Cancer Institute)的詹姆斯·蒂尔(James Till)和欧内斯特·麦卡洛克(Ernest McCulloch)发现,在将骨髓细胞注入受辐射的小鼠后,这些动物的脾脏上出现了结节。每个结节都充满了白细胞和红细胞。通过追踪细胞染色体中的遗传标记,蒂尔和麦卡洛克发现每个结节中的细胞都来自同一个祖细胞:每个结节一个。然后,通过简单地计数结节,他们能够估计每批移植的骨髓中祖细胞的数量。这些细胞的比例非常稀少,大约是1000个细胞中1个。此外,蒂尔和麦卡洛克发现,除了产生各种新的血细胞外,这些祖细胞还能够自我繁殖。
基于这些证据,蒂尔和麦卡洛克提出了一种自那时以来一直被奉为圭臬的理论。他们说,所有血细胞都起源于少数隐藏在骨髓中的造血干细胞。(我们不仅拥有造血干细胞:据说还有皮肤、肝脏和肠道的干细胞,以及负责产生卵子和精子的干细胞。)这些细胞,虽然非凡但却稀少,既能自我更新,又能产生数万亿个血细胞,为宿主身体的生命提供取之不尽的来源。当这些新细胞成熟并死亡时——例如,人类红细胞的寿命只有120天——干细胞会产生新的细胞来取而代之。平均而言,这些细胞每天会产生一盎司(约28克)的新血液——约2600亿个新细胞。
艾尔夫·维斯曼(Irv Weissman)在蒂尔和麦卡洛克进行开创性工作时,是一名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学生和研究助理。他回忆道:“我了解那些实验,我了如指掌。它们令人兴奋。”这些实验让他对器官移植问题有了一些了解,这是他自蒙大拿州大瀑布城高中时期就一直感兴趣的问题。“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理解免疫系统的发育,”他说,“如果你理解了它,那么在进行移植时,你就知道发生了什么。”蒂尔和麦卡洛克关于干细胞的发现给了他一条追随的道路。“我开始越来越深入地理解白细胞的发育,从成熟细胞追溯到越来越早期的细胞。”
当然,维斯曼并非唯一一个回溯的人。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都开始关注早期、未成熟的血细胞。其中包括由生物物理学家扬·维瑟(Jan Visser)戏谑地称之为“荷兰黑手党”的血液学家和生物学家。正是“荷兰黑手党”首先在干细胞研究上取得了突破。1984年,维瑟宣布他和他在荷兰的同事们在小鼠中分离出了干细胞。
这是一项惊人的成就,甚至连蒂尔和麦卡洛克也未能做到。安大略的研究人员只能证明这些细胞的存在,而无法将其分离出来。但在此期间,分子技术已经变得更加先进。维瑟拥有分子探针,这些探针可以通过锁定任何独特的特征来找到目标。因此,在骨髓样本中寻找理论上的干细胞,就像试图通过寻找特定组合的发色、体重和鼻型来从人群中认出某人一样。但这并不意味着这项工作很容易。干细胞是相对原始的细胞,缺乏与其成熟后代相关的多样化特征;它们似乎主要以缺乏独特特征而著称。
为了分离出干细胞,维瑟采用了三管齐下的策略。首先,他按密度分离细胞。多年前的研究发现,具有干细胞活性的细胞——也就是说,所有迹象都表明它们就是长期寻找的造血细胞——的密度比其他骨髓细胞要低。因此,维瑟将一批骨髓细胞(约6000万到1亿个)放入离心机中,只分离出漂浮到表面的细胞。这一步就去掉了大约90%的细胞。
接下来,他转向了一种常用于实验室纯化蛋白质的物质:小麦胚芽凝集素(wheat germ agglutinin)。凝集素与某些与蛋白质相关的糖类结合,维瑟发现它也附着在具有干细胞活性的细胞膜上的糖类。因此,他取了剩余的10%细胞,并将其与标记有荧光染料的小麦胚芽凝集素混合。借助荧光激活细胞分选仪(fluorescence-activated cell sorter),他能够分离出所有发出荧光辉光的细胞,这表明标记的凝集素牢固地附着。通过这种方式,维瑟进一步将样本减少了90%。现在,他只剩下原始骨髓混合物的1%。
最后,他使用了单克隆抗体。抗体是Y形的大分子,是免疫系统主要的感染防御者。它们会直接攻击外来蛋白质,抓住它们,并标记它们以便被其他免疫部队摧毁。到20世纪80年代初,这些微型制导导弹已成为分子生物学家的首选工具之一,因为它们可以被工程化以针对科学家选择的几乎任何目标。维瑟将它们导向当时已知的少数干细胞特征之一:一种他发现存在于干细胞表面多于其他细胞的蛋白质,称为H-2K。抗体忽略的细胞没有这种蛋白质,因此不可能是干细胞。他将这些细胞丢弃。
结果是搜寻范围进一步缩小。抗体将细胞数量减少了三分之二:剩余的细胞仅占原始混合物的千分之三,大约20万个细胞。当维瑟将这些相对较少的细胞注入受辐射的小鼠体内时,他发现只需要200个细胞就可以使每只动物的整个血液系统得到再生。换句话说,每1000个骨髓细胞中至少有1个干细胞,这正是蒂尔和麦卡洛克发现的比例。当然,维瑟的样本并不纯——混合物中还有其他细胞——但从最初的数千万个细胞中,他已经非常接近了。三年后,利用更新的细胞分选技术,他进一步缩小了范围,仅用30个细胞就拯救了一只受辐射的小鼠。他现在估计,干细胞占骨髓细胞的万分之一。
维瑟于1984年在《实验医学杂志》(Journal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上发表了他的初步研究结果。四年后,维斯曼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宣布,他和他的同事们找到了小鼠干细胞。而维瑟的工作只获得了温和的赞扬,维斯曼的工作却登上了头条。维瑟带着些许讽刺意味地指出:“《实验医学杂志》在科学上被认为是最优秀的期刊之一。《科学》杂志更受欢迎。”
维斯曼和他的团队采取了一种更为狭窄的方法来寻找目标:他们仅仅依赖各种单克隆抗体,每种抗体都旨在识别一种不同的干细胞表面蛋白质——或者他们发现干细胞上不存在的其他细胞上的蛋白质。例如,一组单克隆抗体靶向仅存在于成熟骨髓细胞表面的蛋白质,从而使研究人员能够去除几乎所有不是干细胞的细胞。维斯曼将剩余的细胞称为Lin-(世系减去),因为抗体已经去除了所有其他细胞世系。“我们使用这些抗体去除了90%的骨髓,”他说,“剩下的10%具有干细胞活性。”
为了更精确地确定这种活性的来源,他们使用了另外两种单克隆抗体,靶向他们知道出现在干细胞上的两种表面蛋白质。一种是Thy1,低浓度(表示为lo);另一种是Sca1,含量高得多(表示为+)。通过剔除不显示Thy1或Sca1的细胞,维斯曼将剩余细胞的数量减少到总数的0.05%。他将剩余的细胞称为Thy1loLin-Sca1+;与维瑟一样,他发现只需要30个这样的细胞就能在受辐射的小鼠体内重建全套血细胞。他得到的是几乎纯净的干细胞群体。
反应强烈而迅速。《科学》杂志在维斯曼的文章旁刊登了一篇题为《造血干细胞被纯化》的新闻报道,其中维斯曼在没有丝毫提及此前为实现同一目标所做的努力的情况下,被引用说道:“这是寻找干细胞这一特定道路的终点。”他认为他的方法——基于识别细胞的实际外观——效率如此之高,甚至可以用于寻找人类干细胞。无论是专注于细胞密度和凝集素结合能力的维瑟,还是其他任何人,都未曾提出过这样的主张。
《华尔街日报》宣称:“科学家们正在逼近一种至关重要的血细胞。”《科学美国人》则宣布:“心满意足:生物学家们终于抓住了所有血细胞的稀有祖先。”维斯曼通过电视和广播传播了这一消息,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也对此进行了全球报道。但尽管公众欢呼,科学界并非所有回应都赞美有加。例如,《免疫学今日》(Immunology Today)的一篇社论虽然承认研究人员确实分离出了一群具有干细胞活性的细胞,但却问道:“这是否代表了对先前已发表数据的任何进步?”社论指出,维瑟的研究已经产生了具有相似特征且纯度略低的细胞群体,并谨慎地得出结论:“我们尚未走到终点;也许只是其中一条岔路。”
人们开始怀疑,维斯曼所做的几乎没有任何新东西,却声称获得了重大的发现。在此过程中,他忽略了早期先驱者的成就,尤其是维瑟的成就。无论维斯曼获得更大的认可是因为他发表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还是因为他是美国人而非荷兰人,或者他只是比维瑟更懂得如何与媒体打交道,许多科学家都认为维斯曼获得的关注与其成就不成比例。
“维斯曼的团队在小鼠研究中做出了真正的贡献吗?不,根本没有,”马尔科姆·摩尔断言,“所有工作早已在别处完成。维瑟很早以前就做过了。所以有些人非常非常生气,因为他声称发现了干细胞,但他并没有做任何初步工作。”
“不幸的是,事情变成了这样,”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的干细胞研究员伊霍尔·勒米施卡(Ihor Lemischka)说,“我认为维斯曼会第一个承认他获得所有功劳是不公平的。这引起了很多不满。现在该领域有两个阵营。有荷兰轴心和维斯曼阵营,而其他人则介于两者之间。”
此后,维斯曼明确承认了维瑟的先前贡献。他说,当时他没有这样做,是因为他根本不知道维瑟的工作。“我们完成了工作,甚至不知道它,”维斯曼声称。“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一位著名的科学家告诉我,当他认真开始做某件事时,他就会停止阅读文献。他不想被别人的工作分心,或者破坏发现的乐趣。我以此为借口。我知道,承认这一点很糟糕。”
无论原因如何,维斯曼的遗漏都产生了不幸的后果。摩尔说:“维斯曼是一位免疫学家,突然进入了实验血液学的领域,却不了解人们已经工作了很多很多年,并且了解所有这些事情。但不知何故,他获得了发现干细胞的功劳。他踩了许多人的脚。”
这其中有十个人的脚属于维瑟,他如今是曼哈顿纽约血库(New York Blood Center)新成立的干细胞实验室的负责人。然而,维瑟对他同事们对维斯曼策略的评估远没有那么尖锐。事实上,他似乎对维斯曼的才华近乎赞赏。“我是否觉得维斯曼抢了我的风头?”他若有所思地说,“一开始是。我有点为之感到难过。但很快就消失了。他提高了这个领域引起人们的关注,这是我永远无法做到的。在他的光环下,在他制造的所有噪音中,我也被吸引了。我们都去世界各地开会来解释我们的差异。不,毕竟没什么问题。这对我有好处。我得到了很多关注。”
无论他是否是第一个找到干细胞的人,不可否认的是,维斯曼设计了一种非常有用的方法。正是因为他是一个外来者,他才能够挑选现有的技术并以新的方式将它们结合起来。Thy1loLin-Sca1+是一个原始的干细胞配方。
“维斯曼纯化的真正价值在于它描述了细胞表面差异,”勒米施卡说,“Thy1、Sca1和世系标记——这些都是有形的分子。因此,就‘干细胞看起来是这样的,它的表面有这个和那个,但不是这些’而言,维斯曼第一次定义了干细胞。维斯曼的成就不仅仅是像维瑟那样的纯化;它确实是信息丰富的。”
麦卡洛克对他的赞扬甚至更加强烈。“维斯曼仍然是迄今为止实现的最广泛的纯化,”他说,“我认为他的工作是开创性的。将其应用于人类只是他通过小鼠研究所做的研究的一个步骤。”
尽管如此,那也是一个相当重大的飞跃。到1991年冬天,维斯曼和他在SyStemix的同事们已经改编了小鼠干细胞的配方,并宣布他们找到了人类干细胞。和小鼠一样,他们排除了世系标记,选择了Thy1标记。Sca1对人类细胞来说不是一个实用的标记——在人类中,编码该蛋白质的基因有许多外观相似的亲属——因此,研究人员用一种几年前就被发现的蛋白质CD34代替了它。他们称人类干细胞为Thy1+Lin-CD34+。再次,维斯曼的个别成分并非新鲜事物,但他的组合是。然而,科学界再次没有被压倒——其他研究人员,使用许多相同的标记,已经发现类似的细胞。
另一方面,其他研究人员都没有像维斯曼那样宣布他们的成就——通过专利。与通常的科学程序截然不同,维斯曼和他的同事们在他们的工作出现在1992年4月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之前约五个月,就为寻找他们声称的人类干细胞的方法以及干细胞本身申请了专利。由于专利赋予专利物品的独占权利,这意味着维斯曼和他的同事们成为了活生生的人类细胞的骄傲拥有者。
这是一次大胆的举动,尽管并非完全没有先例。“你知道,人们总是为身体组成部分申请专利,”维斯曼说。他说得对。基因、生长因子、血液蛋白——都获得了专利。甚至CD34也获得了专利——SyStemix必须付费才能使用这种蛋白质。但是,整个活细胞呢?
“下一步,有人会为受精卵申请专利,然后你就不能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生孩子了,”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血液学家大卫·戈尔德(David Golde)在宣布消息时打趣道。
“如果有人想商业化生育,谁知道呢?”维斯曼回答道。与任何专利一样,SyStemix的专利旨在阻止除其自身以外的任何人对干细胞进行商业性开发。该公司打算积极捍卫其特权。“人们使用何种工艺并不重要,他们将永远侵犯,”SyStemix当时的总裁琳达·松塔格(Linda Sonntag)宣称。
这种言论激怒了摩尔和该领域的其他人。“在我看来,这是一项荒谬的专利,”摩尔说,“我预测它不会经受任何挑战。如果他们认为任何试图分离和培养干细胞的人都必须向SyStemix支付许可费,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人们可以使用不同于SyStemix专利所列标准的标准来分离干细胞。例如,今年一月,哈佛医学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的研究人员宣布,他们开发了一种全新的、相对简单的分离干细胞的方法,该方法不依赖于抗体,而是基于这样一个原理:干细胞大部分时间处于静止、不分裂的深度睡眠状态,对称为生长因子的蛋白质相对不敏感。然而,干细胞的后代对生长因子有反应。因此,由血液学家大卫·斯卡登(David Scadden)领导的哈佛团队通过施加这些因子来激活干细胞的后代,然后通过用一种称为5-FU的抗癌药物(它攻击代谢活跃的细胞)淹没相同的细胞来迅速杀死它们。剩下的是干细胞。”
扬·维瑟比摩尔更具哲学性。维瑟认为这是实际需要。维斯曼需要他的公司获得专利。
维斯曼同意这一分析。“没有专利,资金就不会投资,”他说,“而如果没有资金,你就无法进行大规模研究。”
维斯曼可以进行这项研究。几乎就在专利宣布之后,Sandoz就收购了SyStemix的控股权,使维斯曼当时的净资产膨胀到估计的2400万美元。“这并没有改变我的生活,”他说,然后又笑了,“好吧,我喝的酒比以前好了。”
“我希望我能像他一样富有,”维瑟怀着渴望的心情说,“这是我自己的错。他做得对——从家庭的角度来看。他笑了。我的孩子们在抱怨。”
然而,在临床领域,SyStemix的专利尚未真正发挥作用。SyStemix在其自己的实验室中已证明,其人类干细胞确实可以再生在与人类免疫系统一起培育的小鼠——所谓的SCID-hu小鼠——中的血液。该公司已获准开始测试其在人类中的能力,方法是将细胞注入20名因化疗而免疫系统被摧毁的多发性骨髓瘤患者。这些测试应该正在进行中——开发一种能够使用Thy1+Lin-CD34+配方来分离足够数量以供人类使用的人类干细胞技术已经花费了这么长时间。
但是,目前进行的其他临床试验均未使用维斯曼的配方。在纽约血库,免疫遗传学家巴勃罗·鲁宾斯坦(Pablo Rubinstein)正在领导一项全球性的努力,通过利用人类新生儿脐带血来移植干细胞。他的方法极其简单。在胎儿时期,干细胞在出生几天后进入骨髓之前,会持续通过血液流动。因此,脐带血相对富含干细胞;鲁宾斯坦和他的同事们可以简单地收集和移植这些全血,并且知道他们正在移植干细胞。自1993年秋季以来,该团队已帮助为13名患者——其中12名为儿童——进行了移植,他们患有晚期白血病或遗传性疾病。其目的是为这些人提供新的血液来源,以替代他们自己患病的细胞。结果为研究人员提供了希望的理由。尽管有3名患者(包括那名成年人)死于无关的并发症,但其他10名患者情况良好。他们的血液已完全再生,病情得到缓解。
此外,这些患者中没有一人经历了移植的祸害——移植物抗宿主病(graft-versus-host disease),即移入的细胞将宿主身体识别为外来物并对其进行攻击。鲁宾斯坦说:“使用纯净的干细胞,应该不会发生移植物抗宿主病。由此产生的免疫系统将在受体体内成熟,因此会被训练识别受体为自身。”
另一项使用脐带血的试验于1993年春季在洛杉矶儿童医院(Children's Hospital in Los Angeles)开始,当时儿科基因治疗师唐纳德·科恩(Donald Kohn)对三名患有遗传性免疫系统疾病(称为ADA缺乏症,更通俗地称为“泡泡男孩病”)的新生儿进行了干细胞基因治疗。患有该疾病的儿童缺乏产生腺苷脱氨酶(ADA)的基因。没有ADA,免疫系统就无法正常工作;这些儿童注定会过早死亡。
ADA缺乏症是1990年在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开始的首批基因治疗试验的目标。这些试验涉及将纠正的基因导入成熟的白细胞而不是干细胞。因此,这些纠正的细胞最终会死亡,这意味着——尽管具有革命性和成功性——这种疗法只能缓解,而不能治愈疾病。另一方面,干细胞有可能提供真正的治愈。在试图提供这种治愈的尝试中,科恩实际上需要分离婴儿脐带血中的干细胞:他通过靶向CD34蛋白质来做到这一点,将ADA基因插入细胞,然后将其重新注入婴儿体内。他希望这些基因已经成功地整合到干细胞中,并被包装到它们的后代中。“在前几个月,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含有基因的细胞,”他说,“然后我们开始看到一些,大约万分之一。现在我们达到了千分之一。尽管在此期间,婴儿正在接受ADA酶的注射,但科恩的希望是,含有插入基因的干细胞产生的细胞最终将产生足够的酶,从而无需补充治疗,从而有效地治愈这些儿童。”
这些开创性的努力可能预示着干细胞疗法的辉煌未来。马尔科姆·摩尔和他的团队正在将耐药基因插入由CD34和其他标记识别的干细胞中,以便他们可以将这些细胞用于白血病患者或接受化疗的癌症患者,因为化疗倾向于在消灭患病细胞的同时也消灭健康的白细胞。一些团队——包括SyStemix的一个团队——正在研究将抗HIV基因插入干细胞,作为治疗艾滋病的可能方法。最后,尽管希望渺茫,但分离干细胞的能力甚至可能减轻日益增长的输血需求。
最终,抛开争议和不快不谈,似乎维斯曼引发了一场革命。如今,人们对干细胞的兴趣以及为支持这种兴趣而提供的资金,前所未有。维瑟说:“由于维斯曼进行了公关工作,获得资助变得更容易了。由于Sandoz收购了SyStemix,所有大公司都开始关注干细胞。”
“伊尔夫·维斯曼带来了什么?”安大略癌症研究所的干细胞研究员诺曼·伊斯科夫(Norman Iscove)问道,“他让这个领域活跃起来了。他把它带入了头条新闻,带入了新闻播报。”
“没有人比维斯曼更欣赏这个领域了。他说,‘我认为你将在三年内看到干细胞在癌症治疗中的首次大规模实际应用,五年到七年内用于其他疾病。最棒的是,我们开发了这种细胞群,它们是完美的。它们不像药物那样有副作用。你知道你提供的是正确的东西,因为干细胞是经过十亿多年进化的产物。’”
而伊尔夫·维斯曼拥有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