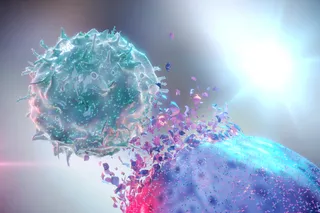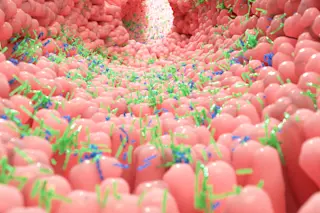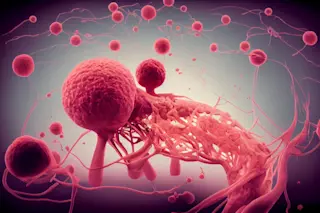如今,大多数人都熟悉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的观点,他将自然选择描述为达尔文的危险思想——危险在于它像腐蚀性酸一样,能够瓦解人类社会既有的结构。这种酸性同样可以腐蚀科学结构,而科学结构本应更不容易受到破坏。因此,一种达尔文主义思想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侵蚀了我自己的研究领域——肿瘤生物学——的根基,并迫使癌症研究人员重新审视本世纪前半叶关于癌症起源的一些普遍看法。如今,随着新基因的发现促成了癌细胞的发展,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癌症首先是一种 DNA 疾病。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这种疾病并非以预先编程的方式发生。只有通过细胞逐渐摆脱控制其正常分裂过程的束缚,细胞才会癌变。而这种摆脱,恰恰是通过达尔文进化机制实现的。
回过头看,也许这并不令人意外。自达尔文时代以来,我们便知晓自然选择塑造世界生物的力量。在过去的50年里,生物学家们已经理解了 DNA 突变如何提供自然选择作用的遗传变异。然而,进化在癌症研究领域的地位却缓慢确立。当然,与物种的进化相比,身体细胞癌变的过程非常有限。但就像我们现在认识到微生物会进化出对抗药物的抗性一样,我们现在也知道癌细胞会进化得对身体的生长控制力量不敏感。这些遗传变化是如何发生的,是基于达尔文的变异和选择原理。
这一见解改变了我们对癌症的理解。它打破了寻找单一关键变化或传染性病原体来解释所有癌症形式的希望。当我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癌症研究时,寻找这种关键变化的斗争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不久一位著名的理论家——柏林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著名的生物化学家奥托·瓦尔堡——认为他找到了它。瓦尔堡提出,癌细胞与其他细胞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对细胞能量来源——糖和氧——的异常利用。碰巧,瓦尔堡的理论部分是基于我曾处理过的细胞。1950年,当我第一次在国际会议上发言时,我是最年轻的与会者之一。我谈论了小鼠腹水瘤,这些肿瘤是由自由漂浮的癌细胞在动物腹腔内生长引起的。当时我不知道,瓦尔堡的一位助手就在听众席上。一周后,这位伟人给我寄来一封信,索要这些细胞,我立刻寄给了他。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瓦尔堡发表了几篇论文,声称腹水瘤细胞倾向于消耗糖,即使有氧气也如同没有一样。他得出结论,与正常细胞不同,癌细胞可以在严重缺氧的条件下茁壮成长。几年后,瓦尔堡写道,我通过寄给他解决了癌症问题的细胞,对癌症研究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不幸的是,我并不信服。癌症研究中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是,实验室中的细胞常常表现出与体内细胞迥异的行为。在我看来,瓦尔堡选择了一个在半个多世纪里、在微氧环境中、在高度拥挤的条件下,经历了大量小鼠的癌症细胞——这就像用鲸鱼来研究四足动物的行走机制一样。在实验室里,很容易产生与自然界不符的现象。
然而,这样的实验可以产生具有历史意义的结果。科学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表面上最重要的东西可能变得微不足道,反之亦然:看似不重要的发现后来可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理论就像正在建设的建筑物的脚手架:它只为被移除而存在,随着建筑物的成长。
例如,佩顿·鲁斯在1911年的实验结果为肿瘤生长提供了意想不到的见解。鲁斯是纽约洛克菲勒研究所的一位年轻研究员,他怀疑癌症是由病毒引起的——当时病毒是一种相当新颖且了解甚少的实体。当一位长岛的农民寻求他帮助治疗一只有肿瘤的获奖母鸡时,他很快就有了检验自己想法的机会。为了分离致癌病原体,鲁斯切除了肿瘤,将其磨碎,过滤掉细胞,然后将剩余的无细胞物质注射到一只幼鸡体内。结果:癌症生长。鲁斯得出结论,肿瘤细胞产生了一种可以传播癌症的传染性因子。
在接下来的四十年里,许多研究人员试图在小鼠和大鼠身上重复鲁斯的实验,但都未成功。然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卢德维克·格罗斯,一位来自波兰的犹太难民,在布朗克斯的一家退伍军人医院工作,成功分离出一种导致小鼠白血病的小鼠病毒。在他发现后不久,其他研究人员开始分离病毒,这些病毒注射到不同类型的实验动物体内可以引起肿瘤。其中一些病毒也能将培养皿中的正常细胞转化为癌细胞。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癌症由病毒引起的理论得到了广泛支持。
这些研究最终确定了两类肿瘤病毒—— DNA 病毒和 RNA 病毒——它们的操作方式不同。当 DNA 肿瘤病毒将其基因插入宿主细胞基因中时,它会扰乱细胞分裂的调控,导致肿瘤生长。(幸运的是,免疫系统通常会识别并清除这些异常细胞。)更令人费解的是 RNA 肿瘤病毒的隐蔽繁殖方式。事实证明,这些病毒会将它们以 RNA 形式存在的遗传物质复制成双链 DNA。然后,它们将这种 DNA 整合到宿主细胞的 DNA 中。在细胞 DNA 中,病毒可以潜伏起来,躲避免疫系统。由于研究人员对此一无所知,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些病毒致癌作用仅仅是它们生活方式的副作用。
RNA 病毒是高效但不精确的繁殖者。与宿主细胞不同,病毒没有纠错机制来校对复制成 DNA 的内容。它可以承受产生大量不正确的副本,包括一些意外携带宿主 DNA 基因的副本。通常,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其他病毒遗传信息就会丢失。由此产生的病毒颗粒是如此有缺陷和不利,以至于它们无法在自然界中生存。但肿瘤病毒学家,出于证明病毒可以引起肿瘤的愿望,可能会拯救其中一些免于灭绝。
回想一下佩顿·鲁斯在1911年所做的事情。他磨碎了母鸡的肿瘤,将物质通过一个不允许细胞通过的非常精细的过滤器,然后将过滤后的物质注射到刚孵化的小鸡体内。然后他观察肿瘤是否发展。鲁斯没有意识到的是,他正在选择那些偶然携带了促进细胞生长的宿主基因的病毒颗粒。他选择的病毒不仅能够感染接收小鸡体内的细胞,还能促使它们不停地分裂。
无限生长的关键是被病毒激活的被盗取的细胞基因,它迫使细胞分裂,而不受有机体正常信号的指示。直到鲁斯实验大约60年后,研究人员才意识到鲁斯病毒中的致癌基因实际上来源于正常的鸡细胞。后来,从鸡、小鼠、大鼠或猴子肿瘤中分离出的其他 RNA 肿瘤病毒也被发现携带类似的生长促进性细胞基因。这些基因在人类肿瘤的自发发展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寻找能够使正常细胞癌变的病毒编码遗传信息,反而导致了病毒可以劫持和改变生长调节性细胞基因的发现。这一发现突显了 DNA 在肿瘤发展中的重要性,后来的研究表明,突变可以在没有病毒干预的情况下激活这些基因并促进癌症。认识到细胞 DNA 中突变的作用有助于理解癌症逐步发展的图景。对人类癌症自然史的研究强烈表明,癌症通过一系列独特的阶段发展,这些阶段通过一系列在不可预测的时间间隔发生的改变而出现。事实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佩顿·鲁斯就开始记录癌症发展过程中组织的改变。他创造了“肿瘤进展”一词来描述肿瘤从坏到更坏的过程。
大约20年后,伦敦切斯特·比蒂研究所的实验病理学家莱斯利·福尔兹制定了一套规则来描述这一过程。他强调区分细胞在走向癌症的过程中,一步步形成的每一个特征的重要性。福尔兹的工作对于我们后来理解突变在疾病中的作用至关重要——事实上,可以将恶性肿瘤的逐级演变称为福尔兹的危险思想。福尔兹谈到了诸如生长速度、激素依赖性、侵袭周围组织或通过转移扩散的能力等特征。此外,他还指出,随着肿瘤的进展,这些特性可以独立于彼此而改变。换句话说,细胞似乎没有一条固定的路径才能癌变。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研究充分证实了福尔兹的观点,但有一个重要的例外。福尔兹认为这些改变不是由突变引起的。相反,他假设癌细胞的基因是正常的;只有它们的表达受到干扰。从这个角度看,癌症是一种异常发育疾病,其中错误的基因被开启和关闭。在这方面,福尔兹显然错了。如今我们知道,癌症不仅是一种基因调控异常的疾病,也是一种 DNA 本身的疾病。
在福尔兹看来,突变不太可能负责肿瘤发展和进展的各个阶段。每个细胞都携带每种基因的两份拷贝,一份来自父亲,一份来自母亲。这两个基因位于两条不同的染色体上,如果一个基因因突变而失去功能,另一条染色体上的正常基因通常可以完成工作。人们预计随机突变只会影响两个拷贝中的一个——两个基因都突变的概率非常低。
然而,我们了解到,如果一个基因的第一个拷贝已经受损,在细胞分裂过程中很容易丢失第二个拷贝。通常,第二个基因所在的整个染色体都会丢失。事实证明,癌细胞对这种丢失的耐受性很好,因为与正常细胞不同,它们不需要执行任何特殊功能。它们所要做的就是复制自身。
换句话说,它们的博弈规则改变了。多细胞生物中的普通细胞遵循控制其生长并确保它们执行特定代谢任务的规则。但随着突变的积累,细胞不再是团队合作者,而是遵循自然选择的规则。而这些规则有利于生长最快的细胞。在肿瘤的进化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许多突变,但获得生长促进性突变最多的细胞将茁壮成长并扩散。
涉及这种渐进式演变的基因属于三个略有重叠的类别。第一类是癌基因,这是病毒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首次偶然发现的致癌突变基因。所有癌基因都会促使细胞分裂,并且只需改变其中一个基因拷贝即可做到。
第二类基因是所谓的肿瘤抑制基因。正常细胞可能含有抑制癌性生长的基因的第一个迹象来自近30年前亨利·哈里斯在牛津与我们在斯德哥尔摩卡罗林斯卡学院的团队合作进行的实验。当我们融合正常细胞和恶性细胞时,产生的杂交细胞——及其后代——是非恶性的。但当正常亲本细胞的一些染色体在培养中的细胞分裂过程中丢失时,细胞又变得恶性。这表明肿瘤细胞遭受了遗传损失,而正常基因可以弥补这种损失。
后来,其他研究人员识别出了单个肿瘤抑制基因。最终人们清楚,抑制基因产生蛋白质,这些蛋白质可以阻止细胞不适当的分裂。最著名的例子之一是产生 p53 蛋白的基因。正常细胞产生的 p53 非常少。但是,每当 DNA 受损——无论是由于辐射、化学物质还是缺氧——p53 的水平都会急剧上升。p53 与 DNA 结合,阻止细胞分裂——从而为 DNA 修复酶争取时间来完成其任务。DNA 修复后,p53 水平下降,细胞分裂可以继续。但如果损伤过于严重,细胞就会发生程序性细胞死亡,称为细胞凋亡。
超过一半的人类肿瘤含有突变的 p53,这些 p53 无法与 DNA 结合,因此无法阻止 DNA 损伤细胞的生长。这种突变的作用不仅仅是损害细胞死亡程序。在 p53 两个拷贝都丢失或发生突变的细胞中,受损的 DNA 不会发出停止生长的信号,以至于无法修复。尽管如此,这些细胞仍然存活,因此容易发生其他突变,包括癌基因和抑制基因的突变。这就是为什么遗传性 p53 突变会导致 Li-Fraumeni 综合征,一种患者常患多种肿瘤,起源于不同组织的疾病。
第三类致癌基因是 DNA 修复基因本身——这些基因确保在细胞分裂过程中遗传信息的每一条链都能被正确复制。这些基因的突变使人类易患遗传性非息肉病性结肠癌综合征。患有这种综合征的家庭有患结肠癌、胃肠道其他部位癌症、卵巢癌、子宫癌、尿路上皮癌和皮肤癌的风险。现在已经发现了至少另外五个 DNA 修复基因的突变,它们与其他癌症综合征相关。
这一系列突变的破坏性影响最早在细菌和酵母等生物体中被发现。由于 DNA 修复基因的突变会增加其他突变的频率,它们可能会增强这些单细胞生物在压力环境下生存的能力。但在我们这样的多细胞生物中,相同的现象可能导致癌症。癌细胞脱离确保身体众多细胞协同作用的规则越多,它们就越像微生物群体。例如,在自由生活的细菌、酵母和变形虫中,自然选择有利于能更有效地利用营养和其他资源的变体。在癌细胞中,自然选择有利于越来越不响应机体生长控制力量的细胞。正如自然选择有利于能够适应新环境的细菌一样,它也倾向于选择那些拥有有助于它们在生长肿瘤的低氧环境中生存的突变的癌细胞。从某种意义上说,瓦尔堡最终是正确的。但只有通过达尔文进化论的视角,才能理解他关于癌细胞能量需求改变的观察。
幸运的是,要让一个普通细胞摆脱生长控制,需要的不止一种基因改变。没有哪个突变本身是致癌的。正如福尔兹近四十年前所怀疑的那样,癌症进展不是以僵化的、预定的方式展开的。它通过一系列突变缓慢展开,这些突变为细胞生长提供了一系列绿灯。
我们目前对可能影响癌症发展的三个基因世界的了解有多完整?还有其他吗?是的,当然,但它们的研究还处于早期阶段。有些基因影响着新兴肿瘤细胞吸引带来营养的血管的能力,这是肿瘤生长的前提。另一些基因则干扰正常细胞衰老过程,帮助使癌前细胞永生化。还有一些基因则帮助癌细胞躲避免疫系统的监视。
我们对肿瘤进化新认识的未来前景如何?我们的一些临床同事和大多数公众长期以来一直在等待癌症的治愈。有人说对癌症研究的投入是徒劳的,或者用一种更糟糕的说法,癌症比它杀死的人支持更多的人。
对于那些追随达尔文和福尔兹脚步的癌症生物学家来说,已经没有回头路了。我们不仅要接受这种新的复杂性,还要拥抱它。尽管肿瘤发展代表着一种非常小规模的进化过程,但它仍然是一个进化过程,有许多微妙的、看似无关的步骤,以及近乎无限的多样性。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在控制癌细胞之前了解所有步骤的细节。新的癌症生物学也可能提供一步控制多重改变的癌细胞的方法。
基因疗法可以通过引入一种强大的抑制基因或促进细胞死亡的基因来阻止癌细胞的生长。其他方法还包括切断肿瘤的血管供应——其营养来源。如果肿瘤的毛细血管供应被切断,它就会死亡。还有一种方法是构建免疫导弹,由毒素或放射性标签以及特异性抗体组成。尽管癌症的起源比鲁斯或瓦尔堡曾经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但达尔文的光芒或许仍能帮助我们找到穿过这片荆棘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