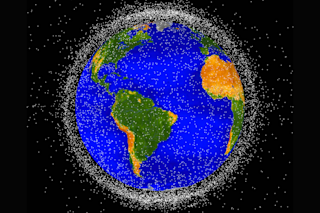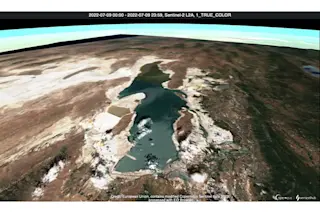太阳已升至库萨湾半空,维多利亚湖棕色的湖水拍打着干旱的肯尼亚稀树草原。一位卢奥族渔民用杆子撑着他的木板独木舟,划入芦苇和纸莎草堵塞的浅水区中开辟出的一条水道。他的六名同伴抓住船首绳索,开始有节奏地吟唱,将船拖上岸。“Harambee, harambee, harambee, ayaaah,”他们一边用力,一边唱道,“团结,团结,团结。”岸上的妇女们笑着,等待着捕获物,她们的篮子和鲜艳的塑料盆在头顶摇晃。
然而,随意瞥一眼搁浅在泥滩上的十几艘独木舟,几乎看不到任何鱼。彼得·奥春巴在它们中间穿梭,检查着每艘船地板上堆放的少量捕获物。二十几条十英寸长的尼罗罗非鱼。几条尺寸不大的尼罗河鲈鱼。一桶哈氏鲷——两到四英寸长的小鱼,它们曾经是这些水域的主宰。还有一条拉贝鱼,当地称之为宁古,这是一种小鲤鱼般的美味,以前数量之多使这个村庄富裕起来。
奥春巴是肯尼亚海洋渔业研究所(KMFRI)的湖沼学家——淡水专家。他比大多数人都更明白,为什么他的卢奥族同胞以及湖边成千上万的其他渔民,辛劳一夜后却收获甚微。他从船底拿起最受诟病的嫌疑犯——一条尼罗河鲈鱼。如果它没有在还是只有一英尺长时被捕获,这条鱼本可以长到六英尺长、200磅重,主要靠吞食这些渔民赖以生存的小鱼。
没有其他淡水鱼像尼罗河鲈鱼那样受到如此多的负面报道——在分类学语言中是Lates niloticus,在英国小报的语言中是“贪婪的外来捕食者”或“厄运之鱼”。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被英国殖民者引入以来,鲈鱼的数量急剧增加,显然已将维多利亚湖曾经特有的400种哈氏鲷鱼类中的一半完全消灭。这些小鱼不仅构成了湖区数百万非洲人食物链的一部分,它们也是世界上的自然奇观之一——一个进化如此疯狂以至于它们曾登上著名的《自然》杂志封面的案例。西方科学家长期以来涌向维多利亚湖研究哈氏鲷传奇般的多样性。其中一位,新英格兰水族馆埃哲顿研究实验室的首席科学家莱斯·考夫曼(Les Kaufman),将哈氏鲷的消逝称为“有记录以来最大的脊椎动物大灭绝”。
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尼罗河鲈鱼可能只是最后一击。整个湖泊正在消亡,而人类而非鲈鱼才是罪魁祸首。
至今没有摇滚明星为热带湖泊举办过演唱会。然而,在非洲热带地区,湖泊与森林一样岌岌可危,其中最岌岌可危的就是维多利亚湖。这座巨大的内陆水体——非洲最大,在世界范围内仅次于苏必利尔湖——最宽处长达255英里,宽155英里。它浑浊的水域从南部的坦桑尼亚塞伦盖蒂广阔的稀树草原,一直延伸到东部的肯尼亚马赛马拉,再到北部和西部的乌干达茂密的热带丛林。
然而,维多利亚湖不仅浑浊,而且被藻类严重阻塞,氧气耗尽。本世纪以来,湖泊可能一直在恶化,但在东非剧烈的社会动荡中,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未被认识。现在,在最后一刻,维多利亚湖已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在湖区周围的三个国家——坦桑尼亚的姆万扎、肯尼亚的基苏木、乌干达的金贾——的研究站,发达国家的缩写随处可见。例如,奥春巴使用的KMFRI路虎,在多年失修后,由维多利亚湖研究团队重新投入使用,该团队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和环境保护署(EPA)等美国机构以及皮尤慈善信托等私人团体资助。这项国际努力的目标是查明湖泊出了什么问题,努力挽救其传奇般的生物多样性中的至少一部分,并为湖岸边的3000万人提供可靠的蛋白质来源和工作。
“这就是当人们说生物多样性很重要时,大家所谈论的,”研究团队负责人考夫曼说。“生物多样性影响着人类。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生态系统正在失去其养活周围居民的能力。”他指出,维多利亚湖的故事“已经变成了一首民谣,警示着干预自然的危险。”
然而,善意地干预他国问题可能很敏感。例如,当地政府和商界许多有权势的人士认为尼罗河鲈鱼是救星,而非破坏者。这是一场生态灾难,没错,但讽刺的是,目前湖泊正在产出创纪录数量的鲈鱼,带来了急需的出口收入。
在当地渔民无法撑着独木舟进入的开阔湖区,大型船只正以无法计数且不受管制的吨位捕捞尼罗河鲈鱼。这些鱼随后被出售给亚洲、欧洲和澳大利亚投资者沿肯尼亚和乌干达湖岸建造的数十家加工厂。数小时内,厚厚的白色鱼片就被从鱼身上切下,速冻,装箱,并装上卡车运往肯尼亚蒙巴萨港,在那里它们被运往欧洲和中东的餐桌。
考夫曼嘲讽地回忆起1992年访问肯尼亚最大的湖滨城市基苏木的KMFRI总部时,被一名挥舞着外国报纸的政府官员打断。“他很生气,”考夫曼说,“因为科学家们被引用说湖泊正在消亡。我当时就看到我的研究许可证要被扔进他的壁炉了。但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并达成了一个解决方案:湖泊并没有消亡;只是湖中的氧气越来越少,而缺氧与生命不相容。”同年夏天,考夫曼被“一个来自冰岛的家伙”找上,他想知道如果他在岸边再开一家鲈鱼加工厂,“利润会有多好”。
商业繁荣不仅对鱼类,也对人类造成了影响。沿岸传统的生活方式正在瓦解。当奥春巴从库萨湾返回基苏木时,他在基苏木郊区停下来,与在炭火上炸鲈鱼碎片的妇女们交谈。这些来自附近渔村的妇女曾经购买本地罗非鱼、拉贝鱼和哈氏鲷鱼,将其晒干出售。随着这些物种的减少,妇女们迁徙到鲈鱼加工厂附近的贫民窟,在那里她们购买鱼片后的鱼骨。肥厚的鱼头和鱼尾被炸熟,在路边的木杆摊位上出售;它们是大多数当地人唯一能负担得起的鱼。
回到KMFRI,生物学家兼内陆水域副主任詹姆斯·奥加里(James Ogari)将自己也算在当地人之中:“我现在连吃饭都很难像四五年前那样吃得起鱼了,”他说。“渔业的主要作用首先应该是为社区提供蛋白质,然后才是提供外汇。但现在的趋势却恰恰相反。我不知道穷人将来会吃什么。”
事实上,如果湖泊继续恶化,过度捕捞的鲈鱼数量锐减,那么依赖维多利亚湖的任何人将吃什么都将变得不明朗。
所有湖泊利益相关者——当地渔民、生态学家、商业船主和加工商——共同的情绪是对维多利亚湖未来的不确定性。为了减少这种不确定性,科学家必须首先拼凑出过去出了什么问题。这个复杂故事的一些关键线索可以在距基苏木约100英里的乌干达金贾找到。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金贾不仅是管理整个湖泊渔业的总部,也是其研究中心。
从空中俯瞰,当你沿着赤道从肯尼亚飞往乌干达时,维多利亚湖看起来仍然与1858年英国探险家约翰·斯皮克偶然发现其南岸并宣布他发现了传说中的尼罗河源头时大致相同。维多利亚湖海岸线的分形手指环绕着数百个像库萨这样的海湾和入口,岛屿点缀在开阔的水域中。湖水很浅——最深处270英尺。流入和流出的河流如此缓慢,以至于维多利亚湖需要一个世纪才能冲洗和更换其湖水。
1875年,另一位英国冒险家亨利·斯坦利环游维多利亚湖,以证实斯皮克的说法,并花费两周时间讲述上帝与英国的故事,以讨好布干达国王、北部湖区统治者姆特萨。随后斯坦利发电报回英国,呼吁传教士前来。传教士们带着士兵和商人来了。20年内,英国掌控了后来的乌干达和肯尼亚(德国获得了坦桑尼亚),到1902年,殖民政府已将铁路从蒙巴萨修到了湖边。
欧洲人很快砍伐了维多利亚湖流域大片森林,种植茶叶、咖啡、糖、烟草和棉花。人口激增,人们越来越多地转向湖泊,不是为了温饱,而是为了满足不断壮大的城市中心对鱼类——尤其是美味的罗非鱼“ngege”——的市场需求。
在乌干达作为“非洲之珠”的鼎盛时期,位于湖泊西北边缘的恩德培机场曾是进步的象征。如今,Ungaro和Chanel香水海报不协调地挂在其候机楼被污渍和弹孔斑驳的墙壁上。尽管机场正在翻新,但仍能看到1976年以色列突击队为解救伊迪·阿明劫持飞机上的人质而留下的残骸。阿明这位从1971年至1979年残暴统治这个国家的独裁者,在维多利亚湖的故事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因为正是在他执政期间,当研究人员被禁止研究湖泊时,湖泊发生了最剧烈的变化。
沿海岸线公路从恩德培向东行驶两小时,便抵达金贾,尼罗河从这里开始其长达4000英里的地中海之旅。金贾曾是一座繁荣的印度贸易城镇,直到1972年,阿明下令将8万名亚洲人驱逐出乌干达,并没收了他们的大型灰泥房屋和一排排铁皮屋顶的商业建筑。湖边一处老旧的灰泥建筑群是乌干达渔业研究所的所在地。传统上,生物学家们都会来这里研究维多利亚湖的哈氏鲷大爆发:多达400个物种,所有这些物种显然都是在过去约14000年间从几个祖先进化而来的。每个物种都有微妙不同的颌骨解剖结构,以适应其摄食策略。有些哈氏鲷吃螃蟹或虾,有些喜欢昆虫,有些吞食鱼卵或幼鱼(那些被称为“吞吻食卵鱼”的鱼字面上是从在口中孵育幼鱼的雌性哈氏鲷口中吸食幼鱼)。其他则以藻类或碎屑为食,或压碎蜗牛和其他有壳软体动物。鱼类学家和进化生物学家一丝不苟地对这些物种进行了分类,并给它们起了色彩斑斓的昵称,如“火焰背”、“粉红潮”、“基苏木蛙口鱼”和“姆比塔红肛鱼”。
但金贾的主要工作传统上是渔业管理。湖泊的捕捞压力始于1905年,当时英国人引入了亚麻刺网,这种渔网很快取代了当地村民的纸莎草网和捕鱼陷阱。随着过度捕捞,捕获量开始下降;渔民们转向网目越来越小的渔网,从而导致许多本土物种的繁殖成鱼和幼鱼数量锐减。到20世纪50年代,ngege已商业性灭绝,拉贝鱼也紧随其后。为了弥补,英国官员决定向湖中投放新鱼。第一个繁盛起来的非本土物种是尼罗罗非鱼(Oreochromis niloticus),它以浮游生物(微小的动植物生命形式)为食。(这种罗非鱼已被引入世界各地的河流和湖泊,包括北美,在那里它经常被混淆地称为尼罗河鲈鱼。)
尽管发生了这些变化,哈氏鲷在20世纪50年代似乎仍在蓬勃发展。事实上,它们看起来如此健壮,以至于一些殖民地管理者主张引入像尼罗河鲈鱼这样的大型捕食者,以捕食他们认为骨头多的小“垃圾鱼”,并将“哈氏鲷生物量”转化为更适合餐桌的食物。生态学家担心当地物种会受到最坏的影响,强烈反对这种捕食者。但在1954年,非法尼罗河鲈鱼还是开始出现在商业捕捞中。既然已经如此,官员们在20世纪60年代初积极向湖中投放鲈鱼。(奥加里怀疑鲈鱼最初是由殖民时期的体育爱好者偷偷放入湖中的,就像思乡的英国垂钓者在东非和南非各地的高山溪流中放入鳟鱼一样。)然而,在接下来的十年左右,这种外来鲈鱼的数量仍然很少。1971年完成的一项联合国资助的调查发现,哈氏鲷仍然占据湖泊鱼类生物量的传统80%。
随后是渔业研究所生物学家佩雷蒂·巴萨西布瓦基(Pereti Basasibwaki)所称的“黑暗时期”,即1974年至1979年间,阿明切断了对湖泊的接触。有一段时间,巴萨西布瓦基试图从金贾这个历史悠久的总部管理渔业。他继续派遣工作人员执行常规任务前往基苏木和姆万扎,这两个位于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分站自殖民时期以来一直由金贾管辖。巴萨西布瓦基被指控“帮助人们逃离该国”,被阿明军队监禁,渔业工作随之停滞。
直到1979年,肯尼亚政府接管了闲置的基苏木设施,工作在KMFRI的赞助下得以恢复。初步调查显示湖泊的鱼类生物量没有变化:它似乎仍然由80%的哈氏鲷和不到2%的尼罗河鲈鱼组成。但在1980年,肯尼亚水域发生了突然变化,两年内,乌干达和坦桑尼亚水域也出现了同样的变化。尼罗河鲈鱼突然跃升至生物量的80%,而哈氏鲷则降至1%。已经稀有的ngege鱼几乎消失了。显然,在20世纪70年代未受监测的时期,有些事情正在酝酿,导致了鲈鱼如此大规模的爆发。至于哈氏鲷,主要的理论是它们简单地为捕食者提供了食物。
起初,官方关注的焦点是鲈鱼在岸上造成的问题。渔民需要更大的渔具来对付能长到六英尺重的鱼。村民不知道如何去骨或烹饪这种大而油腻的鱼,也无法在阳光下晒干。这种怪物没有市场,价格低廉,大部分鲈鱼都被留在沙滩上腐烂。在联合国资金的帮助下,一个KMFRI团队走访了湖边的村庄和内罗毕的酒店,演示如何去骨、冷冻、熏制和烹饪鱼。外国援助团体和投资者带着加工厂和冷藏卡车进驻。事后看来,很想说这项努力过于成功了。如今,住在湖边的人们很少能与酒店和外国客户愿意为鲈鱼支付的价格相匹配——以至于在一个每年出口20万吨鱼的地区,蛋白质营养不良的幽灵正在浮现。鲈鱼的任何部分都没有浪费。KMFRI办公室的一张海报展示了蒙巴萨一家公司用鞣制鲈鱼皮制作的鞋子、皮带和手袋。在内罗毕的报纸头版广告中,干鲈鱼鱼鳔每磅售价高达六美元,这些鱼鳔被送往英国用于过滤啤酒和葡萄酒,并送往东方用于制作汤料。
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非洲很少有政府官员将维多利亚湖鱼类区系的这种变化视为一场灾难。毕竟,美国渔业管理者已将外来物种引入北美大部分水域,主要目的是为了取悦运动渔民。对本土鱼类的威胁是最近才引起关注的问题,而且鱼类不像熊猫和大象那样能引起强烈的情感反应。“试试看停止在安大略湖投放太平洋鲑鱼,以恢复其本土的梭子鱼、白鲑和玻璃梭鲈,”维多利亚湖研究团队成员、加拿大渔业和海洋部淡水研究所的湖沼学家鲍勃·赫基评论道。
但鲈鱼的崛起却是一个更严重问题的明显症状。20世纪80年代末,奥春巴、赫基和其他研究湖泊环境的同事发现的变化令人不安,甚至连政府部长都感到震惊。湖底水域似乎是一个死亡区,没有氧气和鱼类生命。另一方面,湖水中充满了藻类——比20世纪60年代初多出五到十倍。这表明湖泊发生了大规模富营养化,这是一种由高水平营养物引起的缺氧状况,营养物会促进浮游生物(尤其是藻类等植物浮游生物)的快速生长。而浮游生物的腐烂又会耗尽水中的氧气。
1990年12月,为了弄清真相,赫基将一个岩心取样器从船舷放下,轻轻地从湖床的软泥中取出沉积物岩心。一个从180英尺深的水中取出的六英寸岩心,以死亡藻类细胞、硅藻(另一种植物浮游生物)坚硬的硅壳以及氮和磷等植物营养物质的形式,包含了200年连续的水域历史。
根据这些数据,赫基和他的同事们已经开始拼凑出湖泊、人类、鱼类和气候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网络,这些作用导致了生态剧变。“我们的分析显示,在殖民前时期,湖泊相当稳定,”赫基说。“但大约在1900年,早在鲈鱼出现之前,我们就开始看到变化。”随着欧洲殖民者的到来——先是为种植园砍伐土地,后来又在该地区建立工业——污水和肥料、农药以及工业废弃物的径流开始涌入湖中。赫基的岩心显示,到20世纪20年代,这些人为来源的氮和磷水平的增加,已经导致维多利亚湖浮游生物组成发生变化,有利于蓝绿藻——我们大多数人熟悉的水面浮渣。到20世纪60年代,情况已急剧恶化。浮游生物群落中的主要输家是硅藻,因为二氧化硅(硅藻壳所必需的)没有相应增加。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湖中本土的罗非鱼“ngege”是第一批受害者。Ngege是硅藻食者,而到20世纪50年代,硅藻几乎已经消失。过度捕捞和失去其最喜爱的食物,ngege显然衰退了,直到大约1980年,尼罗河鲈鱼在湖中彻底将其灭绝。被引入以取代ngege的外来尼罗河罗非鱼,食谱更加多样化,因此它并没有错过硅藻。它似乎也更擅长与尼罗河鲈鱼共存。
到了20世纪70年代,湖中大量的营养负荷正在助长大规模的藻华。随着藻类死亡并沉入湖底,它们被细菌分解,细菌在分解过程中消耗了越来越多的氧气,导致深水区域氧气稀缺,不适合鱼类生存。因此,鱼类被迫挤入浅水近岸水域和海湾,在那里它们更容易成为尼罗河鲈鱼或人类渔民的捕食对象。然而,即使是浅水区,也可能无法长期提供富氧环境。1990年,另一种外来物种——南美洲水葫芦,显然从其一条支流进入了湖中。这种具有观赏性但破坏性的植物似乎正在迅速蔓延,形成密集的垫状物,并增加了腐烂的生物量,从而降低了下方水域的氧气含量。
考夫曼认为维多利亚湖生态系统没有更早崩溃,这一点令人惊叹。他相信这要归功于其小小的哈氏鲷丽鱼。绝大多数哈氏鲷以湖底的藻类或腐烂的碎屑为食。吞食哈氏鲷后,尼罗河鲈鱼似乎摧毁了湖泊的自我清洁系统。现在鲈鱼被迫转向新的食物来源,主要是捕食少量本土虾或自相残杀幼鱼,这进一步危及其自身的生存。
更复杂的是,这个湖泊可能还是区域性、甚至是全球变暖的受害者。通常,在雨季,维多利亚湖倾向于分层,顶部是暖水,底部是密度更大、更冷的水。在一年晚些时候,当季节性风搅动水体并把氧气送到湖底时,就会发生混合。然而,近年来,高于正常水平的地表温度意味着混合变得更加难以实现。维多利亚湖的分层也受到了大规模藻华的影响,藻华吸收阳光进行光合作用并释放热能;它们也可能使地表水保持温暖和浮力。在20世纪80年代,当缺氧的湖底水最终浮出水面时,经常导致大量的鱼类死亡。
非洲各国政府能做些什么来减缓维多利亚湖灾难性的退化呢?他们是否应该命令畜牧业和糖厂清理污水?他们是否应该对捕鱼量实行严格配额,以保护本地和商业物种?他们是否应该对外国鱼类出口征税,以资助补救措施?当蝗虫在湖盆农作物上蜂拥而至时,他们是否停止喷洒农药?他们是否告诉从未见过湖泊的高地居民停止给他们的小块玉米地施肥?他们是否应该重新引入食藻鱼来取代消失的哈氏鲷?
所有这些措施都可能有所帮助,但在普遍贫困且人口增长速度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几乎没有一项是可行的。“政府需要一个异常强有力的理由,才会做出任何这些改变,”赫基说。他和其他人将维多利亚湖视为一个试验案例,不仅适用于非洲,也适用于世界各地的热带湖泊。他说,维多利亚湖比其他湖泊更早达到危机,因为“它是大湖中最浅的,其流域内人口密度最高,因此它稀释所有这些问题的能力较弱。”
考夫曼、奥春巴和巴萨西布瓦基等研究人员已经在开展项目,旨在帮助人类和本土鱼类,无论湖泊本身发生什么。在考夫曼领导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项目下,40种哈氏鲷鱼(代表了湖泊中演化出的大多数不同摄食策略)以及本土的ngege鱼的繁殖种群,已安全地“流放”到美国和欧洲的30个水族馆中。肯尼亚和乌干达都在扩大其养鱼业,收集哈氏鲷鱼和其他本土鱼类的创始种群,并考虑将它们引入该地区更小的湖泊和池塘的计划。如果维多利亚湖本身的衰退能够停止,有一天,孤立的海湾和入口可能会用网围起来,作为“鱼类公园”或有价值商业物种的养殖场。
这些努力——承认更像是打捞而非保护或修复——引来了不少批评。考夫曼指出,一些西方同行和组织认为维多利亚湖已经病入膏肓,应该放弃。他认为,环保主义者将有限资源集中用于保护未受破坏的野生之地是正确的,但他为“打捞那些永远无法恢复原样的生态系统孤儿碎片”而辩护。
如果世界真的放弃维多利亚湖呢?湖泊的消亡意味着什么?“大自然不会真正死亡,”考夫曼回答道。“真正的死湖的最佳例子是阿迪朗达克山脉数百个酸化的湖泊。微生物存活下来,但没有鱼。它们只是相当无聊。”
但“无聊”根本不足以形容如果维多利亚湖不再为周围居民提供食物或就业机会所导致的局面。对于库萨湾的渔民、基苏木出售鲈鱼碎片的妇女,以及所有其他3000万与湖泊命运紧密相连的人们来说,他们将无处可去。即使在非洲,饥荒和动荡的史诗式悲剧屡见不鲜,维多利亚湖的消亡仍将带来无与伦比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