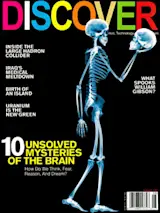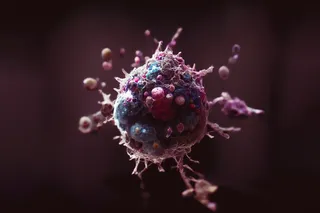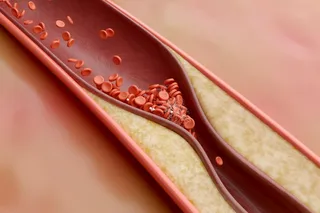他没有脸。他鼻子的位置是一团糊状物,上面粘着一层黑色的东西,仿佛曾经是小胡子。一根塑料管插入一个曾经有嘴唇的洞。他的整个头部都被烧伤,肿胀流脓。爆炸使他面目全非,即使是亲属也很难辨认他。这个人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但我知道。
他在巴格达以北约40英里的巴拉德空军基地空军战区医院(AFTH Balad)的伊拉克人重症监护室。当我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时,我看到旁边的病床上还有更多像他一样的病人。把他送到AFTH Balad的黑鹰医疗救援队说,这名病人可能是一名伊拉克警察部队成员,这支民警部队由伊拉克共和国维持。他们无法确定,鉴于他所受创伤的程度,这个人无法——也不能——为自己说话。一台呼吸机替他呼吸。他偶尔会抽动双手。
“他们最近又带来了一个人,我们听说他是警察,”尼科尔·A说,她要求不透露更多身份。“他失去了双肢,身体30%的面积烧伤。我一直在努力查明他的身份,但伊拉克警方没有记录自己人员的系统。”
据伊拉克内政部长称,自美国领导的入侵以来,在约19万人的部队中,已有超过1.2万名伊拉克警察被杀。
“伊拉克警察内部存在很多腐败,”尼科尔说。“我们训练的一些人正在设置简易爆炸装置。他们白天是警察,晚上是叛乱分子。”
“你是说我们无意中在训练叛乱分子?”我问。
“对,对,”她说。
对于所有被认为是叛乱分子的病人,护士们在AFTH Balad接受治疗的整个过程中都给他们包扎眼睛。一有机会,叛乱分子就会受到审问。对于我面前的病人,那个没有脸的男人,就不需要采取这种措施了。他已经没有眼睛了。

图片由吉恩·博尔斯博士提供 | 无
“每天都不同,挑战不断,”巴拉德空军战区医院的患者联络官查尔斯·斯特雷西诺少校解释说。“大部分工作是弄清楚我们能为受伤的伊拉克人做些什么。好选择实在不多。”
在受伤后的几天内,AFTH巴拉德的所有伊拉克人——警察、被拘留者和普通平民——都将获得美国国防部提供的无与伦比的医疗服务。在美国,类似水平的护理每位患者将花费数万美元。为了将这种护理水平扩展到伊拉克人,军医必须保持床位空置,这意味着要迅速将他们从AFTH巴拉德转移到伊拉克医疗机构。因此,每月在AFTH巴拉德治疗的200名伊拉克人的平均住院时间不到一周就会出院。
“我们转入伊拉克医疗系统的一些病人将无法存活,”伊拉克重症监护室的护士杰克·埃普斯少校说。“不像在美国,我们有资源处理任何程度的任何事情,他们这里没有。”
我问埃普斯,他听到的能沟通的伊拉克病人最普遍的情绪是什么。
“害怕出院,”他说。“他们知道自己将要面对什么。他们知道护理不如这里好。如果他们缺少肢体,或者如果女性毁容,那么他们就没有多大价值,很可能会受到蔑视。被排斥。在医院里,他们会得到稳定治疗,如果他们伤势严重,被放在一边接受舒适护理并不罕见。”
舒适护理主要包括疼痛管理、补水,以及很少的其他治疗。病人预计会死亡。
与一群注定死亡的人打交道让埃普斯身心俱疲。长时间的工作和不可预测的伤员涌入使他面容憔悴。在过去的两天里,已有35名受伤的伊拉克人被送往巴拉德空军战区医院,有传言称巴格达刚刚又发生了一起更大的汽车炸弹爆炸案。伊拉克病人所承受的痛苦刻画在埃普斯脸上沉重的压力线中。
“我到这里已经四个多月了,”他说。“当你日复一日地看到战争带来的这种痛苦,女人和孩子,无辜的平民,这很难。你会有很多情感冲突和很多悲伤。我仍然不习惯看到孩子死去。我所能做的就是熬过每一天。”

齐曼,一个来自巴格达的学生,在2006年一枚迫击炮弹落在她的高中时受伤。她的手术使她无法控制手臂或腿,也没有为她提供物理治疗的系统。| 图片由法伊扎·阿拉拉吉提供
当埃普斯和我坐在伊拉克重症监护室帐篷里交谈时,我再次看向病床上躺着的各种病人。几个孩子缺少肢体;其他病人身上有许多管子从脖子和躯干伸出。在我们谈话的某个时候,一位头发花白的伊拉克男子走进房间,用一种克制着愤怒的表情瞪着埃普斯和我。他的兄弟——一个缠满绷带的木乃伊——连着呼吸机,处于昏迷状态。当这位访客坐下时,他轻轻握着兄弟的手,他的脸变成了一张悲伤和接受的面具。仅仅10分钟后,那人站起来离开了房间,肩膀沮丧地耷拉着。
“很多时候,他们比我们更早知道情况,”埃普斯说。
被带到巴拉德的伊拉克人是幸运的。并非所有受伤的伊拉克人都能被送往美国军事医院接受治疗。如果受伤发生在远离美军巡逻的地区,创伤护理的责任就落在当地医疗机构身上。
16岁的泽曼是巴格达的一名高中生,每天穿着同样的校服上学:一件白色棉衬衫和一条深蓝色长裙。2006年10月,一枚迫击炮弹在泽曼课间走出校园时在校园里爆炸。弹片穿过棉衬衫,进入她的皮肤和骨骼,严重损伤了泽曼的颈部和背部。
在巴格达努曼医院的急诊室,接诊医生尽力减缓泽曼的出血。五天后,外科医生才对她进行手术。
泽曼幸存下来,但脊柱手术使她出现了严重的运动控制问题。当她试图移动手指时,手指会扭曲,她的腿拒绝听从大脑发出的信号。护士将泽曼放在病床上,不知道她是否能活下来。四十五天后,泽曼终于出院了。
泽曼住在巴格达北部父母的房子里。她整天被限制在椅子上,只有家人的谈话能给她带来些许乐趣。甚至连电力也供应不足。在短暂有电的时候,泽曼才能看几分钟珍贵的电视。她的父亲,一位退休的工厂工人,在家门前一个简陋的摊位上卖香烟和蔬菜。这个家庭靠邻居的购买来维持生计。
通过物理康复,泽曼或许能重新控制她的腿和手臂。但她没有地方可以获得任何护理,即使有,带她去那里也要冒生命危险。她唯一的希望是离开伊拉克前往约旦,在那里她可以找到有效的医疗保健。伊拉克护照可能需要400美元,她的家人需要三本。租车费用为600美元。每月收入不到100美元,泽曼的家人不太可能负担得起这次旅行,更不用说抵达约旦后5000美元的费用。
与AFTH巴拉德的伊拉克男子不同,泽曼有脸有名字。但她的身份对她几乎没有帮助。她被困住了。
美国曾经有一项在被占领国家进行人道主义援助的蓝图。在越南战争之前和期间,美国建立了一个协调高效的系统,以维持和稳定越南平民的医疗保健,该系统最初由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建立。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和美国军事援助司令部(越南)的共同努力,军方实施了四项以平民为导向的计划。这四项计划的综合效果是惊人的医疗保健水平。即使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军方也成功建造了三家医院,为平民提供了1100张病床。
美国在伊拉克建造医疗设施的努力遭遇了惨败。最严重的例子是巴士拉儿童医院,这是一个由第一夫人劳拉·布什支持的停滞项目。2003年末,国会最初拨款5000万美元。三年后,施工或多或少地在项目进行到一半时停止,预计完工成本为1.2亿美元。(合同最近从一家美国建筑公司转包给一家约旦公司。)
日内瓦公约要求对病人和伤者给予“特别的保护和尊重”。第四公约第56条规定,“占领国有义务确保和维持……被占领地的医疗和医院设施及服务、公共卫生和卫生”。总共有十多篇文章规定了必要的医疗措施,从医疗用品问题到医生安全问题。
整个20世纪80年代,伊拉克被广泛认为是中东地区医疗保健的首选目的地。海湾战争以及随后的贸易禁运削弱了伊拉克的医疗保健,但一个暴君的政策几乎摧毁了这个国家的骄傲。
“我们到达那里之前,伊拉克医疗系统状况很糟,”空军军医总长詹姆斯·劳德布什中将(博士)说。“萨达姆在他执政的最后一年,每年为每个伊拉克人花费大约50美分用于医疗保健,而皇室成员却拥有整个医院专门为他们的健康服务。”前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汤米·汤普森曾公开谴责萨达姆政权下医疗保健的衰落:“医生被迫眼睁睁看着他们的病人死去,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所需的物资或药物。而且医疗教育被压制了25年,这意味着新的实践和技术无法得到应用,最终,人们受苦了。”
萨达姆的下台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去年3月,伊拉克卫生部长阿里·沙马里,激进什叶派教士穆克塔达·萨德尔的忠实追随者,在腐败和滥用职权的指控中辞职。
如果没有家人打来电话,这位无名的伊拉克男子很可能会被送往医疗城,那是一家巴格达的公立医院,任何时候都收容着2000多名伊拉克人。通常,伊拉克患者必须满足一个重要的标准才能被转到医疗城。
“我们不会将逊尼派病人送到巴格达的两家‘正常运转’的伊拉克公立医院,”斯特雷西诺解释说。“我们曾尝试将逊尼派病人送到提克里特教学医院,但目前看来该医院无法正常运转。我们谨慎地只送那些符合最低护理标准的病人——如果需要,气管插管就位,伤口闭合,胃造瘘管用于营养——因为我们被告知伊拉克医疗系统的护理非常有限,所以需要过多重症护理的病人无法得到。我们真的鼓励家属尽可能带走病人,因为据我们所知,家属会提供更好的护理。”
与伊拉克各地的医院一样,医疗城也受到许多问题的影响。
“很多东西都不够用,”曾于2004年2月至2006年8月担任医疗城总监兼顾问外科医生的阿米尔·穆赫塔尔说。“我们有一台CT扫描仪,它的电线被一名医疗恐怖分子故意剪断,导致这台机器变成了一堆没用的钢铁。我们的医疗设备遭到破坏,卫生部也不帮助修理。即使我有钱,我也买不到器械或药品。我可以买电视或冰箱,但我买不到阿司匹林或抗生素。”
阿尔-穆赫塔尔解释说,与卫生部的官僚主义纠纷使他无法获得医疗资金。虽然资金问题仍然困扰着医院,但安全问题仍然是更大的困难。
美国军方不为伊拉克医院提供安全保障;设施保护服务(FPS),一支由伊拉克内政部监管的安全官员部队,负责这项职责。然而,它充满了腐败。FPS内部的单位已知与穆克塔达·萨德尔的民兵有联系,并在他们本应保护的组织中实施了谋杀和绑架。“我的保镖被绑架并杀害了,”阿尔-穆赫塔尔说。“我的表弟,在医疗城工作,月薪60美元,也被杀害了。在我离开前六个月,我最终配备了一支由15名保镖组成的团队。”
“我想在我的医院自由工作,但我不能,”R.A.(出于安全原因,姓名不予透露)说,他是一名伊拉克医生,最近因生命受到威胁而逃离伊拉克。“他们(伊拉克卫生部)对我们施加了许多限制。我们小心翼翼地工作。现在就像萨达姆政权一样。就像我们害怕说萨达姆错了,我们害怕说萨德尔错了。”
在一些城市,伊拉克病人在医院病床上被杀害,只因他们站在当地叛乱的错误一边。据称,萨达姆政权的前情报官员现在至少负责伊拉克一家公立医院的安全。“我每天平均接诊75名病人,”R.A.解释说。“但有时我们接诊的病人数量难以承受,超出了可用床位。许多病人在我眼前死去,原因是缺乏救命药和抗缺血药,以及缺乏胸腔引流管。”
“伊拉克的医疗系统一片混乱,”德国兰德斯图尔地区医疗中心(LRMC)前神经外科主任吉恩·博尔斯说。美国士兵从伊拉克撤离后被送往那里。他说:“它几乎处于最低限度的运作状态。巴格达有2000多名医生被杀害和暗杀,摩苏尔还有更多。”入侵前,伊拉克有3.4万名医生;此后,1.8万人逃离了该国。
博尔斯看起来像个军人:光头,结实魁梧的身材,握手有力。然而,外表是会骗人的。博尔斯声称,他的任期使他成为了和平的倡导者。
博尔斯在LRMC服役期间,每天都目睹战争在美国人身上造成的恐怖。在极少数情况下,会有不同类型的病人到来。博尔斯特别记得其中一人:一名库尔德军队的将军,被友军火力击伤。
“他有非常严重的颅内损伤,大脑大出血,”博尔斯说。“我给他做了手术,取出了血块,做了去骨瓣减压术——他活了下来。”
博尔斯很快得知他的病人碰巧是伊拉克总统的兄弟。作为感谢,博尔斯收到了参观伊拉克医疗系统的邀请。这次旅行发生在2006年5月,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我和他坐在丹佛科罗拉多州的医院办公室时,博尔斯给我看了一批他在伊拉克医院拍摄的受伤病人的照片。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被各种爆炸炸得面目全非。看了几张照片后,我开始觉得少了些什么,但又说不上来。一张照片上是一个失去手臂的男孩,另一张照片上是一个因全身烧伤而极度痛苦的女人。然后我恍然大悟。病人身上没有插管。没有静脉输液,没有氧气,没有导尿管。背景中也没有常见的监护仪。病人只是躺在床上,只有一张床单和一个枕头。
在访问伊拉克期间,博尔斯受邀参加一台神经外科手术。“那就像我们这里(美国)三四十年前的手术一样,”博尔斯说。“我所在的一家医院,一台CT扫描仪坏了六个月,还有一台核磁共振断断续续地工作。在美国,我们使用自动锯和钻,但他们没有任何自动器械。回到了过去,而我就是那样训练出来的。很多年轻人会不知道该怎么办。”
在一份最能证明美国政策失败的报告《美军占领下伊拉克医院的病痛》中,记者达尔·贾迈勒列举了巴格达及其附近伊拉克医院中明显存在的一系列恐怖事件。在阿拉伯儿童医院,病人自带食物,因为医院缺乏提供膳食的资金。楚瓦德医院仅依靠其所需供水量的15%运转。阿尔卡赫医院重症监护室的厕所看起来就像是恶臭不堪的污水噩梦。
我问博尔斯他访问过的伊拉克北部医院的身体状况。“我去过的医院负担过重,设备陈旧,”他说。“他们的手术台非常简陋,有很多人因为医院没有适当的设备而无法得到治疗。如果病人需要长时间使用呼吸机,他们很可能活不下来。”
“伊拉克医院是否无法处理我们转交给他们的严重程度?”我问。
“我想他们不能,”他说。“他们没有能力给病人提供护理。”
“那么病人就会恶化?”
“是的。或者他们会死。”
弗雷德里克·“斯基普”·伯克尔是科索沃和塞尔维亚等危机后稳定领域的专家,他是2003年3月首次联军入侵巴格达后,美国国防部派往巴格达的第一位非军方美国人。他的主要目标是支撑崩溃的伊拉克医疗体系,首先建立一个监测系统,以查明哪些人得了什么病。在下午沙尘暴过后超现实的模糊中,伯克尔的装甲车队穿梭于巴格达街头,他迅速拍照并快速观察。任务屡次受到威胁:伯克尔的五辆悍马车队在一小时内遭到三次伏击。
“我们的车队遭到小武器射击,”伯克尔说。“我们的射击手声称他们看到附近公寓楼里有一把50口径(机关枪)。我还听到一枚RPG(火箭弹)从我们的车辆之间呼啸而过,但它没有爆炸。”
进入城市之前,伯克尔曾预言巴格达会遭到洗劫,但他对实际策略的独创性感到惊讶。“它以医疗保健为中心。抢劫者通过洗劫医疗保健系统,能够非常迅速地摧毁士气。这是一种高度有组织、专注于医院、公共医疗保健系统、药店和药品仓库的洗劫,而且是无情的。医生和护士如果去上班,他们的家就会被洗劫一空。”
2003年4月,伯克尔参观巴格达的亚穆克医院(一所教学医院)时,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
“洗劫过后,亚穆克什么都没有剩下。唯一剩下的床和担架都在急诊室。他们只有少数几张床单。所有东西都被从墙上扯下来了:心脏监护仪不见了,透析机被砸毁,CT扫描仪的主板被偷走了。病人躺在地板上,因为他们的床被偷走了。”
伯克尔去亚穆克医院是为了说服行政人员允许国防部重建和人道主义援助办公室负责人进入医院进行检查。亚穆克官员拒绝了,声称这会招致叛乱分子的袭击。会议期间,一位年轻的留着胡子的什叶派教士走进房间,愤怒地瞪着伯克尔。这位教士一言不发地离开了。不久之后,伯克尔得知这位教士是穆克塔达·萨德尔,并且已经发布了法特瓦,要求处死伯克尔(事实上,伯克尔的继任者被枪杀了)。此后,亚穆克医院获得了新的桌椅,但据报道,由于药品短缺,病人仍在继续死亡。
伯克尔回顾了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对当地医疗支持截然不同的态度。“越南是一个世界因美国这种承诺而尊重美国的时代,”他说。“我想那时我们了解文化,国务院扮演的角色要大得多。”根据报告《1965-1970年美军在越南的医疗支持》,1970年,美国军事临床医生通过医疗民事行动计划(MEDCAP)每月治疗约22万越南平民。由于军事省级卫生援助计划,由16名美国人组成的团队补充了30家民用医院的临床人员。
“我认为现在根本没有多少MEDCAP任务了,”伯克尔说。“伊拉克医院里没有美军驻扎。我们的部队获得太空时代的医疗,但在同一次爆炸中受伤的伊拉克人有70%会死亡。”
罗伯特·J·维伦斯基在他的著作《军事医疗赢得民心:越南战争中的平民援助》中指出,从1963年到1971年,美国军医在越南进行了近4000万次平民接触。巴拉德空军战区医院每年治疗约2000名伊拉克人。军方在战地医院为伊拉克人提供的护理质量无可争议地是卓越的,但治疗范围(超出军事责任范围)令人严重担忧。尽管伊拉克卫生部拒绝报告受伤平民的数量,但医学杂志《柳叶刀》估计,重伤伊拉克人接近一百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2005年伊拉克共有约3.5万张医院病床。这些数字表明,大多数受伤的伊拉克人即使得到治疗,也是在一个负担过重的伊拉克医疗系统中进行的。
传统上,人道主义援助的主要责任落在美国国际开发署身上,就像在越南一样。但伯克尔称之为“前所未有”的一举动是,布什总统在2003年将这一权力移交给了国防部,留下了一个机构,既负责打击敌人,又负责修补他们炸伤的人。
伊拉克占领开始时,国防部派伯克尔管理该国的卫生部;他此前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曾领导过一个创伤中心,并在索马里到伊拉克北部等战乱地区领导了20多年的恢复工作。伯克尔提出了一项计划,其中包括建立一个卫生监测系统、权力下放的医疗保健以及确保为大量复员的伊拉克士兵提供医疗服务——因为,正如许多以前的战争所表明的那样,被忽视的士兵将继续战斗。伯克尔说,布什政府在两周后将他撤换,声称希望在该职位上安插一名“忠诚者”。他最近被邀请回到巴格达提供咨询,但拒绝了这个机会。他认为这是一种徒劳的努力。
“布什政府违反了几十年来人道主义界所熟知的所有原则,”伯克尔说。“无论实施了什么计划,都是临时的,军方几乎没有得到CPA(联军临时权力机构,美国在伊拉克建立的临时政府)的帮助。还能做些什么呢?”
我知道他在重建其他医疗系统方面的经验,我问伯克尔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将伊拉克医疗系统恢复到受人尊敬的海湾战争前水平,假设这项努力将完美无缺地进行,没有挫折。“哦,我的天哪,”他说。“我可以告诉你,在非洲,这些国家的恢复期大约需要十年。伊拉克要恢复过来还需要很长时间。即使有这种意愿,也没有医生或护士。仅仅是医疗和护理教育就需要很长时间。”
伯克尔解释说,约旦和叙利亚等邻国正在向难民提供大部分医疗服务——如果伊拉克人真能离开这个国家的话。
“他们永远不会看到他们以前的国家,”伯克尔解释说。“人们已经沿着种族、部落和宗教界限分裂。我认为遗产是我们给了他们分裂伊拉克的许可,它将永远不会一样,无论是好是坏。”
在联军临时权力机构(CPA)于2004年6月解散之前,它发布了一份成就总结,声称“整个国家在提供医疗保健方面达到了战前水平。”然而,所有迹象都指向相反。2003年入侵后,伊拉克的婴儿死亡率增加了37%。伯克尔说:“现在,它与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和阿富汗一起,是世界上最差的国家之一,”而过去它曾是中东地区最好的国家之一。根据“救助儿童会”的一份报告,每八名伊拉克儿童中就有一名在五岁前夭折。
医院在没有足够的X光机、呼吸机或救护车的情况下运作,无法满足病人的需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最近发布了一份报告,指出:“人道主义状况正在稳步恶化,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所有伊拉克人……伊拉克平民的困境每天都在提醒人们,长期以来他们的生命和尊严没有得到尊重。”
站在那张没有面孔的伊拉克男子身旁,我被这种悖论彻底击垮了。作为一名美国人,我为我们的国家正在为他提供平民战争伤亡者所能得到的最高水平的创伤护理而感到自豪。他不会在我们手上死去——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来确保这一点。但我们最好的意图在他离开巴拉德空军战区医院的那一刻就瓦解了。如果他被送往医疗城,他可能活不过一周。如果他恢复了一些沟通能力,如果他能写纸条或说几句话,他的身份碎片可能会开始拼凑起来。然后他可能会被送回家。就像泽曼一样,那个没有面孔的伊拉克人每天都需要他全家人的努力来维持他的生命。他将与感染、处方药短缺和失明作斗争。无论是什叶派还是逊尼派,都不会有康复、残疾津贴或医疗保险。对他来说,健康或和平没有任何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