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在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西部边缘,莎伦·斯托克站在一扇漆黑的地下室门前,思忖着进去是不是个好主意。作为辛辛那提大学古典文学的博士生,斯托克正在为她的论文寻找一批特定的青铜时代陶片。她的搜索将她带到了霍拉村的一个小型考古博物馆,以及一个三十年来只偶尔开放的地下储藏室。“博物馆的守卫非常缓慢地打开了门,然后他们退了回去,”斯托克回忆道。“里面堆满了东西。我立刻想让守卫再把门关上。这简直是在大海捞针。”
斯托克强迫自己从阳光下进入黑暗。然后,当她的眼睛适应后,她辨认出粗糙的木箱和下垂的纸板桶之间的一些秩序,它们紧密地堆积到天花板。有些上面仍然印着美国人民的问候——那是1940年代希腊内战期间美国粮食援助计划的遗物。斯托克开始掀开盖子,翻找包在泛黄的旧报纸里的捆绑物,上面的标签已经褪色到几乎空白。她停下来读了一个木制识别标签,欣赏了一张印有年轻杰奎琳·肯尼迪戴着药盒帽的1960年代希腊报纸。斯托克的手越脏,她就越高兴。那里储存着大量的陶器碎片和其他古代残骸。还有动物骨头,很多。三千多年前,这些动物曾供养着希腊西南角一个山顶上的宏伟宫殿的居民。它们的遗骸于1939年4月4日被发掘出来,这可能是考古史上最幸运的第一天。那天,斯托克在辛辛那提大学的前任卡尔·布莱根正在一个橄榄园中挖掘一个勘探壕沟时,他的一名工人从土壤中挖出了一块泥板。布莱根轻轻刷掉泥土,立刻看到泥板上刻有线形文字B,这是一种从青铜时代克里特岛上发现但从未在希腊大陆上出现过的未破译文字。那个春天,在战争降临希腊之前,布莱根争分夺秒地挖出了数百块泥板,为破译这种文字提供了关键的材料。这些泥板揭示出这座山顶宫殿的人们使用一种早期的希腊语书写。尽管他们从未提及国王的名字,但布莱根确信他的名字是涅斯托尔。涅斯托尔。对古典文学的学生来说,这个名字是虚构的。《荷马史诗》中,一位名叫涅斯托尔的睿智老国王与阿伽门农一起参加特洛伊战争,并用他年轻时的英勇事迹鼓舞士气。在《奥德赛》第三卷中,忒勒马科斯在涅斯托尔的王国“沙质的皮洛斯”开始了他寻找失踪已久的父亲奥德修斯的旅程。当忒勒马科斯在黎明时将船的龙骨冲上岸时,他发现这位睿智但啰嗦的国王在海滩上,他的人民聚集在他身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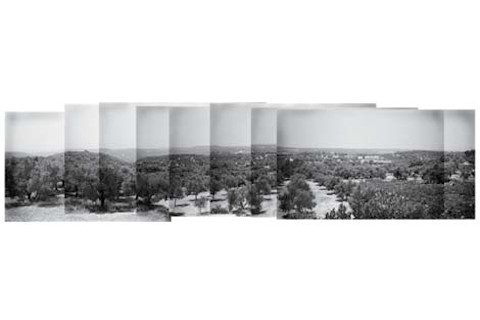
这个位于希腊西南部的橄榄园是考古史上最幸运的发掘地之一,也是最具争议的地点之一。图片由皮洛斯区域考古项目(PRAP)提供。

他们向海神波塞冬献祭,波塞冬拥有海蓝色的鬃毛,震撼大地。他们分成九个营,每个营五百人,每个营献上九头公牛,当人们品尝内脏时,将大腿骨烧给神明。
涅斯托尔的皮洛斯是迈锡尼文明的辉煌之一。他的宫殿横跨一个战略性山脊,可以俯瞰南面的纳瓦里诺沙湾,向北则越过艾加莱昂山的肩部,进入王国富饶的内陆省份。公元前1200年左右,一场大火摧毁了宫殿,预示着整个希腊迈锡尼文化的崩溃。对许多自布莱根以来的考古学家来说,那场崩溃的细节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往往平淡无奇的生活,比它们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的浪漫回响更具吸引力。他们说,荷马是诗人,不是历史学家。对卡尔·布莱根来说,他打包运到霍拉储藏室的那些桶桶罐罐、骨头和陶片,不过是考古盛宴的残羹剩饭——小心翼翼地挖掘,尽职尽责地记录,然后被遗忘。但对斯托克和新一代法医考古学家来说,这些“剩饭”有它们自己引人入胜的故事。斯托克的第一个想法是这个地方迫切需要重新组织。她的下一个想法是,一次彻底的清理可能会带来新的证据。她没有想到的是,隐藏在那堆考古杂物中,在一个不起眼的木箱里,有一些遗骸,它们能够重新唤醒这位希腊吟游诗人的古老声音——以及随之而来的,关于他所谈论内容的争论。
“荷马问题”的现代起源可以精确追溯到1870年4月,地点是土耳其西部俯瞰达达尼尔海峡(连接欧洲和亚洲的狭窄海峡)的希萨利克山。在这里,海因里希·施利曼,一位白手起家的德国商业巨子,摇身一变成为白手起家的荷马学者,带着一件革命性的科学工具——铁锹——来到了这里。他正在寻找荷马笔下的特洛伊城。他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古典学者都认为特洛伊是一个神话。施利曼则有不同的想法。在挖了几条探沟后,他第二年带着一群当地工人回来,在希萨利克开辟了一条巨大的壕沟,切入了一座座失落的城市,就像切开一块婚礼蛋糕一样。他数出了九座。它们从罗马皇帝奥古斯都为庆祝其家族与特洛伊英雄埃涅阿斯虚构的联系而重建的特洛伊九世,一直向下,城下之城,直到小型但强大的早期青铜时代堡垒特洛伊一世。施利曼唯一的问题是决定哪一座是荷马笔下的特洛伊。他选择了特洛伊二世,主要因为在那一层中,他发现了一批古代黄金、水晶和青铜宝藏。如果这是荷马笔下的特洛伊,那么施利曼就可以将他的这批宝藏宣称为“普里阿摩斯的宝藏”(普里阿摩斯是特洛伊国王),而其中的金珠头饰则不啻为特洛伊的海伦的珠宝。施利曼是那种会让任何后代都感到紧张的开创者,他能做出狡诈的行为、彻底的捏造和夸大的宣传。特洛伊二世最终被发现大约建于公元前2400年——比施利曼想象的要古老得多,也太古老了,无法成为荷马笔下的特洛伊。但施利曼确实发现了一些东西,一个关于希腊大陆失落的青铜时代文明的线索。1876年,施利曼认为他已经在土耳其发现了荷马笔下的特洛伊人,于是他去希腊寻找荷马笔下的希腊人。在迈锡尼,传说中阿伽门农国王宫殿的废墟所在地,他发现了一批黄金面具、青铜武器和风格化的器皿,这些标志着施利曼命名为迈锡尼的新文明。迈锡尼人深受克里特岛米诺斯文明的影响,是好斗的海上民族。他们生活在国家控制的经济中,由国王和他的抄写员自上而下严密组织。然后,在公元前13世纪末,他们的权力中心一个接一个地崩溃,只留下了他们的语言、他们的名字,以及对其宏伟壮丽的模糊记忆。大约500年后,许多学者认为,荷马出现了。传统认为他是一位来自爱奥尼亚(今土耳其西部海岸及岛屿)的盲眼流浪诗人。无论荷马是谁,他似乎都了解北爱奥尼亚的地理——因布罗斯岛和特涅多斯岛、达达尼尔海峡,以及特洛伊周围低矮的沿海丘陵和湿地。但即使是施利曼也承认,荷马讲述了一个非常古老的故事,“这是他的前任吟游诗人传给他的,他用自己时代的衣着,将特洛伊战争和毁灭的传统事实重新包装。”
荷马的故乡下图:传统认为荷马(图为公元前2世纪赫勒尼时期半身像的现代复制品)来自爱奥尼亚,即土耳其安纳托利亚西部海岸及岛屿。荷马从未见过希腊西南端的皮洛斯宫殿,但他却最雄辩地歌颂了皮洛斯的战王涅斯托尔。地图由马特·赞绘制


点击图片放大(44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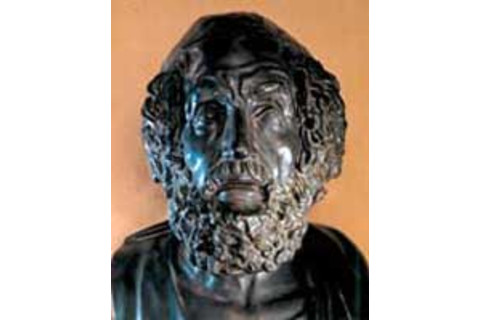
正如施利曼剖开希萨利克一样,古典学者们也剖开荷马的文本,以寻找层层深意。然而,他的诗歌更像一块什锦蛋糕,而非层层叠叠的蛋糕。《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学者们总结道,包含着数百年来由吟游诗人诵读和重塑的非常古老的故事核心。这些故事在公元前八世纪左右,也就是荷马被认为生活的时代,很可能被大幅修改。当时,不识字的希腊人刚刚开始采用腓尼基文字系统,以“alpha, beta”开头。那段文字中包含了许多青铜时代的细节,这些细节在荷马的铁器时代是无人知晓的:战车运载青铜盔甲的战士参战,头盔上覆盖着野猪獠牙,以及半圆形的“塔盾”,大到敌方战士会感觉自己在与树后的人决斗。荷马一口气列举了大约30个迈锡尼王国,它们派船加入阿伽门农对特洛伊的进攻。除了雅典和少数几个之外,这些王国在公元前八世纪时已经消失或变得微不足道。如果考古学家后来追查到其中四分之一,那仅仅是因为荷马让它们在记忆中栩栩如生。皮洛斯就是最好的例子。在一个活着的荷马和一座燃烧的皮洛斯之间,横亘着一个不识字的黑暗时代,充其量只能通过口头传统和流传已久的故事来连接。荷马与雅典人将历史作为事实记录的发明之间,又相隔了大约400年。到那时,皮洛斯的位置已经 hopelessly confused。罗马作家斯特拉博记载,公元一世纪时,热心的当地人将三个不同的地点宣称为“真实的”皮洛斯。他转身走开,咕哝着:“有一个皮洛斯在皮洛斯之前,还有一个。”当希腊人于1832年从奥斯曼帝国手中赢得现代独立并开始重新希腊化地名时,他们将土耳其城市纳瓦里诺改名为皮洛斯。这只是一个粗略的猜测。在1939年那个幸运的早晨,卡尔·布莱根可能发现了真正的皮洛斯,但他几乎没有平息荷马真实性的问题。尽管荷马对青铜时代的服装非常关注,但他经常滑入同时代的铁器时代服饰。例如,他的战士火化死者,而不是像迈锡尼人那样埋葬。阿喀琉斯向特洛伊葬礼游戏的获胜者提供足够的铁,以确保家乡的附庸牧羊人和农夫有足够的工具。然而,铁在青铜时代是最稀有的金属。许多学者说,《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的动物祭祀只是荷马的另一个“错误”。希腊人直到公元前八世纪才开始实行这种祭祀,当时这种习俗是从近东传入的。在迈锡尼遗迹中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存在荷马所描述的那种动物祭祀。换句话说,涅斯托尔在皮洛斯海滩上屠宰的那些光滑的公牛,只是荷马不符合历史的想象力的产物。或者不是吗?

上图:卡尔·布莱根在皮洛斯发现的遗骸中包括这个瓮的碎片,现已修复。布莱根在青少年时期的一次事故中失去了右臂肘部以上的部分,但他仍然一丝不苟地发掘了该遗址,揭示了一个由布莱根称为涅斯托尔的国王统治的青铜时代宫殿的遗骸。图片:左(瓮),由辛辛那提大学古典学系提供

沙伦·斯托克在储藏室发现一年后,她的丈夫杰克·戴维斯决定仔细研究她所发现的东西。戴维斯是辛辛那提大学的布莱根希腊考古学教授,但他与发现皮洛斯的人是截然不同的调查员。戴维斯更多地依赖体质人类学和硬科学,而不是古典文学,甚至不是铁锹的证明。他是调查考古学的倡导者:他倾向于关注遗址的表面,而不是挖掘壕沟寻找文物,他会在大片区域上铺设网格,绘制出所有风化到地表的文物,并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他的遗址通常类似于犯罪现场,生物学家和化学家被请来检查有机线索的证据。为了整理霍拉的骨头,戴维斯和斯托克请来了保罗·哈尔斯特德,一位动物骨骼专家,也是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考古学教授。哈尔斯特德开玩笑说,他在皮洛斯的第一个夏天是“一次发掘中的发掘”。他们一桶一桶地将地下室里的东西搬到阳光下,搬到博物馆后面树下摆放的木桌上。当戴维斯努力辨认布莱根的壕沟主管用铅笔写在发掘标签上褪色的信息时,哈尔斯特德高兴地按类型和外观整理骨头。大多数似乎是标准的食物残渣——破碎的山羊和羊骨头碎片,大多未烧毁——但其中一个收藏“格外显眼”,哈尔斯特德说。“它们几乎全是牛骨,几乎全是股骨、肱骨和下颌骨,而且全部都烧焦了。”第二年夏天,哈尔斯特德带着瓦拉西亚·伊萨基多(伦敦大学学院的博士生,有骨骼经验)回到了皮洛斯。他们用手持放大镜仔细检查了烧焦的骨头,记录了屠宰痕迹、物种指标、年龄、性别以及组织残留物的缺失。这些骨头被猛烈的烤火或布莱根的挖掘者严重骨折,但哈尔斯特德和伊萨基多能够重新组装完整的标本。至少有10只动物,主要是公牛,外加一只红鹿。这些部分被仔细地去除了肉,但骨髓却完好无损——这是为凡人烹饪的人不会做的事情。烧焦的痕迹不像肉骨头在炉火上烧焦或埋在燃烧的宫殿下那样不均匀。它们是均匀的,仿佛整个骨头表面都同时暴露在火焰中。对哈尔斯特德来说,这些骨头看起来就像烧焦的祭祀遗骸。这些话在某些人耳中令人震惊。去年,当哈尔斯特德在谢菲尔德的一次青铜时代圆桌讨论会上分享他的初步发现时,他的同事们感到困惑。“我没有充分意识到缺少烧焦祭祀的证据是多么具有争议性,”哈尔斯特德说。尽管在圆桌会议上没有人提到荷马,但他的名字却在暗中徘徊。这些烧焦的骨头可能是在忒勒马科斯登陆皮洛斯海滩的那个早晨,冒着烟从那里出来的。

自皮洛斯于1939年被发现以来,其残存的遗迹已被整合起来,形成了迈锡尼人生活的生动画面:(从左顺时针)八个修复的花瓶;卡尔·布莱根助手马里恩·劳森的一封信;布莱根巨著的扉页和涅斯托尔国王王座室的重建图;布莱根和劳森在皮洛斯的照片。
实话说,荷马对于21世纪的考古学来说,有些尴尬。考古学家说,他吸引了公众的想象力,却使科学复杂化。“我理解公众对荷马的喜爱,但这可能很危险,”宾夕法尼亚布林茅尔学院的詹姆斯·赖特说。“有些考古学家会说,‘嗯,如果你真的被《伊利亚特》所吸引,让我带你去那个地方。’这已经濒临谄媚,为了让更多人接受而扭曲学术。”赖特说,要证明哈尔斯特德的骨头确实是烧焦的祭品,考古学家就必须指出迈锡尼时代前后类似的遗骸和仪式。“在那之前,”他说,“我认为我们需要尊重中间400年的沉默。”然而,也有人欢迎哈尔斯特德这些令人费解的骨头。德克萨斯大学的史前史学家辛西娅·谢尔默丁曾在皮洛斯与杰克·戴维斯合作,她说年轻的学者和考古学家愿意重新审视荷马和黑暗时代文化连续性的问题。在某些方面,这是对始于1960年代中期的“反荷马”反弹的一种回应。这种反弹的目标是像布莱根那样,即使不是手捧《伊利亚特》进行挖掘,也是对它记忆犹新的考古学家。“到1970年代中期,我们有人说荷马是个骗子,一个伪历史学家,一个虚假的信息来源,”谢尔默丁说。“当时的想法是,如果你想了解青铜时代,你就不要读荷马。你来亲自看看青铜时代的证据。然后你可以回头看荷马文本,然后说,好吧,这是衡量荷马可靠性的一个标准,但你不能用荷马来了解青铜时代。”直到现在,人们才敢于再次采取相反的视角。“荷马通过诗歌描绘的世界和我们通过考古学描绘的世界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有很多接触点,”谢尔默丁说。“动物祭祀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都会出现的事情。每当他们有战斗或逃跑时,他们都会宰杀几只动物,举行盛大的宴会,而且是肉、肉,还是肉。肉是特别的。你不会举行庆祝宴会而吃扁豆。关于这一点的线形文字B文本证据在过去五年才刚刚出现。”谢尔默丁承认,荷马可能不是青铜时代“官方可靠的来源”。“但有些回响是我们无法否认的。”皮洛斯的骨头,最终为考古学提供了一个两全其美的绝佳机会。无论它们对荷马说了些什么,它们也很大程度上揭示了迈锡尼人在其权力鼎盛时期的状况。“仅仅通过分析骨骼材料,研究陶器的位置,并收集壁画的证据,”詹姆斯·赖特说,“考古学就可以自己拼凑出一个故事,一个非常丰富和详细的故事。”例如,斯托克和戴维斯能够将10头牛的烧焦的腿骨和下颌骨追溯到宫殿入口附近的一个房间。斯托克和戴维斯计算,即使考虑到对神祇的祭品,仍然有4000磅牛肉供人类食用。如果所有10只动物都在一次事件中被祭祀,它们可以喂饱6000人——远远超过其鼎盛时期在城堡内和周围居住的人数。再加上平面图、陶片和线形文字B泥板的证据,你开始看到皮洛斯不仅仅是一个堡垒,更是一个餐饮中心。就在中央庭院或“美加隆”(国王坐在王座上接见重要客人之处)外面,是户外宴会庭院,那里有充足的储藏室和厨具。布莱根发现了储酒罐、搅拌碗、长柄勺,以及数千个精致的、带有两个把手的饮用杯,称为“基利克斯”,它们立在一个细长的杯柄上,底部是圆形的。

涅斯托尔在皮洛斯宫殿的重建图。图片由辛辛那提大学古典学系提供。
在合适的人手中,仅这些杯子就能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讲述皮洛斯的故事。剑桥大学研究员丽莎·本德尔利用布莱根公布的发掘记录绘制了每个房间发现的基利克斯杯柄数量。一个杯柄是一个点;一个装有数百个基利克斯杯柄的房间变成了一个红色的斑点。由此产生的地图显示,杯子集中在服务储藏室和入口庭院旁的小房间里——布莱根认为,那是一个供进入宫殿的旅行者使用的酒吧。红点还勾勒出美加隆西面一个大庭院和宫殿大门前的一个大开放区域,那里侵蚀搅乱了沉积层,但留下了大量基利克斯碎片。对于像本德尔这样受过剑桥训练的考古学家来说,这些模式暗示着“社会等级的协商”。对我们其他人来说,它就是一场宴会的座位安排。本德尔认为,地位最低的客人可能在宫殿大门外的广场上饮酒,大概也吃牛肉。次等客人可能在有门控的西庭院饮酒,他们可以为被邀请进入宫殿(尽管不是美加隆本身)而感到自豪。贵宾很可能与国王一起在美加隆,使用更考究的金属器皿饮酒。本德尔还在宫殿的线形文字B泥板中发现了另一类“外带”食客的迹象:国王用这些泥板为他各省的臣民订购葡萄酒和其他奢侈食品。所有这些盛宴都表明宫殿如何将较小的区域权力中心纳入其轨道,并巩固新的联盟。清点基利克斯杯柄与荷马将涅斯托尔描绘成一个海盗般、好战的国王的解读相悖:皮洛斯国王可能更多地用酒杯而不是剑来建立他的领地——或者至少是安抚他新征服的臣民。卡尔·布莱根时代的考古学家对这些陶瓷碎片和骨骼碎片知之甚少。但布莱根,他那永恒的功绩在于,他有远见地保存了这些遗迹,留给了他的继承者。“其他人都在丢弃这些东西,”斯托克说。“在这方面,他远远领先于他的时代。”1960年,希腊考古局在皮洛斯中心遗址上建造了一个巨大的金属棚屋,以保护它们免受风吹日晒。今天你去皮洛斯,你可以沿着通道、房间和庭院追溯3200年前国王统治的地方。七号房间就在宫殿的前门旁边,那是书记员和他们嘎吱作响的泥板的世界。在节日里,三等宴会者会聚集在外面,也许等待国王出现在正门,带着祭祀的遗骸。也许这些遗骸被存放在七号房间的书记员那里,作为国王忠于神灵——以及他富有到能将10头公牛的腿骨和下颌骨喂给熊熊烈火——的证据。线形文字B泥板告诉我们国王崇拜的一些神祇名字:波塞冬、宙斯、赫拉、狄俄尼索斯和阿瑞斯。但最终这些神祇未能拯救宫殿。公元前1200年左右,储存着香油、精纺羊毛、陈年葡萄酒、战车轮和青铜武器的仓库全部付之一炬。国王的书记员将他们的泥板账本丢给了大火。灰烬降落在巨大的户外宴会庭院上,储藏室的架子倒塌,饮用杯成千上万地碎裂在地板上。从国王领地的每个角落,夜间的火焰和白天的浓烟都清晰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宫殿的瓦砾被马基(razor-leafed Mediterranean chaparral)所覆盖,皮洛斯失落了。如果我们今天能看到它的遗迹,那仅仅是因为一位传奇吟游诗人,在宫殿焚毁约500年后,凭借想象力,在记忆中重建了它。如果那段记忆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愈发清晰,那要归功于布莱根和他的继承者们艰苦卓绝的工作——以及他们顽固地坚持,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相信荷马的话。

荷马在《奥德赛》第三卷中歌唱皮洛斯,此处显示的是15世纪的古希腊语版本。“它就像一个巨大的脏雪球,在山坡上滚动时收集了各种东西,”考古学家杰克·戴维斯说。“它收集了来自不同时期、地点和时代的东西,我们称之为荷马的诗歌。但要拆开一个雪球很难。”

阅读《奥德赛》的精简版请访问 www.mythweb.com/odyssey。有关《奥德赛》的更多资源,请参见 www.robotwisdom.com/jaj/homer/odyssey.html。《伊利亚特》的资源:http://academic.reed.edu/humanities/110Tech/Iliad.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