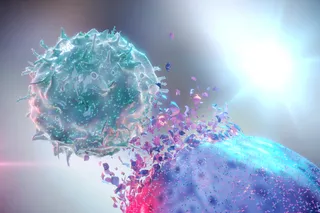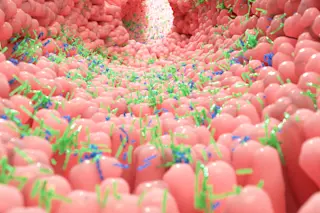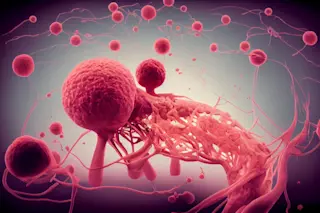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日早晨,在基辅明斯克地铁站外,一家乌克兰麦当劳门前,一辆流线型黄色旅游巴士怠速运转着引擎。司机正在等待前往隔离区的乘客,隔离区是二十年前因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而形成的放射性无人区。
很快,大约20人,主要是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聚集在巴士附近。两名年轻的黑发男子分发了白色和蓝色辐射防护服、黄色塑料雨衣和瓶装水。其中一位一日游游客是亚历克斯,他在普里皮亚特出生并长大,直到10岁。现在30岁的他,是一个虚拟社区的成员,这个社区的大多数年轻人曾居住在普里皮亚特这座被遗忘的城市,这座城市建于1970年代,用于居住距离不到两英里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工人。当时,普里皮亚特被称为未来之城。然而,它在1986年4月27日被遗弃,当时它的居民成为了世界上第一批,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永久性核难民。
这次旅行是前普里皮亚特居民组织的,恰逢爆炸事件20周年。它也碰巧非常接近拉东尼察,即纪念逝者的日子,家人会去探望亲人的坟墓。整个普里皮亚特市就是一个坟墓,一个在20多年前死去,再也不会复活的地方。
我们都集合完毕,辐射防护服、水瓶和午餐袋都已到位,我们登上了巴士。组织者开始介绍自己。人们来自世界各地,包括圣彼得堡、敖德萨、维尔纽斯和基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除了在他们的虚拟社区pripyat.com上之外,从未见过面。来自基辅的亚历克斯和来自圣彼得堡的德米特里坐在克里斯托弗·比松和我的后面。比松是一位法国画家和哲学家,当我和他一同参加布达佩斯的切尔诺贝利会议时,他邀请我参加这次旅行。“我是唯一的英语使用者。我可以为你翻译,”德米特里说。

围绕4号反应堆的“石棺”。图片由维基百科提供。
当巴士向北驶向隔离区,即反应堆周围18英里宽的区域时,网站组织者开始播放普里皮亚特的电影。经过对巴士故障视频播放器的一些调整,一个小屏幕开始显示反应堆火灾后的可怕场景。模糊的黑白画面显示了急救人员在痛苦中的特写镜头,他们的身体上覆盖着剥落的皮肤和严重的烧伤。然后我们看到普里皮亚特的大规模撤离,2000辆城市和校车像一场奇怪的葬礼队伍一样缓慢地驶出城市。
还有4月26日爆炸发生前的画面,那时居民们还不知道危险。家庭录像记录了普通的婚礼,模糊的蓝色画面中新娘穿着白色礼服,新郎微笑着。只有恐怖和震惊的画面留在我脑海中。“人们是如何发现发生了什么事的?”我问德米特里。
切尔诺贝利RBMK-1000反应堆释放出放射性云团后的36小时内,苏联官员对此保持沉默。然后,在4月27日下午,官员们派每栋公寓楼一人向住户分发传单和碘片。碘片已无用,分发太晚以致无效,但居民们并不知道。传单指示他们,由于发生事故,第二天早上将撤离。他们被告知只需携带三天所需的物品。普里皮亚特的49000名居民,包括15400名儿童,将所有物品留在公寓中,他们不知道自己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家、自己的物品或自己的城镇了。
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后,周边76个村庄也进行了疏散,形成了各自的核流亡社区。灾难产生的辐射在斯堪的纳维亚部分地区、波兰、波罗的海国家、德国南部、瑞士、法国北部和英国都有检测到。事故发生四天后,放射性粒子已到达非洲和中国。但普里皮亚特是前线。科学家估计,最危险的放射性元素需要长达600年才能充分衰变,使该镇变得安全。在此之前,在普里皮亚特长时间停留无异于拿自己的DNA玩俄罗斯轮盘。
在普里皮亚特,反应堆从屋顶和露台清晰可见,它是电力、进步、现代性本身的象征。然而,最终,它以他们从未想象过的方式改变了那里人们的生活。“我的十位最亲密的亲属死于癌症,他们告诉我这与辐射无关,”一位前居民告诉我,“你觉得我会相信吗?当然与辐射有关。我也会死于它——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电力。”
巴士已经向北行驶了一个多小时。基辅广阔的单体公寓大楼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田园风光中绿褐色田野间的小木屋。乍一看一切都很平静,但隔离区是一片死寂的土地。尽管树木、鸟类和动物依然存在,但人类却从这片风景中消失了,除了少数人,他们不顾官方禁令,偷偷返回,在他们的小村庄里生活和死亡。这里只有一片寂静的空虚。
我们抵达隔离区检查站。所有进入隔离区的人都需要特别许可证。如果你是普里皮亚特的难民,很容易就能获得。记者、科学家,甚至一些游客也被允许进入,但所有访客都必须由切尔诺贝利信息局的导游陪同,该政府办公室负责监管切尔诺贝利旅游。我们巴士上的所有人向年轻的乌克兰警察出示了护照。他们核对名单,然后放行。整个过程很快,这些人似乎对我们的到来感到厌倦,很快就升起了大门,允许我们进入隔离区。
我们的第一个目的地是切尔诺贝利本身。虽然核设施已于2000年12月关闭,但反应堆仍在清空核燃料,因此需要维护和检查。数千名佩戴徽章监测辐射暴露的工人仍在为核电站服务。他们不住在切尔诺贝利本身,而是在附近。我们停在一个几乎空无一人的杂货店,那是一栋不像是商店的白色建筑,里面有几个玻璃柜,整齐地摆放着物品——几片剃须刀片、三节电池,以及小袋的葡萄干、坚果和美式糖果棒。在行政大楼入口处,列宁的青铜雕像举起手指向核电站。
里面等着我们的是我们的导游尤里,他曾是一名英语教师。他把教书的工作换成了切尔诺贝利信息局的职位。“工资是原来的三倍,所以我接受了。我有一个家庭。为了安全起见,他们每隔几周就会轮换我们离开这里,”他说。我们坐在1987年7月举行切尔诺贝利审判的房间里。苏联最高法院裁定核电站前厂长、总工程师和工程师副手有罪,并判处每人10年监禁。在前法庭的前方,尤里向我们展示了他将随身携带的剂量计(辐射探测器),以便在我们四处走动时测量辐射水平。当我们驱车前往普里皮亚特时,组织者重播了撤离场景,所有人都安静下来。

从前文化宫看到的普里皮亚特摩天轮。图片由基思·亚当斯提供。
尤里带领我们穿过城市街道,绵延数英里,一片虚无。没有汽车,没有人迹,只有铺好的道路,却无人等候。我们停在普里皮亚特的前文化中心,进入了一座剧院。墙壁上一幅鲜红色和蓝色的壁画是唯一完好无损的东西。那是一幅经典的苏联绘画,描绘了大束麦穗、手持食物篮子的妇女以及辛勤劳作的农民。每个人看起来都很幸福。楼上,成百上千本书散落在地板的一端,一直蔓延到其他房间。
克里斯托弗和我跟着另一对夫妇来到一栋校舍。外面,立面上刻着字母和数字。里面是宽敞的窗户教室,阳光普照,翻倒的椅子和桌子堆成一团。然后,在一张桌子上,整齐地摆放着老师的笔记本、出勤记录和学生成绩,全部用西里尔字母书写。这一切是如何幸存下来的——或者是有闯入者重新摆放的?
尤里走进学校检查辐射。他将剂量计靠近椅子和桌子。他所到之处,都能听到辐射的咔哒声:教室里、剧院里、音乐室里、钢琴键旁、公寓里、地面上。无一幸免。辐射水平各不相同,有时接近每小时100微伦琴,但不会高很多。纽约市的背景辐射水平大约是12。100的水平在短时间内不被认为是危险的。“你们可以安全地四处走动,”尤里总结道。
克里斯托弗想走到镇上的游泳池,他上次来时去过那里。德米特里过来警告我们。“游泳池周围有一个钚点。不要靠近,”他说。钚点?他怎么知道的?我们真的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安全吗?当浑浊的黄色液体从其中一栋建筑的天花板滴到克里斯托弗头上时,他拍了一张照片来记录这件事。“这东西掉到我头上了,”他说。“你觉得我会没事吗?”
沿着一条被高高的褐色野草覆盖的漫长而寂静的道路,我们看到一匹矮小的沙色马小跑着离开,想知道它是否是真的。“是的,你看到的是一匹马,”尤里向我们保证。“几年前它们被引入这里,看看它们如何生存。由于某种原因,辐射似乎没有影响它们。科学家们正在研究它们。”
午餐时,克里斯托弗和我吃着乌克兰猪油、黑面包和红鱼子酱,组织者递给我们蓝色垃圾袋。“第一阶段开始了,”德米特里说。“作为我们纪念日的一部分,我们想清理我们的家乡。谢谢你的帮助。”如果进展顺利,他计划进入第二阶段,将普里皮亚特打造成一个活生生的博物馆,以纪念其散居各地的流亡者。?
我们分散在宽阔空旷的街道上捡拾垃圾,大部分是空伏特加酒瓶。“如果苔藓区域有任何东西,不要捡。辐射会在苔藓中积累。那可能很危险,”尤里告诉我们。
我们的旅行团成员亚历克斯向克里斯托弗和我示意跟随他。他试图开口说话,但找不到合适的英语单词,便用手势示意。“我英语不好,”他说。“来吧。”我们跟着他穿过一条长满高灌木和带刺树枝的荆棘小径。他快速穿行,直到到达一栋公寓楼,入口处已坍塌,油漆剥落,窗户破碎。“我,”他说。他拍了拍胸口,微笑着指着大楼顶部,数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我的家,”他说。
亚历克斯走进敞开的前门。我们爬上裂开的台阶,台阶上散落着碎玻璃、生锈的旧管道堆、破碎的瓷砖和成堆的灰尘。楼梯平台上散落着零星的家具,一张坏掉的椅子,一张缺腿的桌子,更多的生锈管道躺在水泥楼梯的台阶上。他探头往电梯井里看。“呼,”他说,然后摇了摇头。那只是一个空荡荡的洞,松散的电缆一直延伸到一楼。事故发生后不久,普里皮亚特就遭到了洗劫,由于这里的一切都带有放射性,所有被盗和出售的物品都将放射性散布到了整个前苏联。电梯轿厢及其部件现在位于其他地方,释放着它们的辐射。
腐朽与破坏有着一种奇特的美。生命与物体任由风吹雨打,变得如同艺术品。它们都是逝去时光的一部分,一个不再存在的时代。切尔诺贝利灾难发生后不久,苏联解体,部分原因正是它所激发的普遍不信任和沮丧。戈尔巴乔夫说:“对我来说,生活分为切尔诺贝利之前和切尔诺贝利之后。”
亚历克斯两步并作一步地向上爬,我们紧随其后。我们爬得越高,碎片越多:废弃的冰箱和炉灶部件、木板条和更多碎玻璃。他迅速到达八楼,指着左边一扇发霉的棕色软垫门。他推开时门发出吱呀声,然后他走进他那发霉、腐朽的公寓。他快速地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仿佛要确认自己不是在做梦。
亚历克斯停下来,脚敲着地板。“这里,卧室,”他说。他站在一间阳光明媚的小房间里,角落里有一张几十年前的床垫,潮湿、破烂、弹簧外露;窗户附近堆着一堆湿漉漉的衣服。他拿起一条孩子的藏蓝色短裤。“我的,”他说,然后把它们扔回地上的那堆衣服上。他穿过旧卧室,走到相邻的房间。“这里玩游戏,音响,”他说。
从公寓客厅外的小露台上,切尔诺贝利反应堆清晰可见,其方块状现在已被“石棺”覆盖,这个混凝土棺材旨在包容其放射性危险。“我们看到了火,”亚历克斯摇了摇头说。他走进厨房,朝窗外看了一会儿,然后离开了家。他穿过走廊,敲了敲门。“我的朋友,在这里,”他说,并抚摸着自己的心。
亚历克斯离开时我跟在他后面。我们什么也没说。他向我展示了他心中亲近的东西。为什么?我不知道。也许亚历克斯想找人见证。也许他想找另一个人和他一起经历这一刻。
整天都有普里皮亚特的回乡者聚在建筑物外面或光秃秃的道路旁,他们围在一起喝啤酒,聊天。很难察觉他们对此的反应。当天晚些时候,在一条小巷里,他们中的几个人找到了一个旧的足球,已经瘪了,沾满了灰尘。他们轮流踢着它。他们是高兴还是悲伤?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人是一种能够适应任何事物,我想这是对他最好的定义。”
“我们的许可证只到下午6点——我们必须走了,”尤里告诉我们。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普里皮亚特的街道上漫步,打开门,窥探人们的家,看着我们永远无法了解的生命遗迹。在一间公寓里,我们发现了一组黑白照片,照片中的孩子们打扮得要去参加派对。这些照片放在一个木制的置物架上,卷曲的边缘显示出岁月的痕迹,但排列仍然完整。是谁留下的?或者这是一种致敬的形式,由另一个闯入者放置在那里,他也曾仔细搜索过这些死寂、被污染的房间?
在我们离开之前,我们驱车前往石棺,那是一座巨大的混凝土建筑。很难相信那里发生过什么,里面仍然在酝酿着什么放射性大锅。切尔诺贝利4号反应堆看起来完全没有动静。没有任何东西能告诉你里面的危险。尤里拿出剂量计,把它放在石棺大门前的地上。它在几秒钟内就升到了1300,这是我们到达以来见过的最高水平。没人想在这里久留。
亚历克斯在石棺前拍了一张合影,我们前面挂着一个大大的www.pripyat.com横幅。然后我们开车离开,此时太阳正在隔离区落下。金色的光线照亮了稀疏的深棕色树木,看起来美丽、孤独且不真实。
将近一年后,我重返切尔诺贝利,与克里斯托弗·比松合作拍摄一部电影。我仍然能看到核电站的走廊,除了向导的鞋跟在黑白瓷砖上发出的咔嗒声外,一片寂静。我们穿过数英里的走廊,地板图案不断变化——黑白地板,金色三角形,然后又是黑白。克里斯托弗说这就像置身于一个巨型野兽的内脏中。
我在这里并不感到印象深刻或惊讶。相反,我接受了它,就像每天来这里的成千上万的工人一样。这似乎很普通,很平凡。只有在前核电站的自助餐厅里,当我们和其他工人坐在一起吃免费午餐时,我们环顾四周,注意到那些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的面孔。“你可以在自助餐厅里拍一部电影,”克里斯托弗说,“看看那两个男人,并排坐着,一言不发。他们穿着绿色的制服,一切尽在不言中。”
我们请求跟随一位工人。亚历克西,一个沙色头发、高瘦、戴眼镜的男人,在爱沙尼亚餐厅与我们见面。我们迟到了,所以我们到达时他已经在吃一个装满小馄饨的小慢炖锅里的东西。“抱歉,”我说。
他没有抬头,只是点点头继续吃饭。
“你选择去切尔诺贝利工作吗?”我问。
“嗯,你可以这么说,”他说。“1987年,当这里还是苏联的时候,他们给了我两个选择:去西伯利亚工作或者来这里工作。这是一个简单的选择。我来到这里。”
“那危险呢?”
“嗯,做很多事情都有危险。”
他继续吃饭,从不抬头。
阿列克谢告诉我们,他每天早上和成千上万的人一起搭乘火车。我们陪着他。工人们鱼贯而入,挤满了座位,常客把钥匙和帽子留在长凳上以标记他们的座位。男人们四五个聚在一起,拿出褪色的扑克牌,摆好棋盘。当克里斯托弗拍摄一些黑发男人打牌时,他们用俄语喊道:“我们不想被拍摄。”语气很冲——在翻译告诉我们之前我们就知道他们说了什么。火车上几乎没有女人。一位女人——克里斯托弗称她为“读者”——全身米色,在闪烁的阳光下翻阅着一本书。
40分钟的车程把我们从隔离区外带到了离反应堆最近的区域。火车缓慢地行驶,穿过白俄罗斯边境,然后返回乌克兰。我们进站时,夜班工人正准备乘火车回家去斯拉夫蒂奇。“不要拍摄,”我们的翻译说。相反,我把一切都记在脑海里:成千上万的人冲向反应堆的场景,成千上万的人冲向斯拉夫蒂奇,背景里播放着老苏联风格的音乐,年轻的制服警卫坐在反应堆入口处的椅子上,检查每个进入的人。这似乎是地球上苏联仍然存在的地方。没有人提及“辐射”这个词。你到达时他们会给你一条小项链戴,一个微型剂量计。
在这片虚幻的土地上,每个人都说一切都好。在这里待了一段时间后,你就会开始相信。也许辐射没那么糟。也许身体确实能适应。老鼠不受影响。也许人类也不会。然后我闪回到基辅的公寓楼,他们称之为寡妇之家,那里急救人员的妻子们比她们的丈夫活得更久,闪回到那位工人撩起衬衫给我看他那长达一英里的疤痕,闪回到他患甲状腺疾病的妻子,以及他们因健康问题被带到古巴的儿子科利亚。
在斯拉夫蒂奇,我们拦住了一群闪闪发光的男小学生,他们正从附近的语法学校步行回家。“你想去核电站工作吗?”我问。
“不,不,不,”他们异口同声地尖叫。

图片由国际原子能机构提供
“你认为核能好吗?”
“不。”
“为什么?”
“辐射。”
斯拉夫蒂奇是苏联于1987年建造的城镇,旨在取代普里皮亚特。那里有爱沙尼亚人社区、拉脱维亚人社区等。这座城镇曾是希望之城,普里皮亚特曾是未来之城。未来和希望都在这些城镇中消亡了。
我们的导游尤里告诉我们:“那是事故发生后,其他反应堆仍在运行时建造的。我们仍然相信未来是光明的。我们曾希望反应堆能继续运行,斯拉夫蒂奇能取代普里皮亚特,一切都能恢复正常。但事实并非如此,然后苏联解体了。接着反应堆关闭,斯拉夫蒂奇的一切都开始瓦解。人们离开了,城市衰败,开始变得像被遗弃的普里皮亚特。人们不再抱有希望。它变得像普里皮亚特一样。当然,人们仍然住在这里,仍然在反应堆工作,但所有的希望都消失了。我不想再住在那儿了。然后我去了切尔诺贝利做导游。”?
在我们的拍摄过程中,我们再次与年轻的乌克兰电影制作人马克西姆一同回到普里皮亚特。他有一个问题。?
“你在拍一部关于死亡的电影吗?”他问。
“不,”我回答。
“辐射就是死亡吗?”他问。
我没有回答。长时间的沉默之后,他又问了一遍。
“是的,我想是的,”我说。
马克西姆看到他的公寓楼时,抚摸着车窗。“我的房子,我的房子,”他用英语说。在他的卧室里,他走向一张巨大的白马海报,抚摸着马的脸。他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拿起东西。他拿起一个蓝色的球。“这是我最喜欢的玩具,”他说。然后,在衣柜门前,他停下来看着一张墙壁大小的1986年日历。他开始撕掉四月之后的月份。
“我需要一些独处的时间,”他说。
他没待多久,当他走出公寓时,他说:“我不会再回来了。这是最后一次了。”然后他把自己一直拿着的蓝色球弹回了公寓里。
他走下楼梯,回到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