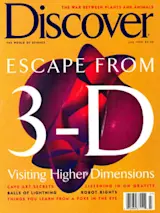“除了人类所知的维度之外,还存在第五维度。”在20世纪60年代,罗德·塞林用他深沉的声音念出这句耳熟能详的开场白,以介绍他那部广受欢迎的电视剧《阴阳魔界》。塞林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宣告显然是邀请人们进入一个怪异的世界。但对于数学家来说,前往更高维度的旅程就像坐出租车穿城而过一样稀松平常。他们不仅经常前往第五维度,还会去第七、第十和第二十六维度。“这没什么特别的,”明尼阿波利斯几何中心主任阿尔伯特·马登说,“对数学家来说,这是家常便饭。”
数学家为什么要离开我们熟悉的三维世界的舒适区呢?因为,说来也奇怪,通过探索更高维度,他们可以更清晰地审视复杂问题——他们能够看到在低维度的压缩世界中看起来 hopelessly tangled( hopelessly tangled)的关系。类似地,天体物理学家进入更高维度是为了观察星团中的模式;粒子物理学家是为了寻找统一理论;工程师是为了分析机械联动装置;通信专家是为了寻找将信息压缩到狭小空间的方法。
没有什么比跳入更高维度更能简化复杂问题了。如果这听起来有悖常理,那就想想进入更高维度到底意味着什么。假设你生活在一条一维线上。你可以像火车在轨道上一样向前或向后移动。但你不能横向移动。这不仅超出了界限,也超出了你的宇宙。现在想象一下,你的宇宙突然扩展到二维。你可以自由地在整个表面漫游:东、西、南、北,或介于两者之间的任何方向。或者,更好地想象你是一个电影角色,在二维屏幕上过着你的生活。增加第三维度,突然你可以走进观众席。你可以轻松地走开,避开那个即将向你开枪的枪手。多亏了那个额外的维度,你获得了新的移动自由。
对数学家来说,维度就是:一个自由度。例如,拿一根打结的绳子。只要你留在三维空间里,你就被困住了,纽约大学库朗数学科学研究所的副所长西尔万·卡佩尔(Sylvain Cappell)说。你解不开它。但如果你能让一小段绳子穿过另一个维度,你就能绕过障碍并解决它。无论它看起来多么纠缠,你都可以进入更高维度并解决它。卡佩尔应该知道。除其他外,他研究十维空间中八维结的性质。
思考维度最简单的方法是将其视为一个变量——也就是说,一个可以拥有多个不同值的量。它可以代表经度或纬度、时间或速度、苹果或橘子、粒子或恒星。你可以通过代入温度、湿度、风速、降水等值来描述一种天气模式。如果你需要12个变量来描述一种情况,那么你就有了一个12维的问题。
但仅有变量并不能构成几何。正如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数学科学研究所(MSRI)所长威廉·瑟斯顿(William Thurston)所指出的那样,“拥有三个变量与拥有三维空间是不同的。”而对于理解复杂关系来说,空间的形状通常与它所占据的维度数量同样重要。以一个标准的二维关系为例——比如,一个将利率与消费者支出关联起来的图表。两者都与几何无关,但通过观察这条线的形状,你可以更好地理解情况。你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它何时达到峰值或谷底。你可以看到曲线的斜率。
在五维甚至十维模型中,情况也是如此。卡佩尔说,从逻辑上讲,几何似乎已经消失了,只剩下数字。但几何学能告诉你仅凭数字无法了解的事情:曲线如何达到最大值,如何从这里到达那里。你可以看到山丘和山谷,急转弯和平稳过渡;甜甜圈形九维模型中的孔洞可能表示没有解决方案的区域。
要描绘这些复杂的物体,最简单的方法是每次增加一个维度,每个维度都向不同的方向延伸。从一个点开始。将点沿着一个维度拉伸,你就得到一条线,由两个点限定。将这条线向垂直方向拉出,你就会扫出一个正方形,一个由四条线限定的区域。要得到一个立方体,将正方形膨胀到下一个维度,你就会得到一个由六个正方形限定的实体图形。要得到一个四维立方体,或超立方体,只需将立方体膨胀到另一个维度:你将得到一个边框由八个立方体组成的物体。同样,你可以将一个二维圆盘在第三维度中旋转,得到一个球体。你可以在第四维度中旋转一个球体,得到一个超球体。
从这个意义上说,增加一个新的维度是一种展开,明尼苏达大学的天体物理学家亚当·弗兰克解释道,他研究六维空间,并通过分析六万维雪茄的几何形状来观察球状星团。“你把头伸进去,整个景观都变了,”他说。“所有这些复杂的运动都能简化成,比如说,一个简单的67维甜甜圈,真是太棒了!太美了!”
当然,你自然会问:那么这些其他维度在哪里呢?或者,从一开始,我们最近的邻居,第四维度在哪里呢?答案很简单:它垂直于所有其他维度,就像我们称之为高度的维度垂直于我们称之为长度的维度一样。不幸的是,感知这个其他维度并不那么简单。但也不是不可能。
比尔·瑟斯顿(Bill Thurston)在至少一些同事中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在世几何学家”。36岁时,他获得了菲尔兹奖,这相当于数学界的诺贝尔奖。如今,瑟斯顿正试图改造MSRI,这个在业内被亲切地称为“苦难”(misery)的机构,使其成为向外界更有效地传达数学乐趣的传播者。为此,他开始将该缩写发音为“信使”(emissary)。
对访客来说,瑟斯顿就像一个喜欢玩形状的大孩子。他的办公室就像幼儿园教室一样,有一张小圆桌,上面摆满了原色的小塑料三角形和五边形。然而,瑟斯顿用它们做的事情却绝非简单。他将四个三角形拼在一起形成一个四面体;然后他将五个四面体像花束一样围绕一个共同的中心排列,指出它们几乎——但并非完全——严丝合缝地吻合。他解释说,剩下的一点点角度,在宽敞的四维世界中,恰好足以将600个这样的四面体装进一个超球体中。
他最喜欢的玩具可能是一个柔软的三孔环面,也就是甜甜圈形状,由24块七边形布料制成——一种复杂的袖套,中间有足够的空间让多只手伸进去。去年夏天,他75岁的母亲玛格丽特·瑟斯顿在明尼阿波利斯几何中心参观他的几何与想象课程时缝制了它。这门课程有50名学生,从高中生到大学教授都有。这个复杂图形的图案是由他的两个儿子设计的。这并不容易。在几何学家中,这种形状非常有名,几乎具有神话般的比例。以前很少有人真正建造过。“这是我一直想看很久的东西,”他说。
瑟斯顿认为,我们难以感知更高维度主要是心理上的,最终与大脑在“线性、分析性思维”和“几何形状可视化”之间的分工有关。许多数学研究都使用我们熟悉的阅读、写作和说话的思维模式。例如,代数方程就像句子。给出立方体面积的公式,x ¥ x ¥ x,可以很容易地用语言表达。但立方体的形状是另一回事。你必须“看到”它。
“当我们谈论高维空间时,”瑟斯顿说,“我们正在学习如何在这种其他的空间处理系统中思考和连接。来回切换很困难,因为它涉及大脑中两个完全不同的部分。我们没有很好的方法来传达这种空间信息。问题不在于数学的实质;而在于如何去思考它。”
早在20世纪20年代,亚瑟·爱丁顿爵士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广泛撰文,试图向大众解释爱因斯坦的四维时空。他告诫读者不要听从内心低语的声音:“在你的脑海深处,你知道第四维度纯属无稽之谈。”爱丁顿提醒读者,我们习以为常的“无稽之谈”包括实际上大部分是空的空间的坚固桌子,以及以每平方英寸近15磅的力压迫我们的透明空气。
尽管有些研究高维空间的人选择简单地忽略那些额外维度究竟是什么或在哪里(“最终你会停止尝试将其可视化,”弗兰克说,“那时你耳边的轰鸣声就消失了”),但也有人,比如瑟斯顿,非常努力地克服常识。几何中心的同事也加入了他的努力——该中心官方名称是“国家科学技术研究几何结构计算与可视化中心”。在这里,马登接待了数十名学生和访客,从教授到大学生学徒不等,他们使用强大的计算机探索高维现实领域。他解释说,虽然用代数方法描述任何高维空间当然是可能的,但“通过实际观察,你会学到更多。就像在三维空间中一样。如果你能看到某个东西,你就可以尝试看看它可能有什么特性。这会引发问题。如果你从未见过一棵树,你就无法提出关于它的问题。”
观察高维物体的一种方法是切片。就像你可以将一个三维的奶酪块切成二维的薄片一样,你也可以将一个四维的块切成三维的薄片。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高年级学生、中心学徒戴伦·迈耶(Daeron Meyer)在他的电脑中编程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工具,利用该中心开发的软件探索四维空间。“4D物体在那里以虚拟物体的形式存在,”他解释说。“你可以指定任何你想要的几何形状。然后你只需插入四维坐标。”迈耶在电脑屏幕上投射四维物体的三维阴影;截取四维空间中打结的三维结的二维切片;并旋转一个超立方体,以便更好地检查它的八个面(当然是立方体)。当你探索超立方体的内部结构时,你会感觉仿佛在空间中飞行,穿墙而过,进入那些像鬼魂一样出现又消失的虚无缥缈的房间。
这种感觉是对现实的准确感知。毕竟,四维视角允许你直接越过、绕过三维空间中的任何实体障碍。一个来自第四维的生物可以伸进你体内,真正地挠你的肋骨!难怪哲学家亨利·莫尔早在17世纪就推测,灵魂是四维生物。
更脚踏实地的思想家发现,高维空间对于理解非精神世界也出奇地有用。例如,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将引力描述为由巨大物体存在引起的四维时空扭曲的结果。该理论不仅仅是一种不同的引力描述方式:在计算巨大物体附近引力效应时,它给出的结果与牛顿引力概念单独推导出的结果截然不同。例如,只有相对论才能产生黑洞等奇特现象。继爱因斯坦之后,物理学家西奥多·卡鲁扎(Theodor Kaluza)在1921年提出,电磁力也可以被理解为几何效应——由一个看不见的第五维度的扰动引起的四维时空结构中的波动。
事实上,几何学家长期以来在研究物理世界真实属性方面表现出色。早在19世纪,为我们带来现代热力学理论的开尔文勋爵,就对绳结的性质与粒子性质的相似性印象深刻。绳结是拓扑学中的一个经典问题,拓扑学是一种流动而灵活的几何学。几何学关注的是刚性的线条、角度和面积,而拓扑学则关注孔洞、交点、缠结等。数学家之间有个老笑话,将拓扑学家定义为“不知道甜甜圈和咖啡杯区别的人”。从拓扑学上讲,它们是等价的,因为一个用腻子做的甜甜圈可以被拉伸和扭曲成一个带一个把手的杯子,而不会撕裂或破坏表面。类似地,绳结的研究是根据你是否能将一个绳结转换成另一个,或者它们在空间中挖了多少个孔,或者你如何在不与线条或表面相交的情况下从绳结的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
开尔文勋爵提出,原子是光以太中的结,光以太是一种人们认为弥漫于所有空间的本质。开尔文喜欢这个想法的一个原因是,结和原子一样,可以分为其成员具有某些特征的家族。此外,可以用同一段绳子打出多种结,也可以推测可以用以太中不同种类的结形成多种原子。最后,从这种缠结的视角看待自然,使开尔文能够将物质和力还原为相同的物质——以太。当然,开尔文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但他的思想对数学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开始非常认真地对待结的性质。
近年来,结和拓扑学已成为试图在引力(由弯曲空间的几何学或广义相对论描述)与其他力(如电磁力)之间寻找共同点的理论的核心,这些力由量子力学描述。例如,空间本质上是由肉眼不可见的微小环圈像中世纪锁子甲一样连接起来的(参见《发现》杂志1993年4月刊),这一观点最初是在物理学家注意到描述结的方程与描述引力场中粒子的某些方程之间存在惊人相似性时提出的。
同样,弦理论将所有粒子和力描述为某种基本物质的环,这些环以谐波模式振动,产生从引力到秋海棠的一切。弦理论只适用于10维或26维空间,这使得许多物理学家不愿去研究它。然而,额外维度的存在并不使弦理论本质上比其他理论更复杂。事实上,额外维度的全部意义在于它们简化了一些关系:如果弦理论成立,所有粒子和力都应该可以用那些额外的、看不见的维度的拓扑性质来描述。
另一种说法是,对于复杂问题,高维空间在更大的对称性方面有所回报——即有更多的方式可以让事物发生变化,但仍然保持不变。以一个球体为例——比如一个完全均匀的沙滩球。你可以把它转半圈,它看起来还是一模一样。你可以把它转四分之一圈,或者十六分之一圈,或者千分之一圈,或者百万分之一圈,它看起来都还是一模一样。你可以绕着任何轴,以任何角度旋转它,它永远不会改变。这几乎是完美的对称性。但是,假设一个救生员走过来,绊倒并摔倒在球上,把它压成一个二维煎饼。如果你从上方看这个煎饼,它仍然是圆的。但从侧面看,它就像一条线。以介于两者之间的角度拿着它,它会呈现出不断变化的椭圆形。在高维空间中完美保持的对称性,在低维空间中,正如物理学家所说,是不可挽回地被打破了。
同样的原理适用于任何维度中的任何物体。例如,一个正方形可以放在它的任意四个边上。这就有四种对称性。一个立方体可以放在它的任意六个正方形面上,每个正方形面都可以有四种旋转方式。这就是六乘以四,即24种对称性。一个四维立方体可以放在它的任意八个立方体面上,每个立方体面可以有24种方向。这就是八乘以24,即192种对称性。一个五维立方体可以被放置和旋转,使其在1920个方向上看起来都一样。
如果你把某样东西里外翻转,它仍然保持不变,那是一种额外的对称性。或者如果你在空间中移动某样东西(比如向右移动四英寸)或在时间中移动(两小时后看它),它仍然保持不变,那又是另一种对称性。你可以在力之间拥有对称性,或者在尺度上拥有对称性。如果某样东西变大或变强,而它所有其他属性保持不变,那又是另一种对称性。更高维度几乎总是意味着更多的对称性。
物理学家热爱对称性,因为这意味着即使看起来截然不同的事物,也可能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而且,越是看似不同的事物(比如电和磁)被证明是同一事物(电磁学)的不同方面,就越容易用几个简单的定律来解释物理宇宙。如果弦理论成立,部分原因将是高维引力中固有的对称性允许物理学家从相同的原始物质中推导出所有已知的力和粒子。
这些对称性甚至不必发生在物理空间中。“物理空间只是许多空间中的一种,碰巧特别有趣和有用,”西尔万·卡佩尔(Sylvain Cappell)说。最近,他发表了一种基于高维空间几何学来计算复杂问题可能解数的方法。但他研究的空间并非那种你可以轻易触及的几何。
在某些方面,卡佩尔(Cappell)是一个完美的数学家。他戴着贝雷帽。他大部分工作是在格林威治村的紫罗兰咖啡馆(Cafe Violet)里一边喝卡布奇诺一边完成的,咖啡馆就在库朗研究所对面——通常是和他的长期合作者、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朱利叶斯·沙内森(Julius Shaneson)一起。他喜欢开玩笑说,数学家不过是一台把咖啡变成定理的机器。
同时,他真诚地坦言,数学要求你反复感到愚蠢。事实上,这就是他解释为何最杰出的数学研究出自年轻人之手的原因。“当你开始一个新问题时,你总是感到愚蠢,”他解释道。“你可能会花一整天在一篇论文上,一个小时在一行字上。而你仍然不明白。当你达到人生的某个位置时,你就不想再感到愚蠢了。在数学领域,那时你就完了。”
卡佩尔(Cappell)已经练习“有用之愚蠢”的艺术有段时间了。他还非常热衷于让数学被理解,并寻找使其变得有用的方法。卡佩尔和沙内森(Shaneson)最近的发明非常有用,可能可以申请专利。
它的运作方式是这样的:假设你有一个涉及大量变量和大量可能解决方案的问题。例如,假设你有最多15艘船,可以运载最多300桶石油到最多25个港口,途径最多100条可能的航线,一年中最多365天,每艘船最多有20名船员,每名船员成本最多1000美元,你想知道哪些选择能让你以最高效率运营。即使仅仅通过计数来计算可能解决方案的数量,也需要近乎永远,因为每个变量都与下一个变量相关联。(如果你进行长途航行到遥远的港口,你一年中就无法进行那么多航行。)但如果你根据这七个变量计算出一个七维图形的体积,你就会立即知道可能解决方案的数量——因为体积内符合条件的每个点都表示所有变量相交的地方(也就是说,一个解决方案)。
当然,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体积并不能完全给出正确答案,因为边缘和角度会把事情搞砸。想象一下一块钉板。假设你在上面画一个多边形。如果你问这个形状包含了多少个钉孔,答案并不清楚。有些线穿过一小部分孔,而另一些线则切掉十分之九;角度则切掉各种大小的块。由于高维图形往往有很多边缘和角度,问题也相应变得更加复杂。但卡佩尔和沙内森最近研究出了一种方法来解决边缘效应。他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使这种方法更加有用。他们希望能够找到那些满足特定约束条件的解决方案——例如,产生特定利润的解决方案,其中利润是所有其他变量综合作用的结果。
将数值问题转化为几何问题,在研究恒星和原子等物理系统的复杂运动时也具有启发性。明尼苏达大学的亚当·弗兰克(Adam Frank)大部分工作在超级计算机中心完成,该中心就在几何中心对面。这种联系是恰当的。弗兰克和他的同事研究一种叫做“相空间”的几何。相空间也不是一个物理空间。它是一种观察具有大量运动部件的动力系统形状的方法。
拿一个粒子——比如,一个在房间里飘浮的空气分子。它可以在三个物理维度中移动。但它在每个维度上也都有一定的速度。事实证明,如果你想象这个粒子在一个六维相空间中,同时考虑到它的速度和位置,它的运动看起来会简单得多。当然,如果你有一个以上的粒子,你就有多于六个维度。两个空气分子在相空间中将总共有12个维度。四个空气分子将有24个。由于相空间通常用于计算气体和星系系统(通常包含数千个粒子)的动力学,维度会迅速增加。
“如果你在常规空间中观察这些运动,它们会非常复杂——它们会不断折叠回自身,”弗兰克解释说。“但在相空间中,它们会展开。你不再有随时间变化的运动。整个运动都包含在其中。如果你必须坐着观察一个粒子并追踪它在空间中的运动,你将不得不永远等待。但在相空间中,你只需观察其形状。重要的是物体。而整个动力学都包含在物体的拓扑结构中。”
例如,计算10,000颗恒星在相空间中的运动,可能会填充出一个像简单环面一样的物体。环面的形状能告诉你很多:这个恒星系统稳定吗?它有多少能量?它将如何随时间演化?
形状如何揭示系统的动态,如果你从简单的机械联动装置来思考,会更容易理解。瑟斯顿从自行车脚踏板的例子开始。推动车轮转动的杠杆可以摆动一整个圆周。这被称为它的构形空间。连接在杠杆上的小踏板——你把脚放在上面的那个——也摆动一整个圆周。圆的圆是一个环面。所以这个系统的构形空间就是一个环面。
其他类型运动的构型空间可以累加成球体、椭圆或其他简单的形状,这些形状可以很容易地分析其动态特性。联动装置的运动方式越多,它们拥有的自由度就越多。因此,最终得到的环面或球体可能不是简单的三维形状,而是一个六维环面,或一个五十维环面。“你想知道事物运动时会发生什么,”瑟斯顿解释说。“数学家对这些事物的几何学了解很多。例如,事实证明,在球体或环面上的动态可以长时间预测。但一个双孔环面必然是混沌的。它具有高熵,或者说倾向于无序。所以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
正如卡佩尔所指出的,你甚至可以通过观察孔的数量来学到很多。想象一组关系填充一个球体(就像身高和体重的图表可能填充一个二维形式一样)。在一个球体上,你只有一个最高点和一个最低点。但假设你有一个环面,你把它立起来:现在你仍然在顶部和底部有两个临界点,但你也有两个鞍点:一个在孔的底部,另一个在顶部,总共有四个临界点。卡佩尔解释说,知道这些临界点非常重要,因为很多系统倾向于流向这些点,并在那里稳定下来。假设你有一个描述所有可能物体位置和所有可能能量量的空间。这会告诉你它将如何演化。
所有这些最大值和最小值到底揭示了什么,这并不重要。它们可以是苹果的数量、能量水平或力的强度。无论是什么,这种方法都同样有效。或者正如已故的理查德·费曼所说:“数学的荣耀在于我们不必说明我们在谈论什么(他强调)。”
奇怪的是,有一件事确实非常重要,那就是你所处的维度。因为维度,结果发现,具有与它们是问题的维度还是物理空间的维度无关的“个性”。例如,事实证明,第七维度具有非常有利于进行某些类型微积分的特性。第八维度则非常适合堆叠球体——就像把橙子装进盒子里一样。虽然很少有杂货商在八维空间中工作,但许多从事现代通信工作的人却在这样做。八维空间正是计算机调制解调器传输编码信息的高效堆叠所需要的——这对银行和航空公司等大量处理信息的公司来说是一个福音。
寻找恰当的维度对弦理论家尤为重要,因为该理论必须与广义相对论(由引力主宰的宏观世界)和量子理论(亚原子粒子世界)兼容。“最重要的是,要找到正确的维度,它必须在两个世界中都表现出相同的对称性,”目前在几何中心工作的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数学家丹·弗里德(Dan Freed)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会是十维。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是11维;后来又上升到26维。天知道下一步会是多少。如果其中涉及物理原理,那就是需要拥有正确的对称性。”
根据哈佛大学的克利福德·陶布斯(Clifford Taubes)的说法,为弦理论寻找正确维度的问题也与寻找一个能产生正确数量的力和粒子的时空维度有关。将维度和粒子之间的关系想象成一个带有孔的椒盐脆饼形状的时空。孔的数量告诉你低能量态。而这又告诉你粒子的数量。你不能有太多孔,否则粒子就会比我们能看到的更多。孔之间相互连接的方式类似于力将粒子连接在一起的方式。(当然,我们感知不到这种椒盐脆饼状的形状,就像我们通常感知不到地球的弯曲表面一样。)
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对这些问题着迷的原因各不相同。“数学是对所有可能宇宙的探索,”陶布斯说。“物理学是对我们所处宇宙的探索。”这使得许多从事物理学研究的人也成了数学家。
即使是我们这些已经接受时空是一个四维橡胶垫的物理现实的人,可能也很难跟随数学家进入他们特别的“阴阳魔界”,在那里,高维空间的复杂性似乎永远无法完全解开。例如,他们可能会引导我们思考:如果我们的时空是一个四维橡胶垫,那么它处于什么样的空间中呢?对于数学家来说,一个物体的维数和它所占据的欧几里得空间的维数之间可能存在很大的区别。例如,一个漫画人物是一个嵌入二维空间中的二维生物,但一个空心球体是一个必须处于三维空间中的二维表面。甚至还有一些二维表面只能存在于四维空间中。
事实上,高维空间种类繁多,卡佩尔说,有些人收集它们就像收集蝴蝶一样。而卡佩尔喜欢所有这些空间。如果你问他有没有最喜欢的维度,他看起来几乎惊恐地回答:“那就像问我有没有最喜欢的孩子!”他沉思道:“你知道,时不时会有人递给你一个盒子,说‘这就是所有的几何学。’它看起来如此整洁漂亮,让你忍不住相信。但随后你会看到有些东西从侧面渗出来。嗯,我们总是关注那些从侧面渗出来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