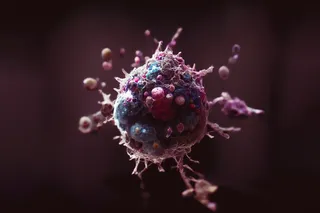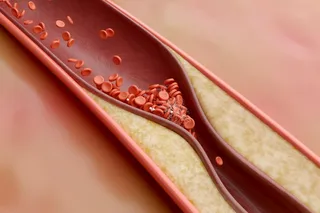保罗·伯格,斯坦福大学生物化学系名誉卡希尔教授,因其在重组 DNA 技术方面的开创性工作于 1980 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他创造了第一个含有来自两种不同生物基因的 DNA 杂合分子。该技术现在构成了遗传学和生物技术产业的支柱。伯格还在 20 世纪 70 年代领导了一项了不起的努力,科学家们自愿暂停某些重组 DNA 实验,直到他及同事们能够就最大限度地降低将生物工程生物释放到环境中风险的指南达成一致。
您 78 岁了。为什么仍然如此活跃?
B:有些事情会激起我强烈的正义感,坦白说,国会正在审议的禁止干细胞研究克隆的法案就是其中之一;其中一项规定对我打击很大,那就是规定该国任何人都不能获得使用克隆技术开发的干细胞疗法。我无法想象一群国会议员竟然会说:“我们对这项技术感到反感,因此我们要禁止这个国家 2.9 亿人获得可能挽救他们生命的疗法。”
您认为加州人为何强烈支持他们的干细胞倡议?
B:我怀疑普遍存在一种共识,即总统在将胚胎干细胞研究限制在 2001 年之前的细胞系上的政策是错误的,而加州应该像多年来在环境和社会项目上一样,支持一项具有前瞻性的计划。还必须认识到,生物医学领域的进步将极大地促进该州的经济。
在治愈方面是否许诺了太多?
B:科学的本质就是一项不确定的事业,预测结果和成果具有确定性是愚蠢的。我相信,胚胎干细胞的可用性为理解疾病的遗传和细胞基础提供了一种新的、强大的方法,因此很可能为那些饱受疾病折磨的人带来新的知识和更好的治疗方法。然而,我坚信,如果没有干细胞研究,我们找到治愈方法或新疗法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
您如何处理纯粹研究的需要与结果和治愈要求的紧张关系?
B:公众和国会议员对听科学本身不太感兴趣,而对科学能做什么更感兴趣。他们想听更多关于你将要治愈的内容。我告诉他们的是,我是一名实验者,我唯一能告诉你它是否有效的方法就是让我去尝试。但如果你阻止我尝试,我们就永远不会知道。
为什么他们不懂?
B:我给你讲个轶事。三十年前,当重组 DNA 受到禁止威胁时,一位相当有名的参议员在参议院发表讲话,说:“我不敢说我能完全理解这个。我高中化学都没及格,所以不可能理解这门科学。但我想说,这是美国进行过的最危险的研究,应该被禁止。”他承认自己的无知,说他对这件事一无所知,却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
您认为人们害怕什么?
B:我将这种偏执称为“我们正在打开什么大门?”的概念。如果“如果”很容易产生。你可以和一群相当聪明的人坐在一起,假设各种各样的结果。所以其中一些会产生恐惧。例如,“克隆”这个词。当科学家说他想克隆干细胞时,您认为公众的脑海中会立即联想到什么?嗯,他们立刻会联想到克隆人。但我们都同意不应该克隆人。克隆干细胞与克隆人无关。但“克隆”这个词只会引发恐惧。你看到了什么?《巴西的男孩们》、《星球大战》。人们不知道,如果没有克隆 DNA,人类基因组计划就不可能完成。他们不知道,如果没有克隆病毒,就不会有疫苗。他们不知道克隆就像一台复印机。
国会将禁止克隆吗?
B:众议院已经通过了一项法案两次。当它通过时,我正在参加一个午餐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比尔·弗里斯特也在那里。我问他:“你认为众议院通过这件事怎么样?”他说他们真的不理解它。我说:“你说笑呢。你是说这些国会议员投票决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他们却不知道自己在投票什么?那么,在以拥有高度智慧人口的强大审议机构自居的参议院,肯定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吧?”他说:“它会轻而易举地通过。”但它没有,不过这个回答说明了很多问题。
您以前也曾卷入过关于人们认为可能危险的突破性发现的争议。20 世纪 70 年代发生了什么?
B:嗯,我们当时正在进行一项实验,试图利用一种动物病毒将新基因引入人类细胞和细菌细胞。我们的目的是研究“外源基因”在这些不适宜的宿主中是如何工作的。但有些人认为携带肿瘤基因的细菌对人类来说是危险的。
这些病毒在一些动物身上引起了癌症,人们担心如果将来自病毒的 DNA 与存在于世界上的细菌结合,就会导致癌症流行。
B:这就是恐惧。冷泉港实验室的某个人发现了这个实验,给我打来电话说:“你要做最危险的实验,你不能这样做。”起初我很恼火,让他滚开。但随后在理清思绪后,我决定我无法确定我们正在进行的实验是否 100% 安全。
所以您以国家科学院的名义召集了一些科学家,并写了一封信,即《伯格信》。
B:我联系了吉姆·沃森、戴夫·巴尔的摩、诺顿·津德、丹·纳坦斯等该领域的重要人物。我们在麻省理工学院一起讨论了这个问题,并得出结论,我们并不真正知道是否存在任何危险。所以我们决定,唯一诚实的做法是给我们的朋友写一封信,说其中一些工作具有巨大的价值,但有些可能存在风险。那么为什么我们不暂停一些实验呢?这正是整个“暂停”想法的由来。
您建议暂停所有实验?
B:我们实际上只确定了三项我们认为值得谨慎对待的实验。将大肠杆菌基因导入大肠杆菌,我们看不到任何危害。你可以在厨房水槽里做这样的实验。但是,将耐药基因导入引起疾病的微生物听起来不是个好主意。将产生毒素的基因导入存在于人体内的细菌听起来不是个好主意。将具有致癌基因的 DNA 导入存在于人体内的生物体可能不是个好主意。那么为什么我们不都同意暂停这类实验,直到我们能够审查整个领域,看看如何处理潜在的风险呢?
那么,来自世界各地的 150 名科学家聚集在加州的阿西洛马?
B:是的,我们争论了三天,有些人反对任何监管,但大多数人认为我们应该说些什么。所以会议提出了一个审慎的回应,表示我们真的不知道风险的大小。然而,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任何风险,会议得出结论,如果存在风险,它们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管理:除少数实验外,所有实验都必须在确保实验生物不逃逸的特殊设施中进行,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物理隔离。此外,我们提出了我们所谓的生物隔离的等级,这意味着你使用特殊的病毒、特殊的生物体来降低从实验室逃逸的可能性。
以前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吗?
B:没有。这就是为什么它如此引人注目。
反响如何?
B:公众赞扬科学家们主动解决疑虑。
然后出现了反弹?
B:在指南发布八个月后,人们才开始说科学家们就像“狐狸看守鸡舍”。但阿西洛马会议确实赢得了公众的信任。并且在数十亿次实验中没有任何不良事件发生。
您没有因为只处理了安全问题而不是伦理问题而受到批评吗?
B:人们对此提出了合理的批评——我们没有处理伦理问题,也没有处理如何应对生物恐怖主义。它们不是被意外地从议程中删除的;这是故意的。由于只有三天时间,我们专注于科学、风险的大小以及如何安全地进行科学。
所以这一切都关乎安全?
B:问题是公共卫生,如何安全地进行实验。
然而,如今,这主要关乎伦理。
B:是的,而且这要困难得多。你如何与那些坚信受精卵是人,核移植产生的囊胚是人,并且摧毁囊胚以获取干细胞是谋杀的人开会?你不能。
但人们使用生物工程药物。
B:令人惊讶的是,人们愿意使用所有通过基因工程在细菌、酵母或上帝知道什么中生产出来的药物疗法,而他们却担心转基因食品。
是否有人提议为干细胞再召开一次阿西洛马会议?
B:不得不处理有争议问题的人总是问:我们为什么不能再开一次阿西洛马会议?它听起来像是一种解决问题的神奇机制,但它无法解决所有有争议的问题。我们在 1975 年严格处理的是安全性,但要解决涉及不同宗教和伦理观点的难题非常困难。我认为你无法在阿西洛马类型的环境中解决这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