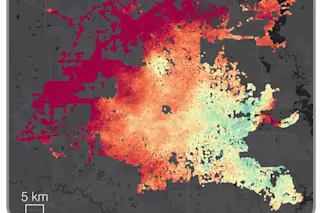曼努埃尔·维托里诺·皮涅罗·多斯桑托斯刚刚射杀了四只白唇西猯,就听到了那声音。那可怕的、令人肝肠寸断的、类似人类的叫声来自大约50米外的一丛藤蔓。“当你听到它的时候,你全身的毛发都会竖起来,”多斯桑托斯说。他丢下正在剥皮的西猯,抓起他切好的用来捆绑尸体到背上的藤蔓,然后朝相反的方向,也就是附近的河流方向飞奔而去。第二声尖叫离得更远,但树木仍然因噪音的冲击而颤抖。第三和第四声呼唤则变得微弱,似乎随着动物的移动,声音来自雨林的深处。但多斯桑托斯在水中等了一个小时左右,直到他觉得安全了,才回去取他的西猯。“我只有一把刀,没有子弹,不想面对那个生物,”他解释道。
没有人——无论是多斯桑托斯,还是巴西亚马逊深处塔帕霍斯河畔小定居点巴拉杜圣曼努埃尔的其他村民,或是广阔雨林中的任何其他人——愿意面对它,无论手中是否有猎枪。马平瓜里(mapinguari)浑身长着红色的长毛,用后腿站立时身高超过6英尺,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恶臭,方圆几米之内的人都会感到迷失方向。它被认为是雨林中最狂野、最稀有、最神秘和最可怕的居民。据说它避水,与成群的白唇西猯一起漫游并保护它们,夜间觅食,用巨大的爪子撕开巨大的棕榈树以吞食柔软的内部,脚趾向后翻,并且普遍对子弹免疫。马平瓜里也被认为是另一个大脚怪,是像多斯桑托斯这样的人——以及一位著名科学家大卫·C·奥伦——想象的产物。奥伦不懈地寻找这种生物,他的传奇故事正像这种野兽本身一样流传开来。
大约两个月后,多斯桑托斯向奥伦和他的“马平瓜里搜寻突击队”讲述了他的遭遇,地点就在巴拉附近森林的同一地点。已是傍晚时分,雨林中本已昏暗的绿色光线愈发黯淡。多斯桑托斯讲述他的故事时,所有人都保持沉默。即使 clearing 一侧的 Copaiba 树巨大的支撑根后面没有潜伏着什么东西,人们的脑海中也能浮现出马平瓜里那模糊的身影。男人们都听说过这些故事,尽管有时这种生物会有不同的名字:capé-lobo(狼斗篷)、mão de pilão(杵手)、pé de garrafa(瓶脚)或 juma。多斯桑托斯说他看到的马平瓜里有巨型犰狳的爪子、猴子的脸,以及一种令人作呕的气味,像蒜藤和腐烂的西猯。
奥伦是贝伦埃米利奥戈尔迪博物馆的鸟类学家和亚马逊生物多样性专家,他听完多斯桑托斯的叙述后,突然双手拢在嘴边,仰头大喊,希望马平瓜里能回应。无论他每天这样做多少次,仍会让随行人员不自觉地颤抖。他那响亮高亢的叫声音阶渐低,最终变成低沉的轰鸣声。寂静。接着,一声刺耳的声音。一只尖叫琵鹭(Screaming Piha),一种哨声酷似午休时建筑工人起哄声的鸟,回应了。但除此之外,再无其他。这支队伍——包括戈尔迪博物馆的技术员迪奥尼西奥·皮门特尔、曾多次陪同奥伦和皮门特尔来到这个地区的蒂亚戈·西帕亚、多斯桑托斯,以及来自巴拉的另外两名男子塞巴斯蒂昂·米兰达和路易斯·克劳迪奥·阿尔伯克基·门德斯——返回营地享用一顿新鲜捕获的西猯晚餐。
然而,似乎没有人感到失望。过去几周里,几位村民都报告说看到或闻到了这种野兽,而且在他们进入森林的第一天,男人们就发现了一组足迹:脚印长约11英寸,宽约5英寸,步幅约3英尺。这次考察还很年轻。而奥伦,为了他已相信的猎人、橡胶采集者和雨林中其他人关于马平瓜里真实存在的说法,冒着他的科学声誉,依然保持谨慎乐观。他知道是什么成就了传奇:将传奇带回来的人。
奥伦并非一直相信马平瓜里。20多年前,当他第一次来到巴西研究鸟类,为他在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进行研究时,奥伦听说了这种生物。他很快将其归入其他亚马逊神话之列:比如博托海豚的活动,它被指责为所有意外怀孕的罪魁祸首,因为它会化身为英俊男子,潜入乡村派对,引诱年轻女性进入花团锦簇的夜晚;或者库鲁皮拉(curupira)的变形,这种多变生物会以动物或毛发浓密、丑陋男人的形象出现,困扰着猎人。有些关于马平瓜里的传说同样充满幻想:它是一个老印第安人,因傲慢自大而寻求永生,如今被贬为永远在森林中游荡的恶臭、蓬乱的“bicho”(葡萄牙语中的野兽);它只有一只眼睛,喜欢烟草,并扭断人类受害者的头盖骨以吸食他们的脑髓。
但大约15年前,在反复听到马平瓜里的故事后,奥伦改变了看法。“我当时和一位朋友聊天,他说,‘大卫,你是生物学家,我是历史学家。这个生物会是什么呢?’”奥伦回忆道。“当我第一次仔细听了一个故事时,我才茅塞顿开。”在1994年戈尔迪博物馆的一篇专著中,奥伦提出假说,马平瓜里确实存在——或者最近才灭绝——它们就是最后现存的巨型地懒,是更新世的幸存者,隐藏在热带地区。这些庞大的生物——今天二趾和三趾树栖树懒的亲戚,但新陈代谢更快,因此速度也更快——大约在3000万年前出现,漫游于美洲、加勒比海和南极洲。它们是红毛食草动物,长着巨大的爪子,四肢行走时爪子会向内卷曲并向后,它们可以像人一样用后腿站立,有些物种有真皮骨,骨板使它们的皮肤坚韧。在古生物学的时间尺度上,巨型地懒仿佛昨天才消失。过度捕猎或气候变化,或两者的某种组合,在5000到10000年前的某个时候将它们灭绝。在奥伦看来,世界上最大的雨林——一个富含地懒化石的地区——仍然可能隐藏着这样的野兽,这似乎是完全有可能的。
奥伦不是第一个得出这个结论的科学家。19世纪末,一位名叫弗洛伦蒂诺·阿梅吉诺的阿根廷古生物学家,根据一份在巴塔哥尼亚南部看到奇特生物的目击报告,认为这表明一种活体地懒的存在。尽管阿梅吉诺从未找到他所寻找的证据,但他的推理在动物学家伯纳德·赫维尔曼的《追踪未知动物》一书中得到了详细描述。这本书于1955年出版,开启了神秘动物学——对隐藏动物的研究——并在多年前奥伦阅读时深深吸引了他。赫维尔曼在他的关于阿梅吉诺和巨型地懒的章节结尾处提出了一个引人入胜的关于亚马逊的问题:“它们是否仍然生活在这片‘绿色地狱’中,并将其视为一片和平的天堂呢?”
在那片绿色地狱里跟踪狂野的马平瓜里并不是打发时间的最佳方式。那里的地形潮湿、茂密、阴暗,并且充满了蜱虫、蜘蛛、蜇人蚁、疟疾蚊、黄蜂、非洲化蜜蜂、无刺蜂(但仍然能用力蜇人)、恙螨、黑蝇、白蝇(携带利什曼病),以及可怕的肤蝇。奥伦经历过所有这些,尤其是最后一种。他的左脚跟有一块硬币大小的疤痕,周围环绕着像静脉曲张一样的网状血管。一只肤蝇幼虫——可能通过蚊子叮咬的伤口进入皮肤——在他的脚上觅食了数周,长成了一英寸长的苍蝇,吃出了一套新的循环系统,并且从未像肤蝇幼虫通常那样保持静止或伸出呼吸管。“它是肤蝇中的雅克·库斯托,”奥伦说,“它有潜水肺。”
除了勇敢面对昆虫和许多其他艰难险阻,奥伦和团队还必须尽可能多地跋涉——有时一天步行长达九小时——试图寻找最近野猪经过的痕迹或踪迹。“这就像在没有磁铁的干草堆里找针,”奥伦坐在营地的黑暗中说道,消化着白唇西猯,搭配着昨日火烤散养凤冠雉的开胃菜。男人们讨论着明天的策略:既然他们已经找到了多斯桑托斯听觉遭遇的地点,团队将尝试找到他记忆中的一个水坑,看看那里是否出现野猪或马平瓜里的足迹。据多斯桑托斯说,团队在第一天发现的巨大脚印已经有一周历史了。他和皮门特尔尽可能地追踪它们,但足迹最终消失了。
自1994年奥伦开始在野外寻找这种生物的硬证据以来,这次巴拉之行是他的第六次马平瓜里考察。“如果把所有时间加起来,实际上还不到四个月,”他说。他从巴西Boticário基金会和一家小型电影公司获得了这项工作的资助;其余时间,他主要依靠他的戈尔迪博物馆工资,其中包括他从麦克阿瑟基金会和世界银行等机构获得的许多研究拨款。到目前为止,奥伦在这些搜寻中收集到的证据——一簇毛发、几个不同地区的粪便样本以及一些脚印石膏模型——都一无所获,像森林中的足迹一样消失了。毛发被证明是刺豚鼠的,粪便样本除了一个巨型食蚁兽的DNA外,没有发现任何DNA,而且正如奥伦坦率指出的,“石膏模型不具有任何科学分量,因为它们很容易伪造。”
有形证据的缺乏很难被忽视。“他是个怪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鸟类学家咕哝道。即使是一些支持奥伦这项探索的科学家,也难以将马平瓜里数据的匮乏与他对鸟类和生物多样性工作的严谨性协调起来。“他是一位顶尖科学家,”自然保护协会的罗杰·赛尔说,“但这就像你在电视上看到的所有那些东西:他们抛出所有那些预告片,然后你就会想,‘大卫,所有的确凿证据都在哪里?’”
其他科学家则更愿意相信。“如果你拒绝相信某物的存在,直到你在博物馆里亲眼看到一个标本,那这个世界将是多么贫瘠。我的意思是,有很多我们愿意相信存在而没有亲眼见过的事物,”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生物学家肯特·雷德福说,他提到了亚原子粒子和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对北约空袭科索沃的描述。“为什么不能是马平瓜里?大卫加油。我希望他是对的。”
奥伦信念的力量来自他收集的50多位目击者的第一手证词,他们都曾与这种生物有过接触。其中一位证人是马里奥·佩雷拉·德索萨,奥伦在前往巴拉的路上第三次拜访了他。德索萨住在伊泰图巴,他在公路部门打零工。在奥伦的轻柔引导下,德索萨再次讲述了这个故事——尽管这显然不是他最喜欢的回忆。他与马平瓜里相遇发生在1975年,当时他为贾马乌钦河(这条河汇入塔帕霍斯河,就在伊泰图巴以南)沿岸的一个采矿营地担任猎人。德索萨说,那个长毛的生物尖叫着,摇摇晃晃地用后腿朝他走来,摇摆不定,站立不稳。但他记得最清楚的,也是他声称再也没有踏入雨林的原因,是那种恶臭。“那可怕的气味进入我体内,让我头晕,”他说,“我足足有两个月不对劲。”
奥伦对轶事故事的依赖让许多研究人员感到不舒服。“我认为那是个骗局,”史密森学会研究员路易丝·埃蒙斯说,“如果你了解当地人,他们就喜欢戏弄任何容易上当的科学家。”尽管埃蒙斯对奥伦的搜寻很感兴趣,但她表示,亚马逊地区存在这种生物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博物学家已经在那里探索了几个世纪:“我从未听任何人提起过我们不知道的任何东西,尤其是一种大型动物。”
“我不认为他被骗了。我认为他很勇敢,”佛罗里达大学盖恩斯维尔分校的地理学家奈杰尔·J·H·史密斯反驳道。史密斯曾在亚马逊广泛旅行,收集民间故事和传说——包括关于马平瓜里的——他在其著作《被施了魔法的亚马逊雨林:来自一个正在消失的世界的故事》中对此进行了描述。“我们不必将当地知识奉为神灵,但有很多自然历史知识被科学家过于轻视了。我的意思是,25年前他们在巴拉圭发现了一种已灭绝的西猯。”
查科西猯(Chacoan peccary)也许是奥伦故事的最佳先例,因为这种生物在当地人中广为人知,但科学家花了很长时间才相信它或找到它。“那也是一种神话动物,”世界银行自然资源管理专家菲尔·黑泽尔顿回忆道,他曾帮助寻找这种生物。“我们周围有这种神话般的西猯,它的体型和一切都令人恐惧。”结果发现它是一种非常大的第三种南美西猯,被认为在过去几百年内已经灭绝。
即使在距离巴拉这样的定居点只有半天步程的雨林区域,也很容易想象,如果它选择隐藏起来,任何东西都能保持不为人知。在第一周的跋涉和艰难穿行于这片茂密的土地后,奥伦团队的挫败感与日俱增。尽管他们遇到了巨型犰狳的洞穴、貘的足迹和一群毛猴——这些都表明狩猎压力很低,该地区基本未受干扰——但那只蓬乱的野兽却未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叫声,也未留下可供收集的粪便。男人们又发现了一组巨大的足迹——同样大约是貘(雨林中最大的生物)的三倍大——但它们甚至比第一组还要古老。有一次,队伍经过一棵被美洲豹(onça)的牙齿和爪子划伤的树,这种生物即使是对在雨林中生活了一辈子的人来说也罕见。奥伦说:“这东西比美洲豹还稀有,”此时队伍再次蹒跚前行,沿着野猪留下的足迹继续前进。
马平瓜里为什么要与臭气熏天的野猪一起奔跑,原因尚不清楚。也许“它喜欢吃和白唇西猯一样的东西,”奥伦沉思道。“或者我错了,它是一种可怕的有袋动物,它吃白唇西猯。但我希望不是,因为那样它也会吃我们。”多斯桑托斯认为这种关联的原因很简单:“它是西猯的保护者。”
奈杰尔·史密斯认为,这种对马平瓜里的看法是亚马逊许多民间传说背后的基础。这位地理学家认为,关于马平瓜里或其他威胁性生物报复的故事,确保了森林社区不会耗尽资源。“许多传说都是为了用生动鼓舞人心的故事来娱乐听众而构思的,”他在《被施了魔法的亚马逊雨林》中写道。“然而,它们也间接减轻了对动植物生命的压力。”
这个解释也许也解释了奥伦的执着,他为何甘冒嘲笑和远征的艰辛:他热爱雨林,热爱巴西,这个他刚刚入籍的国家。奥伦不断谈论寻找广阔的马平瓜里,以便大片土地必须划拨出来保护这种生物。在巴拉附近的森林里,矿权归属于矿业公司CVRD,该公司随时可能决定砍伐树木,剥离红色的土地。在这里找到马平瓜里“将改变这一切,”奥伦说。
雷德福认识奥伦已有二十多年,当时他们还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他指出:“大卫选择将生命奉献给亚马逊的动植物。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坚信马平瓜里的存在,既是为了寻找一个强大的象征来表达保护亚马逊的必要性,也是因为他坚信这种动物确实存在。我认为他在这项探索中所表现出的热情,实际上是对亚马逊雨林持续生存的探索的热情。”
尽管充满热情,奥伦现在似乎对这次搜寻感到厌倦了。一天下午,在考察的最后几天,他回到营地,说他可能会放弃,让别人去雨林寻找这种生物。他说,他提出了自己的假说就足够了;这使得未来其他雨林访客在捕杀马平瓜里时更有可能将其上交。“如果我们这次不成功,我真的应该继续我的鸟类学研究了,”他叹了口气,“你因发表的论文数量而受到认可,而不是因你进行的徒劳搜寻数量而受到认可。”那天晚上,大雨倾盆,团队 huddled 在黑暗中的防水布下,拍打着蚊子,在飞蛾扑灭烛火后重新点燃蜡烛。
饱餐了米饭、豆子和木薯后,男人们在第二天早上7:30离开了营地;成群的黑蝇跟着他们。多斯桑托斯领着路,奥伦双手拢在嘴边,仰头再次呼唤马平瓜里,无论它身在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