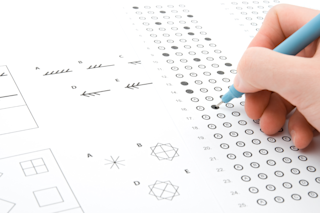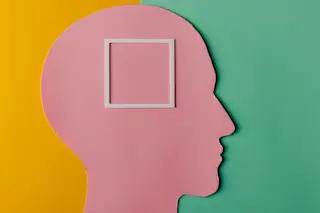什么是意识?它又是如何从大脑的物质中产生的?
几代人以来,这个思想领域一直由哲学家垄断。如今,神经科学家也纷纷投入到这个问题的研究中,他们借鉴实验发现以及历史、文学和哲学的思想。
为此,我们邀请了神经科学家兼神经科医生 Antonio Damasio 和小说家兼散文家 Siri Hustvedt 共同探讨意识、记忆、自由意志以及我们称之为“自我”的那个奇特而熟悉的观念。
Damasio 教授,他的情绪和决策的开创性研究有效地开创了现代情感神经科学,是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大脑与创造力研究所的 Dornsife 教授兼所长。他的新书是《心灵的自我》(Self Comes to Mind)(Vintage 出版社,2012 年)。
Hustvedt 于 2010 年出版的《颤抖的女人或我的神经史》(The Shaking Woman or A History of My Nerves)一书,从历史、哲学和神经科学的角度审视了她自己的癫痫病史。在对话中,他们深入探讨了心灵与大脑——以及艺术与人性的关系。
Siri Hustvedt: 当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英语学博士学位时,当时的学术界普遍认为语言创造意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对此产生怀疑。身体在哪里?我真实而鲜活的体验在哪里?我一生都饱受偏头痛的折磨,后来又患上了一种奇怪的癫痫症。我开始觉得生物学与性格和人类文化的繁荣密切相关,这也是我开始对神经科学产生浓厚兴趣的开端。
Antonio Damasio: 在西方的长期论述中,身体是缺失的。但身体当然至关重要。我们拥有的大脑和心灵是为了服务于有机体的生存需求。生命调节是大脑和心灵的主要职责,这被称为体内稳态。
Hustvedt: 我们所认为的“自我”,我们的主观性,受到无意识力量的影响。以 [本杰明·利贝特 20 世纪 80 年代的著名实验] 为例,这个实验在哲学家和神经科学家中引起了巨大轰动。利贝特让受试者移动手指,并在大脑中发现了所谓的“准备电位”。这个电位在受试者意识到自己要移动手指之前大约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秒就出现了。这引发了关于自由意志的争论:自由意志是否需要完全有意识的行为?如果你口渴,然后拿起一杯水,你对这个动作并没有完全有意识的语言表达。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自由意志。
Damasio: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自由意志,因为对我们人生中许多重要的决定,其做出方式与我们决定移动手指或拿起一杯水不同。重要的决定——比如我们将如何发展职业生涯或将与谁结婚——通常不是“临时”做出的。这类决定我们倾向于思考几分钟、几小时、几周或几个月;我们不会在采取行动的瞬间做出。我们是在“离线”状态下做的。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在思考时会向上看,望向天花板;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当下的感知图像就会与他们制定计划时形成的图像发生冲突。
Hustvedt: 你可以关注外部的事物,也可以关注你内心的叙述者,但同时关注两者是不行的。阅读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有时我会突然意识到自己正在理解文字,但我的思绪已经飘到了别的主题上。我与纸上的文字有某种认知上的联系,但它不是语义上的,不是消化意义上的。
Damasio: 令人着迷的是推理空间的局限性——即我们展示大脑地图的屏幕。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屏幕:视觉屏幕,但也有听觉、触觉、嗅觉的“屏幕”。大脑为每一种感觉都有离散的解剖学空间。毫无疑问,当你在听马勒的交响乐并同时观看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指挥时,你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屏幕空间(听觉和视觉)中产生感知印象。这些空间是如此独立,以至于它们似乎在你大脑的不同区域。
Hustvedt: 脑科学研究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所有这些信息是如何被整合在一起的?这通常被称为“结合问题”,因为我们有一种统一的世界视觉的主观感觉,但这种统一性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却不清楚。
Damasio: 这导致一些人错误地认为,大脑中有一个地方是所有这一切发生的地方。换句话说,因为我们对空间和时间的体验似乎是统一的,所以人们假设有一个唯一的“剧院”在处理这一切。目前,许多人最喜欢的“唯一剧院”是前额叶皮层,这个大脑区域位于额头后面。但对于任何持此观点的人,我有一个坏消息:即使我们的大脑前额叶皮层完全被移除,我们仍然可以拥有统一的感知体验。
Hustvedt: 大多数有内省能力的人都会意识到,经验是有层次的。以小说创作为例。你坐下来,在纸上出现了一个从某个地方涌现出来的世界——一个主要由无意识构成的精神地理。但艺术创作也取决于我们象征化能力。
Damasio: 这些分离的层次和多个世界依赖于大脑中不同的表现空间以及复杂的整合机制。它们还依赖于对一个人综合经验的记忆的形成以及后来的回忆。现在我能看到你脖子上的珍珠、你的深粉色毛衣和白色衬衫,以及你美丽的金发。同时,我能听到你的声音,并处理关于你以及你我所说的一些想法。所有这些过程都发生在我大脑的不同区域,但时序以及我们拥有一个统一的自我,将为我提供统一的时空体验。
我如何记录下这一刻的记忆?我们需要找到大脑中信号可以汇聚并编码事件同步性的系统。之后,汇聚的信号可以被重新激活并发送回它们最初的区域,从而重建一个更模糊的原初体验版本。我相信记忆就是这样运作的。当我们脑海中响起一段旋律,并回忆起当时与我们在一起的人以及上次听到它时的地点时,我们就是利用这种汇聚-发散框架来重建构成原初片段的碎片。
这个框架非常经济高效。你不需要记录下每天与每个人经历的每一件事、读过的书、看到、听到、触摸到的事物,你只需要记录事件各方面的组合。如果明天我记得今天和你谈话,我将重建我们谈话的一些方面,当然,这种回忆会与原初经历相关。但我不会重现一个逼真的记忆副本。我将把这个经验的碎片拼凑起来,它们将重建这个瞬间的某些部分,但重建过程不会完全准确。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甚至可能会产生混淆的回忆,并说你当时穿着一件蓝色的毛衣。
Hustvedt: 我们的大脑和记忆不像录音设备,不像电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时会犯下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可能由经历所附带的情绪引起。根据你的动机,你甚至可以颠倒记忆——创造它的反面。我说的不是有意识的动机,而是一种深刻的、内在的驱动力或冲动,它具有强大的情感效价,然后改变记忆。情绪也能巩固记忆。我们会记住对我们有意义的事情,而忘记那些我们漠不关心的事。
Damasio: 当人们在法庭上作证时,他们会犯各种错误,也会颠倒时间顺序,因为记忆不像电影媒介。我们的大脑不像使用带有光学音轨的赛璐珞胶片。我们拥有的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编码机制。顺便说一句:我们拥有的记忆不仅包括我们出生以来所经历的事情。我们还拥有通过我们之前的整个进化历史继承而来的过去记忆。我们拥有我们祖先所做的事情的记忆,我不仅仅是指人类的祖先,而是指从爬行动物一直追溯到单细胞生物的祖先。
Hustvedt: 意识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
Damasio: 我对意识的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我曾经认为意识是进化的晚期发展,是一种能够进行高级思维和推理的属性,并且主要属于人类,尽管并非完全如此。但现在,我认为意识在许多其他物种中广泛存在——例如,在所有哺乳动物、鸟类和爬行动物中。意识的先驱可以在非常简单的生命形式的管理生命过程中找到。以细菌细胞为例,它们甚至可以进行社会组织。在没有任何大脑或神经系统的情况下,细菌可以感知群体中有多少同类——这被称为群体感应(quorum-sensing)——并根据它们共享的集体信息决定是否发动攻击。在某种程度上,它们通过行为回答了一个尚未提出且复杂的问题,例如“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兵力来争夺这片领土?”
Hustvedt: 细菌有驱动力,但它们没有反思性的自我意识。它们无法在做某事的同时“看到”自己在做什么。它们无法想象明天会是什么样子,也无法明确报告上周做了什么。人类拥有投射能力,这种将自我投射到时间(过去和未来)的能力是想象力的核心。想象领域不能脱离其神经生物学根源,但没有它,我们就不会有文化。
Damasio: 凭借我们复杂的大脑,我们进化出了将意识过程投射到完全不同维度的能力。
Hustvedt: 法国现象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提倡“具身意向性”,它远不止是“关于”的自我意识。它植根于生物学过程,但又向上延伸,扩展到我们识别镜子中的自己、想象自己是别人、怀有对未来的幻想、创造虚构作品和艺术的能力。所有意识过程的底层都是无意识过程或驱动力。狗、猫,甚至蜗牛都有意识——它们醒着,有感知,并且会记住——但它们不会在镜子里认出自己,也不会从其他角度想象自己。它们不会假装。假装似乎是人类独有的能力。
Damasio: 作为有意识的个体,我们可以创造新事物。我称之为“社会文化体内稳态”,因为它针对复杂系统(在这种情况下是社会)中的一个问题,以便系统尽可能高效地运行。道德规则和法律就是如此,它们旨在遏制危险行为,这些行为会损害个体和群体的功能。宗教和艺术是恢复性的努力,通过促进个体和群体的平稳运行来实现体内稳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