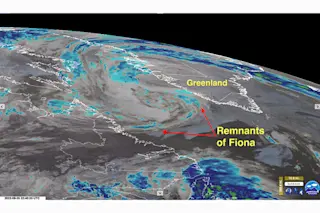很少有船只敢于冒险进入德雷克海峡,这是一片位于智利南部峡湾和南极半岛顶端之间500英里波涛汹涌的海域。在这些纬度,除了冰冷的海水,四周一望无际。没有陆地阻挡风的吹袭,船只可能会遇到两层、三层甚至五层楼高的巨浪。航海船员认为这里是地球上最危险的海域。
今天下午,德雷克海峡名副其实。近乎飓风强度的狂风将不断增大的巨浪拍打在“纳撒尼尔·B·帕尔默”号考察船上,甲板下的科学家们手忙脚乱地绑牢电脑终端,用气泡膜包裹实验室设备。船只右舷,一连串庞大的巨浪排成一线,每个都准备好向船只猛烈一击。甲板上的船员被冰冷的浪花和雪击打,像醉汉一样摇摇晃晃。冰弹般的袭击呈水平方向,如此猛烈,以至于我无法睁开眼睛超过一刻。但在那一刻,我不幸瞥见了身后狂怒的海洋。我曾读到过,在这样的海域,人们会溺水,因为空气中被风吹起的巨量海水,即使你能够将头保持在水面之上,也无法呼吸。当然,如果没有任何防护服的保护,在这冰冷的海水中,你在一分半钟后无论如何都会失去知觉。
在驾驶甲板上,二副保罗·亚基维奇(Paul Jarkiewicz)讲着故事。他回忆起一次凶猛的巨浪,曾经把整个海图桌从支架上抛开,沿着走廊摔了出去。有一次,海洋项目协调员被发现在船尾甲板上,紧抓着设备,双腿被风吹得笔直,像一面旗帜在风中飘扬。最终,他的谈话自然转向了每一个冒险进入这片水域的水手心中潜藏的恐惧:巨浪情景。在海上风暴中,风驱动的海浪会与风向垂直排列。舵手可以操纵船只迎面应对海浪,船头正对着风的中心。或者他可以操纵船只以45度角“斜迎”海浪。船只就是设计来承受这种方式的海浪的。但是大约每10,000个海浪中就有一个不按常理出牌。这种所谓的巨浪会从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方向,从侧面或船尾向船只袭来。“巨浪袭来,会把船的龙骨折断,”亚基维奇一边摆弄着雷达控制装置一边说,“船会在几分钟内沉没。你也会。”
那么,冒着船员被卷入海中、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船只沉没的风险,到底进行的是什么样的科学研究呢?什么能比“纳撒尼尔·B·帕尔默”号上60人的生命更重要?简而言之,是地球的未来。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这次航行的最终目标是收集全球变暖的线索。但更直接的目标是关于南极洲的区域性变暖趋势。没有人确切知道这种趋势对世界其他地区意味着什么,但南极半岛的西侧变暖速度比地球上任何地方都快。与仅仅半个世纪前的气候记录比较显示,这里的气温平均上升了2.5到3摄氏度。在1966年至1989年间,占地502平方英里的沃迪冰架大部分消失了。而在过去18个月中,半岛上最大的两个冰架——拉森B冰架和威尔金斯冰架,已经失去了近1,100平方英里的总面积,这片冰层大约相当于罗德岛的大小。这比过去10年的平均年损失量高出5到10倍。照此速度,威尔金斯冰架的大部分将在几年内消失,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冰川学家特德·斯坎博斯(Ted Scambos)说。“没有人预料到它会发生得这么快。”
尽管很少有科学家仍然否认全球变暖正在发生,但目前还没有人知道其中有多少——如果有所谓的——是由于周期性自然温度循环造成的。这个关键问题的答案在于遥远的过去。要找到这些答案,就必须追溯并研究数百甚至数千年前的温度变化。一种方法是研究长期埋藏的、有数百年历史的海洋沉积物:海底的泥土。
因此,一支海洋沉积物专家团队在“纳撒尼尔·B·帕尔默”号上安营扎寨,希望能将巨大的空心取芯器深深地沉入南极洲附近的海底。这是一次他们中一些人已经进行了十多年的朝圣之旅。这种研究没有什么是容易的——无论是到达那里,还是进行研究。在国家科学基金会极地项目办公室的资助下,科学家们将在船上度过两周。如果一切顺利,他们将打捞出10、20和80英尺长的绿色泥浆柱。这将告诉他们他们正在寻找的故事:古代气候的故事。因为海底是一个记录,是数亿年来所有沉入海底的水下物质的积累。
沉入海底的物质部分取决于气候的温暖程度。当气温足够低,形成延伸到南极陆块和海洋的冰架时,大部分沉降到海底的是冰川在从大陆冰盖缓慢行进过程中带起的沙子和砾石。沙质海洋沉积物与冰盖相关联,当你发现它在远离冰缘的地方时,你就知道冰在某个时候到达过那个地方。当天气变暖,海上没有冰时,海底的沉积物主要是有机物:浮游生物和硅藻的残骸。通过解读岩芯中有机和无机沉积物的上下波动,沉积学家可以追踪过去2万年冰的进退。到目前为止,格陵兰的冰芯和南极的海洋沉积物岩芯显示,在3000到8000年前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暖期。没有人确切知道变暖的原因,但研究人员怀疑地球轨道上的轻微晃动可能是原因。这种晃动可能改变了地球的位置,这可能改变了海洋环流和气候模式。
研究人员更确定是什么正在推动当前的变暖趋势。作为这次航行首席科学家之一的科尔盖特大学海洋地质学家艾米·莱文特(Amy Leventer)说:“我认为很明显,一部分原因在于太阳。但我认为也毫无疑问,一部分原因是人类造成的。”
昨天的风暴已经过去,留下了超凡的寂静,只有雪海燕的叫声和发动机低沉的轰鸣打破了它。我们已经抵达穆勒冰架的入口,靠近拉勒曼峡湾。对于那些认为南极洲只有单调的白色和灰色的人来说,拉勒曼峡湾是一个令人惊醒的景象。今天早上拥挤在船只周围的冰山充满了油漆店般的各种蓝色,其中许多异常不自然,就像漱口水和马桶清洁剂那种明亮、刺眼的蓝色。令人眼花缭乱的不仅仅是色彩的种类,更是其强度。颜色似乎来自内部,就像闷烧的煤块发出的光芒。这是一个巧妙的视觉技巧:随着时间的推移,冰被压缩,光线更容易穿透它。几乎所有人都站在甲板上,望着冰。
并非所有人都对它抱有好感。来自纽约克林顿汉密尔顿学院的沉积学家、本次考察的另一位首席科学家吉恩·多马克(Gene Domack)就是一个例子。去年,他和研究生艾萨·冲(Asa Chong)在这里的水中设置了一系列海洋沉积物捕集器,计划于今天早上回收。“冰架已经覆盖了捕集器,”多马克说,几乎咬着自己的小胡子。冲的捕集器被故意放置在冰架边缘附近。如果你打算研究冰架在数千年间的进退,你需要能够识别冰缘独特的沉积物剖面。对一年沉积物(通常约7到12英寸)的更详细熟悉也有助于科学家解释更长岩芯的时间表。
结果,冰架并没有覆盖那些捕集器。但是,巨大的冰块,有些像公共汽车大小,已经从冰架上崩裂下来。驾驶船只绕过这些危险的巨冰而不与之相撞是件棘手的事情。船员们利用去年航行中获取的全球定位系统测量数据,进入位置,通过声纳确认捕集器的位置。一旦捕集器被精确定位,船员们就会尝试用从船尾放下的一根抓钩将其钩住。接下来的半小时,船只缓慢地向前和向后行驶,就像警车拖曳尸体一样。最终,那些看起来像颜色鲜艳的倒置交通锥的沉积物捕集器被钩住并打捞上船。
多马克从4号捕集器中取出样品,指着透明塑料圆柱中深棕色和浅棕色像冰淇淋圣代般的层理。“看那些年纹!”一位研究生惊叹道,欣赏着这些季节性层理。这些带状物共同构成了冰缘一年份的日历指纹。
几天后,“纳撒尼尔·B·帕尔默”号抵达天堂湾。在甲板上,在南极清澈的阳光下,躺着昨晚的巨型活塞取样器的残骸:一段10英尺长的管道,现在弯曲得像大象的象牙。它从船舷放下时是笔直的。显然它撞到了一个坚硬的地方。当船员们上岸短暂休息时,多马克独自留在船上,仔细查看下一目的地的声纳地图。这张地图帮助他精确地决定在哪里沉下取样器。由于没有现成的该区域海底地图,“纳撒尼尔·B·帕尔默”号一直在生成自己的地图。船上配备了SeaBeam系统,它会像割草机一样在区域上反复扫过,同时将声纳信号从海底反弹回来。这项技术最初由军方在20世纪60年代开发,用于精确识别潜艇位置,使海洋学家能够像绘制月球地图一样详细地绘制海底地图。
多马克指着上周一张地图上一个杏仁大小的浅蓝色区域。“我们正在寻找像这样的狭小区域。”这些地点比该地区大部分海架都要深,使它们免受冰山拖曳底部的影响,在那里它们可以保持数千年不受干扰。这个区域也没有一直深到底部。“大盆地会捕获所有从海架周围高地冲刷下来的沉积物,”多马克说,“这会使信号非常嘈杂。”多马克想要的是一个清晰的信号,为此,他需要取出一个只反映正上方水柱中沉降物质的样本。SeaBeam地图旁边还有一个读数,显示海底以下沉积物层的横截面。为了避免像昨晚巨型岩芯弯曲那样的状况,科学家们会寻找更柔软、压缩程度更低的沉积物。多马克指着读数上一个半英寸宽的明显条纹:我们的目标。
一旦我们靠近目标点,需要六名工人花费六个小时来组装和发射一个取芯器。这项任务既危险又脏乱,而且非常耗费体力。八根200磅重的钢管被运到船舷栏杆处,并连接在一起,形成一根80英尺长、5英寸宽的管道。然后船长发布了暴风警告:海况恶劣,风速30到40节。雪花在船灯下盘旋,浓密得像蚊蚋。天气预报让每个人都紧张不安。如果风速达到35节,海洋项目协调员巴尼·凯恩(Barney Kane)将命令所有人进入船舱。
今晚是多马克和莱文特最后一次尝试80英尺岩芯取样。明天我们将返回智利。管道段终于连接起来了,现在是时候滑入塑料内衬段了。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这些将在四小时后取出,像香肠皮一样塞满了A级橄榄绿色的南极泥浆。前两段很容易进入。到第八段时,前七段的合计重量已经让三名男子齐心协力地搬运。他们看起来就像硫磺岛上插旗的士兵。风正猛烈地拍打着海浪。雪下得如此之大,看起来就像好莱坞片场被风扇吹出的暴风雪。
与此同时,在甲板的另一端,船员们正在打捞一个12英尺长的箱式岩芯。由于巨型活塞岩芯的冲击会把顶部几英尺的泥土炸开,因此会派一个更小、更温和的岩芯下沉,以获取未受扰动的顶部几英尺泥土。箱式岩芯也是一次预演:如果它打捞上来时装满了泥土,就表示可以进行巨型活塞岩芯取样。箱式岩芯顶部从海中浮出,水从侧面的两个小孔中流出:这是一个不好的迹象。当岩芯被打开时,人群围拢过来;一坨可怜的绿色泥土掉到甲板上。从一顶破旧的安全帽下,莱文特看着,与其说心烦,不如说筋疲力尽。她在过去的24小时里已经工作了19个小时。“我们没有时间再打捞一个箱式岩芯了,”她说。“天气变得非常糟糕。”她示意甲板船员继续进行巨型活塞岩芯取样。“如果失去了它,那就失去了它。”
起重机将管道从栏杆上吊起,船员们将其推出足够远,以避开船体。随着快速释放装置的一拉,管道摆入海中。然后通过绞车和缆绳下降了2000多英尺。距离海底约10英尺处,一个触发取芯器触底并释放主取芯器,主取芯器剩余部分依靠重力落下,埋入泥中。在拉出过程中,操作转移到船尾控制绞车站,那是一个甲板上方的窗户环绕的办公室。一个视频监视器显示着绞车缆绳承受的压力——13000磅并且还在增加。首席工程师戴夫·门罗(Dave Munroe)一边看着缆绳读数一边摆弄着一个螺栓。“我见过它断裂。它在船侧撞击的地方留下了一个大大的S形。”半小时后,取芯器头部从甲板侧面冒出。它像泥浆摔跤手一样全身裹着绿色粘液。笑容浮现,如释重负。船长和多马克握手。多马克说,这是从南极大陆架上回收到的最长的岩芯。
终于,我们踏上了归途。南极洲在海平线上化为一条逐渐缩小的白色带。多马克站在甲板上,从整理实验室的工作中抽身休息。沉积物岩芯已堆放在科学冷藏室中,不久将运往佛罗里达州的分析和储存设施。初步的船上磁性剖面分析让多马克喜上眉梢。它们不仅验证了1992年完成的更大岩芯,而且提供了某些关键气候变化的更详细记录。“现在我们将能够了解这些气候转变发生的速度有多快,”多马克说,“以及造成这种环境变化的过程是什么。”船只在涌浪的波谷中低低地俯冲。那一刻,只有天空和海洋。在公海上航行,某种程度上唤起了一种人类与地球的连接感。我想象着,这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多马克和莱文特工作背后必须存在的紧迫感。我转身想问多马克这个问题,但他已经离开了,回到了他的箱子、地图和数据日志之中,这些小小的东西也许有一天能拯救这个大大的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