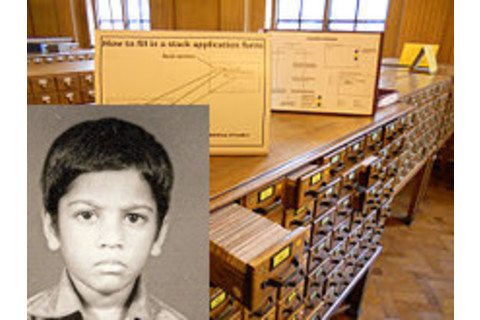
我足够老,还记得卡片目录。它们并不能让我开心。小时候,我经常注意到遗漏和分类错误,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会刻意避开目录,然后通过繁琐的手动浏览,系统地阅读我喜欢的公共图书馆中整批的书籍。我也足够老,还记得互联网在数据组织和存储容量方面仍然很原始(即谷歌、维基百科之前的时代),而图书馆是检索数据的第一、最后也是最好的选择。1995年《勇敢的心》上映时,我跑到当地的大学图书馆,想看看能否找到比《大英百科全书》中更多的关于主人公生平的信息。碰巧有一本关于威廉·华莱士生平的书,**但这已经被借走了,而且在我之前还有十几个预约!**在数据丰富的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前,这种情况并不少见。现实是,关于华莱士我想知道的信息很可能在他的维基百科条目中,但那时还没有维基百科!这些只是我对尼古拉斯·卡尔这样的新卢德分子几乎没有耐心的几个原因。当我读到卡尔的“老古董”式的抱怨时,我总是想,“孩子,你当年见过那些日子吗?”*当我在第九届湾区人口基因组学会议(BAPG IX)**的观众席上时,这个念头就出现在我的脑海中。该会议由斯坦福大学的迪米特里·彼得罗夫(Dmitri Petrov)创立,汇集了彼得罗夫所在机构、伯克利、UCSF和UC Davis等从事人口遗传学和基因组学交叉领域研究的研究小组(这次我注意到相当多的UC Santa Cruz的成员,所以我怀疑它越来越受欢迎)。BAPG会议说明了一个事实,即互联网以一种协同而非对抗的方式改变了我们沟通和消费信息的方式,而不是与传统的面对面交流相对立。会议的核心要素在1990年的人们看来是熟悉的(或许可以用投影胶片代替PowerPoint?),即演示和海报。**但这两种信息的核心都被嵌入到一个更丰富的传播和分发模式的框架中。**我第一次听说BAPG是通过电子邮件通知。毫无疑问,许多人通过Twitter和博客了解到了它(这可能触发了口头传播或电子邮件)。人口基因组学领域的知名研究人员,如迪米特里·彼得罗夫(Dmitri Petrov)、格雷厄姆·库普(Graham Coop)和卡洛斯·布斯塔曼特(Carlos Bustamante),拥有强大且易于访问的互联网平台,所以你可以直接了解到他们的实验室在做什么。由于信息的传播便捷,像BAPG这样的会议可以以极低的开销快速组织起来,而且会议的进展也经常在Twitter上实时转播。然而,BAPG会议“面对面”进行的事实反映了两种现实。其中一个世俗的现实是,由于伯克利-斯坦福轴线以及私营基因组学相关公司的集中,这种会议可能只在旧金山湾区才可行。***但更深层次的真相是,即使是像人口基因组学家这样习惯于计算和信息技术的学者,也仍然受益于面对面的人际交往。他们是人。尽管人们担心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电脑(会议上随处可见!)的普及及其对社交互动的影响,但现场却进行了大量的旧式畅所欲言的交流。**WALL-E**不是真实的。至少现在还不是。人的因素无法被消灭,只能被改变。不幸的是,人的兴趣的稀缺性往往是缺陷所在,而不是技术。当我听凯莉·哈里斯(Kelley Harris)关于基因组突变分布的精彩演讲时,我想到了这一点。利用1000 Genomes数据,哈里斯发现点突变并非随机分布;它们会聚集。而且,它们在**倒置突变**与**转录突变**的比例上表现出出乎意料的模式。正如我所说,这些是非常有趣的结果。但我想知道,为什么是哈里斯发现了这一点。作为一名哈佛和伯克利培养出的数学生物学家,她显然具备一定的技能和才能,但并非没有湾区许多地方(如谷歌)的能干的思考者,他们可以在业余时间做同样的事情。数据就在那里。这让我想起我与一位非常著名的统计遗传学家在剑桥的一次谈话。他想知道,为什么世界各地聪明的头脑没有挖掘出他研究小组可以免费获得的相同的数学和计算财富。**我认为这里的问题在于人,而不是技术对人的影响**。正如《月球人》等著作中所述,似乎
**那些有闲暇和意愿从事智力追求的人的精力会受到时尚和文化**时代精神
的支配。问题不在于技术。技术被人们使用,以服务于他们的利益和偏好。如果你对人性的偏好有问题,那就和人类去解决,不要因为人类的罪过而审判技术。*我在开玩笑,因为我知道卡尔比我年纪大。**为了让您开心。主题演讲者正在快速地说出一系列人口遗传学参数。所以,在我正前方的那个人正在拼命地搜索谷歌,大约30秒钟,他就在浏览我的一个博客条目!我曾想拍拍他的肩膀,告诉他作者就在他身后,但我没有这样做。***我知道现在有一个南加州地区类似的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