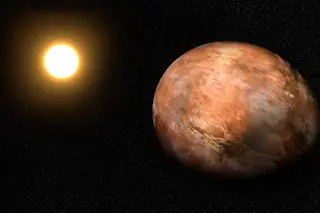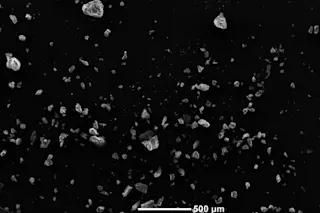美国人在太空经历过不少紧急情况,从阿波罗13号到航天飞机门打不开,但去年在和平号空间站发生的事情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俄罗斯宇航员及其美国客人遭遇了如此多的问题,包括可能危及生命的火灾和气压泄漏,以至于这一年仿佛变成了一场持续不断的危机马拉松。
1993年,当美国和俄罗斯决定在新的国际空间站上合作时,将美国科学家宇航员送往1986年开始运行的、可靠的和平号空间站进行“留学”项目,似乎是个不错的想法。除了学习如何在零重力环境下保持健康,人们还希望宇航员能领会长期任务的文化,并且,谁知道呢,也许还能学到俄罗斯人在面对突发事件时那种传奇般的镇定。在和平号上,美国宇航员被告知要专注于他们的研究,不要干涉操作。而这一切,就是新年开始时的状况。
事故始于2月,一个用作备用氧气的罐子着火了,浓烟和有毒气体充满了空间站,并喷射出熔化的金属块。灭火器不起作用,机组人员眼睁睁地看着火焰自行熄灭了14分钟。尽管和平号在1994年也发生过类似的火灾,但这次要糟糕得多:两英尺长的火焰威胁要烧穿铝制船体,并阻碍了通往当时对接在空间站上的两艘联盟号飞船之一的逃生路线。几个月过去了,官员们仍然无法解释氧气罐为何会着火。
随后在3月,和平号的主氧气发生器发生故障。4月,由于冷却剂开始泄漏到大气中,机组人员不得不关闭空气净化系统;有一段时间,舱内温度高达近90度。此时,莫斯科的任务控制中心开始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记者们争相采访俄罗斯航天局那些脾气暴躁的官员。和平号的指挥官瓦西里·齐布利耶夫也获得了一些宣传。大约在这个时候,人们普遍得知他随身携带一只塑料兔子,并且喜欢咨询他的占星师。
然后,在6月25日,发生了主要事件。齐布利耶夫正使用操纵杆对接无人货运飞船“进步号”与和平号。这个过程本应是例行的,但齐布利耶夫在没有使用和平号雷达的情况下进行了操作。和平号雷达通常会显示飞船的距离、接近速度和角度。任务控制中心担心从位于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雷达工厂获取备件,并且万一当前单元出现故障,他们认为机组人员应该学会如何在没有雷达的情况下对接“进步号”。
关闭雷达后,齐布利耶夫依靠安装在“进步号”上的摄像机进行整个对接操作。他发现自己面对的是和平号,背景是移动的云层,这可能分散了他的注意力。此外,那天“进步号”飞船比平时要重,制动推进器的压力也比平时低。考虑到这些因素,齐布利耶夫比平时多点燃了一会儿制动推进器——但还是出了问题,飞船未能停下。机组人员听到一声巨响。几秒钟后,他们感到耳中传来可怕的减压拉扯感。
碰撞损坏了和平号的六个舱段之一——“光谱号”的船体。“光谱号”恰好是当时美国访客迈克尔·福尔的实验室和睡眠区。几分钟内,一旦机组人员封锁了通往“光谱号”的舱门,最初的危机就结束了。但这也就意味着切断了它连接到空间站其他部分的太阳能电池板,使和平号的动力减半。
事故并未结束。7月16日,宇航员亚历山大·拉祖特金意外断开了电源线,导致和平号计算机关闭,陀螺仪失灵,空间站缓慢旋转,太阳能电池板无用地指向黑暗的太空。8月5日,唯一工作的氧气发生器发生故障,迫使机组人员再次依赖备用罐。在这一切混乱中,俄罗斯人正在权衡如何以及何时修复碰撞造成的损坏,这需要一次棘手的内部太空行走,进入黑暗、冰冷的“光谱号”,以及由谁来完成。原本镇定自若的齐布利耶夫——在危机初期他的反应是哭着说:“谢天谢地,我们还活着!”——在这次磨难中精疲力竭。由于心律不齐(很可能是极度压力所致),他被认为不适合进行维修。
8月派去的新机组人员也日子不好过。飞船的计算机又几次发生故障。即使是8月22日成功的“光谱号”维修任务,也因为一名宇航员的手套漏气而蒙上了阴影。9月15日,一枚美国军用卫星飞近和平号500至1000码,迫使机组人员再次躲进联盟号飞船,以便在发生碰撞时能够迅速撤离。
事态稳定后,互相指责开始了。回到地面,齐布利耶夫因他在这次惨败中的角色,受到了俄罗斯媒体和他在星城(宇航员训练中心)的上级的严厉批评;他作为宇航员的日子很可能结束了。他反过来将和平号的困境归咎于俄罗斯基础设施的崩溃。他说,不仅备件难以获得,而且通信卫星的故障迫使宇航员只能在空间站经过俄罗斯上空时进行棘手的操作,即使这意味着打乱他们的夜间休息。
不管是否情愿,到了秋天,NASA已经从一个客户更多地变成了和平号的合作伙伴。宇航员承担了更大的操作角色——例如,福尔曾一度被考虑作为齐布利耶夫的替代者,负责重新连接“光谱号”的电缆,这在几个月前是不可想象的。莫斯科现在在重大决策上咨询NASA。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对新安排感到满意。众议院科学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詹姆斯·森森布伦纳(James Sensenbrenner)认为和平号早就该报废了,并抨击NASA官员危及美国宇航员的安全。NASA毫不退让。NASA“航天飞机-和平号”项目副主任詹姆斯·范·拉ak(James Van Laak)说:“人们对和平号的设计寿命为五年议论纷纷,但事实是,和平号的认证寿命是五年——就像航天飞机最初只认证了十次飞行一样。其中大多数都飞了二十多次。如果我让一个工程师设计并认证一个能在太空中运行25年的硬件,他会说:‘我不知道怎么做。我会尽我所能设计它能在25年内运行,但我只能认证它五年,五年后我们将需要重新评估。’这正是俄罗斯人设计和平号的方式。就在森森布伦纳的听证会之后一周,9月下旬,该机构派出了第六名乘员大卫·沃尔夫(David Wolf);并计划在1月下旬用安迪·托马斯(Andy Thomas)接替他,后者是最后一批计划访问和平号的美国宇航员。
NASA认为,虽然在和平号上的这一年充满惊险,但它是一次宝贵的经验教训。范·拉ak说:“虽然宇航员在紧急情况发生时可以随时降落航天飞机,但这在空间站上通常不是一个选项。空间站上的情况更像是一艘在海上航行的船。你必须处理危机直到结束。跳进救生艇回家当然是一个选择,但由于飞船的价值,这只能是最后的手段。这些因素渗透到空间站的设计和操作以及机组人员接受的训练中。”
今年的一系列事故会不会预示着国际空间站的生活?国际空间站的首批部件预计将于明年6月在太空中发射和组装。国会图书馆的空间专家玛西娅·史密斯(Marcia Smith)说:“在新的空间站上,就像在旧的空间站上一样,可能会发生和平号上发生的那些事情。这是载人航天的一部分风险。”事实上,NASA预计国际空间站的硬件故障会比和平号多,因为它会更加复杂。范·拉ak说:“我保证,这些问题中的一些将在国际空间站上以某种形式出现。当事故发生时,宇航员们只能设法应对。我们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