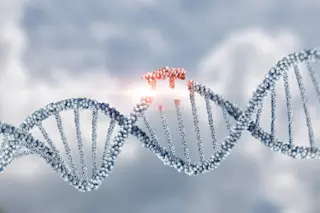肖妮·梅迪纳是个快乐的女孩,但总觉得自己会英年早逝。
当她还是库莱布拉的一位年轻姑娘,以及在阿拉莫萨成为一位年轻妻子时,人们首先提到的总是她的美貌。照片和零星的录像片段并不能完全捕捉到这一点,因为人们谈论的根本上是她的个人魅力。当你站在她面前,看着她甩动那一头浓密的黑发,全神贯注地与你交谈时,这种魅力便透过她的容貌展现出来。然后,她的美貌仿佛成了一个锚点,她其他的外部特质都由此发散开来,就像海中海带的叶状体随波摇曳。那时的肖妮充满磁性,爱美,待人和善,笃信宗教,有趣,有点傻气,而且固执。

iStockphoto
正是这种固执或者说不讲道理的品质,被阿拉莫萨和丹佛的医生归咎为她的死因——因为肖妮对于自己英年早逝的预感是正确的。她的细胞里携带一个危险的基因突变,28岁那年,在拒绝了针对她侵袭性遗传性乳腺癌的手术后,她去世了。她珍视自己的身体,却对那个基因一无所知,坚持要另一种治疗方式。
肖妮·梅迪纳在科罗拉多州的圣路易斯山谷长大。她的家庭是西班牙裔,是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他们比北美的其他西班牙裔更古老,自称在新墨西哥州北部和科罗拉多州南部有400年的历史。他们的村庄点缀在格兰德河北段,曾经像东欧的犹太人定居点一样充满活力又与世隔绝。
肖妮遗传的这个基因,被称为BRCA1.185delAG,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在西班牙裔社区的发现,证实了半个世纪前在西班牙发生的事件至今仍在回响。这个突变最有可能的来源是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时期,在压力下皈依天主教的塞法迪犹太人。他们从西班牙来到新大陆,最终在那里孕育了现代的西班牙裔人口。印第安血统和新的土地抹去了那些移民所携带的部分历史,前提是他们自己还意识到自己的犹太遗产。对于新墨西哥州北部和科罗拉多州南部的西班牙裔天主教徒来说,犹太血统就像是记忆和文化中一缕捉摸不定的鬼火,许多人听说过,却不知真假。肖妮的突变证明了这是真的。
乳腺癌突变185delAG大约在2500年前进入犹太人的基因库,时间大约在他们被流放到巴比伦的时候。这个突变随机且不请自来地出现在某个人的染色体上,这个人被称为“奠基者”。科学家们称位于遗传金字塔顶端的人为奠基者,这和亚伯拉罕被认为是犹太民族的奠基者是同样的道理。这位特殊的奠基者生来就在其一个BRCA1基因拷贝的185位点上,缺少了DNA链中的字母A(腺嘌呤)和G(鸟嘌呤)。BRCA1是一个肿瘤抑制基因;这两个字母的缺失使其保护功能失效。但这个突变对奠基者本人并无即时危害,因为他或她还有另一个正常的基因拷贝在工作。
研究人员不知道这位奠基者是谁,但他们可以根据历史证据推断出他或她生活的年代。当犹太人被允许在巴比伦之囚后返回耶路撒冷时,并非所有流亡者都回去了。那些留下来的人是伊拉克犹太人的祖先,他们的人数如今已大大减少,但几个世纪以来曾是信仰的一个重要中心。除了生活在美索不达米亚和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中东其他地方也出现了卫星般的移民社区。基因库的分散化已经开始,群体之间的距离成了DNA交流的障碍,这些障碍一直持续到现代。当以色列的科学家测试来自这些分散的犹太人群体的BRCA1携带者时,他们发现所有人在185delAG基因区域都有相同的基本拼写。但是一些犹太群体之间的匹配有一两个字母的差异,这表明自群体分离以来发生了微小的变化。通过倒推人口统计学的时钟,科学家们推断,其奠基者必定生活在这些群体分裂之前——也就是在巴比伦分水岭之前。
鉴于185delAG突变起源于犹太人,科学家们认为,当这个突变出现在另一个民族或种族群体中时——比如肖妮·梅迪纳的西班牙裔——那是因为有犹太人或其后代与之通婚。在犹太人范围之外,185delAG的踪迹很少。医学文献中有零星报道,在西班牙、智利、斯洛伐克、荷兰、巴基斯坦、印度,甚至非洲都有非犹太携带者,但这些地区大多数现在或曾经都有犹太人聚居区。有许多美国携带者并非犹太人,但这些人,就像梅迪纳家一样,很可能至少有一些犹太血统。
所以,这个基因跟随着肖妮从巴勒斯坦到伊比利亚半岛,在犹太人被驱逐出西班牙后又到了墨西哥,然后从墨西哥沿着蜿蜒的格兰德河而上,最终在偏远、群山环绕的圣路易斯山谷追上了她。1998年,肖妮住院且生命垂危时,被建议进行BRCA检测。她的父母约瑟夫和玛丽安动用了他们所剩无几的积蓄,支付了2800美元的分析费用,这笔费用不在她的保险范围内。“嗯,”遗传咨询师说,“你的女儿是185delAG的携带者……但那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突变。” 这是在该突变与西班牙或塞法迪犹太人建立联系之前的事了。
考虑到肖妮当时的情况,梅迪纳夫妇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这项检测对病人本人已无用处——它本是给女性亲属的癌症警报,但要么是这个信息没有被正确地传达给家人,要么是他们没有领会。
最初来自中欧和东欧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是世界上人数最多的犹太人群体。有五百五十万到六百万美国人有阿什肯纳兹血统。在他们不得不面对遗传性乳腺癌及其主要元凶——BRCA1.185delAG突变之前,上一代的阿什肯纳兹人曾对抗过另一种遗传病——泰-萨克斯病(Tay-Sachs disease)。泰-萨克斯病过去是(现在也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神经系统疾病。患病婴儿出生时很健康,但在六个月大时开始失去肌肉控制。他们的头会无力地摇晃,视力变暗;经过一段时期的抽搐后,他们会陷入昏迷并死亡。
虽然泰-萨克斯病很罕见,每2000名犹太婴儿中不到一例,但孩子们的痛苦令人震惊,而且其遗传模式的可预测性让社区的医生们感到恼火。泰-萨克斯病是一种隐性遗传病,需要父母双方都是携带者,他们生下患病孩子的几率为四分之一。这个数学计算简单而残酷。基因是成对的。父母双方都是健康的,因为他们各自携带一个正常的基因拷贝,但他们的孩子却遗传了两个受损的拷贝。犹太父母们意识到,如果泰-萨克斯病的携带者能够识别自己的状态,这种疾病将无处藏身。就像一个恶灵错误地附身于一个灵魂,这种疾病可以被揭露并可能被消除。
当泰-萨克斯基因出现缺陷时,它无法制造一种关键的酶,叫做氨基己糖苷酶A。在1960年代,远在致病突变被精确定位之前,研究人员就能够测量血液中的这种酶。泰-萨克斯病携带者表达的酶量大约是正常量的一半,这足以预防疾病;而患病儿童则完全检测不到这种酶。
针对该酶的人群筛查始于1970年代初。首先在巴尔的摩和华盛顿特区,然后是其他城市,犹太男女可以查明自己是否是泰-萨克斯病携带者。在他们的拉比、医生和当地卫生部门的宣传和教育下,成千上万的人怀着自豪感聚集在犹太教堂接受检测。1971年5月的一个周日,一千八百名男女冒雨在马里兰州的贝塞斯达接受了检测。1975年的某一天,一位名叫哈里·奥斯特勒的医学生和他的同学在纽约里弗代尔为500人抽了血。这次经历激励了年轻的奥斯特勒博士决定专攻医学遗传学;他后来成为纽约大学医学院人类遗传学项目的主任,在那里他倡导对犹太人的遗传病进行DNA检测。
当地医院响应了泰-萨克斯病筛查计划。携带者夫妇的怀孕可以通过羊膜穿刺术进行监测,如果胎儿患病,可以终止妊娠。很快,统计数据显示泰-萨克斯病的发病率急剧下降,在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中从每年约40至50例降至不到10例。到21世纪初,近一百五十万美国犹太人接受了携带者检测。数百个胎儿被终止妊娠,但同期,约有2500名健康的孩子出生于夫妻双方都是携带者的家庭。随着群体筛查所能做的已经做到极致,如今的泰-萨克斯病检测在门诊、大学校园和通过在线服务进行。仍然发生的少数病例最可能影响非犹太人,这些家庭携带的突变不同于泰-萨克斯基因独特的阿什肯纳兹变体。
东正教犹太人,尤其是极端保守的哈西德派犹太人,他们认为生儿育女是一项不容干涉的基本义务,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中最后一批利用泰-萨克斯病筛查的人。携带者检测不仅为避孕和堕胎打开了大门,还可能毁掉一个人的婚嫁前景。在哈西德派紧密联系的城市社区里,拉比比医生更有权威,医疗信息并非私密。当两个家庭在评估一桩婚事时,仅仅是遗传问题的风声就可能玷污一方的所有人。“对污名化的担忧不应被低估,”哈里·奥斯特勒说。“一旦邻居们听说什穆尔去了遗传学家那里,他们就会对他有遗传病的情况做最坏的设想,并可能进行一场耳语运动。”
东正教拉比最初拒绝与泰-萨克斯病筛查合作。然后在1980年代初,布鲁克林的一位哈西德派拉比约瑟夫·埃克斯坦设计了一种检测方法,将东正教徒带入了DNA时代。深居简出的埃克斯坦对泰-萨克斯病有第一手了解。他和他的妻子都是携带者。他们的前两个孩子在4岁前就因此病夭折。超出概率的是,这对夫妇最终在10个孩子中生了4个患病的孩子。出于羞愧,埃克斯坦曾将他第四个注定夭折的孩子藏起来;孩子死后,他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更加羞愧。
埃克斯坦是犹太饮食法(kashruth)中复杂规则的专家,他开始自学孟德尔的遗传定律。毕竟,遗传学就是应用自然法则的条文。这位拉比相信上帝创造了一个秩序,一个自然的事件进程,科学家和医生应该去研究它。“一切都由上天掌控,”他用沙哑的声音解释道,“但自然也有其规则。”就像大洪水之前——自然的各个分支,成双成对地,在诺亚审视的目光下走上斜坡——这个与那个配对,但绝不与这个配对,这生命奇妙的、细致入微的秩序,其中没有比生化规则更奇妙的例子了:A与T配对,但绝不与C或G配对;互补的规则是G与C配对,但绝不与T或A配对。
埃克斯坦的想法是,从一开始就劝阻他社区里的泰-萨克斯病携带者走到一起。在他的项目下,高中男女生提交血液进行检测,但结果不会告诉他们本人。后来,当一对情侣开始认真约会,或者他们的家庭正在探讨一桩婚事时,他们会联系数据库,了解他们是否在基因上相容。大多数时候他们是相容的。如果不相容,他们会被强烈建议分手,另寻他人。一切都以保密方式处理:不记录姓名,只有每个年轻人的识别号码和出生日期。埃克斯坦将该项目命名为“Dor Yeshorim”,意为“正直的一代”。到1980年代末,东正教社区内泰-萨克斯病出生率的下降比社区外更为显著。
Dor Yeshorim 占据了布鲁克林东河滨水区附近,轰鸣的威廉斯堡大桥以南一栋小小的、满是涂鸦的褐石建筑。在办公室一楼,六名戴着头巾的年轻女性在电脑终端前接听电话。这看起来像一个转为严肃的电话营销业务。“我们利用医学科学,并将其应用于社区的需求,”埃克斯坦自豪地 gesturing 说。
这位拉比相信,他生来就是泰-萨克斯病的携带者是有原因的。“我必须通过艰难的方式来发现,”埃克斯坦解释道,“但我们认为一切发生都有神圣的目的。我们可以用善行来战胜宇宙中的坏事。如果你是一种疾病的携带者,那是命中注定的,但也是有目的的。你也同时被给予了保护自己的方法。这就像是抵御天气的衣服。你必须保护自己,用全能者给予你的任何工具。”
埃克斯坦接着去解决影响他社区的其他隐性遗传病,如尼曼-匹克病、家族性自主神经功能异常症和卡纳万病。这些是症状与泰-萨克斯病不同的神经系统疾病,它们致残且通常是致命的。通过在他的项目中增加携带者检测,他实际上扩大了东正教年轻人之间不相容的理由。尽管如此,每100对情侣中仍有99对获得Dor Yeshorim的祝福,可以继续他们的求爱或约会,而他们的携带者情况并未向他们透露。与此同时,Dor Yeshorim收集的数十万份血液样本已成为DNA研究的宝贵资源。Dor Yeshorim为发现或确认卡纳万病、戈谢病(攻击脾脏和肝脏,导致疼痛和疲劳)和范可尼贫血(骨髓衰竭)的基因做出了贡献。
在20世纪90年代,一场发现家族性自主神经功能异常症基因的竞赛中,埃克斯坦和他的科学合作者与一个包括哈里·奥斯特勒在内的竞争对手团队展开了竞争。这并未改善两人之间的关系,他们对遗传信息报告的不同看法已经使关系变得紧张。
这位哈西德派拉比希望犹太人免于了解自己DNA的心理负担,这样他们就可以专注于建立美满的婚姻和健康的家庭。他们将按照全能者的命令生养众多,而他则致力于从社区中根除遗传病。但对于奥斯特勒来说,他是一位改革派犹太人、科学家、自由派人士,首要的诫命是知情同意。奥斯特勒和另一个人一样,都想根除阿什肯纳兹人的疾病,但不是通过一个秘密的项目。“埃克斯坦拉比想要控制谁能得到信息,谁不能,”奥斯特勒曾说过。“如你所知,这与遗传咨询的平等主义和参与式风格是相悖的。”
埃克斯坦反驳说,那种遗传咨询“不是为了消除担忧,而是为了增加担忧”。在与许多医生和科学家合作多年后,他认为专业人士让生孩子的男女变得更困难,而不是更容易。有太多不必要的检测,产生了太多技术信息,而这些信息对产生它的人并没有支持作用。通过检测和扫描,医生为父母提供了一种控制孩子出生和健康的错觉,但在埃克斯坦看来,他在此期间也造成了巨大的焦虑——而且最终,这也不是医生的问题。“遗传学是一件了不起的工具。它可以非常好,”埃克斯坦说,“但大多数医生没有正确使用它。他们对病人缺乏同情心。”
哈里·奥斯特勒并不缺乏同情心。他听到先天受损儿童的故事时会感到心痛,他对犹太人群DNA的全球性兴趣源于一种愿望——再也不想握住一个心烦意乱的犹太父母的手。在纽约大学医学中心,一个位于曼哈顿的庞大综合体,与埃克斯坦的据点隔东河相望,奥斯特勒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提供遗传检测,每年约有5000名患者。许多患者是怀孕的、受过教育的白人女性,她们担心出问题,并希望尽快得到答案。他的遗传咨询师团队在检测前后提供信息和转诊。
这些信息可能会带来严酷的后果,但奥斯特勒相信,如果一个人想要检测,就应该提供,只要患者理解其影响。“消费者不希望被告知该做什么,”他说。“我们正在为患者护理增值——这是一个增长中的业务。让市场来决定。”
这位医生完全同意拉比的观点,即夫妻不应该在怀孕期间探讨他们的遗传学问题,因为那已经是一个压力很大的时期。携带者状态应该更早地被考虑进来。因此,奥斯特勒定期去大学校园为犹太学生做筛查,意图在他们结婚前进行干预,就像埃克斯坦所做的那样。在纽约叶史瓦大学等宗教校园里,奥斯特勒和他的助手们直接与Dor Yeshorim竞争,以提高学生对隐性遗传病的认识。“我正在努力预防泰-萨克斯病,”他坚定地说。“人们仍然在掉以轻心……现代东正教的孩子们想知道他们的结果。”像Dor Yeshorim一样,他为自己的研究保存了血液样本,尽管对于这部分工作,受试者签署了同意书,规定他们的名字将从样本中移除。他持续发表文章。2011年,奥斯特勒从纽约大学转到布朗克斯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步伐并未放缓。
在圣路易斯山谷,梅迪纳家族对他们新揭示的犹太遗传遗产的反应更为迟疑。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漫长遗传链条的一部分。肖妮去世后,玛丽安·梅迪纳会拿出那张写有女儿DNA检测结果的纸。她反复思考着这个发现——引发癌症的BRCA1.185delAG突变——并在脑海中列出她听说的丈夫女性亲属中的癌症病例。大约在同一时间,但独立行动,约瑟夫·梅迪纳在丹佛地区的两个表亲开始从亲戚那里收集健康史。当癌症记录叠加在家族树上时,景象令人恐惧。约瑟夫的八个姑姑中,有五个死于乳腺癌或卵巢癌。(BRCA1突变使女性易患乳腺癌或卵巢癌,有时两者兼有。)他的八个表姐妹,年龄在三十多岁和四十多岁,都曾患癌,其中三人已去世。他的两个姐妹,在不知自己是携带者的情况下,很快也将被诊断出癌症。然后是肖妮,她一定是从她父亲那里遗传了这个突变。
2002年,玛丽安和她幸存的女儿,29岁的艾奥娜,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与一位遗传咨询师会面。艾奥娜应该接受突变检测吗?她显然处于风险之中,但艾奥娜请求更多时间来决定。与泰-萨克斯病和其他隐性遗传病不同,遗传性乳腺癌是一种显性疾病。在显性疾病中,功能失常的基因迟早会压制其健康的对应基因。五年过去了,然后是六年。像许多处境相同的女性一样,艾奥娜想象着这个基因,如果她携带它,就像是癌症本身的一个微小部分,但小到也许可以被压制成无物。
困扰她家族的基因是在1994年经过一番紧张的搜寻后,由遗传学家马克·斯科尔尼克和玛丽-克莱尔·金发现的。它位于17号染色体上,非常长,其序列中可能出现数千种可能的拼写错误。从那时起,已记录了超过2000种BRCA1突变,影响所有族裔群体,但其中一种突变很快脱颖而出。
尽管BRCA1的共同发现者没有特别关注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但其他研究人员,既然知道了去哪里寻找,很快就注意到185delAG突变在他们的研究样本中的显著性。他们立即确定了它与犹太人的联系。那些样本来自患癌率很高的阿什肯纳兹家庭。
下一步是弄清楚这个突变在普通犹太人群中的普遍程度。研究人员回过头来,在几十年前泰-萨克斯病筛查项目中储存的DNA样本中寻找BRCA1突变。185delAG的患病率为1%——这意味着每100个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中就有一个携带这种本身就能致命的基因,这与隐性突变不同。评论这一突变出人意料的高频率时,遗传学家弗朗西斯·柯林斯,现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院长,表示由185delAG引起的乳腺癌和卵巢癌可能是迄今为止在任何人群中发现的最常见的严重单基因疾病。
接着,一个频率较低的BRCA1突变,名为5382insC被发现,随后是在第二个基因BRCA2上发现的6174delT,构成了一个典型的犹太乳腺癌突变三联体。它们显然源于犹太古代三个不同的奠基者。在大多数其他族裔群体中,BRCA突变的患病率很低,大约是400分之一。而阿什肯纳兹犹太男女的BRCA携带率是40分之一——是背景率的10倍。阿什肯纳兹人仅占美国人口的2%,但他们得知自己占了全国BRCA携带者的三分之一。
作为第一个进入犹太人意识的突变,185delAG成为了世界上被研究最多、最令人担忧的DNA片段。很大程度上因为它,接受过BRCA1检测的人数超过了任何其他人类基因。1996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对更广泛的犹太人群体进行的初步筛查,沿用了泰-萨克斯病检测成功的程序。在华盛顿特区地区,借助拉比和社区卫生官员的帮助,招募了约5000名志愿者。他们向研究人员提供了DNA样本和家族癌症史。和以前一样,前来参与的人们即使在这次初步摸底中没有得到个人检测结果,也愿意提供帮助。
从NIH的研究和其他研究中,科学家们确定并非每个BRCA携带者都会发病,因为这些突变并非完全外显。外显率是一个技术术语,表示一个强大的基因可能会手下留情。由于不完全外显——因为有像肖妮·梅迪纳的祖母多萝西这样的健康年长携带者——由185delAG和其他BRCA突变引起的癌症风险必须用概率来表示。估计的范围很广。最乐观的研究表明,只有一半的携带者在一生中会患上乳腺癌,最悲观的则认为90%会。最常给出的数字是80%。卵巢癌的外显率较低,大约在40%左右。有什么东西削弱了基因的作用,但没有一个女性携带者能指望这一定会发生。
当阿什肯纳兹BRCA的消息传到犹太社区时,它常常被过分简化,以至于引起恐慌。如果亲属中有任何乳腺癌的报道或迹象,女性往往会高估自己携带突变的风险。报纸和杂志发表了关于阿什肯纳兹女性为BRCA问题而苦恼的文章。根据调查,犹太女性比其他少数族裔更可能去看遗传咨询师。这些女性知道,如果她们做了检测并且结果是阳性,下一个困境将是选择预防性乳房切除术,还是尝试通过额外的乳房X光检查和更密切的监视来规避风险。这份知识就像夏娃递给亚当的苹果。咬一口苹果就会诱惑另一口,姐妹、姑姨、父亲和女儿们纷纷提交自己的DNA进行分析。阳性结果带来了恐惧和羞耻,阴性结果则带来了解脱和内疚,情感的激流撕裂着家庭。
为了拯救生命,一些科学家建议对阿什肯纳兹人群进行大规模筛查。另一些人则说不,现在还太早,最好等更多的研究完成。但这些研究将如何被使用呢?健康保险公司会把BRCA称为既有病症而拒绝承保吗?虽然有法律禁止在健康保险中进行基因歧视,但这些法律不适用于人寿保险。犹太人会成为一个不可投保的群体吗?
东正教犹太人挣扎于所有这些焦虑,甚至更多。在他们的圈子里,正如埃克斯坦拉比比任何人都更清楚的,乳腺癌的诊断可能会促使一个女人去另一个城市寻求治疗,以免家里人发现。她最担心的是自己孩子的婚嫁前景。如果一个年轻人被告知她的家庭中检测到了BRCA突变,或者,天哪,她自己就是一个突变的携带者,那么在她的求爱过程中,她有义务在什么时候向她的潜在配偶披露这个信息?她是否应该因此被拒绝?埃克斯坦无法为他照顾的夫妇设计出一个变通办法,他发现这种情况令人痛心。“筛查一个没有治疗方法的病症、一个突变,有什么好处呢?”他质问道。“这只是在制造更多的悲剧。在她余生和她的后代中,她将背负着忧虑的重担。”埃克斯坦强烈反对BRCA检测。
但无论喜欢与否,犹太BRCA携带者都是先锋。多亏了185delAG突变和它的两个同伴,BRCA已经成为每个女性癌症风险的代名词。当犹太女性参与研究以测试该基因的外显率时,结果被应用于所有其他族裔,尽管在这些族裔中突变并不那么常见。一个与世界其他地方隔绝而产生的基因畸变,通过科学贡献给了全世界,增进了对BRCA普遍行为的了解。如果说在遗传学研究中使用阿什肯纳兹人有什么不利之处,那就是他们的血亲比其他群体更难找到。他们的大家庭往往更小,他们的家谱因东欧的大屠杀以及近代的纳粹大屠杀中犹太人的损失而中断。
在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城市,对这种检测的需求激增,部分原因是拥有BRCA检测专利的Myriad Genetics公司直接向医生和消费者推广这项服务。该公司在2008年报告称,接受检测的人数每年增长50%。阴性结果远超阳性结果,但这并没有削弱人们想要知道的欲望。Myriad估计,美国仍有50万BRCA携带者有待发现,其中包括15万犹太人。在500万美国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中,可以推算出有5万名185delAG的携带者。遗传学界再也没有人称185delAG为阿什肯纳兹突变了。到这个时候,它已经在犹太人蛛网般的迁徙路径上十几个遥远的地方出现,包括新墨西哥州和圣路易斯山谷。
艾奥娜的姑姑万达和卢皮塔在2007年检测出该突变呈阳性,并于2009年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万达的病情已是晚期,她于那年春天去世。接二连三的坏消息让艾奥娜无法再推迟自己的BRCA检测。她开始失眠。“我意识到我太自私了,”艾奥娜说。“如果我能做点什么,让我身边的人再经历万达和肖妮所经历的一切,那就太自私了。”
在实验室留下了血样后,艾奥娜回家等待结果。她的心开始狂跳。为了发泄,她对着一个沉重的沙袋做搏击操。一天,她感到胸口一阵刺痛,被送往急诊室,以为自己心脏病发作了。结果,她只是拉伤了一块肌肉。然后遗传咨询师打来电话:艾奥娜,就像她已故的姐姐和至少10位近亲一样,185delAG检测结果呈阳性。
2010年,艾奥娜参加了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彭罗斯癌症中心的一个新项目。该项目名为“高风险乳腺诊所”,为BRCA携带者提供与乳腺外科医生的免费咨询,以及乳房X光检查或MRI扫描。加入这个项目让艾奥娜感觉好多了。她的第一次MRI结果是阴性。在她心里,她通过警惕性等待,而不是手术,控制了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风险,这正是埃克斯坦拉比所推崇的策略。预防性乳房切除术不在考虑之列,在了解了更多关于卵巢切除(另一种预防措施)的信息后,艾奥娜决定她也不想做那个手术。她多年服用避孕药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对卵巢癌有保护作用。
焦虑发作和不知所措的感觉已经过去,但在叙述这些时,艾奥娜语速很快,尽量回避自己的情绪。“经验表明,”埃克斯坦说,“即使是受过最高等教育的人,也很难用理智来主宰情感。”
艾奥娜知道她DNA深处的答案,知道那个2500年前的突变已经进入了她的身体,是的,她知道。她知道她那个固执的姐姐所不知道的。虽然肖妮并不会在意。
杰夫·惠尔赖特是《发现》杂志的长期撰稿人。他的新书《流浪的基因与印第安公主:种族、宗教与DNA》已于本月出版。经出版商W.W. Norton & Company, Inc.许可摘录。